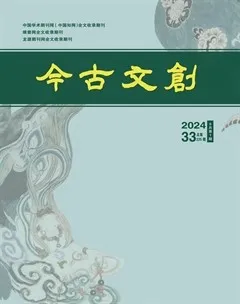柏拉图《理想国》中蕴含的正义思想研究
2024-09-24胡晓乐
【摘要】《理想国》是柏拉图的代表性著作,描绘了柏拉图心中的乌托邦国家,其中所蕴含的正义思想也是不容忽视的。柏拉图将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进行类比,城邦的正义就是城邦里的三种群体按照各自的天性各司其职,个人的正义则是灵魂的三要素和谐统一,论证了个人把自己奉献给城邦是有利的,力图实现整体的善,最终证明正义的人是最幸福的,个人要追求灵魂的正义。
【关键词】柏拉图;《理想国》;城邦正义;个人正义;灵魂;幸福
【中图分类号】B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3-0053-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3.017
《理想国》作为柏拉图的经典代表作和学界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描绘了一幅理想的国家蓝图,对后世学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其内容涉及多个学科领域,但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即个人与城邦是正义好还是不正义好以及正义到底是什么。《理想国》中对正义思想的讨论是人类历史上关于正义问题最早的系统论述。
一、柏拉图正义思想的背景
任何哲人思想都不可能凭空产生,都与他的个人经历和社会现状相关。柏拉图也不例外,他在《理想国》中提出的正义观及对理想社会的描述也都与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紧密相关。雅典在与伯奔尼撒之间的战争中惨遭战败,从此之后雅典社会危机四伏,战乱时常发生,整个希腊的城邦制度开始走向衰败。面对这样的现状,身为名门之后的柏拉图心系百姓,对堕落为寡头政治的雅典贵族政治产生不满。柏拉图早期跟随苏格拉底学习直至苏格拉底被处死,随后与苏格拉底的其他弟子一同周游各地,他的思想受到了苏格拉底的极大影响。在柏拉图看来,过分的民主制度造成了精英制的寡头政治,因此,只有真正的正义才能够改变现状、拯救社会。柏拉图的正义观中表现出对平息战乱和稳定社会的理想,对城邦和个人的设定也在事实上反映了渴望奴隶主贵族统治回归的愿景。
《理想国》原名是“republic”(共和国),这本身并未包含“理想”之意,但书中却描述了一个正义、和谐、美好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与战乱动荡、世风日下的现实社会形成了鲜明对比。《理想国》所描绘的蓝图是正义的公民在正义的城邦中从事正义之事、过着幸福的生活。因此,对“正义”的探求便成为贯穿本书的主线,柏拉图也因此可以被认为是系统探讨正义问题的鼻祖。
二、柏拉图的正义思想
(一)在《理想国》中寻找正义
根据对正义的不同方面的探讨,可以将《理想国》划分为五个部分,第一卷是第一部分,是整部作品的引入部分和预备阶段,讨论了正义的本质与作用。第二卷至第四卷是第二部分,讨论的主题是何为正义以及正义的人是否比不正义的人更幸福。第五卷至第七卷为第三部分,谈论的是善的理念问题,并认为正义本身来自善。第八卷至第九卷是第四部分,围绕四种堕落体制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三套完整的“推论”,最后得出正义者更快乐的结论。第十卷则为第五部分,通过灵魂轮回论证灵魂不死,说明正义者生前死后都比不正义者更幸福。
在《理想国》的首卷中,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与好友的辩论引出了对正义的不同看法。克法洛斯的正义观代表了老年人的观点,认为正义就是不欠债;柏拉图以武器不能还给变成疯子的朋友为例来反驳他。玻勒马霍斯的正义观则代表了中年人,认为正义就是每个人被给予恰如其分的报答。色拉叙马霍斯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我说正义不是别的,就是强者的利益。”[1]338柏拉图反对这种说法,认为强者犯错时,反倒有利于弱者。之后进入第二回合,讨论正义者是否有益。柏拉图做出四个反驳:第一,将技艺与挣钱之术分离;第二,正义者不愿意与不正义者争强好胜,由此证明正义的人又好又聪明,而不正义的人则又坏又笨;第三,不正义者会为了保全自己利益残害敌人,但不至于自相残害,原因是他们之间存在正义;第四,所谓正义是指心灵的德性,而不正义则是心灵邪恶。
在第二卷至第四卷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对正义的定义进行了讨论。在这里,柏拉图将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进行了区分。柏拉图认为,正义的城邦需要不同人各司其职,各自充当自己的职责并发挥作用。城邦中的三个阶层分别是统治者、护卫者和生产者,统治者拥有智慧的美德,护卫者拥有勇敢的美德,生产者则拥有节制的美德。他们分别发挥各自的美德,在哲学王的统治之下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在这种状态下的城邦可被看作正义的。而关于个人的正义方面,苏格拉底认为灵魂的三要素是理智、激情和欲望,这三方能分别与智慧、勇敢和节制相对应。理智是聪明智慧的,可以代表灵魂进行谋划;激情是勇敢冲动的,需要服从和协助理智;欲望则是代表贪婪,需要用理智和激情来管理并节制欲望。当一个人的理智起主导作用,引领激情、控制欲望,即理智、激情和欲望三者处于和谐有序的状态时,个人的正义就获得了实现。
随后在第五卷至第七卷中,柏拉图指出“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1]505,他认为善是最高的知识,正义本身也来自善。那些知识匮乏、脱离善、凭借运气生活的人是不正义的、浑浑噩噩的,因为他们不了解善、知识和正义。一个真正有知识的人会竭力寻求实在的善、正义和美。在人类的认识活动中,“善”发挥了中介作用,一方面赋予人类理性认识的能力,另一方面赋予可认识事物的本质。换言之,人类理性借助“善”的理念从真正意义上认识事物的本质。
第八卷至第九卷讨论的中心话题是正义者是否有益,即做一个满口仁义的伪君子,还是一个正义的人。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谈论了四种堕落的政制:荣誉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僭主政制。这四种政制在缺陷程度上是层层递增的,荣誉政制则是由美好的王政国家退化而来。这五种政制对应产生了五种人物,首先是最完美的王者型人物,其次是分别存在缺陷且缺陷层层递增的贪图名誉型人物、寡头型人物、民主型人物和僭主型人物。这五种人物中,王者型人物具有王者气质,最能自制,因此他是最善者和最幸福的人;而僭主型人物是最不正义者和最不幸的人,因为他处于疯狂的欲望驱使之下,他的心灵充满大量的奴役和不自由,这不仅使自己成为极端悲惨的人,也使得周围人成为悲惨的人。由此证明了正义者更为快乐。至善者和正义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在第十卷中,通过肉体的疾病导致死亡,引申到灵魂的恶对灵魂的伤害,说明恶不能毁灭灵魂,“既然任何恶都不能毁灭它,可见,它必定是永恒存在的。既然是永恒存在的,就必定是不朽的。”[1]416柏拉图论证了灵魂是不朽不灭的,而正义本身就是最有益于灵魂自身的,通过灵魂轮回的观点,柏拉图想说明正义者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都能得到荣誉和报偿,正义者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比不正义者幸福。柏拉图提出的这种惩恶扬善的正义,似乎是一种灵魂的正义的回归,也是整篇对话的完美结束。
(二)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
在柏拉图之前的哲学家大都认为正义是某种外在的东西,而柏拉图则持有不同的观点,他追求个人灵魂深处的和谐。他从城邦正义切入,再与个人灵魂的正义进行对比和类推,认为这个思路会更清晰的表达正义的内涵。
“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1]420一个完整的城邦由三类人构成,分别是:统治者、护卫者、生产者。三个阶层的人由于天性具有差异和不同,因而从事不同的工作,但不同的工作不是任意分配的,而是根据他们不同的天性分配到最适合他们的不同岗位。在柏拉图看来,这种不同人根据自己美德各司其职的城邦是正义的,“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1]158另一方面,尽管三个阶层的不同人各司其职,但并不是相互割裂,而是相辅相成,才能共同建立一个正义的城邦。统治者拥有智慧和理智,统领城邦的发展;护卫者拥有勇敢和激情,听从统治者智慧的安排以保护城邦安全;生产者智力低下且拥有欲望,因此需要有节制的美德,同时听从智慧的统治者与勇敢的护卫者的指挥安排。不同的人各司其职又互相合作建立了一个正义的城邦,这个正义的城邦是善的,同时拥有智慧、勇敢、节制三种不同的美德。当有人违反自己的天性与美德,从事其他行业的职位,例如,一个拥有医学天赋的人去从事苦力做最下层工人,一个鲁莽无知的人成为统治者,这些都会给城邦带来损失甚至灾难,从而堕落为一个不正义的国家。换言之,任何与美德相违背的行为都会给城邦带来灾难。
城邦的正义是三个阶层按照各自的天性各司其职,将城邦与个人类比,还需考察个人的正义。柏拉图指出,灵魂的三要素是理智、激情和欲望。理智与智慧相对应,激情与勇敢相对应,欲望与节制相对应,只有灵魂中的每一个要素都只从事自己相对应的事物才是正义的、“善”的灵魂,“我们每个人如果自身内的各种品质在自身内各起各的作用,那他就也是正义的,即也是做他本分的事情的。”[1]171当一个人违背了天性,灵魂的要素与美德进行了错误搭配,就会对灵魂造成伤害。例如,一个灵魂中带有欲望的人同时拥有智慧的美德,那么他可能通过他的智慧去实现无尽的欲望,这个人的灵魂就是不正义的,并且会对他人、对城邦造成伤害。另一方面,只有一个人的灵魂中同时拥有智慧、勇敢、节制的美德,这个人才是正义的、是“善”的,缺少任何一种美德,这个人都不是正义的人、都会对灵魂造成伤害。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的“灵魂分析不单是通过类比来解释社会——无论是美好社会还是堕落社会。它已预设并丰富了人类作为政治动物的概念,人的动机必然具有社会性的维度”[2]210,因此,他得出正义的个人与正义的城邦是一致的,因为它们都遵循着同一个原则,即每个部分都只做符合自己天性的工作而不相互干涉,并且在善的指导下成就了各自的美德。
(三)善主导下的正义
整个《理想国》对正义的考察从未离开过“善”。格劳孔将善分为三种,第一种善是“我们乐意要它,只是要它本身,而不是要它的结果”[1]44;第二种善是“我们之所以爱它既为了它本身,又为了它的后果”[1]44;第三种善是“我们爱它们并不是为了它们本身,而是为了报酬和其他种种随之而来的利益”[1]44。面对格劳孔的提问,苏格拉底认为第二种“善”是正义的“善”,也是最好的“善”。换言之,在可知的世界中,正义是最高的“善”,同时正义的过程会带来“善”的结果,人们可以在这种“善”的正义过程和正义结果中获得幸福。
然而,要证明正义本身是一种善无疑是困难的,这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善,因为“没有一个人在知道善之前能足够地知道正义和美”[3]110,人们对善的理念知之甚少,只有对善的理念进行深刻解读才能对正义的理念进行理解。柏拉图在这里借用苏格拉底之口提出了“洞穴喻”,如果将“洞穴”比喻为人们生活的世界,生活在洞穴中的我们认知能力有限以及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而无法窥见正义。虽然苏格拉底声称他无法对善进行直接的定义,但为了能够进一步解释“善”的概念,他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即“善的儿子,就是那个看上去很像善的东西”[1]266。苏格拉底指出,人要完成“看”这个活动,需要三个要素,看的能力——眼睛,看的对象——客观物体,以及中间介质—— “光”。“光”将看的能力与看的对象相连接,使得“看”这个过程顺利完成,而光的真正来源则是太阳,换言之就是太阳具有如此特殊的性质使得“看”这个过程能够完成,因此,太阳就是在可见世界中“善的儿子”。
根据上述的“太阳喻”,我们可以推测认为,正义就是可知世界中“善的儿子”。当正义表现在城邦方面时,正义就是每个人各司其职;当正义表现在个人方面时,正义就是灵魂要素与美德相互匹配。由此可以推论,正义代表着某种理性秩序,这个秩序类似于太阳以自身光亮照亮世间万物。同样,在可知世界中,正义的理念规范城邦以及个人处于理性秩序之中,从而拥有了善,不同的美德在“善”的统领下各司其职,城邦与个人获得自身存在的意义,这样的城邦和个人都是正义的。换言之,正义的理念统治着可知世界,就如同太阳统治着可见世界一样。因此可以说,在可知世界中,正义就是“善的儿子”。
(四)正义与幸福
在《理想国》这本著作中,有关正义的人更幸福还是不正义的人更幸福的证明是贯穿在整部作品中的主线。在这里柏拉图所说的幸福不是指感官上的满足,他所说的幸福是人们对正义的主观感觉,即对灵魂三部分的内在和谐而产生的感觉。人的感官的满足可以带来快乐,但是快乐并不必然地达到幸福。柏拉图认为,要想获得幸福的必要条件就是正义地生活,幸福是依附于正义的。在柏拉图看来,正义是一种美德,并且正义的人是最幸福的人,不正义的人是最不幸福的人。为此,柏拉图进行了两次论证。
第一次论证是在对色拉叙马霍斯提出的“不正义的人比正义的人幸福”的观点进行反驳时。首先,柏拉图提出了相对复杂的方法去反驳色拉叙马霍斯的观点。第一,正义的人只想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不想比其他正义的人拿得多,相反,不正义的人就没有正义的人的觉悟和高度,他们想胜过同类和不同类;第二,真正有知识的人从来不想和他同类的人去争上下,而无知的人不仅仅是想胜过与他不同类的人,甚至于想要胜过任何人;第三,有知识的人是好人,没有知识的人是坏人。综上所述,正义的人必然接近于好人,而不正义的人则接近于坏人,色拉叙马霍斯的观点被以上论证完全颠倒了。其次,柏拉图用政治后果来论证。正义能够带来和谐,而不公正只能引起仇恨和厮杀等,并且实施不公正的人的内心会非常挣扎。最后,柏拉图用其提出的功能理论驳斥了色拉叙马霍斯所说的“不正义的生活是更幸福的生活”。第一,每一事物都有自己的功能,这种功能是指对于每个事物来说,只能由其来做的工作或者只有它才能做得好的工作;第二,如果一物的功能发挥得非常好,那么它就获得了美德;第三,人的灵魂也有功能,而灵魂的美德就是正义;第四,灵魂一旦获得正义,那他就会幸福。所以,正义的人是幸福的。此处反驳只是引入一些概念,并未完全展开,因此未能使人感到完全信服。
第二次论证是在利用语言和想象构造完“理想国”后,又描述了四种堕落的制度和这四种制度中的不同品性的人。最好的制度是贤人制,以德性为善,公民是正义的人;贤人制堕落的第一步是变成荣誉制,以荣誉为善,公民是爱好荣誉的人;荣誉制堕落变成寡头制,以财富为善,公民是爱好钱财的人;荣誉制堕落变成公民制,以自由为善,公民是爱好自由的人;公民制堕落变成以专制为善,即最坏的僭主制,公民是专制的人。此四种制度和公民的描写,其目的是为了证明贤人制中的人,即坚守正义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僭主制中的人是最不幸的人,从而重扣整个讨论的主题——正义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三、《理想国》中的正义观评析
(一)古典的正义观
柏拉图所理解的正义概念和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正义概念是不同的。或许以现代的目光来考察它,是无法看清它的面目的。在《理想国》中,正义是囊括其他所有德性于其中的德性。《理想国》中的正义观是古典的正义观。在继承了毕达哥拉斯思想的基础上,柏拉图把德性设想为和谐,“正义则是灵魂的内在和谐”,这一观点是一种道德式的说明。在与玻勒马霍斯的讨论中,讨论的错误在于使正义成为许多技艺中的一种。正义探寻整体的好,苏格拉底认为知识是最高的好,而玻勒马霍斯认为财产是最高的好,正义只不过是获得财产的手段而已。色拉叙马霍斯认为,个人利益和统治者的利益是矛盾对立的。“哲学恢复一个人的生活的统一性。正如要求于各种技艺的,哲学要求对其对象的完全献身,同时它给予其从事者丰厚的奖赏,因为它是他的天性的完美化,并使他感到最大的满足。只有在哲学中,对技艺之适当运用的关心和对一个人自己利益的关心才达成一致。”[4]56只有共同体的利益和个人利益保持平衡,个人才会履行正义。
(二)灵魂的正义观
柏拉图将城邦的正义与灵魂的正义进行类比,柏拉图的正义观指向人的内在灵魂。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才能实现正义。灵魂的正义是讨论的主题,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表述过城邦无法实现,那关于城邦正义的讨论的意义何在?“一开始在城邦中寻找正义的决定,以及城邦中的正义和个人身上的正义之间的最终区别,始终把如下问题置于我们面前:使一个城邦健康的正义是否与使一个人健康的正义相同?这一问题的答案决定着另一问题的答案:一个人把自己奉献给城邦是否有利?”[4]69柏拉图假定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是相同的,个人把自己奉献给城邦是有利的。柏拉图的正义观力图实现整体的善,只有实现灵魂正义,并证明正义的人更幸福,那人们都会践行正义了。这是一种灵魂的正义观。
(三)柏拉图正义观与罗尔斯正义观的比较
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罗尔斯的正义观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柏拉图的正义观以社会秩序为中心,而罗尔斯的正义观以人的自由权利为中心,下面将两者的正义观进行简要对比。
柏拉图的正义原则是社会中三个不同等级的人们,即统治者、护卫者和生产者,各自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做与自己性格相适应的工作,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不能妄图其他等级的人的工作和位置。柏拉图的正义论认识到了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但柏拉图认为这种等级划分是永久的、无法改变的,这表现出其思想受到奴隶制较大的影响。他的目的是依靠把人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各司其职看作一种永恒的正义,来实现一个既能维持贵族特权、又可为贫苦阶级接受的社会。因此,柏拉图的正义论是服务于贵族统治的稳定,代表着没落的贵族的利益。柏拉图的正义论观点尽管有着局限性,但对于柏拉图所处的时代的特点以及其理论中所蕴含的思想方法而言,依旧是一种值得认识和研究的理论,如公民对待法律态度观念上要求守法、统治者要有良好的德行、提倡人们追求心灵的智慧等。
罗尔斯则是在开篇提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为了论证他的正义原则,罗尔斯进行了“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的设定。在无知之幕后的人们,个人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天赋等信息,只能进行一般考虑。罗尔斯认为在这种状态下的人们选择的原则才是最符合社会、最正义的原则,即平等的自由原则,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最少受益者的最大利益是罗尔斯所最为强调的,要保证给所有人提供真正意义上平等的机会,对于那类天赋较低或社会地位相对不利的人们,社会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将更多的资源花费在他们身上。与柏拉图所不同的是,罗尔斯认为个人天赋同样属于社会的共同资产,由于偶然的分配,每个人拥有的天赋也会不同,正因如此,更需要从经济利益或社会层面上对天赋较低的人群给予补偿,最大可能地缩小他们与天赋较高者的差距,从而扩大社会福利平等。
总体来说,通过对比分析柏拉图和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发现,他们在各自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提出不同的正义观,现代性的扩张和自由主义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传统道德的作用机制,制度约束机制规则成为实现现代社会正义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2]马尔科姆·斯科菲尔德.柏拉图:政治哲学[M].柳孟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
[3]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郑伟威译.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
[4]布鲁姆.人应该如何生活[M].刘晨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5]刘飞.论柏拉图《理想国》中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的一致性[J].哲学动态,2014,(6).
[6]罗跃军.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正义观辨析[J].哲学研究,2012,(8).
[7]黄颂杰.正义王国的理想——柏拉图政治哲学评析[J].现代哲学,2005,(3).
[8]杨佳.柏拉图的正义观解析[J].人民论坛,2010,(08).
[9]王万松.柏拉图《理想国》正义论研究[D].贵州大学,2019.
[10]陶一桃,张超.柏拉图经济正义思想研究[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