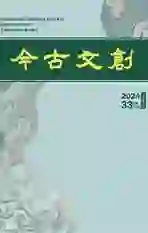白先勇文学作品风格艺术探究
2024-09-24云萌雨
【摘要】白先勇在当代文坛享有重要的地位。本文采用文献法和对比分析法来研究白先勇的具体作品,主要简单介绍白先勇及其作品,研究白先勇作品的语言风格,对白先勇叙事语言的阐释以及分析其作品的艺术手法。
【关键词】白先勇;语言风格;叙事风格;表现手法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3-003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3.012
一、白先勇及其作品简介
白先勇著有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寂寞的十七岁》以及长篇小说《孽子》等。白先勇的艺术手法主要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具体到语言习惯上还是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他多用蒙太奇手法进行场景的转换,注意人物个性化语言和修辞格的运用,整体呈现“中西合璧”的特点。
他的作品有比较明显的前后分期,一般认为以《芝加哥之死》为分界线。笔者对白先勇作品的分析也是从他的前后两期出发,并分析整体特点。白先勇的作品中往往表现出浓厚的命运悲剧色彩,这也是他的作品吸引人的地方。他的前期作品大多是在台湾完成,带有浓厚的幻想意味;后期作品融现代与传统为一体,笔者认为这个时期更能代表他的个人特色。
二、白先勇作品风格研究
白先勇的语言风格经历了一个从尖刻到圆润的转变。总体上看,白先勇作品呈现“中西合璧”的特色。
(一)前期风格:冷峻犀利
白先勇前期作品透出一种冷峻的气质,这使得他的讽刺十分尖锐。他在用词上也十分大胆,二者结合使得他的文章展露出一种犀利的风格,这有利于他前期所写世情小说主旨的表达。以《玉卿嫂》为例,白先勇在文中并不避讳一些俗语词的出现,对于死亡场景的描写也十分详细。他明晃晃地写出了以小王为代表的男性仆人对她的觊觎,以胖子大娘为代表的女性仆人对她的诋毁,在这样直白的描写下玉卿嫂的生存困境直接被点了出来,而她之后采取的反击手段就显得愈发高明;在描写庆生和玉卿嫂的死亡时,他写道“庆生和玉卿嫂都躺在地上,庆生仰卧着喉咙管,有一个杯口那么宽的窟窿,紫红色的血凝成块子了”,“玉卿嫂伏在庆生的身上,胸口插着一把短刀,鲜血还不住的一滴一滴流到庆生胸前,月白的衣裳染红一大片”。他将死亡场景写得极尽详细,极大地刺激了读者的感官,深刻体会到玉卿嫂在爱情破灭后的孤注一掷。在这二者的对比下,可以清晰地认识到这样一位有手段的女性在封建压迫下是难以追求自己的爱情和自由的,讽刺意味愈发浓重。
(二)后期风格:锋芒隐现
白先勇后期创作中没有前期那么直白露骨,他的意蕴变得含蓄深沉。在这个时期白先勇十分注意对字词的锤炼,以此帮助白先勇完成作品的表达。在《游园惊梦》里,钱夫人被程参谋的目光所触动时写道“程参谋那双细长的眼睛,好像把人都罩住了似的”,这里的“罩”字用得很巧妙,它把程参谋的目光比成罩子,铺天盖地地盖在了钱夫人心上,一个“罩”字便能窥探到当时她内心的动摇。在《树犹如此》中,当白先勇回到圣巴巴拉的院子,怀念与亡友王国祥的时光时,“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他们之间的距离已经跨越了生死,此生难再见,这样的距离不是天裂又是什么呢?没有直白的描写,只有一些字词的精心,浓烈的情感掩藏在浅淡的文字下,反而更加深刻、隽永,提升了文章的质感和可读性。
(三)整体风格:中西合璧
白先勇的整体风格便是“中西融合”,在运用西方写作技法的同时,注重传统文化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新壶装旧酒”。但笔者认为这对于当代的中国文学创作者是一个比较好的借鉴,作者应当具有民族性,不能一味追求新的写作方法而忽略传统文化的应用,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也不能满足大众对于文学作品的期待。白先勇是以其深厚的中西文学功底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三、白先勇的叙事风格艺术
本章是对白先勇叙事艺术的讨论,是从叙事视角、叙事策略、人物语言等四个方面讨论的。总体来讲,白先勇的叙事有着强烈的民族性和讽刺性。
(一)活用第一人称叙事
运用第一人称叙事,可以很好地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增强感染力和真实性,便于议论和抒情,但是白先勇将它用出了新意:第一人称的叙事者与故事主人公往往不是一致的。这使得人们在感受故事的同时,又弥补了第一人称带来的客观视域的局限。以白先勇第一篇短篇小说《金大奶奶》为例。白先勇在讲述金大奶奶的悲剧故事是以“容哥儿”也就是“我”的视角讲述的,金大奶奶的再嫁后的痛苦不是从金大奶奶自身出发的,而是通过旁观者的视角也就是“我”来讲述的,正因为这种巧妙的设置,读者在感受金大奶奶命运悲剧时会有更深层次的感悟并且对背后深层次的原因进行思考和反思。金大奶奶的故事是由“我”所见所闻拼到一起组成的。一方面听到“小虎子”对金大奶奶的描述,“她算哪一门的伯娘,‘老太婆’罢了”;另一方面又由“顺嫂”补全全貌,“金大奶奶的身世不知道多么的可怜呢”。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完善了这个故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一方面沉浸其中,一方面又以“上帝视角”观看金大奶奶的一生。人们清楚地感觉到了隔阂的存在,但也正是因为这个隔阂才能激发人们的思考:在天理之下,善恶无所遁形。文中的天理自然是“我”的眼睛。可以说,这篇文章的讽刺内涵完完全全通过“我”的漠视表达出来了。
白先勇通过活用第一人称叙事使得文章变得轻巧灵动,将讽刺表达得深刻冷峻。
(二)综合运用多种叙事策略
在白先勇的叙事策略中,比较出众的是空间叙事和死亡叙事。
1.空间叙事
白先勇一方面利用空间参与小说的叙事建构,同时注重继承中国文学的传统的空间叙事方法:通过丰富的空间意象以及生动、独特的意象建构和纯正的中文写作,使得他的人物鲜明,语言优美易读,作品意义深远。另一方面,白先勇也运用了许多现代叙事技巧,积极研究西方现代主义意识、符号和多视角叙事的流动,探索人物的内涵空间,拓展小说的艺术表现力。白先勇空间它不仅具有物理维度,还具有历史文化维度。这在《芝加哥之死》里可以很好地体会,吴汉魂在窄小的地下室回忆之前的美好记忆,一面是故乡淳朴的风土人情,一面是异国他乡文化认同的危机,自己获得了博士学位,却失去了母亲与女友,前路茫茫,将归何处?在回忆中不断地转换空间场景,让读者切实体会到了吴汉魂内心的痛苦,也就理解了他自杀背后的动因。
2.死亡叙事
白先勇通过对死亡的书写记录了某一时期社会风俗面貌以及人物的悲欢离合,为他的作品氤氲了一种孤独而悲伤的艺术氛围。白先勇短篇小说中死亡叙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具有多种结构功能,并随着文本的变换形成不同的主题。作者对人物死亡的态度意味着对历史、社会和命运的严肃思考,并强调小说主题的意识形态重要性。白先勇的死亡叙事是通过独特的视角解读人生,这不仅凸显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也让读者对死亡进行了思考,将小说的思想内涵提升到了更深的层次。
《芝加哥之死》中不仅仅运用空间叙事,还在此基础上运用了死亡叙事,在这种综合运用之下,读者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吴汉魂的心情变化与转折,代入感极强,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
3.注重上海书写的角度
白先勇的作品与上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白先勇的作品中反映出了并驾齐驱的两个上海:传统上海与现代上海。他十分推崇传统上海。但是他也明白传统上海也具有其难以示人的一面。他通过描绘过往上海繁华的景象,以此激发人们追求美好的欲望与动力。在精神家园的建设中白先勇并没有一味地歌颂,他保持了辩证的批评立场,这有利于传统的批判继承,白先勇没有痴痴挽留逝去的繁华,也没有惧怕现代文化的冲击,这给人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4.人物语言的个性化
人物语言在叙事中占有很大作用,可以说一些材料的补充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人物语言。白先勇作品里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得益于他对人物特点与本质的精确理解,以及他深厚的社会经验积累。在白先勇的著作中,没有一个人物的语言是完全相同的,阶级身份不同,语言自然不同。摘取《梁父吟》里的一段对话:“朴公说道:‘虽说身后哀荣,也不能太离了格。我看到孟养的那个男孩子,竟不大懂事……开吊这天,灵国葬的仪式,千人万众都要来瞻仰你父亲的遗容,礼仪上有个错失,不怕旁人物议,倒是对亡者失敬了……’雷委员点头附和道:‘家兄办事,确实还少了一点历练。’”
这段对话的主体一位是浸淫官场的官员,一位是熟悉官场的幕僚,他们是对一位老官僚的葬礼申发的议论。在他们对话使用的语言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双方都受到了文言句法的影响,都使用了一些文言词汇,没有那么白话,比较书面。这显然十分贴合两个人物当时的身份和处境,让人们可以闻言如见人。
四、白先勇作品的表现手法
白先勇的艺术手法受到西方象征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影响比较大,但是也融合了传统的寓情于景的手法,这是最能体现白先勇“中西融合”特点的。
(一)通过意象群表达情感流动
在白先勇先生的作品中常常采用花、梦、冬、日、月等意象,每种意象都有其深刻的内涵,白先勇在这些意象身上寄托了某种特定而又相对稳定的意义。在这些意象之中,“月”与“冬”是最具代表性的,它们贯穿了白先勇创作的始终。
月亮这一个意象不仅仅是以其色彩的变化、月相的转换来暗示人生际遇与情感态度,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观察世情的“上帝视角”,这样可以使读者更好地体会,以《月梦》为例,吴医生少年时与静思的情事,就是在纯洁而又凄清的月色见证下进行的,这抹月色正是他们纯洁的情感和悲惨的命运的隐喻和写照。他们的情感在月色下升华,在月色下消亡。月亮是最好的见证人和旁观者。而冬天意象在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中也占据了重要作用,他暗示着“终了”与“终局”,金大奶奶服毒自杀是在冬日,玉卿嫂殉情是在冬日,顺思嫂在冬日感觉到了家族的衰败,依萍在冬日体悟到了文化苍白的走向。冬天为一年打下了句点,“冬”之意象也让读者体会到了沧海桑田。这些意象组成的意象群将白先勇的言外之意表达得透彻,作品的情感流动也在其中显现。
(二)以情为线,情景交融
白先勇的文字中常常表达一种悲剧美、感伤美,他往往将这种悲情的表达与景色的描写联系在一起。以《金大奶奶》为例,行文的线索其实就是“我”,以我的所见所闻来推动剧情,这其中我对于金大奶奶的同情也就串联了整片故事;白先勇对于金大奶奶死亡场景的描写是典型的“以乐衬哀”。一边是觥筹相错、座无虚席的宴会场景;另一边的金大奶奶却在逼仄的房间服毒自尽。这种强烈的对比更是凸显出了金大奶奶死亡的凄凉。
(三)采用意识流的手法
“意识流”这一概念一般被认为是伯格森的“心理时间”说中首先提及。在白先勇的许多小说中,白先勇把“现在”和“过去”以及对“过去”的回顾和改写同意识流结合起来,两两相互对比,并在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历史材料,戏剧冲突鲜明。因此人们总能在白先勇的小说里感觉到一种沧桑感和历史的厚重感。以《孤恋花》为例,通过叙述者“我”的今昔联想让过去在上海发生的事和现在在台北发生的事在“我”的意识领域里交相呼应、今昔混淆,现实与回忆糅合在一起。在叙述者潜意识中同一类似的场面包含着两个女孩的悲惨命运。“我”看娟娟正如“我”看五宝,在相同的场景下两个女孩的命运好像发生了重叠。这更能启发我们的思考:五宝不是第一个,娟娟也不是最后一个,只要有卖酒女这种职业的存在,她们的命运就不会被逆转。同时,在这部作品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白先勇有些时候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与心理描写纠结一起难解难分。这给了人们一个启发:在将要运用大量心理描写的作品中不妨模糊意识流手法与心理描写,以叙事者的心理活动来推动发展,也是会显得别有韵味。
五、结语
白先勇的作品风格脱胎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兼采西方的表达技法,以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为素材不断完善自身的语言表达。在语言风格方面,白先勇注重锤炼字词,文章脉络清晰、语汇丰富、不避俗语,语言细腻又不失锋芒。在艺术手法方面,辞格运用有他个人的风格,尤其是反复和互文的使用,环环相扣,前后呼应;同时,又有着意蕴丰富的意象群式的作品言有尽而意无穷。在叙事语言方面,白先勇注意多种叙事视角、叙事策略的综合运用,注意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总体看来,白先勇的作品呈现出丰润细致之美。
参考文献:
[1]白先勇.寂寞的十七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4.
[2]白先勇.白先勇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202
[3]赵艳.论白先勇的上海写作[J].文学评论,2011,(04).
[4]刘俊.论白先勇小说中的意象群落[J].学术论坛,1994,(02):77-82.
[5]殷相印.白先勇小说的语言审美[J].毕节学院学报,2011,(07).
[6]陆正兰.论白先勇小说中音乐—空间的社会象征意义[J].当代文坛,2017,(03).
[7]孙秋英.浅谈白先勇小说创作中的青春理想主义[J].名作欣赏,2015,(21).
[8]黄璐.白先勇小说创作与地方文化互动关系研究[J].文化与传播,2015,(03).
[9]孙秋英.浅析白先勇小说中的死亡主题——以将军之死为例[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4,(07).
[10]田敏,邵平和.一曲放逐者的苍凉悲歌——论白先勇小说的放逐主题[J].语文学刊,2009,(21).
[11]尤妤冠.白先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书写[J].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10).
[12]朱寿桐.白先勇文学存在的文化意义[J].小说评论,2016,(03).
[13]林幸谦.岂容青史尽成灰:白先勇的历史叙事与时代悲情[J].当代作家评论,2013,(02).
[14]黄伟雄.论白先勇小说的命运意识与悲剧人生际遇[D].南京师范大学,2009.
[15]周瑶.论白先勇短篇小说的空间叙事[D].湖南师范大学,2018.
[16]杨小露.论白先勇对女性悲剧命运的书写[J].焦作大学学报,2015,(3):20-23.
[17]蔡西希.白先勇《谪仙怨》修辞解读[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2,(3):105-106.
[18]宋美英.白先勇小说中的意识流[J].文史博览(理论),2008,(07):22-23.
[19]易明善.略论白先勇短篇小说的语言描写艺术[J].当代作家评论,1984,(06):119-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