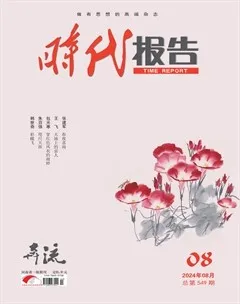家乡的饭市
2024-09-21刘天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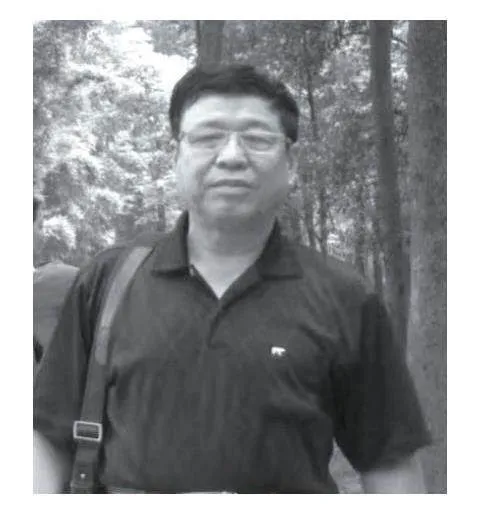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少农村地区由生产队体制衍生出一种习俗,人们不在家吃饭,而是端着饭碗出门,聚在村里的街道上边吃边聊天。这种聚集吃饭的地方称为饭市,又叫饭场。”
偶读这个富有乡土特色的词条,不由勾想起牵念故里抚慰乡愁的缕缕思绪,想起诸多亲人亲切的面容和那热闹有趣的饭市来。按我的回忆,家乡饭市的形成时间,不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可能是在解放初期,或者更远。
一
我四五岁时,正是农村土地改革圆满结束,乡亲们“腾欢今日新天地”的喜庆岁月,也是我记忆开始的年头。至今,我还能回想起那个时段的饭市场景,甚至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和感人细节。例如谁家兄弟俩将离家多年的老母亲接回来了;夜校的女老师和本村的二小子结婚了;或是谁家媳妇生双胞胎,请邻居们吃肉臊子喜面条了,等等。这些由“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带来的欢喜之事,至今还清晰如初闻。
来吃饭者,都是清一色的老少爷儿们,那年代男女有别的意识相当严重,女的很少出门,在家吃饭。当时我们村有1500多口人,像这样的饭市,村上不下百个。他们依着墙根吃饭,一溜儿成排地蹲着或坐在鞋上或石块砖头上,吃着说着,说着笑着,一片崭新景象。
我在饭市吃饭的时候,常常怯懦羞涩,不敢看人,不敢说话,像小羊羔一样依偎在爷爷身旁,主要是为爷爷送碗送筷,拿烟袋。农闲时节,爷爷和几位老人会抽着烟唠着嗑,一聊就是半晌。
四老头当过私塾老师,是一位最有学问的长者。他说,饭市由来已久,小时候就是端着饭碗跑到这里吃饭。灾荒年,年轻人背乡离井逃奔外乡,在家的穷苦人吃着上顿摸不着下顿,也就没有饭市。解放了,百废俱兴,天下太平,当然又到这里吃饭了。
饭市随着季节和天气的变化而迁徙,酷暑季节,会迁在百米之远的东寨门和一座门楼之下,因为那里格外凉快。冬天,小孩子一清早就叫冷叫饿,母亲常在红薯稀饭没有冲面糊之前,先盛点红薯给小孩子充饥。可是他不在家吃,却端着碗跑到饭市晒暖,和小伙伴们一起聚餐。有时,会对着故意站在前面的人唱起歌谣:“谁给我挡堵影儿,给谁划个锁儿!谁挡住我的日头地儿,给谁划上牛鼻犋儿。”
后来,农村建起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也应运而生,乡亲们都到食堂就餐。村里的饭市仿佛在一夜间消失了,而且长达三年。
二
饭市真正恢复发展的高光时期,是农村实行生产队体制的六七十年代。那时候,为多挣工分,多点吃的,每天都要听着上工铃声下地干活。他们清晨即起,荷锄出下田,下午继续,日暮而归,从来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几乎没有一天休息时间。于是,他们把一日三餐的饭市当成轻松减压、赋闲取乐、吐露心声的平台,以达到休整自我、展示自我、发泄自我、实现自我的一时满足。
饭市还在原来的场地上,但北面建了五间保管屋,西边建了一座七檩三间牲口屋,成了一个院落。中间的那棵槐树,被牲口啃掉了几块皮,有几块疤痕,树冠长得郁郁葱葱,绿荫盖地,能为老少爷儿们遮阴挡雨。南面的村中主街与北去的胡同交会,就构成了一处来去方便,老少聚餐的上佳之地。
冬天为给牛马驴骡保暖,保护好生产队的宝贝疙瘩,牲口屋会垒个土坯煤火,日夜不熄。三犋牲口槽与牛把式的床铺列置两头,当中的西边是煤火,暖和宽绰,就是牛铺的异味有点儿刺鼻,但村上的乡亲们从来不嫌牲口脏,直到现在养牛户还是人牛同住,其乐陶陶,于是这里就成了近悦远来的附属饭市。
日升三竿,约在八点时分,下工回来的乡亲们都齐呼呼地来饭市了。男人大都是左手端着神垕古镇烧的大白碗,右手拿着筷子和一沓子四五个的红薯面饼子。大白碗里盛着红薯稀饭或是小米南瓜稀饭,上面盛着萝卜丝或辣椒茄子的时蔬炒菜。盛得上一碗下一碗,无以复加,为的是不回碗,多在饭市呆一会儿。
吃饭者不论距离远近,都是从家里出来,都是不吃一块馍,不吃一口饭,直到饭市“开火”,为的是先抢个好位置,说话都听见。饭菜几乎一样,只是味道各异,因为萝卜白菜麦子红薯都是集体分的,谁家也不特殊。
来早者抢块石块、砖头,在墙根前的中间落座,来晚者使出历练多年的蹲功,就地一蹲,直到吃完饭。有的端着饭菜,腾不出手来,就用一只鞋尖蹬着另一只鞋的鞋跟,脱下来垫在屁股下,才急切切地贴住碗边,吞吃着快要溢出的饭菜。然后就看也不看,听也不听地打开话匣子,顺融在欢声笑语之中。
人们说天道地,谈古论今,纵横捭阖,漫无际涯,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不过,有时也会出现一些有趣的小插曲,或者是争执吵闹的抬杠事情,难以收场。
那年立夏时节,麦子丰收在望,饭市上议论的主题是如何按工分人口分成。没想到,家里只有老爹的广哥与子女5个的二尚吵起来了。广哥说:“按工分占6,人口占4合情合理。我们整天没死没活地干,理所应当多吃点!”二尚说:“日子都是过人的,谁也又老了干不动的时候。遇事要看远点,人口占6,工分占4最合理。将来你成了五保户,谁养活你?”这句话戳到广哥的痛处,有点儿过火,只见他大吼一声,大步奔到二尚面前,疯了一样地吵嚷。二尚也不示弱声音更高,像两只公鸡斗架。队长见二人吵得没长没短不可开交,就上去劝说,恁俩都是嘴上抹石灰——白说,到队里开会时再说中不中?结果二人悄然收兵,一群鸡子却把饭菜叨光了。麦天,生产队按对半分红,交罢公粮,每人按水平线分了80斤麦子,广哥家多了30多斤,创历史新高。
三
近来我回老家看看,特地到保管屋牲口屋的遗址重游,想和老少爷儿们叙旧聊天,捡回旧时的乐趣。不承想几处宅院几栋小楼占据了当年风景。
中午时分,恰好遇见一位用三轮车送孙子上学的老弟。正要问些情况,他却抱歉地说,送学生不能晚点,没时间细谈了,就匆匆离去。另一位老友迎上前说话,不料他的孙女跑到跟前,非要他到附近超市买沙琪玛。老友说年轻人都出外打工了,他和老伴招呼着十来亩地,还得看管孙子孙女,整天忙得不亦乐乎。看着孙女哭着闹着的情形,我只好知趣地与他再见。
街上没人了,静悄悄的,家家户户想必都在围桌吃饭,只有几只花喜鹊登枝鸣唱,好像唱着“谁挡堵我的影儿,给谁划个锁……”的旧时歌谣。
作者简介:
刘天义,河南襄城县王洛镇人。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襄城览胜》《乾明寺》《从柴童到将军 武传胪刘金华传》《白塔寺传奇》等书,曾校注明嘉靖《襄城县志》,参与《襄城县志》《襄城县地名志》《襄城县名胜古迹》及多部地域丛书的撰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