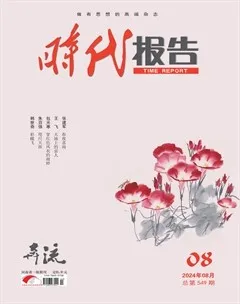小姨
2024-09-21徐志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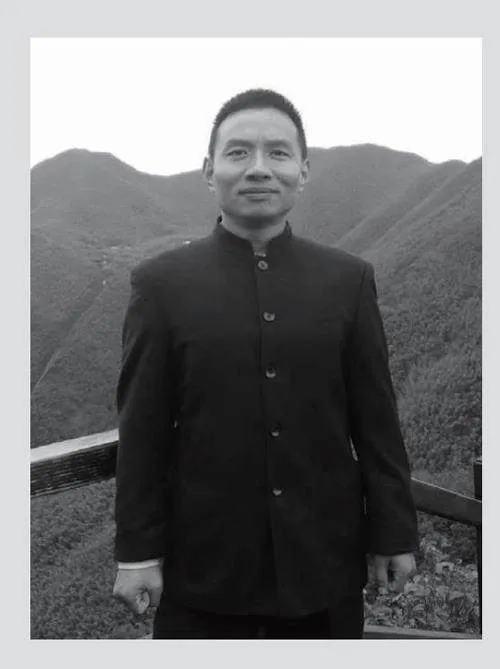
若用两个字去总结小姨的一生,我想“承受”二字最为贴切了。
山乡的风没有吹裂小姨的皮肤,相反她脸上泛着一股水润的俊气,两根黑油油的麻花辫子在她胸前甩来甩去。从小学到高中,她的成绩总是位列三甲之内,所以她也是众多姨妈中最出色的一位。
高考时她由于胆囊炎发作,导致高考失利。听妈说,小姨高考时,突然脸色煞白,汗珠如黄豆粒般往下滚。她硬撑着答完了试卷,结果因三分之差,和大学失之交臂而报憾终生。
小姨个性要强,挑担、挖沟、割稻、收麦……生产队的那些农活,她一样也不输给村里的男人们。乡亲们送小姨一个外号叫“一丈远”,因她不管干什么农活,总能甩开同伴一丈远而得名。
有一年农闲,村里举办了农技大比武。比赛的内容就是乡亲们日常的劳作项目。小姨不但手脚麻利,而且头脑灵活,一举夺得了大比武的冠军头衔,比起亚军,她足足多出了二十多分。
常有人问她,累不?她总是淡淡一笑。要说不累那是假的,她知道,姐姐们都已出嫁,外公又是个病秧子,只有自己拼命挣公分,家里的几张嘴才不至于被饿着。
转眼,小姨就到了出嫁的年纪。小姨父是外公相中的,论样貌与能力,小姨父比不上小姨。虽说是在农村,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那一套,早就被年青男女所摒弃,小姨完全可以反对这门婚事。但是,这门婚事是外公的选择,小姨不想薄外公的面子,让外公伤心。
外公自然不会把小姨往火坑里推,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他常挂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荒年饿不着手艺人”。小姨父不但是手艺人,还是远近闻名的能工巧匠:小姨父17岁开始,就跟着当地一位颇有名气的老木匠学艺。
都说做八仙桌是木匠的基本功。小姨父做的八仙桌,台裙的八仙人物雕刻得栩栩如生,榫头拼接之处更是丝毫不差,台面用个十年八载,也始终不见裂痕……这也许就是外公相中小姨父的原因吧。
订婚是农村流传已久的习俗。男方为了表示结婚的诚意,需买一定数量的信物送于女方。然后再办上一桌订婚酒宴,这婚也就算订婚了。订婚相对于结婚,只是一个前奏,并不具备法律效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订婚就是对外宣告,这两个青年已名花有主,说亲做媒之类的事宜,就绕道而行了。
在这期间,若男方反悔,所购的信物,就甭想收回了;反之,女方则要全部退回所收之物……这些都是百姓间不成文的规定。但还有不按常理出牌的。小的时候偶尔也能看到有人因为订婚后撕毁婚约,而大打出手的事情。
小姨父虽说在邻村,平时却是很少上门的。但每次过来,总会大包小包的带上很多东西。他为人忠厚,有时甚至显得有些卑微。就连像我这样的小辈,他都会毕恭毕敬。小姨对小姨父谈不上讨厌,也谈不上喜欢。她一脸平淡,仿佛面前的这位与她毫无关系一般。
小姨父并没有因为小姨冷淡的表情而生气。正像妈说的那样,小姨父从来就没有过脾气,何来的脾气可发呢?经过一个阶段的考察,亲戚们都认为小姨父为人老实、厚道。经过双方父母的商量,决定在那一年的腊月,选一个好日子,把婚事给办了。
小姨结婚那天,天公不作美,早晨便下起了雪花,密密匝匝,飘飘洒洒,不一会儿功夫,地上就全白了。小姨父的家与我们村有一条数里长的田埂连着。雪花把田埂盖得严严实实。一眼望去,除了对面的村庄,就是雪白无垠的田地了。
按农村以前的习俗,新娘子是要坐花轿的。但小姨父家穷,请不起花轿。他自己动手做了一个类似于黄山滑杆之类的轿子。在外面刷上红漆,系上红绸,在众人的簇拥下,吹吹打打,格外热闹,也算是挽回了一点儿面子。
“拎子孙桶”是娘家的男童必做的事情。子孙桶一般用痰盂代替,男童拎到男方家后,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得在痰盂里面尿上一泡尿,才算大功告成。老人们说,这样做的寓意就是希望新郎、新娘,子孙满堂……当我作为最佳人选后,母亲不厌其烦地跟我重复了好多遍其中的环节,生怕因我的过失而使得小姨的婚礼不和谐。
由于大雪把路盖得严严实实,结婚的队伍只能依靠感觉在阡陌间行走。为了确保新娘“轿子”的安全,共有七八位亲友在队伍的前方探路。结婚队伍浩浩荡荡,向着小姨父家的方向游走。
不知道是由于天冷还是紧张,我到了小姨父家后,不管大人们怎么催促,我都难以完成自己最后的使命。在我百般努力之后,大人们还是无奈地摇了摇头……不过,小姨并没有因此而后继无人,相反,她第一胎就生了个大胖小子。
初为人母的小姨格外地喜悦。她把刚出生的表弟视若珍宝。表弟也在小姨甘甜乳汁的滋养下,长得白白胖胖。小姨父则整天在外面揽木匠活,没日没夜地干,他们一家的小日子过得很是幸福。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小表弟5岁时的那年春天。突然发热,热度几小时内就飙升至四十度。此时小姨父正在十多里外的一户人家做八仙桌。小姨独自一人,抱着小表弟坐着颠簸的拖拉机,来到了县里的医院。本以为小表弟只是普通的感冒,用点退烧药就可以了,谁知,这一去竟是永别。
小姨经不起这打击,整个人一下子就蔫了。她开始茶饭不思,没日没夜地看着小表弟的相片发呆。娘家人怕她跨不过这个坎,轮流派人看着小姨。后来,小姨生了现在的小表妹。小表妹生的水灵活泼,活脱脱一个全家人的开心果。有了小表妹后,小姨渐渐地忘却了先前的那份失子之痛。
小时候,每年暑假,小姨都会邀我去她家住上几天。小姨家有几十亩地,还有鸡、鸭、猪、鹅之类的禽类需要她去照料,但是就算再忙,有我这个娘家的小亲戚来,小姨每顿都会弄上好几个不一样的菜来款待我。
虽然小姨父常年在外做工,家里缺少男劳力。但这并不影响小姨持家的节奏,小姨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几十亩地的庄稼每年都能有个好收成,遇到雨天抢收小麦的季节,小姨天蒙蒙亮就钻进了麦田,一直到天黑还头带着矿灯在地里干活。
后来小姨又承包了几十亩蟹塘,雇佣了两个劳力,开始了螃蟹养殖。她没日没夜地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忙活着,她愿意承受生活带给她的所有,心中只有一个愿念,那就是生活能够一天天地好起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村子里流行盖楼房,要强的小姨自然不甘落后,把银行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像模像样地盖了三间楼房。除了盖房,小姨剩余的钱都用到了培养小表妹身上去了。用小姨的理论就是——用以后留给孩子的钱来培养孩子,等孩子有了出息,一年可能就会把这些培养她的钱给挣回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小姨日子过得非常节俭。一双皮鞋还是刚结婚时买的,她当宝贝似的保存着。只有在走亲戚或过节时,才拿出来穿一下。回来后她立刻用破布头把它擦拭得干干净净,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到鞋盒里。
小表妹很是争气,她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了省城里的有名高校,毕业后在省城找了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后来,小表妹又在省城成了家,妹夫家里有家族企业。结婚后没多久,小姨与小姨父都来到妹夫的厂里帮忙。
小表妹在她同一小区买了一套房,给父母居住。去年我去省城办事,特意转道去了小姨家。小姨看到我去,拉着我的手,非要留我住上一夜。盛情难却,当晚我就留在了小姨家。小姨为我做了几样她的拿手菜,还特意关照姨父陪我喝上几杯。席间小姨跟我说了很多关于外婆家的往事。她并没有因为自己在外婆家多干活,而埋怨外公、外婆,更没有因为外公做主把她许配给了小姨父,而有半点儿责怪。相反她满脸的喜悦——虽然回忆里有苦、有酸。
第二天一早,小姨就到外面街市上买了早饭,还特意为我做了我小时候最爱吃的糖焗米粉饼。
搬到省城后,小姨父就到妹夫的厂里看起了仓库。妹夫说,以前的仓库出了漏洞,给企业造成了不小的损失。现在,他只相信岳父。这话其实有一半真,一半假。仓库失窃确有其事,但是后来他们家花了大价钱,给仓库装上了无死角的监控,就算无人把守,也不会再出现以前那种情况了。这其实是妹夫的一个借口,因为妹夫知道,只有把小姨父也叫到身边,小姨才能待得长久。
小姨父没吃早饭就赶着去仓库了——他每天都去的很早。小姨叫他吃了早饭再走,他说不吃了。小姨又说了一句,语气有点儿果断,但不是命令式的。小姨父仍旧说,不吃了。他边走边看着小姨,到了门口没有马上就走,而是依依不舍地看着小姨。这时候,小姨又说了一句,路上骑车注意安全。
这看似夫妻间的简短对话,却震撼了我的心。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但我确信,小姨与小姨父刚结婚时不是爱情的使然,他们相濡以沫一辈子,已经把彼此的棱角打磨得格外光滑。他们就像两只咬合紧密的齿轮,没有一点儿卡涩,彼此间的节奏是那样的和谐。
假如小姨刚开始找的丈夫不是现在小姨父,是其他人,我想,他们同样也会磨合到现在这个模样……
作者简介:
徐志俊,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散文百家》《翠苑》《参花》《鸭绿江》《奔流》《西北散文选刊》《青海湖》《文学少年》等。散文《南门坛上》入选北京丰台区2021年高三语文期中考试试卷;散文《父亲的算盘》入选《中考现代文阅读》;散文《捕猎》入选2024年北京房山区七年级期末考试现代文阅读理解试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