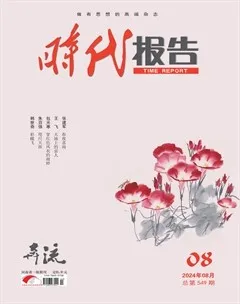老庄
2024-09-21封延阳

闻听说自己死了,老庄差点儿一口饭噎死。
当天中午,老庄正在家门口烩面馆吃饭,听得背后门帘哗啦一声,一个大嗓门塞满了一屋子:“丙院老庄,唉,一声不吭,就死了!”
老庄闻听,一个激灵,把刚进口的一团面囫囵吞了下去,噎得半天上不来气,缓口气伸伸脖子,站起来转身盯着屁股刚挨上座位的老金。猛然看见老庄,老金两个大眼珠都快掉了下来:“唉,这、这、这,老庄,这咋回事?”
“是该我问你吧,咋回事?”
老金抹一把脸:“刚才打牌,那几个货说你、你……我还说别瞎说。他们也是听传说,好像是你院老张说的,还说已经有好几天没见你去打牌了。你看这弄哩。”
老庄一摔筷子:“别人咋说你不会问问?”
老金还要解释,店老板小杨赶忙上前扶住老庄:“叔、叔,别生气,也不怪金叔,这两天我也听有人说,可能是这些天没见着你,瞎开玩笑。”
“这是开玩笑的事吗?”老庄一脚踢开蹬子,搞不清他接着要干啥。
“来,金叔,您陪庄叔喝两杯,我请客。”
“嘴痒!”老庄掏出两张票子摔在桌子上,出门往百米开外的家属院走去。
家属院是指当年建厂后,邻着厂区陆续建成的甲、乙、丙、丁四个职工住宅大院,后来经过房改、改建,职工掏钱买了,也都是商品房了,但人们习惯了还是叫家属院。
老庄家住丙院1号楼1门栋5层,一套三居室。老张和老庄一个门栋,住一楼。当年进厂时两人同在一个车间,老庄因为喜欢写写画画,后来调到厂办,干到办公室副主任退休;老张热情随和,说话、办事粗粗大大的,一直在车间干到退休。两个人一个安静、一个热闹,因是老同事,又住在一块,上班时没断过来往,退休后更是时常一块进出、结伴而行,算是一辈子的朋友了。
老庄窝着一肚子火走到家属院门口,瞅见门卫老李目瞪口呆的样子,火苗子直往脑门上蹿,径直走进门洞对着老张家门“咣、咣、咣”一顿猛敲,不见动静,返身来到老张窗户下,厉声厉色地喊:“老张,你给我出来!”
老张家没一点儿声响,楼上倒是有几扇窗户打开,有人伸头往楼下瞅。门卫老李赶忙跑过来,小着声音说:“他两口前天回老家了,说是要把老家的院墙修整一下。”
老庄瞪一眼老李,喘着粗气走进门洞,上电梯回到家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老庄两口就一个儿子,前些年全家凑钱交首付在新区买了一套住房,小两口带孩子搬过去五六年了。半年前,儿媳二胎生了个儿子,老伴过去帮忙照顾,老庄自己留在家里,想孙子了就过去看看,吃顿饭当天回来。一个星期前的一天晚上,儿子开车过来,说,我明天去北京参加培训,你过去接甜甜上下学吧。老庄立马收拾几件衣服,乐踮踮地跟着儿子去了。昨天儿子回家了,今天上午老庄收拾收拾回来,正赶吃饭点,就直接去了面馆吃饭,不想竟吃出这么一档子恶心事。
老庄掏出手机,戳着老张的名字打电话。不通,再打,还不通,气得老庄把手机一把摔到茶几上:“这鳖孙躲进山里了!”
老张老家在南边几百公里外的山里,前些年老庄去过。山里手机信号不好,基本打不通。老庄浑身憋气发不出来,在沙发上闷头坐到天黑,随便弄口饭吃,重又回到沙发上黑灯瞎火地坐着。
老企业老职工多,每个年头差不多总有十数几个上年纪的退休职工去世,现在啥都是社会化管理,厂里管的事也少了,加上住的也越来越分散,有的老人悄无声息地就去了,隔了好久才听传说知道。“我这身体一直都好好的,再说我又不是七老八十了,这简直,从何说起啊?”老庄越想脑子越乱,可楼下院子里的说话声却听得越来越清:
“老李说老庄回来了,没有死。”
“真的?抢救过来了?”
“我就说嘛,要是真死了还能没动静?”
“回来了,咋也不见亮灯呢?”
老庄听得头都要炸了,起身掂了个小凳,出门下楼。
迎着院门口是个小花坛,到了晚上,便有一些老年人聚在花坛边聊天。老庄“咚”的一声放下凳子,目不斜视,直愣愣坐上去。老庄虽不拿眼看别人,但感觉得到人们立马朝他瞄来瞄去,嘴里说些不疼不痒的闲话,声音却一下子低了下去。
一夜睡不安生。吃了早饭,老庄在屋子里转圈:“干啥呢?”老头们凑摊打牌的地方,不去!去遛弯?触景生情,若是勾想起和老张一块遛弯的情景,还不把人气死。到了下午,老庄取下挂在墙上的宝剑,在手里比划了比划。
街边公园树林里有块小空地,一小群人聚在那里舞剑,清早、傍晚两个时段。老庄觉着挺有趣,拉了老张,买宝剑、置行头(浅色长身大褂),参加了进去。老张身子硬,性子急,兴致不太高,去一下不去一下。老庄学得还算有模有样,一直坚持着,不过或早或晚,一天只一次,隔三差五也有不去的时候。
今天可能来得早了,树林里一个人也没有,过一会,又有两个人过来。看他们打招呼的神态,老庄知道,舞剑这群人也是听说了自己的死讯。看看临到结束也就只有他们三个人,老庄心说,还是怕鬼的人多啊。
往回走到面馆门口,老庄想想:进去!进得屋内,老庄不再像往常那样往角落里去,而是迎门坐下,宝剑“啪”的一声放到桌上,要两个小菜、一瓶啤酒:太他妈憋屈了!老板小杨笑着打招呼:叔,您来了!
来面馆吃饭的,基本就是厂里的职工、家属,都是熟人,吃饭聊天,平日里一个乐趣。今天却有点儿异样,点头打个招呼,只是埋头吃饭,说起话来,也是压低了嗓门。期间,有人挑门帘进来,看见老庄就是一惊,老庄心想:咋了,撞见鬼了?
回到家属院老庄也不上楼,就在花坛边沿坐下,宝剑竖在身旁。周边人一时清净片刻,接着便又嗡嗡嘈嘈起来,老庄全不理会,只拿眼盯着院门口,似乎要看出个子丑寅卯来。
老庄不是一根筋,但这次不知道是要和谁较劲,树林舞剑,面馆吃饭,花坛静坐,一连几天,准时准点。不过,老庄的这份倔犟很快就被瓦解了。
这天,时间点一到,老庄便披挂、仗剑,走进电梯,行至三楼停住,电梯门打开,三楼老太太候在门口,看见老庄猛地一怔:“哎、哎,忘了钥匙了,先走、先走。”说着慌忙后退,转身拿钥匙去开房门。老庄摇摇头,哭笑不得;但低头一想心里不免一惊:这几天上下电梯,好像每次都只自己,难道这7层楼房的住户,全都是爬楼梯上下吗?
真把人当鬼了?老庄越想越恼,舞起剑来便虎虎生风。见老庄这架势,这几天还来舞剑的三两个人便有点儿面面相觑,草草舞了几把就收场走人。
看看成了自己的“专场”,老庄不知为何也泄了劲,收拾收拾去面馆吃饭。点好饭菜坐下一会,老板小杨便端着小菜过来,笑着说,叔,要不您还是往里点坐,清净些。老庄抬头看一眼小杨,没吭声。小杨把小菜摆到桌上,说,没事,叔,您慢用。
老庄扭头扫一眼,只见稀稀拉拉几个人,没声没响地吃着饭,暗暗叹一口气:唉,影响人家生意了。吃到半截,便把钱放在柜台上出门走了。进院径直走进门洞,爬楼梯回到家里。
第二天,老庄便窝在家里不再出门。他翻箱倒柜,扒出往前的书本、笔记、信件等等一些旧东西,堆在沙发上一样一样翻看,想把自己埋进故纸堆里。可是到了晚上,楼下的嘈杂声还是挡不住钻进耳朵:“老庄咋又不见了?”“也不见屋里亮灯,可别再出啥事啊!”“人没死,可那样子是不是神经出了啥毛病?”……
听见有人开门,老庄一惊,见是儿子进来了。“咋不开灯呢?”儿子看着乱糟糟的一屋子,说,咋回事,楼上李叔给我打电话,你这几天有啥不得劲?老庄叹口气,不知道该咋说。
儿子在屋里转了一圈,说,明天把屋子收拾一下吧,我下班来接你。我妈一时半时回不来,你一个人住这也不是个事。
第二天傍晚,老庄坐在沙发上等儿子,手机响了,是老张。老张扯着嗓子:“我看见有你电话,山里打不通,我今天来镇上买东西,能打电话。你回来了吗?”
“我死了!”
“啊,啥呀?”
“不是你给人说我死了吗!”
“啊?啥呀?咋回事啊?我……咋会……”
手机声刺刺啦啦,老张的喊叫声时高时低,断断续续。老庄把手机丢在茶几上,往沙发背上一靠,耷拉下眼皮,任凭老张“喂、喂、喂”喊个不停。
坐上车,儿子的手机响了,孙女甜甜兴奋的声音:爸爸,接着爷爷了吗?快回来,有好吃的!
老庄扭头往车窗外看了一眼,暗暗地一声叹息。
在儿子家,老庄正事就一件——接孙女上下学,其他的,一切听从老伴安排。一天,送孙女上学回来,老伴吩咐老庄去买菜,一二三交代一遍,老庄点头应承,来回一个小时,一头汗跑进家门,打开袋子向老伴交差,谁知老伴一看就皱起了眉头:“这黄瓜、生菜咋都不新鲜?”
“是新鲜的呀,就是不太水灵罢了。卖菜的剩这两样,说全要了便宜,我一看好好的,就买下了。”
“给你说过,甜甜他们要吃新鲜的。”老伴交待说看好孩子,拿着袋子出门去了。老庄盯着地上的黄瓜、生菜,心想,这吃起来有啥区别呢?等老伴赶回来,老庄慌忙认错,老伴急慌慌只顾干活,不搭理老庄。
如此这般,老庄经常需要认错、改错。对此,老庄虽说态度端正,但不免有点儿憋屈。在自己家里,憋屈了还能想法往回找找,可在这就只能憋着。
这天中午,饭菜做好了,儿媳打电话说有事不回来吃饭(儿子路远平常中午不回来,只儿媳回来吃饭)。照顾孙女吃完饭,老伴叫老庄把剩菜倒了。老庄看着好好的菜下不去手,就收拾收拾放在案板上,老伴扭身看见了,说,还放那干啥?
“好好的,还能吃嘛。”
“他们不吃剩菜你不知道?”
“放这我吃。”
老伴正要张口训斥,老庄赶忙拿起剩菜走进他俩住的房间,反手把门关了。晚饭前,老庄把剩菜拿到厨房,下一把面条自己吃了,出门去街上溜达。
老庄颇有些后悔,怪自己不该为一盘剩菜惹老伴不高兴。在街上溜达了一晚上,回到家老伴已经睡下,他洗漱一把摸黑爬到床上,睁着双眼,大气不敢出。
正是难熬这两天,上午,弟弟突然打来电话,问候几句后,弟弟说:天热了,嫂子你们回来住一段吧,山里凉快。老庄对老伴说,老二请咱回老家住几天。
老伴头也不抬:“我走得开吗?”
到了下午,老庄向老伴“请示”:“我在这也帮不上多大忙,要不我回老家呆几天?”
“随你便。”
晚上,老庄给儿子说了后给弟弟回了电话,第二天坐网约车回到老家县城。县城距离省会三百多公里,是个三面环山的一块小盆地,依山傍水,环境宜人。
老庄姊妹四个,他老大,一个兄弟、两个妹子。他和小妹在外地工作,弟弟一直在老家,大妹嫁在邻村。弟弟大儿子在县城做生意,老庄父母过世后,弟弟两口到县城给儿子帮忙。县城到家十多里地,弟弟两口乡下、城里两头跑,也很方便。
在县城侄子家住一晚,第二天侄子开车送老庄和弟弟两口回到乡下老家,吃过中午饭,侄子回了县城,弟弟两口留下陪老庄。第二天,大妹和妹夫也过来了,中午吃饭时,老庄听见弟弟和大妹商量明天给薛家老九打发闺女递礼的事,问,那我递不递?
弟弟说:哥你不用了,你常年不在家,以往也没啥来往;往后在家常住了,再说。
大妹说,咱这客性大,隔三差五的就是娶媳妇、嫁闺女,还有老人过世、小孩过生,都是人情。大妹还提醒老庄说,咱这乡下,人穷礼数多,你就别掺这个茬,有时钱花了,反而得罪人。老庄心想,哪有这道理?
老家这里叫葛沟村。村是行政区划的叫法,实际上没有葛沟这个村子,葛沟是这道山沟的名字。一道沟二十多里地,蔓延分布着十几个自然村。老庄家的村子位于沟口,叫岗口村,后面接着西岗,隔小河再往前便是东岗。东岗、西岗往南延伸出一片低矮丘陵,邻接着县城。
村子二三十户人家,主要是庄、薛两姓。两姓人家连亲带故,邻里相处还都融洽。这些年,村子的场貌地形没多大变化,但房屋、院落变化挺大,主要是房子盖多了,大多是两层小楼、砖砌院墙,也有几家老式院落,起脊瓦房、土坯院墙。因侄子、侄女都住在县城,老庄家的老房屋就没再翻新,正屋三间老式瓦房,厢屋四间砖墙平房,屋子院落虽有些老旧,但安静、凉爽,很适宜居住。
村里有些年轻人和侄子一样在县城安家,但因邻近县城,还有不少人仍住在村里,白天在城里干零活、晚上回家,没活了就在家闲着,农忙时干点地里活。虽说没有以往年代那样人气旺盛,但往来聚散还算热闹,不像偏远农村那样冷清。
弟弟两口陪老庄住了两天便又去了县城,老庄自己在老家住下,三五天下来,四邻五舍便都已有过走动。年龄上下相当的,小时候在一块你争我抢,现在见面说话都一团和气;晚一辈年轻一点儿的,老庄大多也都认得出来,一下就熟识了。老庄家院子宽敞,到了下午傍晚,就有些弟兄、晚辈侄子过来串门。院子里有颗大槐树,有人过来,老庄就搬出小桌、板凳,把带回来的茶叶烧水泡了,坐在槐树下喝茶聊天。
这天老庄午睡刚起来,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堂侄大林。大林进门就急慌慌说,五叔救个急(老庄在庄家弟兄中排行老五),老庄问啥事,大林说,城里朋友给介绍了个活,叫下午去给人家送个礼,手头没现钱,五叔先借点。说是得一千元。
老庄犹豫一下,说:大林啊,我临时回来没带多少现钱,这样吧,我给你凑二百元,你再别人那凑点。
大林接过钱转身就走。老庄想起大妹的话,摇摇头苦笑一声。
天气越来越热,来院里乘凉聊天的人也多了。这天半下午,堂兄弟长生瘸着腿推门进来。长生比老庄小十来岁,老实本分,一辈子做庄稼没出门打过工,前几年一次骑三轮车去卖粮,在村口下坎处翻车把左腿摔折了,从此成了拐子,地里活还能干,就是不利索,也出不了大力气。
进出山的路,从东边贴着村子穿过,路里边是农田房舍,路外侧立陡一道坎,坎下是小河。路到南边村口,有一个北高南低十来米长的下坡——村里人叫“下坎”。下坎处,里侧紧靠着高出一截的田埂,外侧陡坎三四米高,坎下河道里有几处水流冲出的水坑,看上去有些险峻,长生就是在这里把腿摔骨折了。
老庄还记得,他小的时候乡村没有机动车,人们进出山拉货,运东西,用的都是架子车。有几年,县里在城边修河、造坝、建桥,几万人吃饭,每天都有十多辆、几十辆架子车进山砍柴,回来走到下坎处,车上柴禾蹭住里侧田埂,把不稳就连人带车翻倒在坎下河道里。坎不高,人、车一般也都摔不坏。每当这时,村里人就热热闹闹地围过来,说笑着帮忙把散落在河沟里的柴禾抱上来、架子车抬上来,重新装好。老庄那时也踊跃参加“抢险”,觉得挺好玩的。
前些年修村村通公路,本来应该把这条老路改造了,但因老路穿过十来个村子,加宽路面常常需要占地毁田,村民工作不好做,公路就从村后沿西岗坡跟修了过去。因公路绕弯,开汽车的走公路,行人和骑摩托、三轮的,还是习惯走村里的这条老路,翻车“事故”也就没有完全断绝。
“没留下别的啥毛病吧?”老庄问长生。
“别的没啥,就是干活不中用了。”
“现在地里有多少活干?”“这把年纪,没毛病也该歇歇了。”大家纷纷说长生。
“早年那时候差不多天天有翻车的,你咋就摔得这么厉害?”老庄问。
“年轻人手脚利马,顶多摔坏车子。我这老胳膊老腿,骨头脆。也是倒霉,那年雨大,河里水坑冲得太深了,窝了进去。”
老庄看看大家,说,没给村里说说,下坎那一截,从河底往上用石头包上来,路面加宽个一米,再修个路帮,就不会翻车了。
“现在都是各干各的,村里谁管这事。”
“村里想管也没钱呀。”
“花不了多少钱吧?”老庄问,“村里没钱,大家多少凑一点儿,几千元钱就够了吧?”
“咱岗口凑?山里那几个村呢?路大家都走。”
“谁愿伸这个头?谁伸头谁得拿钱。”
“五哥,”对着老庄说话的是薛家老七,“你们国家干部,干不干月月拿钱,三五千不当啥,农村人挣个钱多不容易。”
“七叔你说的也不对,还是咱村没大款,人家南湾沟口那座桥,不就是赵家大春自己掏钱修的?听说花了一两万元呢!”
“五叔,”一个稍年轻一点儿的侄子对老庄说,“你找几个在外工作的,赞助一下呗。”
没待老庄回话,长生叹口气,说,我是不操这个心啦,再修这腿也修不回来了。
老庄进屋拿出几瓶啤酒,叫大家拔拔凉。
隔两天,老庄转到下坎处,绕着路边看了看,心想,要是修也真花不了多少钱。正看着,“吱”一声一辆摩托停在身边,大林跨坐在摩托上,说,五叔,您要修这下坎啦?这可是积德行善的大好事啊!
“别瞎胡扯!”老庄白一眼大林,转身走了。
隔天中午,大妹过来做好饭,俩人在小桌边坐下,大妹问:咋说你要修下坎?
老庄心里烦烦的,说了那天聊天的事。大妹说,你可别再提这事了,现在啊,做好事也落不住个好。你听他们说了南湾赵大春修桥的事了吧?南湾那条河平时就没水,可夏天一发水就得绕道过。赵大春在县城搞建筑,也懂得修桥,就花钱在村口修了个水泥桥,也就两丈来宽。人们当着面都夸赞大春,但背后里也有人风言风语,说赵大春有钱显摆,还说修桥是为了他自己开车方便。前年涨大水,桥洞被刮倒的树堵了,水漫上来淹了河边几块庄稼,人家找赵大春赔偿损失,赵大春气不过,把桥给拆了。
一场大雨下来,仿佛把老庄压抑、憋闷的心情也冲刷得舒畅一些,修下坎的事也渐渐不再有人提起,可没过两天,一场翻车事故又把这事给搅腾起来了。
这天下午,几个老头在院子里聊天,一个堂侄推门进来,说,薛攀子在下坎那摔了。有人要起身去看,堂侄说人已经送医院了,众人一惊:摔得不轻?
攀子是小名,大名叫啥村里人不知道或记不起来了,因为攀子是个傻子,好像用不着大名。薛攀子不聋不哑,可能是脑子没发育好,有点儿痴呆,能明白个简单话,也能干些粗活,一辈子没成家。他就弟兄俩,父母去世后一直跟着他哥住。他哥叫长根,薛家弟兄里排行老四,和老庄小时候是同学,年长老庄两岁,家境稍微艰难一点儿,六七十岁的年纪了,还在忙地里活,老庄回来见面聊过两次,但他没来院里坐过。
那天,薛攀子按他哥吩咐,用架子车拉着几块石头,去村南边准备把被雨水冲坏的地埂垒一下,走到下坎处翻车了。看见的人说,薛攀子不知道是被车里滚出的石头砸着了头,还是头碰着了河里的石头,当场就昏迷了。送医院好几天了,人还没醒过来,人们说,会不会成了植物人。
薛攀子出事后,人们见着老庄就说:还是你说得对,应该修;要是有你这样的人伸个头就好了;五哥你看这事该咋办……老庄心里郁闷:这咋就成了我的事了?
这天早上,老庄出门便迎面碰见长根两口,看样子是往医院赶。老庄问:四哥,攀子咋样了?
长根摇摇头,叹口气:老五,要是按你说的,修一下,咋会出这事呢?
长根老伴瞪一眼长根,说:该咱倒霉,能埋怨谁?
看着长根两口走远,老庄回身关上门,坐在院子里发呆。中午也没安生睡着,就早早起来把衣服、零碎收拾好装进背包,锁好门往镇子上走去。
村子到镇上有三四里地,走到镇子边上,看见有只黄毛小狗在路边直盯盯望着老庄。老庄停住脚步看着小狗,小狗也拿双眼和老庄对视。看了一会老庄扭头继续走路,走出几步回头一看,小狗紧紧跟在身后。老庄停住脚步,小狗也停下不动,如此三番五次,老庄索性在路边石凳上坐下,小狗离老庄几步远趴到地上,抬头看着老庄。老庄从包里摸出几块碎饼干扔过去,小狗用鼻子拱拱,并不吃。相持一会,老庄起身继续走路,小狗仍碎步紧紧跟着。
到了公路边,就有拉人的摩托、机动三轮车围过来。老庄谈好一辆带篷子的三轮车,坐上去,车子发动走了一截,老庄忽然发现,那只黄毛小狗在车后小跑跟着。车子越跑越快,小狗仍穷追不舍。老庄叫车主停住,向小狗招招手,小狗一个飞跃跳上车,在老庄脚边卧下。
老庄摸摸小狗的脑袋,望着车外的田野山岗,心里说:小家伙,你是找不着家了,还是本来就无家可归?
作者简介:
封延阳,河南西峡人。长期从事科技图书编辑工作,曾任国有企业集团副总裁。曾发表《霞姑》《手机丢了还找吗》等小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