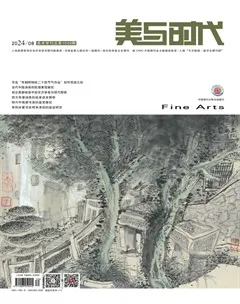形式突破与意象捕捉
2024-09-18李琪
摘 要:张大千晚年所创的泼彩山水,集大成地体现了其艺术生涯的技法表现与审美意趣。其创作大致可以分为泼墨实践、渐次摆脱传统笔墨而走向色彩表现、走出借古开今的墨彩冲合三个阶段。泼彩山水画以色造境,从传统的随类赋彩走向独立的色彩表现,有去形、写意、造境的特质。去国离乡是张大千走出传统创造泼彩差异化发展的契机,立足中国传统绘画设色、探寻中西方艺术的共性是张大千得以成就泼彩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张大千;泼彩;色墨关系
张大千相循参伍各时期的笔墨特质,因革通变,以其庞大而多元的综合性手法所开创的泼彩技法,成就了其在中国艺术史上难出其右的折中式综合主义的典范[1]。论其笔墨内外,有变,也有不变,但常于变中以求不变更多一些。其早年大多在极力地摹古、仿古,鲜少有明显的个人绘画风格特征。在历经离乱与漂泊的晚年时期,他却大胆走出以往成熟的风格,将于敦煌习得的厚重浓丽色彩融入青绿山水,并重新进行诠释。同时,他把传统绘画所倚重的笔与墨的关系转向色与墨的关系,更倾向于以图像表现本质,遂开创出氤氲瑰丽的泼彩技法。艺术观念的变化是张大千画风转变的前提,在中西文化交融的20世纪,张大千衷中参西之艺术观念是其画风转变的内因,故其泼彩作品于当下追求文化多元的世界环境中愈发彰显出中国文化特有的自主性与包容性。
一、变:没骨青绿出泼彩
从没骨的角度看泼墨,不妨视其为泼彩之先声。而泼彩山水,正是张大千以没骨手法不见笔迹地运用传统青绿等色彩于山水画中的一种独特技法,有着较为清晰的华丽蜕变过程。张大千的“泼”法创作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从大写意延伸而来的泼墨、加入青绿二色的早期泼彩、走向抽象的中期泼彩、回归传统意蕴的晚期泼彩。
张大千在创作泼彩之前,先进行了泼墨实践。这一阶段的创作仍采用许多传统大写意风格的泼墨手法,但是张大千将线条、皴擦等较清晰的笔触融入混沌的色块中,这体现了他从“师古人”“师造化”转向“师心”的变化特点。其泼墨泼彩创作,一般以1959年秋于巴西八德园创作的《山园骤雨》为起点。然而此前作于1956年的《珠江夜月》,除了右下角极小处以浓墨勾出船只轮廓、淡墨勾出水纹外,还有以淡墨侧锋横扫出大面积的月色景象,其中的江面与天际融为一体。张大千在画面主体上舍弃了线条造型,仅仅依靠墨色进行渲染。
1963年创作于八德园的《泼墨青绿山水》与《观泉图》,大概也是张大千对泼彩技法的早期尝试。值得注意的是,张大千中年归蜀时的《西康游屐》写生图册,其中数幅作品均依稀可见泼彩山水的影子。如果说《观泉图》与《西康游屐》中的《五色瀑》的山峦造型与瀑布点景的位置经营只是存在相似之处,那么《蜀中四天下》四屏之一与《西康游屐》中的《飞仙关》则从山峦造型到画面留白都大致相同。《五色瀑》与《飞仙关》均以线造型为主,青绿设色与皴笔结合,薄施色彩仅作提亮装饰之用。《观泉图》是张大千初试泼彩的重要作品,他先以较传统的笔墨打底,以干笔侧锋横扫表现树石,并以中锋勾勒出房屋、人物,形成完整的构图布局,后用赭石色打底,在画面上半部分的山峦位置泼青绿二色。渲染由上而下,富有流动感,色彩浓烈并与墨线相互协调照应,将植被繁茂的幽静山谷中所暗含的盎然生机尽呈笔端。脱离线条“骨力”的支撑后,转而以色为骨的张大千尚未探索出能够表现原有力量感的技法,此时所作之青绿仍主要在山体上与墨色流动交融,整幅作品的张力与表现性尚弱,处于泼彩的初步探索阶段。
到了1965年,张大千的泼彩逐渐摆脱“笔”的限制,不再依赖于墨,转而直接用色彩独立创作。1967年的《瑞士雪山》《秋山夕照》两幅作品,画面表现都极具西方现代艺术感,与传统山水的关联性十分微弱。张大千在《瑞士雪山》中,抛弃了构图中上留天、下留地的习惯,改为西画常见的满构图,或参考了摄影构图亦未可知[2]。传统山水中表现云雾所常用的留白也换成了西画中以直画法的方式施加白粉,展现传统山水未有的强烈光影感。《观泉图》以墨色为底、上施众彩的方式,将彩色变成画面主体。《秋山夕照》更是大胆地放弃了墨,整体以色彩构建主体造型,打破了传统设色重于还原自然物象本来相貌的随类赋彩原则。
值得一提的是,创作完成《观泉图》四年后的1967年,张大千又开始逐渐在更高层次上向传统回归,力求以其雄浑的“混沌手”开辟出一片似与不似间的新平衡。这一年他创作的《蜀中四天下》,虽然保留了抽象意味的特点,但画面主体已经摒弃了传统山水画中以线造型、以皴笔表现体积的手法,不再依托传统笔墨,而是变青绿二色泼彩为画面主体,画面中央的山体几乎全用“泼”法进行表达,几近于西方抽象画的艺术观感。其总体造势及隐蔽边角有具体的对景表现,在一片墨色交融中以少许笔墨收拾山石肌理、树木形态,再加上山顶作点景的楼阁、用墨色挤出留白泉水的溪流等,从而“于混沌中放出光明”。这幅作品结合了“泼”“破”手法,虽仍以墨色打底,但线的表达极为微弱,亦无勾勒与皴擦。此时,张大千的泼彩技法已颇为娴熟,大尺幅、大气度的画面表现非常得心应手与潇洒自如,笔下的色彩也不再局限于传统山水画中较平面的表达形式,已有了表现山水隐隐肌理、动势,甚至情绪等方面的效果。其在最后的绢本水墨泼彩横幅巨制《庐山图》中,纵情恣意地表现其胸中山水,倾情挥洒,达到了中国山水画“师心”之最高境界。
二、不变:泼彩天生为写意
“山川草木,造化,此实境也。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虚而为实,是在笔墨有无间,故古人笔墨具此山苍树秀,水活石润,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3]张大千泼彩作品的流动感,正是对自然中“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的捕捉与重塑。中国画讲究寄托精神所在,素重由画入道。艺事之极,故与道通,因而技法易变而意境难改。“泼”法游心于无垠中以显大气势、大寄托之“意”,从舍弃具体的山水物形到追求色彩写意,再到回归传统意味的山水画境,张大千不同阶段的泼彩实践特点十分鲜明:去形、写意、造境。“要在像和不像之间得到超物的天趣,方算是艺术。正是古人所谓遗貌取神,又等于说我笔底下所创造的新天地,叫识者一看自然会辨认得出来。”[4]
(一)去形:由实入虚,曲尽蹈虚揖影之妙
中国山水画的最高艺术境界不是对客观物象的真实表现,而是构建向往的“心中山水”。书法用笔与传统水墨画相通,形态多样,变化丰富,常常作为山水画的基本表现手法。写意山水不是真山水,而是主观再现的“真山水”。如果说工笔山水是让观者看到画家所看到的山水,那么写意山水是让观者意会到画家所感受到的山水。“得意而忘形”的思想使绘画逐渐脱离客观具象而转向“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抽象形式美。具象实质上是由移情或假借之象转化而形成的,本质仍存在写意的意味。而抽象也并非不表现任何形象,实为凸显人形象思维的纯形式图像。没骨的泼彩山水既能够表现具象,亦可表现抽象。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画的创新相较技法与媒介而言,更注重精神与思想上的突破。
张大千早年曾拜于曾熙门下。曾熙好以草篆、行狎之笔来展现山水草木,笔墨寥寥但强调骨力,具有空旷萧散的审美特性。从强调骨力走向没骨,王洽创泼墨并赋予了大写意这一全新阐释。泼彩衍自泼墨,在注重笔法的时代,这一重表现材料本身的技法并未受到重视。张大千的泼彩山水并非站到了传统骨法用笔的对立面,二者互有内在联系。“从没骨观之,写是对骨的回归;从骨观之,写是对骨的弱化。”[5]张大千以色墨为形,以势为骨,以水为气,气行而形骨俱活。当水冲破传统笔墨后,原拘于笔墨框架内的“泼”与“破”开始关注材料本身所产生的独特质感,即走向材料自然。
张大千以“泼”法进行创作的过程与波洛克的抽象主义创作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其在传统水墨材质的基础上融入随机性的特点,使画面物象脱离了具体形态。纵观整个水墨发展史,可以看到虽然形体一直在随着时代审美发生变化,但笔墨语言却成为相对形来说更加稳定的因素。这意味着形的表达是次要的,要更侧重于笔墨的表现与意象的生发。
(二)写意:画骨不易,色之形即意之表现
清唐岱在《绘事发微》中以诗意化的感性表达描述四季之景:“春山艳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洗,冬山惨淡而如睡。”这又何尝不是人的情感与真山真水相互交融后产生的第二自然?对此,传统山水在设色表现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文人往往贬斥绚丽的色彩,正如先贤所说,“恶紫之夺朱也”。这些思想也都不同程度地在传统绘画中得到了体现,并直接导致了唐宋以后色彩发展的停滞。南朝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谈到“以色貌色”,“貌”是表现手法,画家通过主观概括以达到期望的色彩造型目的。中国画色彩的象征指代存在于传统文化中,二者间存在稳定而特殊的关联。寄托于礼的、带有象征指代意味的色彩类属于形,不同的形含有不随时代变化、指向相对稳定的意蕴。同时,中国画设色具有鲜明的类色特点,如青绿山水中不同的山石采用相同的石青、石绿、赭石,不同的花木采用相同的花青、藤黄和胭脂调出。这种概括来源于自然又与自然不同,其“象”中之“意”来源于人与自然合成的有机共同体。中国的色彩富有人文情怀,与主体意识和宇宙生命观紧密相连。不同于西方设色注重微妙的时空变化,中国古代设色是高度概括且时空合一的,其概括愈纯粹,意象生发的空间愈大,可以说是一种色彩中的“留白”,也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色分五彩”。
张大千的泼墨泼彩创作,有着对不可形而可见意象的表现优势,弥补了传统写意的不足。由古及今,笔墨之写意自文人画始就研究者颇多,而研究色彩写意者相较之下显得匮乏。“墨主色补”的设色原则一直延续到清末,因受“西风东渐”的影响而有了改变,人们对色彩的追求逐渐走向视野的中心。张大千早年师法石涛而后上溯“董巨”,继而走向敦煌的绚丽多彩,也是受20世纪中国画坛对色彩重新开始重视的影响。张大千的泼彩在色彩的意象表达上进行了相当时间的探索,其画中的青绿二色与自然界中的色彩颇为相近,而且在泼的过程中,色彩流动、沉积的状貌又展现出自然山川起伏之相,既有色彩的象真,又有自然景物体量的表现,山水之“意”自然浮现于笔端。
(三)造境:游心妙用,笔补造化以夺天功
内心体验在画家的艺术实践中起着决定作用,正如画家石涛所说:“画受墨,墨受笔,笔受腕,腕受心。”石涛不仅描绘了书画创作过程中的物理动作链,还隐喻了创作背后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写境以客观存在为基础,创造出的作品为实有之境;而造境以主观意识为基础,创造出的作品为意象之境。山水画的造型为典型的意象造型,其形即为“象”,而要探讨“象”,就必须探讨其背后之“意”,写意具象化表现在画面中即为形的取舍。艺术家用理性的认识引导感性的感受,再从感性的感受向理性的认识回归。张大千早年开始便致力于入古,中年遍游青山,晚年移居海外后又受现代艺术思潮的启发,其艺术实践恰恰经历了这一过程。
中国传统艺术在造境时素重虚实相生,对于空间宇宙的理解常于有限中见无限,又于无限中回归有限,中国画的构图也因此具有“提神太虚”山川入我胸怀的观照意识。张大千泼彩所造之境,也是巴蜀民间文化、地域特质、道禅思想及特定时代的反映和再现。西南地区泼辣且自由的民风民俗,使得他创作的泼彩画更加厚重、绚丽。再加上多年的旅外生活,使他的画中融入中西结合的特点,视觉效果奇绝多变。道禅思想认为,万事万物皆可圆融互通,“一切皆一”,并非仅执于“耳只是耳、鼻只是鼻”的本相,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张大千的艺术创作。
张大千的“泼”法从自然物象的生动意态与肌理质感的体悟中生发,形成了包含物理、物态与物情的整体意象。他题《西康游屐》图册云:“西康景物,虽无危峦奇峰之胜,然丛山万重,急湍奔逝,亦复雄伟深邃,有拍塞天地之概。”其中的多幅作品均能在晚年泼墨泼彩创作中看见踪影,可为前句之明证。不论张大千此后去往何处,均能从其作品中品出一派雄伟深邃,晚年居海外所作泼墨泼彩作品更是饱含了“辟混沌”之感。
张大千无论是对“泼”法的探索,还是对色彩意象的追求,其目的皆为能“尽其灵而足其神”地表现出所感与所发。他突破了传统青绿山水难以自由地表达个人情感的工整特性,与受到一定制约的程式化语言表现。本文分析了张大千的泼彩绘画探索,探讨了笔墨与色彩的关系,或能为当代山水画意象设色找到一条新的可行路径。
参考文献:
[1]汪毅.张大千的世界[M].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08:149.
[2]冯幼衡.借古开今:张大千的艺术之旅[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316.
[3]方士庶.天慵庵随笔[M]//周积寅.中国画论辑要.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5:263.
[4]李永翘.张大千艺术随笔[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10.
[5]林若熹.水论中国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126.
作者简介:
李琪,四川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画与书法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