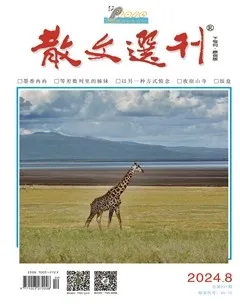听!那胭脂花开的声音
2024-09-18单国伟
我与文学结缘始于1992 年的春天。
那时,我正读高一。一个课间休息时间,同学们都跑到教学楼下玩耍去了,唯有这位来自山丹的同学捧着一本装帧精美的《焉支山》杂志正读得津津有味。
他在看什么呢?我十分好奇。于是,我搞了个恶作剧想吓唬他一下。不料,他像沉睡于梦中一般无动于衷,这让我不禁大失所望。
到底是什么让我的同学如此着迷,竟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我开始学着同学的样子,用心去读它,认真欣赏它,有事没事想它念它琢磨它,希望从中找到答案。
慢慢地,我对这本杂志产生了某种特别的兴趣。在课后的操场上,在宿舍的台灯下,在柳絮飘飘的小河边,到处留下了我们相依相伴的身影。它那精美的外表,散发着油墨芳香的文字,还有同学亲笔所写的那首优雅别致而充满淡淡忧伤的《无题》小诗,渐渐吸引了我,也深深激励了我。
随后,我也学着同学的样子开始写稿投稿,希望能像同学那样在《焉支山》发表一篇署有自己名字的文章。起初,我不敢告诉老师和同学,只是悄悄地写,又悄悄地投,像个偷偷做坏事的孩子。
可是,半年多过去,一封封投稿信犹如泥牛入海,打消了我的写作积极性,也差点儿打碎了我的文学梦。
那段时间,我不再做宁肯三顿饭不吃,也要省出一枚投稿邮票那样的傻事,也不再每天课外活动和晚自习时间都泡在阅览室里一本接一本地读书写文章,更不会和班里的文学青年高谈阔论那些有关文学和文人的故事。我甚至怀疑以前老师总把我的文章作为班里的范文来念是多么虚假,简直是哄骗同学们按时交作业完成任务的可恶的伎俩。
一气之下,我把一支抄写文稿的心爱的钢笔踩得稀巴烂,把以前写的文章底稿全都撕成碎片,通通扔进了茅坑里。
可是,就像一个人的灵魂之于肉体,有些东西与生俱来,怎能割舍得下呢?
不久,我终于收到了《焉支山》杂志编辑部老师的来信。随信寄来了我的小小说《命》的样稿,还在样稿上用蓝色钢笔工工整整地修改了几处不妥的地方。在信中,老师诚恳地指出了我在历次写稿中存在的不足,还鼓励我要持之以恒,大胆地写下去,最终实现我的文学之梦。
直到今天,我一直像宝贝一般珍藏着这篇样稿。
后来,我参军到了部队,与家乡远隔万水千山。没想到,当兵第二年竟又与一位山丹老乡结下了“梁子”。
当时,电脑绝对算得上是稀罕之物,就算在装备保障并不差的部队机关,能用得上“四通”打字机的也是凤毛麟角。在当时几千人的老部队仅有三台打字机,在许多人都想把一手钢笔字变成漂亮的铅字的情况下,我这位山丹老乡居然掌握着一台“四通”打字机的使用权,而且,没有政治部首长的签字,谁也别想找他打到一个字。你说,牛不牛?
当连队文书时,我自掏腰包买好烟好酒讨好他巴结他,请他帮忙打一份铅字稿,可他铁面无私,就是不肯。当了机关报道员,我与他同一个饭堂里吃饭,同一个澡堂子里洗澡,课后一起光膀子打篮球,还隔三岔五请他打个牙祭什么的,希望他看在老乡分儿上,帮忙打份新闻稿投给报社,可他视规定如圣旨,没有给过我一次照顾。
我越想越生气,越想越不是个滋味。
不就一个小小的打字员吗,有啥了不起?
等哪天当了领导,看我不给你小鞋穿!我甚至开始讨厌起这个愚顽不化的老乡,经常借机远离他,不再与他形影不离。
可是,随后发生的两件事,慢慢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
由于部队办公条件的改善,机关科室和营一级单位先后配备了一台电脑打字机。可全旅会打字的就那么两三个人,好多单位排队来找这位山丹老乡学打字,都因他工作实在太忙根本排不上号。
有一天晚饭后,他主动对我说:“知道你一直想学电脑打字,我来教你吧!”说着,拉着我来到他的电脑打字机房,随手送了我一本学习打字的书。他先是一字一句地教我背记电脑打字的口诀,而后手把手地带我练习上机操作。很快,我就能单独上机操作电脑打字了。
那天,他一直陪我练到晚上两点多,直到我单独打完一篇简短的新闻稿,我们才打着哈欠搂着肩膀返回了宿舍。
第二天,他见我学习很用心,也很刻苦,就把我叫到他的机房,主动把他每分钟盲打180 字的“秘诀”传授给了我。在他的耐心教导下,我的打字速度很快提高起来,已经可以单独执行打字任务了。
过了几天,他主动找到管我的科领导,推荐我当了科里的打字员。这让我可以随时随地打出自己所写的新闻稿,既方便了我修改完善稿件,也大大地提高了我的稿件命中率,还在年底评上了旅里的先进报道员,获得了一枚优秀士兵的奖章。
日子过得飞快,很快到了年底的五公里越野考核。由于平时疏于锻炼,加上营区外的道路崎岖不平,我不小心被绊倒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皮,还流了血,疼得我龇牙咧嘴站不起来。
看见我的这副狼狈样后,他赶紧从队伍前面倒退回来,从我身上取下军用背包和行李扛到他的肩上,使劲儿用臂膀架起了我,帮我一瘸一拐地完成了年度考核任务。
虽然我俩最终都没考及格,但他那一身的汗水和满腔的真诚,深深地打动了我,也让我从此彻底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再后来,我在部队要结婚了。听到这个消息,那个对一本杂志如痴如醉的山丹同学,给我寄来一套全新的《焉支山》。他在杂志扉页写下这样一句话:“读好书,走好路。祝你们一生幸福!”
而那位乐于助人的山丹老乡,则寄给我一包胭脂花粉,说是送给新娘的礼物。我问他何意,他讲了一个动人的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胭脂山下住着年轻的两口子,结婚三年仍没有怀孕,四处求医无果。有一天夜里,突然梦见院子里长出了鲜艳的胭脂花,他们以为是神灵的旨意,耐心等待,终于喜得千金,便取名胭脂。
胭脂长大后,漂亮贤惠,聪明伶俐,村里没有一个人不夸她。有一年大旱断水,瘟疫流行。村里的人都病倒了,唯有胭脂姑娘没有得病。她为救乡亲们来到山上,想在山坡上凿出山泉,救出水深火热之中的乡亲们。直到她累倒在石头上,也没能凿出山泉。胭脂的诚心感动了王母娘娘,给了她一把金斧和一袋花种。胭脂用金斧一挥,便劈出了一股清冽甘甜的泉水,聚在山坳里形成了一个湖泊,叫“百花池”。
胭脂姑娘用双手捧着花种往水中撒去,山上湖边立即开满各种各样的鲜花。水流到村里,疫病解除了,庄稼返青了,村民得救了,胭脂花也开遍了山野。
人们为了纪念胭脂姑娘,就把她凿石取水的山叫胭脂山,又叫焉支山。胭脂花,又叫指甲草,当地人把指甲草和明矾放在一起捣碎,再给女人染指甲。这样染出的指甲红中透黄,颜色鲜亮,非常漂亮。
我明白了,他大概是希望我的新娘像胭脂姑娘一样勤劳善良,又有如胭脂花的天然之美。
我期待着,想象着,明年这个夏天能和家人一道,千里迢迢,从南国他乡返回魂牵梦萦的北国故里,与梦中的那山、那水、那人,来一次浪漫的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