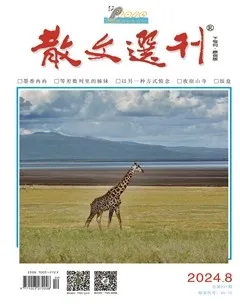慢慢即漫漫
2024-09-18郝永伟
2023年,岳母、舅父、伯父接连病逝。当他们不再足踏晨霜、为俗世奔波的那一刻,当他们携一世记忆离去的那一刻,我深深陷入无尽的关乎入世的挣扎与反思。
世间生命最终会消散于太虚,归于平静,那么,眼前的一切是否真的就如空爪擒幻龙?烛光照千寻,亲情天地流,这些亲人深深关联着我的前半生,陪我走过了或长或短的一段人生路。正如外卖骑手王计兵所言:“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而他们作为终生赶时间且没有太多人生选择的人,却都被迫选择了在自己的最后一站下了车,生命竟如流星划过苍宇般迅忽。一种放下又拿起、最终要放下的情感伏击了我。就在同一年,老家一个发小,因脑出血而昏迷,需要做开颅手术,所幸手术很成功。尽管已经到了悟得镜中身的年龄,但同龄人游走于生死之间所引发的那种内心灼热感,还是一下子烫伤了一起挂在老槐树上的我们在故乡的乳名,令我一度悲怀难遣,乃至在乡风几度中不停打探其他故交的下落。毕竟曾经我们都是“相思无固见,怅望凉风前”的少年。
“转身回望来时路,才知生时为何哭”,父亲的持续衰老和孩子的不断成长,让我豁然理解爱伦堡的“我恍然大悟,我的一生已裂为了两半”,莫名就具备了一种让生命淡泊的心态,接受自己的普通,越发看重家庭与亲情,体味到何为担当和肩荷。水流云在见人心,说实话,我没有做到东坡先生《哨遍》中提及的“我今忘我兼忘世”,反而这一切,成了我人生中的一种怕,怕自己最终会想不起经冬的韭菜、风中的榆钱、闪耀着大写青春的故乡的容颜,还有那些木槿花不再伤痛的夜晚。这一人生之怕,虽然不至于在生活的变故到来时,让我再次自乱阵脚,但是比任何时候都让我清醒地意识到自身与岁月,进而无形中促成了我对回归生活本质的渴望。这种渴望,并非“耗精神于号呼,掷光阴于醉梦”,亦非朝镰暮锄的田园牧歌,而是在马不停蹄的生活中让失序的心灵有所整顿和皈依。待一世奔波,繁华落尽,好快然消失在风雪中。文章憎命达,江湖秋水多。鲁迅先生认为“世间许多事,只消常识,便得了然”。确实如此。可以解读的一种维度是,日常群体性生活环境之下,大可依他人思绪行事,不必过多在意那些交往中产生的有待过滤的气泡。甚至在无法参透局中珍珑时,心甘情愿去做一个局外人。另一种维度是,有且只有短暂的“寄迹江湖”、同归林下,才能怀揣生命深层孤独大旨,据自己想法而活,无惧年龄,再次获得与天地共融的崛起之力。置身于时代的滚滚洪流,我的另一种怕,自然是担心自己不幸把一生活成了别人眼中的、前一种维度的总和,活成了马克·吐温笔下的“有时候真实比小说更加荒诞,因为虚构是在一定逻辑下进行的,而现实往往毫无逻辑可言”,永远失去拥有那个“有且只有”的机会,失去我之为我、我竟成为我的途径,再也无法在温暖逐渐缺席的时空里,亲挽衣袖,去触摸世界的本质,感受被天地正气赋形后的另一种样貌。禅悦不因寒寺远,世态有如云变故。因缘际会之下,梅州之行和景德镇之行,一前一后,为我提供了生命再次飞翔的经验以及理想着落的地面,让b1966c24293382ef49274adeda4961df868bef85c7261cf0d918e61a958e177f我感到精神不再迷离,经脉不再乱转。这短暂的江湖奇迹所蕴含的治愈力与生命活力已不待言。
关键是,两次出行,分别受研学时代的同窗好友杨杰、周小泉相邀。
我们从中国客家博物馆出来,再冒雨驱车到达松口古镇客家人下南洋的地方——火船码头。客家人历史上自秦始皇时代始到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止的五次南迁,五次与现实世界的战乱、瘟疫、自然灾害等的不屈抗争,仿佛一根极细极细的生命琴弦,又似一江被南风裁开的壮阔水面,随之鲜活呈现。烟波横陈,细雨蒙蒙,片片孤帆引入天际,在生命大节上立得住的客家人,就是从这里出发,用生命书写着别样的乡愁。
而景德镇之行,无疑可以视为我向“细湿衣衫岚酿雨,长避天日树垂藤”的江南,表达别后重逢欢喜之情的又一个例证,赣东北,大皖南,立体而惬意。从瑶里古镇到浮梁五品古县衙,从陶溪川到三宝蓬艺术聚落,乃至延伸至上饶婺源的江岭与江湾,绿水、青山、明清古建筑,在雨水的浇灌下,有密度的反复,有强度的叠加,有热度的回旋,无形中构成一种无界限的、独树一帜的时代之思。宋代僧人释心月《示圆阇梨偈》曰:“而今尘尽光生,照破青山万朵。”伴着将晚的行云,浓浓的红茶,而我想说的是,所有风景在人间真情面前都会降维。不要问那个握手言别的站台和共同淋过的那场雨还在不在,“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人生在世,衔理想之命,谁都逃不开现实的侵扰,唯有阅历可将胸次不断推向寥廓。
星辰布满天,风骚挽手行。这几年,深度调和了文化传播者与文学创作者之间的角色关系后,写作几乎化成了生命的一部分,给我以无尽的代入与投射。作为一名编辑出版人,虽无倚马可待、下笔千言之才能,但在对当代书画印艺术的品读式缓慢书写中,我依旧致力于用文学引领笔墨、用诗意提炼画意,因为,艺术品评或者批评毕竟不是跑艺术的龙套,最终要归结在从性情的抒发到人文的自觉上来。
博尔赫斯认为:“具有现代性就是具有当代性,和时代共脉搏、同呼吸;事实上我们都是这样,无一例外。”关于这一点,我在闫平女士的“母与子”“时间的观光者”“美人鱼”等油画系列中,在尼玛泽仁先生吸收唐卡、中国水墨画以及西方绘画技法营养而创作出的藏画风情中,在梁明先生、白联晟先生等富有地域特色的山水里,在赵熊先生、崔志强先生、傅永强先生等独特而带有滚烫的情感熔岩的篆刻天地间,在夏湘平先生、刘云泉先生、丁申阳先生、胡秋萍女士、张维忠先生、李明先生等的书法笔墨形象中,分别得到了验证。当代艺林,他们堪称不离不弃、守护到终了的敲钟人卡西莫多,“行发乎迩,见乎远”,用手中的笔与刀,决然拦下了从王小波口中喊出的那句“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艺术的语言镜像,除了拿高超的技法做支撑,最终需要巨大的人文精神做基石。
不必细数有几分明月当头,仿佛在胸前的和田玉上磨亮的品性与心境,此次结集出版的文字,冠以“既见君子”之名,汇集三十九名当代书画印艺术家的篇章,悄然成了我心头最为真实的一季花开。我知道,这样的书写样式与表达情怀,未必会被公允而严酷的时间看在眼里,但它确乎是我将个人笔墨书写汇成时代映象的一种努力;是把书画印艺术家刀笔世界呈现出来的无穷大与无穷小,以语言文字中表达敬意的一种尝试。无意却意合,无法却法随。天外问天,梦外说梦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