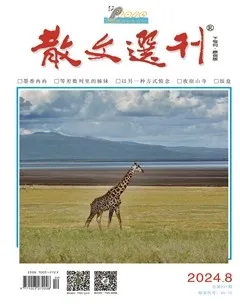芦花姑娘
2024-09-18刘国强
盛夏里,坑塘的青蛙老早地把韩家酄村叫醒了。
我拉开窗帘,推开窗子,一团薄雾飘了进来,遮住了视线。忽而薄雾又偷偷地溜出了屋子,不知飘到哪里去了。在离屋子十几米处的坑边上站着一位二十出头的姑娘。她穿着白纱裙和蓝纱无袖衬衫,身材苗条、长发披肩,显得清秀飘逸。我的推窗声显然惊动了她,她笑眯眯地向我张望。
我一时手足无措,慌张地猫下腰,躲闪到墙旮旯,拽过椅子上的衣服迅速穿好,用手指拢了把头发。
见她还在笑眯眯地往这边看,她竟然冲我婀娜地走来,站在窗前,羞红着脸跟我说话:“您是工作组的刘老师吗?”
我诧异地看着她,犹豫着问:“你是?”
她羞答答地低下头,又偷偷瞟着我说:“我是村里的小学老师,我们经常在《唐山晚报》上看到您写的散文,听校长说,您就在我们村下乡,我想看看真人儿。”
我不好意思地说:“有点儿让你失望了吧?我写得不好,是闹着玩儿的。”
“刘老师忒谦虚,您写的就是我们身边儿的事儿,特生动、特真实!”她又说,“刘老师,您今天还得上课去。哪天我请您到家里吃顿便饭行吗?我特想跟您请教。”
我赶忙说:“不用吃饭,有空儿咱们随便聊聊,请教谈不上,我还要向你们年轻人学习呢!”
她问:“您的手机号是?”
我刚报给她,手机就响了,她说:“这是我的号,我叫董芦花。”说完,她把我手机抢过去,几下就把她的名字储上了。她说:“刘老师,您就算答应啦啊?不能食言啊?”
说完,她就像河渠里的一朵水莲花,随着潺潺的流水在一团薄雾里漂走了,漂出老远,又回头望了我一眼。
芦花没有食言,一个周六的早晨,她果然打来了电话,让我中午到她家去吃饭。
我赶忙说:“哎呀!今天不巧,我已经答应董伯付了,今天在他家的鱼铺上吃去,咱们改天吧!谢谢啊!”
“不行!刘老师,您可是答应过我的,我爸早起就把大公鸡杀了,还捞了一条大鲤鱼,人家好不容易才盼到这一天嘛!”我听出她那焦急耍疯的样子。
“这……这……我还有两个队友呢。”
“您让他俩去伯付家吃呗,我想让您一个人来。”
这咋跟他们说呢?我心里嘀咕着,最后支支吾吾似乎勉强地答应了下来。
到了中午,我只好编了一个漏洞百出的理由,跟他们请假,汝龙和伯付非常不满意,对我急赤白脸。
我走在大街上有种心慌的感觉,生怕碰见熟人,还好街上无人。我按照芦花在电话那头指引的路线,穿过两趟街后,才看到她站在街的中央冲我招手。她穿了件红裙子、白色T 恤衫和一双白色厚底儿凉鞋,散发扎成了牛尾辫儿。她羞涩地红着脸微笑着把我让进院子里。
院落宽敞洁净,有三间正房和三间厢房。正房的窗前种着一溜茉莉花,青白色的花朵喷薄着芳香。我有些发怯地透过窗户往屋里望,想找到她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屋子里没人。她意会到了这些,赶忙说:“别找了,家里就我自己,我妈在我姐家伺候月子呢,我爸在鱼铺上不回来。”
她在厢房里的厨房炖着鸡,在正房的灶台里熬着鲤鱼,堂屋的地上放着一张矮脚的长方形饭桌,饭桌上已经摆好了一盘黄瓜炒鸡蛋、一盘青椒炒河虾、一盘醉蟹。
她说:“刘老师,您先上西屋坐会儿,鸡跟鱼马上就好。”
我掀门帘进了西屋,屋子很干净,墙上有她的照片,炕的被单是蓝花格子的,夏凉被叠得整齐,枕巾是枣红色的。看得出这一定是她的房间。屋子的北面有一个大衣柜和一张写字台,写字台上摆着一溜书籍,有《唐诗三百首》《萧红文集》《冰心文集》《大浴女》《十万个为什么》等。
“刘老师,开饭咧!”她掀帘子露着一双黑亮迷人的眼睛叫我。
她已经把鱼和鸡端上饭桌。饭桌上还有一瓶白酒,两个小酒盅儿。
“芦花,你也会喝酒?”
芦花腼腆地说:“刘老师,我知道您会喝酒的,您的许多文章里都有喝酒的情景,今天就让芦花陪您喝个痛快!”
“那好,倒上。”我们并肩而坐。
我见那酒竟是“山庄皇家窖藏12 年”。
我说:“这可是河北的名酒啊,据说康熙皇帝在承德平泉围猎时,就用此酒宴请过大臣们。你是怎么得到的?”
芦花笑着说:“我是托在城里住的老师捎来的,我只告诉他买瓶好酒,要那种有一定历史文化的名酒,结果他就买来了这个,您喜欢就好。”
我连忙说:“好、好,好酒,我很喜欢,只是别这么破费,下不为例啊。”
“刘老师,咱们对诗吧,我说上句,您接下句,接不上来就罚酒一杯,您看怎样?”
我说:“可以,要是接上来了呢?”
“那就都喝呗!”
“好!你说吧!”
说实话,我会的唐诗实在有限,这小女子伶牙俐齿的,我很快就败下阵来,我磕磕巴巴地对不上来,只好认罚。后来她看我一个人喝,着实没了意思,就陪我一同受罚。酒到浓处,我们都不再拘谨,她对我的称呼也不是刘老师了,改叫刘兄了。“刘兄,咱们来一樽。”说着,双手端着酒盅跟我碰一下就一饮而尽。接下来她再吟诗一首,再和她的刘兄来一樽。
我的天,她还真像结婚前的李清照!
就这么一阵厮杀,大半瓶酒下去了,我们都有点儿搁不住。我说:“不行啦、不行啦,不能再喝了。”
芦花说:“没事儿,刘兄,咱们来个一醉方休。”说着她就摇晃着身子去抓瓶子倒酒,已经醉了的她一把没抓住,把酒瓶碰倒在饭桌上,一些白酒洒在了炒菜里。我赶忙把瓶子抢过来,把她搀扶住,她身子软绵绵的,顺势就瘫在了我的怀里。这可咋好唉!我把她抱起来放在西屋的炕上。她的嘴里还一个劲儿刘兄、刘兄地喊个不停。
我站在那儿,不知所措,生怕他的父亲突然闯进来说不清楚。我稍微冷静了一下,把夏凉被拿过来给她盖上,给她脱下凉鞋,又倒了一杯热水放在椅子上,回到堂屋又把餐桌收拾了一番,洗刷了碗筷。听她有了鼾声,就悄悄地退出了屋子,把堂屋的门轻轻带上,出了院子把大门带上。我还是有点儿不放心,就这么走了?万一来串门子的,正赶上是个坏人,乘人之危怎么办?我的责任可就大了……踌躇半天,想进去看看。一推大门,锁上了。还好,有锁,我总算放心地离去。
第二天早上,她打来电话,问我喝多了没有。她说半夜醒来,发现自己没枕枕头、没脱衣服很是诧异,想了半天,才想起跟我喝酒的事。
“很抱歉,连饭都没让您吃一口,”她还说,“这次不算,等下次一定让您喝好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