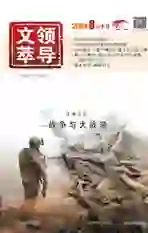进贡:乾隆君臣之间的难题
2024-08-27卜键

大臣个人向皇上进贡,乃乾隆政坛的一大弊端,它不属于朝廷制度,但在康熙朝已经存在,而随着一些封疆大吏和朝廷重臣的积极加持,在乾隆朝呈现愈演愈烈之势。此类相关论述较多,一例地予以谴责,矛头多指向乾隆帝与和珅。
王杰为乾嘉间著名的清正之臣,他筹措备办贡品之事,对千夫所指的大臣贡献风习,或也能有些新的认知。
王杰为乾隆二十六年(1761)状元,弘历在审阅进呈试卷后对排序做出调整,王杰由第三变为第一,以立身至诚和谦谨清廉,深得乾隆器重倚信。乾隆四十九年(1784)春夏间,王杰因母亲去世在家乡韩城服丧。当年三月,第六次南巡的乾隆帝驻跸镇江,传旨:“兵部尚书员缺着王杰补授,仍着在籍守制,俟服满来京供职。”服丧期间被擢升者,少之又少。兵部汉尚书显赫且关键,必须得到皇上的特别信任。王杰在韩城闻知此事,虽有欣慰,而更多的似乎是犯难。
王杰打算在乾隆帝自江浙返京时,前往山东德州的大运河畔迎驾,但总不能两手空空,首先要准备一份“面贡”。面贡,即臣子在接受召见时呈进的贡品。王杰希望能在四月之前备齐贡品,由京邸中家人携带前往德州会合。但购置贡品需要花钱,家人到德州也需要盘缠,王杰恰恰没钱,只能向朋友借。
在京借贷并非易事。不得已只能去找钱庄,为此要支付高额利息。有人说古代官场中没有纯粹的清官,否,王杰就是一个,“素风到老如寒士,公论同声说正人”,乃文史大家赵翼的诗,要知道这位同年当初可是对王杰占了自己的状元耿耿于怀。数年来,王杰先是为母亲治病,然后扶丧归里,为二老操办丧事,早已是东挪西借了,怎么还呢?他打算卖掉在京的宅院,换一个小点的房子住。
闰三月二十二日,王杰在办妥父母的合葬之后终于赶在皇驾之先抵达德州,受到皇上召见。他精心(也是竭力)准备的贡品,乾隆帝仅拣了四件价值低廉的收下,其余都退给了他。
赏收,指皇上收下臣子献呈的贡品。除了各地土仪(土贡)之外,臣工的贡品一般只有少数被赏收。弘历深知王杰的道德人品,知他一生清素,是以收下的更少。乾隆帝对王杰赶来谢恩很高兴,表示君臣之情就该如同自家人一般亲切自然。
王杰曾为筹备此次“面贡”挖空心思,不惜借贷和求人,却也只是一些挂屏、砚台、漆盒之类。而皇上知道他的拮据境况,对其贡件大多退还。此时的和珅已炙手可热,在办贡上出手阔绰,进单上动辄是“玉无量寿佛成龛”“无量寿佛七塔龛成座”。王杰赶赴行在谢恩,应会遇见总在皇上身边晃悠的和珅。
王杰在乾隆五十年(1785)九月结束丁忧,回朝任职,自此在政坛快速跃升:十二月赐紫禁城骑马;次年四月兼尚书房总师傅,十二月任军机大臣;五十二年(1787)一月钦授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所不变的是其清谨严正的个性,以及经济上的困窘。三年前的欠账不知是否还清,贵而不富,每年到了皇上的万寿节等节点,他还是要为购办贡品之事焦虑。
其实乾隆帝对此也有一些焦虑。登基继统的第二个月,弘历就传谕“禁止贡献”,看得透彻,说得明白,效果却似一般。后来,乾隆帝也曾多次颁布禁贡之旨,同时对进贡者的资格、贡品的种类和进呈的时间场合都做出限制,也无数次予以“驳回”“掷还”“概行发还,不许呈览”,仍难以禁断贡献之风。
乾隆五十三年(1788)九月,距离他的“八旬万寿”差不多还有两年,弘历就颁发明旨“禁贡”,要求不得再进呈万寿贡品。而就在五十四年(1789)夏天,各省督抚仍纷纷派员前往热河,呈进各种贺寿物件,数百里山道上车辆交错,人声鼎沸。皇上念其业已远道而来,“准其呈览,而不赏收者多于往年”。旧谚有“当官的不打送礼的”,皇帝虽说只是少量赏收,也足以让那些个真的遵旨未进者惭愧惶悔。
而王杰奉命先期前往,乃至于离家匆忙,皇上八旬万寿的贡品还没有着落,王杰为之焦急,与家中信函往复,所写多与办贡相关,真真是煞费苦心!
不是已有多道“禁贡”谕旨吗?但那主要是指各省的总督巡抚,此辈已为举办贺寿典礼扣除了部分养廉银,故皇上传谕不令再贡。至于枢阁大员与部院堂上官,上谕中虽称“王公大臣等亦无庸备进”,倒也不宜无所表示。像王杰、彭元瑞这样的文学侍从,只能选择书画插屏之类,即便如此,也是勉力筹备,不得不处处精打细算。
活到八十八岁、统治中国超过六十三年的弘历,一生丰富而驳杂,臣工进贡之风的愈演愈烈,诚为乾隆朝一大弊端,作为皇帝的他难辞其咎,却也不应忽视另一面,即所谓“联上下之情”,包括贡与赏两个方面,甚至接受颁赏的臣工远比纳贡者为多。以其聪察敏锐,弘历怎会意识不到贡献之弊?那些个禁贡之谕皆属有感而发,并非做做样子。
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山东巡抚国泰贪污案审结,因其中有逼迫属下“帮贡”等事,乾隆帝特发长谕:
各省督抚每逢年节及朕万寿呈进贡物,原以联上下之情。而伊等之升迁倚任,则全不系乎此也。从前尹继善、梁诗正、高晋诸人,或由封疆简任纶扉,或由卿贰晋参密勿,伊等并不以贡献见长。此天下所共知,亦屡以申谕矣。……
此案主犯国泰出身满洲镶白旗富察氏,父子同朝,一督一抚,皆得弘历倚信;从犯于易简系大学士于敏中之弟,由微员加恩任为山东布政使,始终帮着国泰掩饰罪行。乾隆帝虽决然将二人赐死,而不无痛惜与感伤,应也不无反思。
本来是有贡有赏,本意是联上下之情,却出了李侍尧、国泰这样的恶例,乾隆帝在处理时应是五味杂陈。而若说他“言行不一,打着禁贡之名,以行赏收之实”,失之偏颇。清臣王杰的贡品,皇上对其寒素境况的理解,那种数十年一贯的信重,应能提供一个反证。
(摘自《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