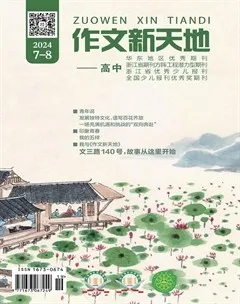方寸之间话人生
2024-08-27张艾
标签
母亲渴望把我打造成最完美的“艺术品”。
毫无悬念,琴棋书画全方位地填满了我的童年。
而这四者中,国画是我最抵触的。
国画不似油画容色昳丽,不比素描栩栩如生,不如动漫平易近人……总觉它曲高和寡,况且初学皮毛本身不足让他人以艺术之态青睐三分。我明白,精通国画是母亲打造“完美女儿”必不可少的一环。除了“为了母亲”这个理由,我找不到学习国画的意义。
随之而来的是,总调不出应有的浓淡,水渍总在不合时宜处晕染,临摹总无法复现原作的灵感……狂风暴雨在数次“中道崩殂”后倾盆而下。看墨花于雪白宣纸上方洇开,特别刺眼,我的满心愤懑点着了书画室的角落。逃避着自我原因导向虚无的真相,在母亲问起时,我将对国画的倦怠归咎于天赋缺位、能力消弭。从此,为自己打上“不会画画”的标签。
锁
同样毫无悬念,越往上读,家里“成绩优先”的音量就越大,大到压住了琴声,封住了棋局。而书法尚能定格于鞭炮声中书写新桃换旧符的任务中,国画则因工具繁多、顾虑未消,甚至没有聊以自娱的力度。
于是,儿时的书画院在心中落了锁,窗棂间没有白鸟飞过,常青的盆景不复葳蕤沃若。只是还有些东西,会从锁眼里漏出来。
在涂满算式的纸上,我总习惯地把手中的铅笔立起,不经意地来来回回涂抹,一如学画之时,一遍又一遍。在旁人瞥见时,我忙擦去痕迹,唯恐这稚拙的“伪国画”被人发现。
国画也总以各种形式溜进学业的缝隙。春晚《只此青绿》以清丽舞蹈作筏,渡我入少年王希孟的“千里江山梦”;画展唐伯虎《山路松声图》以栩栩然之意象,携我于泉石烟霞间体味山川秀美;故宫《清明上河图》以寻常百姓的生命流动,向我细陈传统喧嚣的市井百态。
但锁依然紧闭。当代人为何要学国画?除去不可否认的审美鉴赏和历史记录价值,这些鸿篇巨制都属于过去,与当今社会的个体悲喜又有何关联?
道
在名为“诗书画字”的挑战计划中,出现了让我重新审视自我与国画的契机。教授一袭麻布长袍,骨节分明、有力的手不过半分钟,便绘就《秋兰薜芷图》。很快,轮到我们自主创作。正当我与尺素相望而叹,不知从何处落笔时,诧异发现竟有同学已完成了绘画。一幅极简单的画——绘着憨态可掬的花猫——甚至不合国画所规。无从谈起浓淡枯润,更不具意象构想之精髓。
那不是完全的国画——可又是完全的国画。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我一直追求“全”,依照所谓的金科玉律——技法要全、工具要全,甚至连画画意图都要全。依照“完美女儿”目标TdzQE+DVRw7sOOzr+wAh5g==,我也要样样都全面发展,少了一个才艺,便是不符合母亲的要求的。
当无法求“全”时,我就选择了逃避。
然而,国画绘就的不正是“不全”之境吗?在色如点漆、墨分五彩的世界里,神韵胜于造型,不求谨细,但求意足。正是这不全,成就了国画最完全的魅力;正是这不全,道尽了画心。
张璪用秃笔作画甚至用手作画,仍旧画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丹青妙笔。这不全之理、这不全之道,我怎就忽视了?
我
我用温水化开冷凝的毛笔,取出了早已积灰的颜料盒。日子依旧如流水般平静流过,朱红和群青重新缀入我的生活。
我会在读姚鼎《登泰山记》时浮绘丹霞万丈,会在远眺家乡山水云影时偏爱青绿一抹。课业重压而人世熙攘。关上门,阻断一帘风雨,屏却两耳杂音。宣纸一卷,镇纸一方,永远静静在檀木桌前含笑以待。我仍无法做到复刻大师法度,可信手剪裁亦是风景,偶有败笔亦无伤大雅,纤毫阙漏实不足惜。
观纸之肌理,感墨之筋骨,透过翰墨风神,我与丹青的联结在分离后更显紧密。它不再是母亲一厢情愿的才艺要求,我也不再是等待雕琢的附属作品。
无须为一厘米的差错踟蹰,无须为细微处的不完美纠结。人生本就是绘就一幅独属于自己的、美丽而写意的丹青。
不全之全,方为丹青,方为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