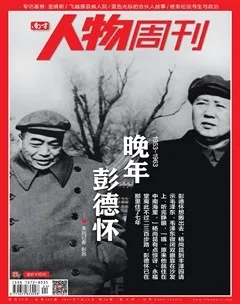包刚升:传统大国的“大”如何影响其现代转型
2024-08-23徐琳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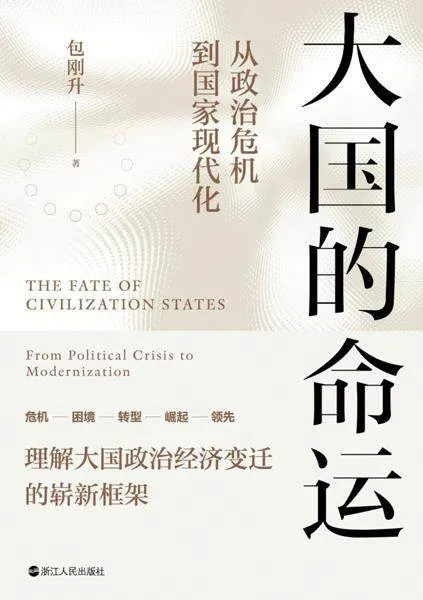




在熟悉包刚升的人看来,这位现年48岁的政治学者过着一种“严肃,紧张,活泼”的高产生活。
近两三年来,他一本接一本地出版原创性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著作:2023年推出《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儒法道:早期中国的政治想象》;2024年2月出版《演变:西方政治的新现实》,6月出炉《大国的命运:从政治危机到国家现代化》。这还不包括他为大众撰写的政治学入门讲义。
2024年2月春节假期起,他又给自己压了一项新任务:每周六晚9点整在个人微信平台上做通识课讲座,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领域的中外思想学术经典。直播后,公开课内容经合作团队精剪、配上字幕,在哔哩哔哩网站二次播出,吸引了一大拨粉丝。其中,他讲授《枪炮、病菌与钢铁》的这期,点播量达到17万,完整收看该期课程的占到近30%。
为了保卫时间,他早已尽可能地屏蔽掉与自己的学术使命相关度不高的事务,包括占去许多高校教师大量精力的会议、活动等等,以及种种“言说”的诱惑。“青年学者要善于保卫自己的时间,想一想爱因斯坦,如果他在最有产出的年份里一天到晚处理各种事务,不可能在物理学上有什么重大成就。”
投身比较政治学二十多年,包刚升有一个核心关切——现代政治文明何以可能?以及更具体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政治文明是何以成为可能的?“身处一个有着古老历史传统的、到今天为止现代化道路尚未完成的国家里,跟一个欧美大学的白人教授相比,这可能是我们做学问很大的背景不同。”
《大国的命运:从政治危机到国家现代化》倾注了他近年来的思考心血。该书以英国“工业革命”开启的公元1800年为时间轴的起点,以全球范围内六个“遭遇”西方的传统大国为研究对象,重点拆解了奥斯曼帝国、俄罗斯、伊朗、埃及、印度这五个文明古国所历经的政治社会危机和现代化转型路径,剖析这背后的共同逻辑、挑战、困境和出路。
构思始于他在2018年年底的一次20分钟的公开演讲。那时,他已经隐隐觉察到一个重要的政治学问题——放眼全球,非西方的传统大国在现代转型方面总体上不太成功,尤其是跟它们在欧亚大陆上应有的地位比起来。
“但是,如果你回到1750年,会发现这些国家多么了不起——它们当时都还是欧亚大陆的支配者。因为英国当时还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所以,这个问题就促使我去思考:在政治经济学理论里,有一个概念叫‘资源诅咒’。我想这里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大国的诅咒’——就因为你是一个大国,因为这一系列‘大国之大’的机制,最后使得你反而没有办法很好地发展。”
人:人物周刊 包:包刚升
无法想象的对手和敌人
人:自晚清以来,中国精英群体最为关切的是中国的近现代化转型。通常,一个是考察和学习邻国日本,另一个是因着过往意识形态去研究俄罗斯和东欧的社会转型。但你的视野放到全球,并以1800年英国“工业革命”作为时间轴的起点,对所有非西方传统大国遭遇西方后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历史变迁进行了比较研究。为什么会想到去做这么一个颇具雄心的研究?
包:但凡上过中学或大学的,都会上一门中国近现代史的课。我早年学这些课本,觉得中国从1840年起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和坎坷,好像中国的命运是很特殊的。
但我后来成为一个比较政治学者,去深入地研读类似俄罗斯、印度、奥斯曼土耳其这些国家的历史和政治变迁后,发现中国的问题其实并不特殊。社会科学研究或者历史学研究有两种路径,一种是把个案研究得特别清楚,这种研究往往注重某个国家的特殊性,但是社会科学有个更高的抱负,总是在想这些类似的事情背后有没有一般的逻辑。不同国家之间总有相似性和差异性。问题是,这种相似性背后有没有一般的逻辑呢?然后还可以再问,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又是如何造成的?这是我作为学者具有的一个问题意识。
人:在你提到的非西方传统大国里,既有中、印、俄等世界公认的大国,也有早已解体的奥斯曼帝国,还有像伊朗、埃及这种——在地缘政治上还很重要、但已不被视为主要国家了。到底怎样算“传统大国”?是人口多、疆域广,还是文明辐射圈大,或是今天常常谈到的“帝国”概念?
包:关于什么是“大国”,我这里有两个标准:第一,它有着很强的文明、宗教和历史传统,甚至包括帝国的历史和记忆。这些东西通常仍然会对现在有着重要影响。第二,这样一个政治体今天仍然有相当的地理疆域和人口规模。像土耳其,它有78.36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约8500万人口;伊朗的人口将近8860万,国土疆域是164.5万平方公里。在世界范围内,它们都不算小的国家,至少是区域性大国了。这方面,一个反例就是历史上的蒙古帝国,今天显然已经找不到一个对应蒙古帝国的传承者。
而当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因“工业革命”兴起后,这些传统大国无一例外都遭遇了危机,这个危机是全面的政治和社会危机。近代中国显然经历过,印度甚至还沦为英国的殖民地。那么,当它们遭遇了这些危机后,会要求自我调整和转型,努力寻求现代化,这是一个国家的基本诉求。但是,大国之“大”,会影响到它们后面寻求现代转型与现代化的一系列逻辑。
所以,我研究和关注的问题是:这些大国遭遇政治危机后,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或者实现政治再造,在这个过程中的逻辑是什么?会经历什么?其中的逻辑跟小国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大国遇到的问题更有挑战性?为什么这些国家现代转型的难度可能会更大?


人:英国率先进入“工业革命”后,德、法等欧洲国家和北美随后跟进、模仿,并随着整体实力的剧增,构筑起新的世界秩序。非西方传统大国是在“遭遇”西方列强后开始跌跌撞撞地学习。为什么这套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制度创新扩散到欧洲、北美就很容易,到这些传统大国时就很难?是因为文明之间的异质性吗?
包:在讨论类似于普鲁士这些国家,包括美国模仿英国的时候,我强调的是两个因素。第一是地理上的某种接近性。你看伦敦、巴黎和柏林之间的距离,基本上就是在北京到上海的距离范围之内,这是很重要的因素。美国离得远一点,但北美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地理距离没有产生那么大的负面影响。第二,它们之间共享着一整套的历史、传统与观念。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浙江出现一个创新,江苏人要学习,这是非常容易的。但西北或西南的省份要学习浙江的创新就不一定了。
对那些传统大国来说,存在两个最基本的问题。第一,这是它们从来没想过会出现的事,就像我曾写道:“对1800年的大清帝国来说,世界历史的行进很快就将使其首次遭遇它过去从未遇见过的对手。”大清以前也遇到过很多对手,包括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三藩之乱”、准噶尔汗国等,都是它能想象到的,但是英国这样的对手是它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所以,对帝国的君主、高级官员和士人知识分子来说,此时此刻外部世界的变化完全超出他们的想象。英国的兴起实际上创造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范式,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帮助大清理解:英国、西欧、工业革命是怎么回事,现代的经济和技术又是怎么回事,它的制度和观念是怎样的。
紧接着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些传统大国面临的挑战不是来自某个方面的,而是政治、经济和观念系统的组合。你看最早的俄罗斯的彼得一世,他想向西欧学习,但当时的俄罗斯只学了一些方面,没能完成国家的系统再造。中国、日本前后差了十几年都遭遇了西方,中国是鸦片战争,日本是“黑船来航”事件。中国的精英首先感知到的是西方的“船坚炮利”,这个是经济系统中技术层面的东西,尤其是军事技术。后来,他们发现只考虑“器物”而不改制度是不行的,所以就从“洋务运动”走到“戊戌变法”,再从“戊戌变法”转向了“辛亥革命”。中间十几年,中国都试图在政治制度上探索。又过了一些年,当时的中国精英发现,还有观念上的问题,所以又开始了“新文化运动”等。在当时的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讲得非常清楚,他说首先要改变人心,然后要改变制度,最后再去改变器物或者技术层面的东西,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
所以我们会看到,非西方传统大国的现代化会遭遇很多困难,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需要学习的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求一个传统大国马上进行全方位的学习,挑战实在太大了。
人:我们看到日本在“黑船来航”后,至少在走上军国主义前,他们学得很快也很成功。甚至,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学习的大量关于西方的资讯,是以日本为中介的。落后小国的现代化道路似乎容易得多,大国就特别难,这主要是因为大国本身的历史包袱太重了吗?
包:如果单纯从中日比较来说,它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日本其实在近代化之前也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小国,那时候它的人口规模就有3000万左右,但它不是那种自身有着古老文明传统的国家,唐朝的中华文明对他们就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日本在遭遇西方之前,它本身的一些传统就是外来的。
具体到日本,我觉得有两个变量非常重要:第一,日本不是一个君主制中央集权官僚国家,我把中国从秦到晚清称为“君主制中央集权官僚国家”。日本是一个封建主义的结构,包括存在着幕府-天皇这种二元的权威,再加上中央幕府-地方大名之间部分意义上的分权和制衡。所以,当日本遭遇西方时,有更多的因素使得它有机会做一些调整。
第二是地理因素的重要影响。日本是一个狭长的岛国,人口密集的地方基本都在沿海地带。黑船来航后,日本的紧迫感是很强的,因为它的决策中枢基本都在西方军舰的射程范围内。相比之下,大清是一个巨大的帝国,有很大的地理战略纵深。当像广东这些地方跟英国人开战时,位于北京的帝国决策中枢的感受,跟当时日本精英的紧迫感完全不同,他们会觉得还有很大的腾挪空间。
但总的来说,还是回到这样一个话题——这些非西方传统大国,你会发现它们的历史非常古老,有着很强的政治、历史、宗教等传统。在它们要寻求现代道路时,这些历史和传统可能会部分程度上提供一些资源——比方说中国的科举制使得我们有比较成型的知识阶层、过去的官僚制比较发达使得后面的国家构建可能相对更顺畅——但也可能会构成非常沉重的包袱,这个包袱会通过很复杂的机制作用到它们后面的现代化过程。
另一个方面涉及国际政治因素,大国更容易跟西方发生竞争。因为小国如果被打败了,一般就老老实实接受这个结果,但大国没法接受这个屈辱的现实,这些东西会沉积在它的历史记忆中。一旦它有机会重新崛起,也有更大概率与西方世界之间形成一种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又会影响到它后续的政治经济转型。

奥斯曼帝国留下的漫长历史阴影
人:横跨亚非欧、国运六百多年的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后崩溃瓦解,原奥斯曼军官凯末尔击退了外国的瓜分潮,建立了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推动了国家的现代化和世俗化。土耳其一度是一个发展得不错的新兴国家。但到今天,它的经济显然碰到了麻烦,执政多年的埃尔多安在大力推行跟“国父”凯末尔相反的逆世俗化道路,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土耳其的民主出现了倒退迹象。在你看来,土耳其的现代转型陷入困境了吗?
包:我们如果从比较政治的文献来看,大概20年前,也就是2004-2005年前后,关于土耳其的文献基本上对这个国家持积极、肯定的评价。那时候,土耳其被认为是整个中东、北非地区一个政治和经济上都比较成功的样板,它的经济增长不错,被认为建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民主政体,加上人口较多,所以它在中东地区影响力也非常大。
但是,后来有两件事可能使情况改变了:第一是土耳其一直寻求加入欧盟没成功,中间经历非常复杂的谈判,但欧盟一直比较犹豫,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跟土耳其的族群、宗教这些人口因素有关的。毕竟它较多的领土在亚洲地区,而且大部分人口是穆斯林。谈判陷入困境时的一个流行说法是:既然土耳其不能面向西方、成为欧盟的一部分,或者成为欧洲主要国家的一个小兄弟,那么不如索性调整自己的战略,面向东方,成为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一个大国。
这里很微妙。对一个国家来说,有着很复杂的选择,这种选择不是怎样最有利于现代化就选什么,而是与历史、现实,与情感、与民族国家利益等等很多因素纠缠在一起,甚至可能与政治领导层对影响力的某种想象有关。
另外,大概从1970年代以来,中东、北非地区基本上迎来了一大波伊斯兰的宗教复兴,包括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位于欧洲的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最大、最重要的城市,它是较为现代化、欧洲化、世俗化的一个地方。但是,土耳其更大规模的人口在它的亚洲腹地,那里要保守、传统得多,更加伊斯兰化。对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来说,如果他持有某种宗教立场,可能是符合其政治利益的。
所以,在高度伊斯兰化的国家,我们会看到一个悖论:如果推行民主,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伊斯兰主义的,而不会成为一个世俗国家,因为政治家鼓吹伊斯兰主义可能帮助自己赢得更多选票。如果要成为一个所谓的世俗国家,要尊重现代法律意义上的世俗自由与平等,那就很容易走向威权主义。“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就是在推行威权主义的同时推行世俗化,而今天的埃尔多安更多地走向伊斯兰主义,但是他有相当的选民基础。当然,由于种种原因,现在的土耳其也被国际社会认为已经出现了民主衰退。
我们从土耳其的案例可以看到:作为一个非西方传统大国,它有着古老的宗教、历史、文化传统,甚至是奥斯曼帝国的记忆,以及今天仍然有比较大的地理疆域和人口规模。这些“大国之大”的因素结合到一起,对它今天的政治演化道路产生着很重要的影响。
人:你刚才提到伊斯兰世界的普遍现象——大城市的精英拥抱现代化、世俗化和全球化,广大基层社会则更保守、更宗教化,彼此似乎很难达成共识。像这样一些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是不是会特别难?
包:所以,我称之为困境,也就是传统大国的现代转型难题。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逻辑:一是这些国家历史上跟西方国家有很多互动,但这些互动经历对它们来说不愉快。你看奥斯曼长期被俄罗斯和其他西方国家欺负,西方国家欺负埃及就更不用说了,印度则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这种负面经历会导致传统大国有种奇特和尴尬的心理:一方面,他们认为西方代表现代和进步,寻求现代化变革和转型很大程度上等于学习西方;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西方殖民、好战、虚伪甚至邪恶,是西方国家给本国带来了灾难,这容易引发敌视西方的政治立场。这两方面观点恰恰在传统大国制造了两个互相竞争或对立的派别,一派是自由-理想主义者,还有一派是民族-现实主义者,两派斗得不可开交。
在土耳其国内,主张加入欧盟的是自由-理想主义者;提出重新面向东方、成为一个伊斯兰地区大国的是民族-现实主义者。在很多传统国家,我们都会看到类似的争斗。
还有一个逻辑:所谓的大国,一旦通过改革或革命,国家的绩效和综合实力显著提升,往往要在西方建立的国际体系中寻求自我角色的独特定位。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凸显自身传统的独特性,由于传统大国往往是某一古老文明的主体性传承者,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和独特的文化资源,这样做不仅便利,而且符合国家政治阶层的需要,所以,这些国家就走上了重新定义传统之旅。
这样,它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如何一方面坚守传统、发扬传统,另一方面又能进行完整的现代化。这里充满了各种悖论,会面临社会传统和推进现代转型之间的巨大张力。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传统大国越是强调其自身传统的独特性,就越难完成充分的现代变革和转型。

印度崛起的难题:难以“丝滑”的现代化
人:说到另一个我们关心的亚洲国家——印度,这些年它的经济一直增长较快,美国也在竭力拉拢印度。但同时,莫迪政府很多做法背后的价值观、政治立场跟西方并不完全一致,包括它和美国是盟友,又与俄罗斯保持很多合作。有个事非常值得注意:2023年,美国政府公开谴责印度官员在美国本土策划暗杀锡克教分离分子的行动,在加拿大是暗杀已遂。你认为印度的崛起之路会顺利吗?它接下来是否会想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
包:印度这个案例很特殊。美国一些机构做了民调,调查其他国家的人对美国、对西方主要国家的态度,我们之前提到的几个非西方传统大国的国民多数对西方、对美国的看法是负面的,唯独印度是特例。印度对美国、对西方的总体看法是较为友好的。这里可能有几个主要原因:第一,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相对较为温和。印度的精英阶层基本上都受英国教育的影响。相比其他国家,英国对印度精英阶层的同化比较成功;第二,印度独立后,在政体维度上与西方国家也更接近,彼此不会由于制度原因而发生冲突与对抗;第三,印度在地缘政治上的压力很大,它倾向于跟其他主要大国搞好关系以获得支持。
但是,印度的演化中也有很多我称之为“大国命运共性”的东西。这些年,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崛起和复兴。如果印度不是一个传统大国,那么它大概率既没有资源、也没有必要去找寻一个古老的传统。这两年,它被西方国家批评较多的就是因为印度教的复兴,它在政治和宗教层面不够宽容,尤其对特定少数宗教群体不够宽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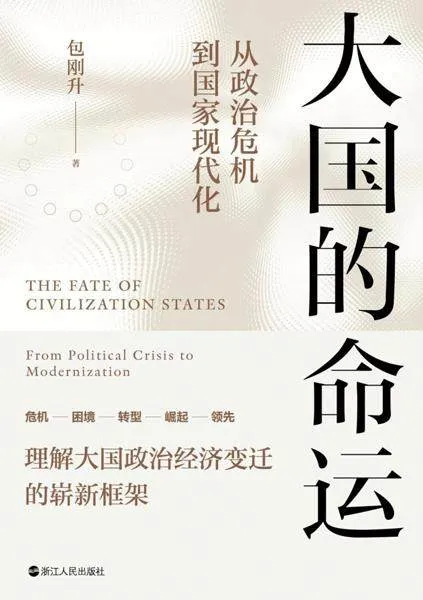
人:你觉得印度未来在现代转型中会碰到怎样的挑战?
包:印度接下来的一个主要挑战,恐怕还是它的现代化没有充分地完成,而现代化过程一般都会面临经济、政治、社会转型的方方面面的挑战。这让我们想起亨廷顿提出的一个经典议题,他说现代性是孕育稳定的,但现代化有可能会带来不稳定。那么,印度这么庞大的人口规模,原先这么落后的经济和文化基础,当它要变成一个更现代的国家时,一定会经历很多重大的挑战。
今天印度的人均GDP不到3000美元,恐怕也不是偶然的,两千多美元对应的社会、政治、经济和观念系统,其实有一个构成清单。要把人均GDP提升到5000美元甚至1万美元,社会的经济、政治和观念系统等一系列的构成清单要随之发生重大调整,去适应一个更发达的、新的、现代化的印度状态。这个过程不会那么“丝滑”地过渡,中间一定会产生各种实际问题。至于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还很难准确地预见。
人: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看,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之后,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给世界贡献了一整套“可扩展”的制度创新。你觉得这一整套的政治、经济、观念体系,在多久时长内还会被认为是要去学习、借鉴的一种模式呢?
包:我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大部分时候是比较缓慢的。拿经济来说,我们会发现:10000至14000年前的农业革命发生后,人类社会的经济演化速度其实是相当缓慢的,但是会因为某种原因发生突变,工业革命就是这样一个新的突变。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一个范式的转换。只要在一个地方首先出现这样的突变,并且这个突变取得了巨大的优势、成为一种新的主流范式,从人类已有经验来看,其他较为落后的地区就需要学习和模仿先进地区的做法。
当然,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每个国家都有特定的情境和特殊的条件,没有一个国家能完全复制先进国家的模式。比如,日本今天已经被认为与英、法、德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相当了,但我们不会觉得它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西方国家,它仍然是一个东方国家。所以,我们不必过分担心,尤其作为一个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的国家,当我们学习别人的时候,我们是不会丧失自我的。我们学习先进经验越成功、现代化程度越高,越有机会让过去的传统成为值得今天的我们感到骄傲的东西。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没法走向现代化,甚至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很落后,这个时候,它的传统、文化反而更容易被放弃、被否定,它自己也不会有信心。要我说,真正成为一个完整的现代化国家,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能够走向世界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