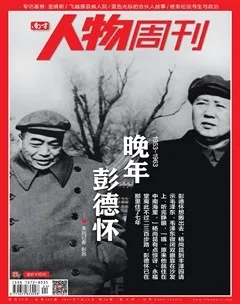AI的出现让创新成为哲学问题
2024-08-23陈洋


人:人物周刊 梁:梁建章
智能时代,人类必须掌握创新的方向盘和最终决策权
人:你的新书书名是“创新主义”,你个人对创新最大的焦虑体现在哪里?
梁:创新不能靠焦虑,对不对?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创新都是核心竞争力,但也没什么好焦虑的,就是尽量地去跟,跟上技术和产业的变化趋势。我们这样的大企业,像个小社会,创新不可能完全自上而下,而是要营造鼓励创新的氛围和机制,这样各个部门的员工才能有条件和动力去尝试微创新。环境好了,自然会有一些好东西冒出来。
人:这两年对你冲击最大的技术创新是AI么?
梁:是。不过从实际运用来看,当前大家可能对它存有过高的估计。此前,互联网搜索引擎,以及移动互联网技术出现不久,便涌现出了很多现象级应用,但这轮AI热潮至今都没有孵化出一个足以匹敌移动互联网数量级的应用。
AI对我最大的震撼还是来自哲学层面。它证实了人类大脑并不特殊,计算机神经网络完全可以模拟和取代人脑,长远看这已经是一个确定的结论,实现只是时间问题。既然AI已经对人类的自我认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类现在就必须作出选择,哪些事情可以交由AI做,哪些不能。
对人类来说,创新不仅仅是技术或经济层面的概念,也应当是智能时代人类生命意义的重要组成。如果把创新也让渡给机器来做,人的特性很可能面临被替代甚至消亡的风险。所以,人类必须掌握创新的方向盘和最终决策权。
提出正确的问题比找到具体的解决方案更重要
人:这也是你提倡教育改革的出发点之一。
梁:对。当前我们还会有一些专业技能性工作,赚钱也不少,但未来很可能都会被替代掉,人类的价值就在于能解决一些机器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人类未来只剩下创新这块自留地,就需要以创新为原点来改革整个教育体系。虽然教育要以创新为导向是个老话题,但人工智能的出现让教育不变不可。
人:你有一个七岁的女儿,AI带来的这些变化会如何影响你的教育观?
梁:虽然创新宏观上看应该由人来做,但其中某些步骤可由AI代为执行。机器可以模拟人,但它并不是人。智能时代的这种分工意味着,提出正确的问题会比找到具体的解决方案更重要。前者要求我们对人类群体自身有更深刻的理解,能掌握不同领域的知识并将其连结。这就很像创业,最关键是找到你要解决的问题,想明白这个东西为什么有用,是不是一个能解决人性需求的事情,怎么赚钱。
当下,从事创新的群体可能只占社会总体的个位数,再过一代人,可能会到10%-20%。虽然直接参与创新的依然是小部分人,但这个比例会越来越高。自动化的发展使部分工作需要的人力投入减少,更多的人力就可以用来创新,推动社会更加富裕。当然,这也对人的整体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AI对社会的塑造相较于移动互联网,有哪些不同?
梁:移动互联网能帮助二十多岁的人去颠覆五十多岁的。AI则倒过来。有了AI的协助,五十岁的人可能不再需要二十来岁的助理。所以,AI工具不仅对于较初级阶段的专业性及创新性工作有替代作用,也更加放大了更高级别的研发人员、创意人员、企业家等的能力,这对于年轻人的发展可能起到抑制作用。但长期来说,也不会一直是这个趋势。
另一个影响是,年轻人的受教育周期被拉长。直到现在,大学生实习还比较普遍,不仅能有一些收入,也能提前接受一些职业技能培训,未来这部分工作可能也被AI替代了,学生就不得不继续提升学历,扩充知识面。
现在创业环境不能算“差”,更难的是“20后”创业时
人:怎么看待人口分析角度和框架的局限性?
梁:在一些不存在规模效应或者存在规模负效应的行业,人口多的国家和人口少的国家可能差不多。人口规模也不是影响创新的唯一因素,其他因素包括文化传统、制度、政策等也非常重要。
短期波动当然会有,不过长远看,人口肯定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缺乏移民的国家。中国GDP同比增速从超10%(注:2007年为11.4%)到5%左右(注:2024年一季度为5.3%),下这么大一个台阶,跟人口结构的变化是有很大关系的。
人口结构越年轻的国家越具有创业精神。相反,当年龄结构呈现年长者多、年轻人少的倒金字塔形时,员工必须等待更长时间才能晋升到高级职位,无法在年轻时就得到成为企业家所需要的锻炼和积累。当他们最终获得晋升时,既便获得了成为企业家所必需的技能、资金以及社会影响力,那时他们已经是四五十岁的人,错过了创业的黄金窗口。这种阻挡效应会极大损害年轻人的创业活力,年轻人的机会少了,会使得整个经济缺乏活力,需求和投资低迷。
人:携程创立于1999年,那年你30岁。许多年轻人会认为比起过去,现在创业越来越难,挣钱越来越难。你能感知到这种变化么?
梁:现在也不能算“差”。当下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年轻群体的数量还相当庞大。中国相对美国的弱项就是对外开放的程度弱了些,没有太多对外的深度交流。外国人到中国来的移民网络也不太畅通。这些方面都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
相比现在,早年间确实上升空间更大,但这也是因为那时候起点低,又处于时代红利期。实际上直到前几年,这波红利都还在。目前总体人口在下降,经济增长在放缓,创业确实会越来越难。创业机遇也常常可遇不可求。移动互联网就是特别适合创业的技术,属于千年难得一遇的机会。如果把AI看作是模拟人的能力,那移动互联网就是“千里眼顺风耳”,是超人的能力。目前,完全自动驾驶还没实现,机器人端盘子也还不成,这些反而需要更长的时间。
要说真正的“难”应该是“20后”出来创业时。那时,中国的年轻人已经少了太多太多。
地缘政治风险很难预测
人:包括携程在内,很多中国企业都在积极地国际化,但阻力也前所未有,比如TikTok就面临“不卖就禁”。国内巨头要成长为世界级企业,如何跨过沟壑?
梁:出海的必要性也跟人口有关。国内市场增长放缓,但国外人口还很年轻,部分市场的需求还很旺盛,很有发展前景,所以中国企业不得不走出去。携程的策略还是一步步来。以中国为原点,慢慢往外扩,先从东南亚、东北亚开始,再到整个亚洲,最后是欧美。这样政治风险也会稍微低一些。但总体上,旅游产业国际化过程中的政治风险相对低一点。
人:有遇到过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么?
梁:目前还没有,我觉得(携程)大部分商品都还是可以(做国际化的)。美国可能是个极端。无论是旅游,还是新能源,都是互惠互利的,所以除了个别国家外,空间还是很广泛的。
人:2024年是全球“选举大年”,如何把控不确定性?
梁:目前我们还是以中国为核心在逐步推进国际化。出境游主打中国人服务中国人,我们的全球主要目的地已经覆盖了欧洲,但目前还是离中国越近,国人去得越频繁。在亚洲,中国也是个主要目的地,也在推入境游等等。其他的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很难预测,也很难控制。当然,中国如果在外交上能跟更多的国家保持好的关系,或者中立的关系,或者更好的关系,对中国企业出海肯定是有帮助的。
“人总要留下些什么”
人:你觉得与三四十岁时相比,自己变化大么?很多人会用“多面”来形容你。
梁:“面”总得一个一个地攒。我是三十多岁去念的经济学博士。念博士前,我主要是一个理工男,当然企业做得很不错。40岁以后就一直在关注人口经济问题,这也算是我的第二面。AI出来后,我开始更关心人文和哲学方面,创新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哲学问题。
人:很多企业家以做一个基业长青的百年企业为人生目标,这对你似乎并不够?
梁:对,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创新和传承,二者是一体两面。你还是要留下些东西。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学者,都是为社会留下正面的遗产,我正好两方面都希望能有。
人:未来还会有哪些“面”?
梁:可能会从经济层面向哲学层面做些跨越。国际化方面,我希望在业态上有更多的创新。过去,我们有些创新并不成功,但我会继续做一些尝试。孩子的教育也是一个创新的方向,希望对她的教育能起到一定的正面作用。其他方面就不知道了。说不定几年后又有一些新的想法。
人:作为一个经常成功的人,你如何看待失败?
梁:外界看到的都是成功的,我当然也会有一些小的失败。比如同样做五个项目,别人可能成功一个,我作为董事长,可能想法更好一点,或者执行力更强一点,能成功两三个。失败的话,有的成本会比较高,有的成本就没那么高。失败就失败了,失败就把精力放到其他地方去。我对于失败的印象通常不太深,很快就朝着下一个方向去努力了。其实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不用太想它,因为过去的事都不是创新,未来才是真正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