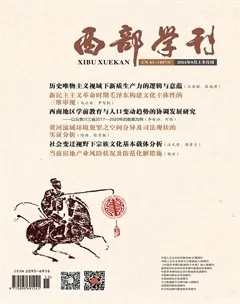从《大都会》看德里罗对后现代日常生活的书写
2024-08-21田会轻张晓婷
摘要:唐·德里罗在其小说《大都会》中,借主人公埃里克在城市街道一天的穿梭之旅,展现了美国后现代日常生活的驳杂性。这条街上的日常活动,既反映出网络资本的强大操控和转化力量,又体现了媒介和图像对日常生活的全方位主宰。但日常生活并非全是网络资本和媒介图像的被动演练场,小说里的人物以强烈的主体意识,开展了颇具反抗精神的实践活动,尽管这种反抗只是一种暂时的解脱,最终难逃被资本收编的命运。正是通过对纽约日常生活的书写,表现出德里罗对美国后现代状况的深刻反思。
关键词:《大都会》;日常生活;网络资本;媒介图像;主体反抗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4)15-0146-05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雷蒙·威廉斯生态知识生产研究”(编号:HB22WW003)的阶段性成果
The Writing of Post-Modern Everyday Life in Don DeLillo’s Metropolis
Tian Huiqing1Zhang Xiaoting2
(1.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2.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Abstract: By depicting Eric Packer’s one day trip through the city streets, Don DeLillo’s Metropolis shows the complexity of everyday life in post-modern America. The daily activities in this street not only demonstrate the manipulating and transforming power of the network capital, but also reflect the dominance of omnipresent media images in everyday life. However, daily life is not necessarily a passive field where network capital and media images perform their functions. The main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with their strong sense of subjectivity and fighting spirit, adopt different practical ways to resist, although this resistance is only a temporary and ineffective relief, and it will be absorbed by capital forces. It is through the writing of everyday New York life that the writer makes his profound reflection on the post-modern cul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Keywords: Metropolis; everyday life; network capital; media images; subjective resistance
美国作家唐·德里罗(Don DeLillo,1936年出生,代表作有《地下世界》《天秤星座》《白噪音》等)创作的《大都会》以纽约这一大都会为背景,描述了主人公埃里克·帕克(Eric Packer)在一夜无眠之后,决定从自己所在街区专程前往儿时理发店理发的故事。小说通过主人公穿行各个街区时所遭遇的各种恐怖事件展现了纽约的后现代日常生活图景,其间不乏人类的生存困境。“行走在纽约的街道,就是走在一个全球化的场景之中”[1],纽约不仅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会,不同国家的人在此进行自己的日常活动,它也是网络资本家聚敛财富的交易所,是媒介全方位施加宰制和操控的演艺场。虽然德里罗在采访中表示自己不会用“控制”这个词来形容媒介,但是他认为媒介有巨大的影响力是确凿无疑的,甚至会使人屈从于技术的发展[1]。通过书写网络资本对日常生活节奏的干扰、媒介与图像在日常生活中的泛滥,以及人们或轻微或激进的反抗姿态,德里罗呈现了他对后现代日常生活的批判性思考。
一、日常生活中的网络加速与资本操演
(一)日常生活节奏的加速
在早期社会,人类尚未与自然分离,人们往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般不会体会到当下后现代生活的紧张和急迫。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钟表得以发明,它不仅标识了科技的进步,更表征了人们对时间感知方式的变革,这突出地表现为“理性和工业技术已经打破了循环时间”[2]。因此,置身后现代社会,人们开始独立于循环时间,并受限于线性时间的管束,而这在网络资本时代表现得尤为明显。随着互联网和资本在结构上的紧密交织,网络资本开始全天候运作,“它在全球范围内疯狂地进行着积累、开采、流通、生产、运输、建设活动……速度惊人、无孔不入的数字网络和人为激发的欲望,驱使人们肆无忌惮地去争夺、掌控、觊觎、嫉妒、憎恨”[3]4。也就是说,资本的网络化以更加惊人的速度侵入日常生活领域,人们必须调整自己的日常节奏以适应网络资本的快速发展。
在《大都会》中,网络的普及加快了日常生活的节奏,而资本向来无孔不入、无远弗届,它在网络的空间中找到施展拳脚和发挥威力的舞台,这进一步刷新了人们日常生活的面貌。“资本主义制度的关键前提是信息”[4],速度就是关键,是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成功的法宝。因此,埃里克的公司雇用了各类顶尖精英来分析市场动向并给出切实可行的建议。由于信息更新速度的加快,所有的员工都时刻处于警醒状态,即便是非工作日。员工迈克尔·钦(Michael Chin)在睡梦中还在计算时间周期;财务主管简·梅尔曼(Jane Melman)即使在休息日长跑的时候仍时刻关注着日元的动态,并将最新消息汇报给埃里克;埃里克作为金融公司的老板、最终决策的执行者,也时刻处于紧绷状态,丝毫得不到休憩和放松。因为他必须密切关注货币汇率的动向,适时做出必要的应对调整,“每隔十分钟就要分析成百上千的信息。模式、频率、索引、整个信息图”[5]14。他的特殊身份、他所参与的日元购买活动以及资本和技术的合谋,都注定了他无法拥有正常的作息,无法享有正常的休闲。在加速的逻辑怪圈下,任何人都无法独善其身。埃里克的前雇工本诺·莱文(Benno Levin)因无法保持竞争力被“减速”,也即降职降薪直至最后被解雇。
不仅是金融资本公司的员工处于加速循环的逻辑下,进入埃里克眼帘的大街上的行人都行色匆匆,“仿佛他们是世界上行动最快的物种”[5]20,人们之间也不进行目光的交流,“似乎无形地存在着一种互不碰撞条约”[5]66。正如学者蓝江所言,社会的加速变动不仅将人们从熟悉的环境中连根拔起,也带来了现代人越来越陌生的疏离感[6]。人际关系的异化成为后现代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
(二)经济不平等的加剧
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现在网络已经完全被金融化了,其背后隐藏的是“少数人无休止的财富积累,是不断加剧的经济不平等”[3]8。因此,技术和资本的勾结带来的最终结果是:财富越来越聚集到极少数人的手里,穷富之间的鸿沟正在越来越大。《大都会》借埃里克的豪华轿车之行——从摩天大楼到第十大道,呈现出沿途城市景观空间分布的不均匀,这直接映射出一幅经济不平等画面,其中的落差显而易见。
埃里克居住在一个拥有48个房间的公寓里,内部的设施非常齐全,包括游泳池、纸牌室、健身房、鲨鱼缸、影视厅以及两部私人电梯,室内的装修画和音乐配置都非常考究。像埃里克这样的金融大亨不仅享有对空间的选择权,也能按照自己的喜好对空间进行改造,使得家庭空间兼具实用性、休闲性、娱乐性等多种功能。但是,当他的轿车行驶至第十大道时,这边的房屋再也不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而是一排排的旧式廉租房,“四楼的窗户都是黑黑的,外面的火灾逃生梯上也没有装饰花草”[5]159。周围环境非常差,“河面上天天漂浮着化学废品和垃圾、被丢弃的各种家庭用品,还有零星几具被棍棒打死或枪击致死的尸体”[5]158。这里的环境相比于埃里克所在的富人区而言,完全谈不上休闲与舒适,充其量就是一个免于留宿街头的住所。
在网络与资本的操演运作下,纽约不仅是拥有大型公寓和豪华轿车的投资银行家、风险投资家、软件企业家、全球卫星通信寡头等资本巨擘的日常活动地,也是资产阶级的反转形象——流浪汉的日常落脚点。在这里,“网络资本的力量足以把人们甩到路旁的沟里去,让他们呕吐和死去”[5]90。在资本投机的风险中,身价过亿的金融资本家也可能摇身一变沦为留宿街头的乞丐,正如小说结尾处,埃里克的一意孤行最终葬送了他的巨额财产,他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穷光蛋,一个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称之为资产阶级反转形象的“流浪汉”[7]。由此可见,在资本操演的场域中,贫富差距无限扩大,经济不平等严重加剧,后现代生活中资本的力量既令人向往,同时也让人充满戒惧。
二、日常生活中的媒介泛滥与图像狂欢
美国学者尼古拉斯·米尔佐夫(Nicholas Mirzoeff)曾在其著作《视觉文化导论》中有过这样的描述:“现代生活就发生在荧屏上……在这个图像的漩涡里,观看远胜于相信。这绝非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正是日常生活本身。”[8]换言之,日常生活已经成为媒介全方位运作的场域,我们进入了一个媒介泛滥和图像狂欢的时代。这样的图像时代也被德里罗精准把握,他在《大都会》中书写了媒介和图像的景象,其间交织着他对这一后现代生活镜像的隐忧。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素以严肃著称的政治、宗教、商业等领域也充斥着图像传播。人们每天必须处理海量的信息,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埃里克的白色大豪车不仅是网络资本敛财的交流工具,也是一个媒介充斥的表演场。车上的“仪表盘电子屏”“夜视仪”“红外线摄像头”“可视设备”“偷拍器”等每天都传载着大量的图像,以至于埃里克每隔两秒就得关注一下这些屏幕,消化吸收屏幕上的种种信息和数据。他这一天的汽车之旅中,有关大人物被暗杀的事件竟出现了两次,而且都被完整地报道出来。国际货币基金会总裁阿瑟·拉普(Arthur Rapp)在直播过程中遇刺身亡,媒介技术为赚取商业利益,在不断地重播中反复消费拉普的悲剧。为了制造媒体热点,提升收视率和关注度,他们将镜头对准裙子被撕开到了大腿的女记者。这样一来,令人恐慌的意外事故在媒体反反复复的演绎中变成了人们乏味生活的调剂品,人们耽于消遣这一媒体事件,忘却了其惨痛的经历和后果,难以唤起足够的担忧和警醒。这样的推演逻辑必然引发严重的后果,致使一切严肃事件都在可视化和娱乐化的感官享受中丧失了应有的人性反思和人文情怀,纽约到处弥漫着“娱乐至死”的浓厚氛围。
不仅如此,超真实的拟象混淆了现实与虚拟的差距,变得比真实更加真实,这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感知模式[9]。当英格拉姆医生(Dr. Ingram)为埃里克做超声波心电图的时候,后者通过一个歪斜的监控器看到自己心脏的图像,但“他无法确定他看到的是他的心脏在电脑中的映射,还是心脏本身的影像”[5]44。由此可见,现在的媒介严重制约着人们的思维结构与判断能力。比起现实本身,人们更愿意相信媒介信息表征的现实。不仅是大人,小孩子由于缺乏判断力与抵制力,更容易遭到媒介、图像的“洗脑”。《白噪音》中的海因利希(Heinrich)宁愿相信收音机播放的“雨要到晚上才下”[10]这一天气预报是真的,却对已经落在挡风玻璃上的雨点选择视而不见。
现如今随着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流行,人们对周围的事物充耳不闻、视若无睹,任由图像、声音、讯息等充塞了他们的时间缝隙。媒介的泛滥增加了人们处理信息的难度,使人们在信息泛滥的时代变得冷漠,缺乏应有的同情心。同时,这将不断削弱人们的判断力,影响人们的思维能力,将人们抛到与全面自由发展相背离的境地。这从德里罗的《大都会》中得到了确证,作者流露出的隐忧恰恰就是他对后现代日常生活和人类未来发展的思考。
三、日常生活中的主体意识与反抗精神
在《大都会》中,面对日常生活中网络、资本、媒介、图像、技术等异己力量对人的控制和操弄,不同主体采取了不同的实践方式来彰显自己的反抗精神,尽管这只是德赛都(Michel de Certeau)所言的惰性反抗,一种短暂性的解脱[11]。小说的主人公埃里克、他的前妻埃莉斯·希夫林(Elise Shifrin)、前雇员本诺·莱文都展现出一定的主体意识,都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抗争精神。
在又一夜无眠之后,埃里克动身前往自己儿时的理发店。尽管他的安保主管告诫说今天肯定会遇到交通堵塞,他依旧没有改变自己的主意。在前往儿时理发店的路上,他遭遇了各种各样的事端——总统出行导致的交通阻塞、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总裁被杀、街道发大水、流行歌手的葬礼等,之后才于傍晚时分抵达许久未曾光顾的那家理发店。在理发店里,没有烦躁不安的喇叭声,远离了总部持续不断的消息轰炸,“他感觉到有一种寂静正在降临”[5]158。不同于白天的喧嚣与快节奏,这里的时间似乎慢了下来。埃里克静静地听着老人讲述自己父亲的故事,尽管每次的内容都大体不差,但这就是他想从老人那儿得到的东西。正如王军指出的那样:“典型的平凡而和谐的家庭故事与帕克现在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他短暂的逗留中,稍纵即逝的温暖和宁静抵消了白天的混乱。”[12]不仅如此,老人和司机的温馨谈话也成了埃里克逃离的途径,“为他逃离夜夜失眠的困境开辟了一个通道”[5]165,良久无眠的他终于合上了眼睛。但这终究只是他面对竞争社会的一种“有限或暂时的减速形式”[13]46,在头发理到一半的时候,他又一头扎进了喧嚣和纷扰之中,这说明他的主体性和反抗性有着严格而必要的限度。
埃里克的前妻埃莉斯既是一个富有的财产继承人,也是一个无法忍受城市整日喧嚣的诗人。城市此起彼伏的噪音是因为人们都在追赶时间、提升速度,“当每个人都想求快时,会形成交通堵塞这种反而完全静止的现象”[14],即一种病态的减速形式。为了寻求短暂的清净之地,她在一家书店静静地看书。在第二次与埃里克相遇的时候,她提议一起迁居到宁静的湖边,远离城市的纷扰,就像独居在瓦尔登湖的梭罗一样,更多地亲近自然。学者欧蒂·兰塔拉(Outi Rantala)和阿努·瓦罗宁(Anu Valtonen)曾研究了芬兰拉普兰地区游客的睡眠习惯和节奏,发现不去参加日程紧凑的活动,没有这样特定的日程表,提升了人们对身体基本需求的感知度,由此她们建议人们从日常的繁忙生活中暂时解脱出来,以获得彻底的放松和休息[15]。我国学者刘天玮指出:“如果要治疗疯癫,就要增强对自然、对心灵、对自我的感受力。”[15]因此,埃莉斯回归自然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埃里克的失眠等精神症状,帮助他得到短暂的心灵疗愈,使他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需求,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精神解脱。但是,她的建议被埃里克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商业自由使人的思想永远不能接近真理,使人的本性必然陷于矛盾,使人的时间脱离四季的变化,使人的欲望屈从于利益的法则。”[16]这是福柯的判断,这一判断揭示了埃里克决然拒绝的缘由,也标识着人疏离世界和他人并不断自我异化的真实窘境。
不同于上述两种暂时性的规避,《大都会》中还描写了一群高喊着“一个幽灵在全世界游荡”的抗议分子——一群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用燃烧的轮胎筑起了路障,对一辆辆豪华轿车进行破坏,在投资银行外面扔掷炸弹,他们抗议带有一种反现代性的性质。金斯基随后的话道出了人们抗议的原因:“你(埃里克)的想法越有远见,就有越多的人跟不上。”[5]90这场大暴动尽管是非理性的,但彰显了人们在面对资本技术相互勾结和金融市场动荡起伏的深刻不安,面对被异化了的日常生活状况的强烈不满,自然地属于主体抗争的典型形式。
但是,正如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在其《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抵抗,最终都难逃昙花一现的命运,最终也必然徒劳无功[13]53。小说中以上述三个人物为代表所进行的反抗,其效果是有限的,这反映了日常生活背后社会机制的深刻矛盾性,在厚重坚硬的体制之墙面前,任何人都难免显得无助与无奈,即便是德里罗也很难找到圆满解决问题的方案。
四、结语
德里罗在《大都会》中对后现代日常生活的书写,为我们揭示了一幅全景图,其间资本与网络联手操控,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深刻裂变,越来越脱离自然的循环节奏,越来越被线性时间所奴役和驱使。这导致了生活节奏的提速、人们对自己身体需求的漠视,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疏离。媒介的全方位主宰使得纽约成了一个由许多电子屏组成的图像世界,构成了景观社会的“浮世绘”。媒介的霸蛮、图像的充斥和信息的泛滥,使人们应接不暇,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新的压迫,让人们在新的异化中接受经济不平等的现实结果。在这样的重压下,小说中的人物进行了有意识的抵抗,他们要么选择暂时远离城市的喧嚣,颇具知难而退的逃亡色彩,要么采用暴力的形式来表达不满,来抗议网络资本对市场秩序的破坏,虽然都蕴含着明显的主体意识和抗争精神,但毕竟只是暂时性的惰性反抗,很难取得根本性的改观。倘要真的拥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人们或许应该像克拉里所提倡的那样——拒绝资本的全面控制,而这无疑需要对当下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审视和加以修正。
参考文献:
[1]周敏.“我为自己写作”:唐·德里罗访谈录[J].外国文学,2016(2):141-152.
[2]LEFEBVRE H.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I[M].Trans by JOHN MOORE.London:Verso,2002:48.
[3]乔纳森·克拉里.焦土故事:全球资本主义最后的旅程[M].马小龙,译.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2.
[4]NAIMA S S,BENABED F.A Postmodern Reading of Global Capitalism in Don DeLillo’s Cosmopolis[J].Revue El-Tawassol,2021(1):456-467.
[5]DELILLO D.Cosmopolis[M].London:Picador,2011.
[6]蓝江.可能超越社会加速吗?:读哈特穆特·罗萨的《新异化的诞生》[J].中国图书评论,2018(7):9-17.
[7]LEFEBVRE H.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M].Trans by JOHN MOORE.London:Verso,1991:11.
[8]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M].倪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
[9]付林.《大都会》:被围困的城市[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1(4):51-57.
[10]DELILLO D.White Noise[M].London:Picador,2011:25.
[11]CERTEAU M D.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M].Trans by STEVEN RENDALL.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95-96.
[12]WANG Jun.Technology and the Predicament of Time in Don DeLillo’s Cosmopolis[J].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2018(8):1069-1073.
[13]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M].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14]RANTALA O,VALTONEN A.A Rhythmanalysis of Touristic Sleep in Nature[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14(4):18-30.
[15]刘天玮.电影《大都会》中的疯癫诸相[J].电影文学,2019(12):140-142.
[16]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201.
作者简介:田会轻(1970—),女,汉族,河北辛集人,河北工程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和西方文论。
张晓婷(1999—),女,汉族,山西运城人,单位为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