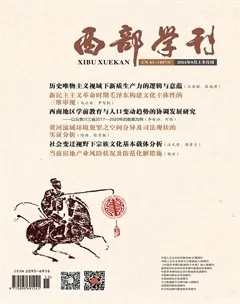《武家义理物语》中的武士形象分析
2024-08-21张拓
摘要:武士阶级出现于平安时代,在镰仓和室町幕府时代继续发展,至德川时代武士的身份从战斗者过渡到统治者,在德川幕府“士农工商”的身份制度下,“义理”作为规范武士行为的道德伦理,要求武士的行为必须符合“义理”。町人作家井原西鹤在《武家义理物语》中从“义理”的角度描述了武士的形象,如重视名誉的武士、恪守约定的武士、忠君奉公的武士等。西鹤对不同形象武士的描述,反映了町人对武士的认识以及对其伦理行为的评价,并从不同角度表现出町人的伦理观念,即通过对武士形象的描述来折射新兴町人的主情主义思想。
关键词:町人;武士;义理;名誉;主情主义
中图分类号:I3/7;K31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4)15-0142-04
An Analysis of the Images of Samurai in Samurai Family Giri Story
Zhang Tu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dong Technology College, Zhaoqing 526000)
Abstract: The samurai class appeared in the Heian period, and continued to develop during the Kamakura and Muromachi shogunate eras, the samurai’s identity transitioned from that of a combatant to that of a ruler during the Tokugawa era. Under the identity system of the Tokugawa Shogunate’s “scholars, farmers, artisans and merchants”, “giri” as the moral ethics that regulates the behavior of samurai, requires that the behavior of samurai must comply with “giri”. The chonin writer Ihara Saikaku described the images of samura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iri” in Samurai Family Giri Story, such as samurai who valued honor, samurai who abided by their promises, samurai who were loyal to the Tenno and served the public, etc. Saikaku’s description of different images of samurai reflect the chonin’s understanding of the samurai and their evaluation of their ethical behavior, and expresses the chonin’s own ethical concepts from different angles, that is,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the images of the samurai, refracting the emerging chonin’s idea of emotionalism.
Keywords: the chonin; samurai; giri; honor; emotionalism
井原西鹤(1642—1693年)是日本元禄时期的俳谐家、町人文学家,其著有《好色物》《町人物》《武家物》等文学作品。《町人物》主要讲述町人依靠勤俭持家、聪明精干发家致富的故事。《好色物》主要讲述町人终日沉溺于烟花柳巷纵情酒色的故事。《武家物》中西鹤将目光从町人转移到武士,从义理的角度描述了武家社会的伦理道德,一般认为西鹤的《武家物》文学价值小于其他两部作品,但其作品中折射出的人文主义思想仍不容忽视。
江户初期,德川幕府引用儒学(朱子学)作为官学,并根据朱子学的“名分论”,推行严格的“士农工商”身份等级制度,武士为统治阶级作为四民之首,手工商业者则被置于四民之末。自“元和偃武”(指大阪夏之阵结束的1615年至1853年黑船事件之间的日本历史,因为这段时期内日本国内再无大的战乱,而1615年天皇改元“元和”,故名“元和偃武”。编者注)后,原以战斗为职业的武士阶级就已经完成其社会使命,失去了用武之地,因此也只能发挥维持社会治安和稳定作用[1]77。武士的身份从中世时期的战斗者过渡为近世时期的统治者,与之相对的是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町人阶级“以营利为善”和以正直、简约、精算手段致富的伦理价值和精神指向,在经济活动和文化创造力上的作用日益增大,町人的奋争精神和物质力量足以左右时代的潮流,使他们成为近世文化的主力[2]。因此,至“元禄时代”出现了如井原西鹤、近松门左卫门、松尾芭蕉这样的町人文学巨匠。井原西鹤在《武家义理物语》中以町人的角度对当时的武士伦理道德进行审视,并主张武士的应有之道。本文通过分析和解读该作品中的武士形象,以期为理解日本近世武士阶级的伦理道德提供参考。
一、武士阶级的起源与发展
要阐述武士形象,有必要先了解日本武士阶层的源流及发展,一般认为武士起源于平安时代(794—1185年),到八世纪随着班田制的瓦解,代表土地私有制的庄园制开始出现,为争夺领土,各庄园主之间斗争不断,武力的强弱决定着占有土地的多少,为了保卫和扩大土地财富,庄官、有实力的名主等地方豪强,国司、郡司和遥任国主及其代理人,还有宗教团体,都组织起自己的武装力量——武士[3],自此武士集团开始出现。
随着日本各地武士集团的发展以及军事力量的增强,武士集团成为日本封建社会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最终源赖朝打败平氏建立日本史上第一个武家政权即镰仓幕府(1185—1333年),标志着武士集团正式转变为幕府官僚对地方进行治理。
镰仓幕府后期,幕府内部开始出现势力动摇局面,最终实力强大的足利尊氏推翻镰仓幕府后成立室町幕府(1338—1573年)。“应仁之乱”(1467—1477年日本室町幕府时代的封建领主间的内乱,在八代将军足利义政任期内幕府管领的细川胜元和山名持丰等守护大名之间发生争斗,其范围除九州等部分地方以外,战火遍及其他日本国土,动乱使日本进入将近一个世纪的战国时代。编者注)后,幕府的统治日益衰退,武士集团间凭借武力进行土地争夺的现象愈发激烈,此时全国范围内的武士都被卷入这场战争之中,至此武家社会的发展开始步入战国时代。
室町幕府后期的战国时代(1491—1568年),各武士集团为守护大名而互相展开斗争,最终织田信长率先展开统一日本的行动,但在统一大业即将完成时,却招致部下背叛,最终由部下丰臣秀吉继承其夙愿后统一日本。丰臣秀吉去世后,德川家康举兵战胜丰臣集团[4],最终“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康于1603年建立德川幕府,直至1867年“大政奉还”,德川家族统治日本长达200余年。
德川家康通过幕蕃制度、身份制度、闭关锁国等手段巩固统治,在一系列政策的作用下,日本社会稳定发展。德川幕府采取“太阁检地”“狩刀令”等措施,使兵农分离[5]211,武士离开农村,居住在城下町,依靠领取主君俸禄为生。“士农工商”各阶层人员各司其职,武士阶级作为统治者,被要求作为士大夫应具有与其社会地位和职责相符的伦理道德,加之受中国的宋明理学亦称“义理之学”影响缘故,“义理”成为武士道德律说教的主要内容[6]。
二、《武家义理物语》内容简介
《武家义理物语》于贞享五年(公元1668年)发行,全书共6卷26章,每章都为独立的故事,内容大多以武士为履行“义理”展开,“义理”出自古代中国,原指事物正确之道理,传入日本后,“义理”作为一种伦理道德用来规范武士行为,一般多指武士对主君的义务。西鹤在《武家义理物语》序文写道:“弓马之事,乃武家之道,得主君之俸禄应护其左右,若因一时之争而舍命,实非武士之道。”可以看出西鹤所主张的武士应有之道即是得主君俸禄应尽忠报恩,为一己之私舍命等行为并非武士的职责。西鹤在《武家义理物语》中批判了武士的杀戮好战形象,赞扬了基于仁义道德的武士形象,如将为维护名誉让儿子跳河的武士描述为可怜(卷1之5),将营救仇家、主命优先的武士描述为“武道之本”(卷6之3),将克服恐惧之心的武士描述为“勇猛之士”(卷3之5),将收养仇敌之子为义子的武士描述为“振兴家业,留名后世”(卷2之4),将信守约定的武士称之为“忠诚和诚信”(卷1之2,卷3之2)。下面,笔者将具体解读该作品中的武士形象。
三、《武家义理物语》中武士形象的解读
源了圆将《武家义理物语》中武士的义理归纳为:1.对好意和信赖报答的义理;2.为维护名誉舍身的义理;3.习俗或习惯上的义理等。因此,武士的形象也以概括为重视名誉、恪守约定、忠君奉公等。
(一)重视名誉
武士的名誉观念是武士对于自身价值受到社会和武士集团及自身的认可,承认和赞扬,即肯定评价的认识价值[5]73。西鹤在“若死同浪枕”(卷1之5)中描述了这样一则故事:神崎护送主君之子村丸出游,其子胜太郎跟随同去,同僚之子丹三郎也一同前往,然而在渡过大井川时丹三郎因神崎指导失误落入水中不知去向,神崎得知是因为自己失误所致,于是他为守护自己的名誉,让胜太郎跳河自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如果没有完成任务,那么作为武士将颜面无存,武士维护自身的名誉的行为是急迫的36e54f62f2ffcd6e37fc64c8cb7c82f1bd89b0d625344e99eb8c108e3fbf922f,有时候显得不近情理[7],因此神崎不惜以让儿子自杀为代价,来维护自己作为武士的名誉。西鹤感叹道:“世间再无比义理可悲的了”,来揭示武家社会“扼杀人情”的愚昧与荒唐。
“往日威风已不再”(卷3之3)写道,某武士抱怨因病无法出征,遭到其他三名同僚嘲讽,于是反击将三人刺死后自杀。武士为守护名誉,因口论舍命。蒙受耻辱时,任何是非善恶都不应该在考虑范围之内,只有洗刷耻辱才是武士最应该完成的任务。虽然要以生命为代价,即使舍弃生命也不能抛弃名誉,武士只有以死才能挽回自己的名誉。
西鹤除了描述武士通过赴死的方式维护名誉外,还赞扬了武士重视名誉的行为,比如在“择日再论复仇”(卷6之3)中写道:“藤五郎得知其父被尾濑所杀,随即踏上复仇之路,然而却接到主君托付的任务,又得知尾濑患病在身,藤五郎选择先完成主君托付的任务,还为尾濑送去药方,让其早日康复。”趁人之危有损武士的名誉,同时“主命优先”为主君效忠符合武士之道,最后世人皆对藤五郎大加赞赏。
名誉作为武士的重要的价值取向,既包括武士对个人行为是否符合特定身份的评价,也包括外界对自身行为的认同,因此武士的名誉取决于自我和外界两个方面。西鹤分别从内在名誉和外在名誉描述了武士的形象,如在同僚之子不幸遇难后,竟令自己儿子跳河牺牲来维护自己的名誉;武士被同僚取笑后,为挽回名誉,竟直接将同僚杀死后自尽,本该为主君奉公报恩,却因口论丢命,最终遭至世人嘲笑。西鹤评价道:“因口角拔刀相斗,在大事面前却毫无作为。”他对武士藤五郎拯救仇家之事表示赞扬,认为其“既通人情又达义理”,即对主君尽忠的同时又送药方拯救尾濑,其行为乃武道之本。
(二)恪守约定
除描写重视名誉的武士外,西鹤在“一场意想不到的婚姻”(卷3之4)中描述了遵守约定的武士的形象:生国有两名武士隼人和外记,某天外记去拜访隼人,隼人大受感动,答应外记将女儿许配给其子龟之进,但外记回家途中不幸遭暗杀,隼人未忘昔日之约,最终两家结缘家业日益繁荣昌盛。
外记不幸遇难后,隼人坚持履行约定,因为这是作为武士必须履行的义务。类似恪守约定的武士形象在“雪天的早饭约会”(卷3之2)中也有所体现,小栗从备前国前往京都拜访石川,只为遵守一饭之约,这也可以说是人与人之间情谊的纽带,同时也是西鹤在其文学作品中想表达的价值观,即代表新兴町人伦理价值取向的“主情主义”思想。
但在“武尊町卑”的社会现实下,被置于“四民之末”的西鹤只能通过抑或赞扬抑或讽刺的手法反衬其“主情主义”思想的优越性。在“黑痣为昔日娇容”(卷1之2)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武士十兵卫早年同近江城主之女红花约定,于七年后喜结良缘,然而红花却意外患病,城主让胞妹红叶同十兵卫结缘,遭到十兵卫坚决反对,并写信表明自己的决心,最终两人得到世人祝福。这是一个武士恪守约定的故事,彰显了人与人之间的“人情”。
“义理与人情”作为一个伦理命题,从根本上来讲,是町人阶级的命题而不是武士阶级的命题。因为主张以朱子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为道德标准的武士阶级,只承认“义理”的伦理价值,而完全否认町人主张的“人情”有任何道德价值[1]124,因此西鹤通过对恪守约定的武士形象的描写,看似在写武士,实则在写町人,正是通过主张人与人之间情谊与恩义来意图打破封建伦理道德对人性的压制与禁锢。西鹤的文学作品不仅描述了武士的义理,还描述了町人的义理,在《町人物》中的“义理”一般分为“偿还金银的义理”“人际交往的义理”等,大多都与诚信有关。如《日本致富宝鉴》卷三之四“高野山建冢还债”中就写到大阪富商伊豆翁在烟花柳巷寻欢后,至家业衰败,最终为偿还欠债,通过日夜营生,不仅重振家业清还借债,还用余钱在高野山兴建石塔,名为债冢,荐其冥服[8]。西鹤赞扬了町人的勤劳致富伦理和恪守诚信的价值取向,这种诚信伦理与前面提到的武士十兵卫有异曲同工之处。
(三)忠君奉公
在武士义理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尽忠奉公”,山本常朝认为武士作为奉公人,如果在面临生死选择之际,应当直接选择死,不应有丝毫犹豫。武士奉公最著名的是发生在元禄十四年(1701年)的“赤穗义士复仇”事件,赤穗藩藩主浅野长矩奉命接待贵宾,但因送礼原因浅野受到吉良义央的嘲讽,感到颜面尽失后浅野立即拔刀刺向吉良,最终浅野被将军纲吉下令剖腹。浅野死后,赤穗藩47名武士在历经一年多的计谋策划后最终杀掉吉良为浅野复仇。翌日,在将军纲吉的裁定下,赤穗藩武士被要求集体剖腹自杀。
“赤穗义士复仇”事件可以说较好地说明了武士的“忠君奉公”,作为藩国武士,效忠藩内的主君是最基本的社会责任,也是武士生存于世间最重要的使命,故而,武士生存于世间意义就在于忠君奉公[9]。赤穗藩武士合谋为主君复仇,最终又集体剖腹自杀,正体现了武士对主君的绝对忠诚。因此山本常朝说:“所谓武士道,即死而已。”因为只有看透了死亡,才能真正领悟作为武士之道。
那么《武家义理物语》中武士是如何“忠君奉公”的呢?在“松风弥留之际”(卷2之2)中西鹤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京都两女子因貌美深得将军宠爱,因此招致殿中其他女性嫉妒,一名叫松风的女子准备报复两人时,被侍从发现后处死,但其怨念一直在殿中作祟,将军命武士太平丹藏和柳田久六除妖,夜半松风显露人首蛇身之际被丹藏降服,将军得知后对其两人予以赏赐,自此大殿又恢复了往日宁静。
血气方刚的武士不惧生死消除鬼怪圆满完成主君传达的任务,最终荣获将军的赏识,因此西鹤写道:“丹藏武勇奉公,久六主命为先,乃义勇之士。”类似武士奉公的还有“表面夫妻的秘密”(卷6之2)写的是金子合战后柳井右进遭讨伐至死,其妻将女儿托付给年老武士后患病离世,后来年老武士舍命保护主君之女的事情。
可以看出,对于武士的奉公伦理,西鹤一般是以赞扬或者正面形象去描述,这也正符合《武家义理物语》的序文中提及的武士领主君俸禄就应为其效忠之事,然而在《武家义理物语》中专门描述“主从关系”的君臣伦理的故事并不多,大多都是描述武士之间的义理,也就是西鹤大多描述的是基于人际关系的义理。可以看出,西鹤主张的武家义理同山鹿素行的“士道论”一样,否认战国余风的武士好战杀戮伦理,尤其对于武士的“尽忠奉公”,为成功达到尽忠的目的,就要深思熟虑,仔细谋划,坚强忍耐,运用兵学,纵使武士自己被活捉也不能轻易放弃生命[10]。
四、结语
以上对《武家义理物语》中的武士形象作了简要分析,揭示了西鹤笔下的武士具有“重视名誉”“恪守约定”“忠君奉公”等特质,西鹤把因口舌之争而舍命的武士描写成愚昧,称赞忠勇奉公和恪守契约的武士为武道之本。虽然西鹤笔下既有杀戮好战的武士,又有通晓人之常情的武士,但可以看出西鹤的“义理”与武家社会的“义理”有本质不同,西鹤主张的“义理”带有町人的“主情主义”思想,虽然在《武家义理物语》中不同于《町人物》和《好色物》中将町人对金钱和情欲的追求赤裸裸的表现出来,《武家义理物语》中西鹤重在描写“情谊或恩义”等基于“人情”的义理,因此可以看出《武家义理物语》的创作意图在于主张町人“主情主义”伦理、人道、自然和真实的优越性,虽然作品中部分武士形象为虚构,但依然可以从中捕捉和观察到游离于现实生活中的义理人情。对以上武士形象的考察和分析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日本近世武家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也能为阐述元禄町人价值伦理及精神指向提供一定的参考。
参考文献:
[1]刘金才.町人伦理思想研究:日本近代化动因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王宣.略谈江户时代的町人文化[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1):89-91.
[3]娄贵书.日本中世纪军国主义探析:武士、武士道、武家政治与军国主义[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55-60.
[4]张如意.论日本武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J].日本问题与研究,2021(1):66-71.
[5]王炜.日本武士名誉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6]黄建华.论日本人的义理观[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65-66.
[7]王炜.简论日本武士的死与名誉[J].日本学刊,2008(2):102-115.
[8]井原西鹤.井原西鹤选集[M].钱稻孙,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87.
[9]朱坤容.向死而生:武士道生死观之述评:以《叶隐闻书》为中心[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42-46.
[10]张晓明,乔莹洁.再探日本江户时期的武士道:以山鹿素行士道论和《叶隐》武士道论为中心[J].日本问题研究,2011(1):35-41.
作者简介:张拓(1994—),男,汉族,湖北荆州人,广东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日本近世文学。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