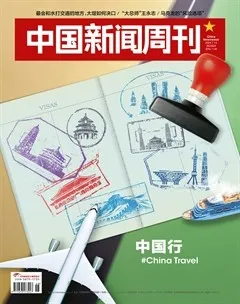朱国华:文科何为?
2024-08-08霍思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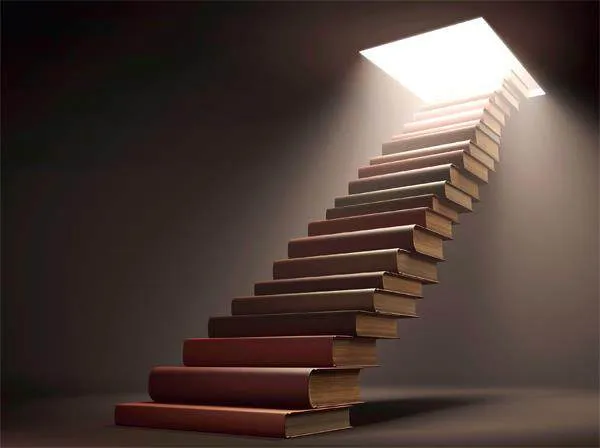
“学习文科有什么意义?我们这个学科是不是就是个笑话?网红张雪峰先生在一场直播中说,文科都是服务业,什么是服务业?总结成一个字,就是‘舔’。”
日前,一篇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2024届毕业典礼致辞在网上广为传播,演讲人为该院院长朱国华。恰逢填报大学志愿的关键时期,上述言论再次引发公众对于“文科危机”这一话题的热议。与此同时,文科生的就业形势也引人关注。
近日,智联招聘发布了《2024年大学生就业前景研判及高考志愿填报攻略》,从毕业生薪资来看,工学专业的收入依然最高,占据了前50强中的41个席位,文科处在末流。此外,连续几年的秋招“大战”中,文科生都收获惨淡。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朱国华做了题为《文科何为》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到百度原公关副总裁璩静的观点:“员工闹分手提离职,我秒批,为什么要考虑员工家庭?”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冷冰冰的资本逻辑”,但人文学科“反抗物化”。他希望,文科生可以从绩效主义的操控下解放出来,获得精神自由。
2020年担任国际汉语文化学院院长前,朱国华曾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和他交流,能感到其身上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他说,明年即将卸任院长,为了准备最后一次毕业致辞,他殚精竭虑,多次失眠。
文科真的无用吗?如何看待文科生在就业市场上的艰难?文科专业如何选择?近日,围绕这些问题,朱国华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为迷茫的文科生打打气”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院长的最后一次毕业致辞,为何选择“文科何为”这一主题?
朱国华:我自己的专业是文科,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理论本身最强调的就是反思性。当然免不了对自己所在学科反思,比如文科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近几年,我也看到过很多替文科进行辩护的言论或著述,但感觉都不够通透和清晰。因此,我选择在毕业典礼的公开演讲中,为文科存在的理由与价值辩护。现场听众虽然主要是国际汉语文化学院的2024届毕业生,但由于毕业典礼这一场合的特殊性,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我是在通过毕业致辞对整个社会说话,具有一定的社会批评性质。
人文学科的危机,其实是一个老话题。但在国内,近几年,社会对文科的轻视越来越难以掩饰。互联网的存在,又让文科生的艰难处境变得更加可见。但其中,最让我痛心的是文科人自己也开始产生怀疑,很多学生感到很迷茫,觉得文科收入低、就业难,学习到的知识不被社会认可。这是我想要站出来说话的一个重要动机,想要为这些迷茫的文科生打打气。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两三年,社会舆论确实对文科的评价总体不太积极。最典型的就是张雪峰称“文科都是服务业”。从过去谈论多年的“文科无用”到今天的“文科是服务业”,是否意味着“文科危机”的升级?当下,“文科危机”有哪些新的表现和趋势?
朱国华:我在1982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世纪80年代,我们谈到“文科无用”时,和现在的情形截然不同。当时,通常把“无用”和自由联系在一起。自由指可以自由读书,自由思考,不要考虑读书思考有没有用。1982年,全国高考人数187万人,录取人数32万人,录取率仅17%,每个大学生都是天之骄子。所以,那时虽然说“无用”,但不存在任何就业压力,大学生毕业出来是包分配的。
但在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大学生群体已非常庞大,教育部数据显示,2023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763.1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了60.2%。最近几年,年年都是“最难就业季”,文科生就业难的问题也更加凸显。
实际上,人文学科的危机,有几个不同层次:一是学科内部的危机,如文学的终结、哲学的终结……也就是说,具体的不同学科作为一种文科知识体系,它的活力在哪里?二是从文科与社会的关系来理解这一危机,例如招生、就业以及文科知识对社会的效用等。一定要看清,哪些属于理性的批评,哪些是错误的认知,甚至是情绪的发泄。这几年,我看到越来越多情绪上的宣泄。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社会对文科的评价中,哪些属于错误的认知或情绪宣泄?
朱国华:在中国,社会对文科的一个常见错误认识,是仅从就业角度理解文科的价值,这本质上是按一种经济上投入产出的逻辑来理解高等教育,仿佛大学文科培养的终极目标,就是按照职业划分,把学生培养成一个优秀的秘书、人力资源管理者、语文老师或者档案馆馆员,文科培养近乎沦为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当然极为重要,但对文科的学习而言,重要的并不仅仅是技能方面的训练,而是人文素养的熏陶,基本的人文素养决定着学生长远的潜能。

“选择专业,要充分尊重孩子的爱好”
中国新闻周刊:单纯从就业角度理解“文科价值”是狭隘的。但近几年,找工作变得越来越卷。对于文科生来讲,就业更是愈发艰难,你如何分析这一现象?
朱国华:最近,我随机调查了国内20所大学中文专业学生近五年的就业情况,这些大学既包括高水平的顶尖大学,也包括地方的师范院校和几个“双非”院校。结果发现,中文专业的就业率在全校所有专业中的排名,总体属于中等偏下,部分学校近两年下滑明显。某学校中文系的老师告诉我,该校中文的就业排名原本常年在全校前几,最近两年沦为倒数,尤其今年,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造成就业率下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有老师认为,受经济环境的影响,这几年国内的就业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文科就业的影响尤其大,以某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为例,就业情况比中文系学生更糟;另一方面,学校对学生就业规划上的关心与引导也不够充分,再加上现在大学生有时在选择上有些盲目,这些都会影响到文科生的就业结果。
还有老师分析,文科生中很多选择考编考公,这几年“上岸”难度加大,一次考不上,不少学生选择“二战”。此外,这几年出国深造的文科学生减少。这两个因素也会把文科生的就业数据往下拉。与就业率形成对照的是,在我调查的大学中,多数学校中文专业的招生分数在全校位居前列,甚至是第一。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我认为,今天的社会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关系组织起来的一个共同体,而在一个服从经济逻辑的社会系统中,很难与文科产生密切的关系。
中国多数大学校长是理工科出身,大量的民间研究经费,主要用于资助技术,支持人文社科研究的相对较少。相较文科,理工科的变现能力更快。在经济不好的时期,文科危机会更加明显,从全球看,情况都是类似的。有西方学者调查了美国人文学学生注册人数在大学生中占比的变化,发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降至20世纪以来的最低点——6%。
中国新闻周刊:在这样一个经济逻辑中,文科的出路是什么?
朱国华:英国201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球超过一半的领导人拥有人文社科领域的学士学位。这表明,社会精英群体中,很大比例的领导者接受过人文学科的训练。因为文科培养的是人的批判性思维、审美能力、良好的沟通技能、对社会形成整体认知的把握,以及人文主义的关怀,这些人文素养有利于人们更好地从事领导工作。
如果文科生能把这些人文素养与能力,充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未来一定有很好的出路。我的建议是,不要只看到眼前的就业情况,可以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点。
中国新闻周刊:现实是,很多文科生在学习过程中,既没有形成很好的批判性思维与审美能力,也无法学到适合快速就业的具体技能。对此,你如何看?这是否说明,在一些学校,文科的培养出了问题?
朱国华:在文科生应具有的多项优势中,批判性思维是最重要的,其形成取决于两个核心因素,首先是大学的环境与老师的引导,如果在一个不支持自我探索的学习环境中,上课的内容也是老一套,很难对学生思维产生很好的激发作用。
与此同时,学生自身的主体性也很关键。到了大学,不能再像高中一样上完课、考完试就结束了,从高中到大学,需要经历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在课下,学生要去主动思考老师提出的问题,大量阅读书籍与文献。在论文写作中,要带着问题意识去寻找论文材料,面对同一个问题,要去审视不同专家有哪些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各自的优点和不足是什么。这就是批判性思维训练的过程,也是构建对复杂问题思考力的重要过程。反过来,如果学生连论文都不认真完成,或人云亦云,自然无法形成这种思维。
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的高考志愿填报即将结束,很多考生和家长仍在纠结文科专业如何选。很多升学规划师将选择逻辑简化为“未来是否考公”,“考公就报法学、财会、汉语言、思政”。对此,你有何建议?文科专业的选择要参考哪些因素?
朱国华:志愿填报前,家长应先问孩子两个问题——喜欢什么?觉得自己有能力做什么?这是专业选择时要考虑的两个核心因素,相较而言,喜欢更重要。但如果孩子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能做什么,家长可以参考一下孩子的性格或性情,看其更适合哪些职业。
有一种说法是“穷读理工富读文史”,我不认同。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小时候家境贫寒,但我选择了喜欢的文科,现在也有了不错的成果,如果当时让我去学理工,可能就会学得很痛苦。因此,对于理科、文科都不错的学生,如果特别喜欢文科,我也建议家长不要逼孩子去学理。关于专业选择,我的建议只有一条,充分尊重孩子的爱好。
“对绩效主义的裹挟,勇敢说不”
中国新闻周刊:现代大学理念的奠基人洪堡认为,大学教育主要是为了培养完善的人性,哲学才是首要学科,负责引领其他知识,包括自然科学。但进入20世纪后期,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化愈加明显,西方各国逐渐出现文科边缘化的趋势。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转向?
朱国华:从文艺复兴到近世以来,大学的灵魂一直是人文学科。近代大学在诞生之初,就是为了培养所谓“自由而无用的灵魂”。
但从20世纪中后期起,全球文理学科的地位迅速发生了逆转,原因可能是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过去十年中崛起的领域,几乎全部是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人文学科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最近十几年,美国的文理学院和研究型大学中,文科的衰落尤其严重。美国《大西洋月刊》201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到,2008年以来,文理学院的人文专业学生人数已从三分之一下降到四分之一以下,研究型大学的文科学生数也下降了30%左右,而这两类大学是美国人文学科的主要阵地。人文学科的危机首先表现为招生人数的萎缩,以及人文学科领域的教职岗位和科研经费的削减。
中国新闻周刊:与西方相比,在中国,文科逐渐边缘化的过程,除了同样受到现代化大潮的影响外,有何特殊之处?
朱国华:文科在中国的边缘化有很复杂的原因,其中最核心的一点,是文科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没有得到充分尊重。国内一种很普遍的错误观点认为,文科专业多数没有门槛,有些人读了几本关于《红楼梦》的书,就觉得自己对红学的理解不会比专家逊色。
与理工科相比,文科知识形态自有其特殊性。文科的知识对象是人与社会。社会是区别于自然的非常复杂的现象。社会内部本身就是互相冲突的。而人类是时间性的动物,与人类相关的一切都处于持续变化中。我们人类对同一个现象,可能存在爱恨交加的难以简单解释的情况。文科就是在这些不确定性中,去寻找某种确定性,难度其实是非常大的,门槛也很高。
中国新闻周刊:文科在中国的边缘化,是否也与近年来日益显性的高等教育市场化趋势有关?
朱国华:的确如此。高等教育市场化,与社会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文学科,就成了屠龙之技。现在,大学越来越具有商业化特征,办大学就像办企业,终端产品是学生,首先考虑的不再是如何将他们形塑出更好的人格,而是如何打造出更适应时代的劳动力,这与人文学科倡导的学术自主性原则格格不入。
因此,高等教育市场化,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由大众来决定大学的价值,大学不再将知识本身的深度或内在意义作为评判标准,人文学科为了证明自己的“效用”,也放弃了自己的“无用之用”。目前来看,这也是一个必然趋势。
中国新闻周刊:人文学科有没有办法一定程度上扭转这一趋势,或找到一条“中间道路”:既与社会保持距离,又与时俱进、不与时代脱节?站在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应如何把握?
朱国华:人文学科要想真正有所发展,必须在对真理追求的驱动下保持学术的自主性。人文学科鼓励批判性思维,可以说,人文学科是社会的他者,在一定程度上预设了自己与社会世界的距离。但沿着这条路走到一定阶段,人文学科和社会间就会存在一个巨大的“脱序”,也就是偏离社会太远。当然,人文学科也预设了自我批判的要求,它实际上会对自己的激进化姿势在不同历史语境下进行主动或被动的自我调适。
大学也面临同样的困境。一方面,大学不应该与社会贴得太紧,如果社会上流行什么,高校就一窝蜂地去扎堆培养,反而会被社会所厌弃,就像20世纪90年代中国曾经大火的文秘专业,后来很多学校就办不下去;另一方面,高校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也要满足社会期待,为社会提供多样的知识选择。因此,大学应以一种与社会保持距离的方式,与社会发生互动。
举一个例子,过去,西方古典学中两门重要语言课是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在很多国外的大学都有开设。但21世纪以来,它们的重要性急剧下降,因为这两门语言已经成了死语言,和现代社会关系很远,所以大学自主调整了自身的学科结构。这种互动是在历史进程中自然而然发生的。当然我们这里谈论的是一种理论上如此的情况,实际上,高等教育的过程非常复杂,会有很多外部干扰因素。
中国新闻周刊:回归现实,面对文科发展的种种挑战,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文科应如何重新确立自身定位,找回自己的“无用之用”?与理工科相比,文科在当代的意义是什么?
朱国华:我为什么做这个演讲?文科何为,是个大问题,三千余字的篇幅当然远远不足以回应这个问题。我只是为世界范围内被攻击得遍体鳞伤的文科做一点辩护——当这个世界遭到“物化”威胁的时候,当我们被绩效主义的逻辑裹挟的时候,还可以有勇气说“不”。
实际上,我的批评并不是在否认当代社会中的经济法则,而是反对以投入产出为核心的资本逻辑成为一个霸权逻辑,侵占了社会的所有领域,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物化”。现在的物质水平比我年轻时好多了,却有更多人患上了焦虑症,这就与人文学科的缺席有关。
而在人工智能时代,AI技术越是发达,社会对人文学科的渴求就越强烈,因为在一个技术革命所带来的高度物质发达的社会中,“物化”已成为一种严重的病症,人与人间的关系更加冷漠疏离,人文学科必须要回应社会提出的最新挑战。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文科才显现出它自身的意义。
理工科关注的是事实和效用,人文学科关注的是价值:何谓良好生活?什么是正义的社会?如何认识感情的复杂性?用康德的话来说,人文学科试图接近的本质问题只有一个:人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持续回答,让我们得以从习焉不察的生活中抽身而出,换个视角重新打量社会、历史、经验和自我。
理想中的文科,是照耀娑婆世界的灯塔,但现实中的文科,只是一个花瓶。今天,中国在不少科技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是人文学科与西方相比,整体水平还存在着不小落差。在我看来,当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的时候,这对我们来说,也许才意味着中国人文学科最大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