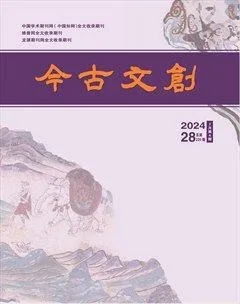明清广府地区鲥鱼历史文化考述
2024-07-31王思昊


【摘要】鲥鱼,在广府地区又有“三黎”或“三来”等称谓。其作为一种江海洄游性鱼类,在过去是一种极具经济价值的水产。明清时期,鲥鱼在广府地区资源丰富、分布较广,古人对其的认识与利用十分成熟。然而,我国的鲥鱼如今几乎绝迹,故本文通过系统地梳理相关的历史文献,具体呈现明清时期广府地区对鲥鱼的认识与利用,并试图以古鉴今,对我国当前的生态环境保护有所启示。
【关键词】明清;广府地区;鲥鱼;历史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8-0132-05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8.041
鲥鱼,鲱型目鲱科江海洄游性鱼类,在广府地区俗称三黎、三鯬、三来、三鯠等,体长且侧扁,背部呈暗绿色,两侧及腹部为银白色,体被大而薄的圆鳞。鲥鱼已于1988年被我国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Ⅰ级野生保护。在我国,鲥鱼曾分布较广,生殖期溯河入长江、钱塘江及珠江等。作为一种珍贵的经济鱼类,鲥鱼在动物学、生态学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我国古代虽很早对鲥鱼就有记载,但真正科学意义上对鲥鱼资源的研究则是在20世纪30—40年代以后。然而,从历史学角度对珠江鲥鱼进行研究至今暂付阙如,虽偶有研究也多提及长江鲥鱼的记载、认识与利用,但未见有专门、系统研究珠江鲥鱼历史的论著。因而,本文在利用广东方志与其他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历史时期鲥鱼的名称及广府先民对鲥鱼的认识进行梳理,并按时间顺序归纳明清时期鲥鱼在广府地区的分布情况。此外,结合鲥鱼与渔业生产、广府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大致勾勒明清时期鲥鱼与广府地区之间的文化意蕴。
一、历史悠久:鲥鱼古今名称考
(一)鲥鱼的命名
鲥,古称“鯦”或“当魱”,其称始见于《尔雅》。《尔雅·释鱼》曰:“鯦,当魱。”晋代郭璞注:“海鱼也。似鳊而大鳞,肥美多鲠,今江东呼其最大长三尺者为当魱。”[1]以“海鱼”言之,可晋人很早就认识到鲥鱼具有海栖的习性。而“鯦”则是因其多骨而得名,宋代陆佃的《尔雅新义》有云:“以忠鲠得咎,非其为之,不能济矣。”[2]由此观之,古人很早即开始捕捞并利用鲥鱼,从而观察到其“多鲠”的特点。
在宋代以后,“时”或“鲥”已普遍成为该鱼类的名称。宋代戴侗的《六书故·动物四》曰:“以其出有时,又谓之时鱼。”[3]这说明宋人们已经对鲥鱼洄游的时间规律有所了解。又如宋代司马光的《类篇》有云:“其鱼出有时,故名鲥。”[4]鲥鱼平时海栖,但在生殖期间则须得溯河产卵,因其来去准时,故又有“时”或是“鲥”之称谓。
此外,鲥鱼在各地区有着不同的称谓。蜀人将鲥鱼视之为“瘟鱼”,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曰:“惟蜀人呼为瘟鱼,畏而不食。”[5]宁波府地区的人们则将鲥鱼称之为“箭鱼”,雍正《宁波府志》有云:“箭鱼即江湖鲥鱼,海出者最大,甘肥异常,腹下细骨如箭镞,俗名箭鱼,味甘在皮鳞之交。”不同地方的称谓亦是基于鲥鱼在形态结构或生活习性中某一特点的观察。具体到广府地区,多称鲥鱼为“三黎”或“三鯬”。这亦与鲥鱼洄游的时间规律性有所关联,清代吴震方的《岭南杂记》曰:“鲥鱼绝无味,土人名三黎鱼,土音‘来’。”[6]
(二)广府地区对鲥鱼的认识
从史料记载得知,广府地区的人们对于鲥鱼的认识应当是走在前列的。元大德《南海志》中的物产部分,已有关于“三鯬鱼”的描述。大德《南海志》曰:“三鯬鱼,一名鲥鱼,甘腴可爱,肉中多生横刺。楚渊材曰:‘吾平生有五恨,第一恨鲥鱼多骨是也。’”[7]可见元代广府地区的沿海,鲥鱼的食用较为普遍,而这也间接促进人们对鲥鱼的认识不断提升。
明代,广府地区的人们对鲥鱼的形态结构、洄游习性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始撰于明万历年间的《种鱼经》,是我国古代一部有关鱼类养殖方面的著作。其中关于鲥鱼的体色、体征与洄游的时间规律都有详细的描述,黄省曾的《种鱼经》有云:“盛于四月,鳞白如银,其味甘腴,多骨而速腐。广州谓之三鯬之鱼。”[8]这些认识大概来源于古代渔民的生产实践。
清代广府地区的方志多有记载鲥鱼,基本上与明代的认识水平保持一致。此外,明清广府地区的人们对鲥鱼的认识,普遍采用化生说的理论来解释鲥鱼与鰽白的关系。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曰:“相传鲥乃鰽白所变。在海为鰽白。在江为鲥。”[9]清代李调元的《然犀志》有云:“《琼府志》云,相传鲥鱼是鰽白鱼所变,在海为鰽白,在江为鲥鱼。”[10]笔者推测,鰽白,是另一种鱼类——鳓鱼。鳓鱼,又称曹白鱼,它与鲥鱼同为鲱形目鲱科,均有近海洄游的生活习性。因而,“在海为鰽白。在江为鲥”的关系,很可能是古人常将鲥鱼与鳓鱼混淆而产生的错误认识。尽管其用化生说来解释鲥鱼的一些生物现象,与近代科学意义上的认识存在一定差距,但反映的是我国古人对自然之道的一种独特探索方式。
二、天时地利:鲥鱼在广府分布
(一)明代广府地区鲥鱼的分布
明代始设广州府,以元代广州路为基本范围,下辖番禺县、南海县、顺德县、东莞县、新安县、三水县、增城县、龙门县、清远县、香山县、新会县、新宁县、从化县及连州所领阳山县、连山县2县,其涵盖了现今珠江三角洲的大部分地区。
表1明代广府地区鲥鱼的分布
地区 相关记载 资料来源
南海 鳞品:有鲥 崇祯《南海县志》(卷六)
顺德 鳞:有时 万历《顺德县志》(卷一)
东莞 水族:三鯬
水族:有三鯬 天顺《东莞县志》(卷一)
嘉靖《东莞县志》(卷一)
香山 鳞属:三黎 嘉靖《香山县志》(卷二)
新会 鳞:鲥 万历《新会县志》(卷二)
本文基于《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的记载,将其分布地区整理成以上表格。虽留存下来的明代广府地区方志较少,但仍然能够根据有限的史料窥知一二。嘉靖《广东通志初稿》曰:“鲥,一名三黎,产于夏月,肇庆极多。”[11]在珠江流域,鲥鱼常于农历三月洄游,至西江段的肇庆府极多。另据广东方志记载可知,在广州府的近海城市皆有鲥鱼踪影,如南海县、顺德县、香山县、新会县及东莞县。
(二)清代广府地区鲥鱼的分布
到了清代,连州及所属2县从广州府分出。所以,清代广州府,加之新设的花县,共下辖南海县、番禺县、顺德县、花县、东莞县、从化县、龙门县、新宁县、增城县、香山县、新会县、三水县、清远县、新安县14县,其行政区域整体上与明代广州府的地理范围相差不大。
表2清代广府地区鲥鱼的分布
地区 相关记录 资料来源
番禺 鱼之属:鲥
鳞介:鲥鱼
鳞品:鲥 康熙《番禺县志》(卷一五)
乾隆《番禺县志》(卷一七)
同治《番禺县志》(卷七)
顺德 鳞:有时
鳞:有时
鳞:鲥鱼 康熙十三年《顺德县志》(卷一)
康熙二十六年《顺德县志》(卷一)
咸丰《顺德县志》(卷一)
南海 鳞品:有鲥
鳞品:有鲥
鳞:鲥 康熙《南海县志》(卷七)
乾隆《南海县志》(卷一二)
道光《南海县志》(卷八)
东莞 鳞属:有三黎
鳞属:有三黎
物产:鲥鱼 康熙《东莞县志》(卷四)
雍正《东莞县志》(卷四)
嘉庆《东莞县志》(卷四十)
新宁 鳞品:鲥鱼
鳞品:鲥鱼 道光《新宁县志》(卷四)
光绪《新宁县志》(卷八)
香山 鳞属:三黎
鳞属:鲥鱼
鱼:鯦
鱼:鯦 康熙《香山县志》(卷三)
乾隆《香山县志》(卷三)
道光《香山县志》(卷二)
光绪《香山县志》(卷五)
新会 鳞:鲥
鳞之属:鲥
物产:鲥鱼 康熙《新会县志》(卷五)
乾隆《新会县志》(卷六)
道光《新会县志》(卷二)
三水 鳞之属:为鲥 嘉庆《三水县志》(卷一)
清远 鳞之属:鲥
鳞之属:鲥
鳞之属:鲥 康熙元年《清远县志》(卷五)
乾隆《清远县志》(卷一二)
康熙二十六年《清远县志》(卷一二)
清代广州府的鲥鱼分布情况基本上可从广东方志的记载得知,广州府各县县志大多皆有鲥鱼的描述。康熙《广东通志》记载广州府,“有鲥”。以县为单位统计,得出广州府有番禺县、顺德县、南海县、东莞县、新宁县、香山县、新会县、三水县、清远县总共9县皆可见到鲥鱼身影。此外,清代广州府的区域内还出现了几个优质鲥鱼的出产地。如,乾隆《广州府志》有载:“鱼出顺德之甘竹滩者美”[12];道光《南海县志》有载:“南海九江、堡江中,有海目山所产鲥鱼,亦美”[13];嘉庆《东莞县志》有载:“出石龙及凤涌者佳”[14];道光《新会县志》载:“产三江村外,四时皆有得。苦瓜调之,更佳其味,不亚于顺德甘竹滩所产云”[15]。由此观之,清代顺德县的甘竹滩、南海县的海目山下江段,东莞县的石龙、凤涌及新会县的三江村附近一带所产鲥鱼的品质均闻名遐迩于一时。
(三)西江流域鲥鱼集中的原因
明清两代进入珠江的鲥鱼大多溯西江而上,像顺德县的甘竹滩、南海县的海目山皆是位于西江段。缘何大部分优质的鲥鱼出产于珠江流域的西江段呢?自然环境是影响西江流域鲥鱼集中极其重要的因素。
林书颜的《广东鲥鱼及其渔业志》载:“鲥鱼喜逆游广阔而急流之河面,水以清而冷为佳。”[16]西江作为珠江水系的主流,梧州到西贤滘河宽约700—2000米,且在肇庆境内形成的“小三峡”收束河床。长江水产资源协作组在1977年所编写的《长江鲥鱼调查研究》中提及鲥鱼产卵场的形成环境,多为“河床穿过两岸丘陵地带时有宽有窄,宽阔处在1000公尺以上,狭窄处仅有几百公尺”[17]。而西江两岸的地形正好与鲥鱼所喜欢的环境相吻合,故洄游至此的鲥鱼数量极大,这里成为古人捕获鲥鱼的一大良佳渔场。
另有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记载:“凡鱼皆藏于渊潭。鱼花从渊潭出易养。西江多渊潭,而其源从滇、黔、交趾而来甚远,故鱼花多而肥,池塘中可以多养。”[9]文中“渊潭”,即水下深坑。《长江鲥鱼调查研究》中亦提及鲥鱼产卵场的形成环境,需“江中浅滩络续不断,在浅滩之间往往有深潭相间”[17]。由此观之,西江“渊潭”较多对鲥鱼集中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此外,西江水经海目山分为两路,一为甘竹滩河,一为马宁河。甘竹滩入口处,河道狭窄,水流湍急,礁石极多。所以,西江流域的整体地貌,尤其是局部的甘竹滩极符合鲥鱼产卵的环境。渊潭为幼鲥生长提供庇护,而礁石则为洄游至此的鲥鱼提供短暂休息的地方,故而这可能是清代广府地区方志重点提到甘竹滩所产鲥鱼品质极佳的原因。
三、耕海古式:鲥鱼捕捞的渔法渔具
(一)广府地区捕捞鲥鱼的方法
广府地区的渔民们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捕鱼技艺。由于鲥鱼在产卵期即溯河入珠江,在内河形成了极其密集的群体数量。故广州府地区每年所捕获的鲥鱼中,以内河的鲥鱼占主要部分。而鲥鱼大致每年的农历三月开始到珠江生殖,因而,广府地区的渔民皆有于每年农历四至六月期间捕捞珠江鲥鱼的习惯。
此外,鲥鱼有夜间浮游于上层水面的特性,尤其是一天黎明与黄昏的时候。渔民谓之“朝红晚旺”,这两个时段是捕捞鲥鱼的最好时机。为此,广府地区的人们主要采用网捕法。同治《番禺县志》载:“《新语》俗呼三来鱼。出以仲夏,其性喜浮。网入水数寸即得。”[18]文中描述了番禺县捕捞鲥鱼的方法,因其生物特性使之极易为渔民所获。
(二)广府地区捕捞鲥鱼的渔具
广府地区捕鲥的渔具则主要是“罨”与“大网”。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载:“顺德甘竹滩,鲥鱼最美。其滩上鲥鱼,以罨取之。滩下鲥鱼,以大网取之。罨小,一罨仅得鲥鱼一尾。以滩小不能容大网也。”[9]可见古人主要依照地形选择渔网捕鲥。“罨”即小网,由于受地形限制,渔民只能利用小网捕鲥,然这种小网捕捞的效率不是很高。
鲥鱼十分爱惜身上鳞片,一旦为渔网所捕获便不再挣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其肪亦在鳞甲中,自甚惜之”[5]。鲥鱼的鳞片是否完整,影响着鲥鱼的口感与价格,故古人亦十分珍惜之。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又载:“渔民以丝网沉水数寸取之,一丝挂鳞,即不复动。”随着渔业的发展,古人也在不断改良渔具。李调元的《南越笔记》亦记载:“取鲥鱼以泼生钓,以轻丝为之,往来游,则不损其鳞。”[19]由于丝的材质较为丝滑,渔民使用丝制的渔网,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鲥鱼鱼鳞的损伤。虽然明清时期广府地区亦有部分渔民使用钓钩捕鲥,但钩捕终归数量有限,始终是丝网为明清时期广府地区捕鲥之最佳的选择。
四、七寸鳞鲜:鲥鱼的利用与广府文化
(一)药用价值
鲥鱼作为广府地区一种极具特色的水产,人们亦在实践中不断发掘鲥鱼的使用价值。其中,明清时期关于鲥鱼的药用价值有着不少的记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载其肉:“甘,平,无毒,主治补虚劳”[5],另可“蒸下油,以瓶盛埋土中,取涂烫火伤”[5]。于药方的描述中,鲥鱼的鱼肉、鱼油均可入药。一为内服,一为外敷,对人体产生不同的功效。当然,鲥鱼也不可过量食用,否则容易导致“稍发疳痼”的情况出现。
鲥鱼除其肉及鱼油有药用价值外,它的鳞片也有着重要的医药用途。清代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记载鲥鱼鳞可以治疗多种外伤,如治疗烫伤“《逢原》云:‘用鲥鱼鳞用香油熬,涂之’”[20];治疗腿疮“茅焦之云:‘鲥鱼鳞贴腿疮疼痛,立效’”[20];治疗疔疮“陈氏传方:‘疔疮用鲥鱼鳞贴上,则咬紧,先须与酒饭吃饱,然后将鱼鳞边略略揭起些须,用力急揭去,疔根便带出也’”[20];治疗下疳“《救生苦海》:‘鲥鱼鳞焙干煅研,白色名白龙丹,敷之卽愈,得此可包医’”[20];治疗血痔挑破不止“蔡云白言:‘人生血痣挑破血出不止者用鲥鱼鳞,贴之卽痂而愈’”[20]。总而言之,它的鳞片具有敛疮、拔疔的功效,古人取之适量外敷于烫伤及疔疮之处。
(二)食用价值
鲥鱼的鲜美,很早就为人们所熟知。大约自宋代始,鲥鱼逐渐成江东区域的鱼中上品。宋代梅尧臣《时鱼》为此有诗云:“四月时鱼逴浪花,渔舟出没浪为家。甘肥不入罟师口,一把铜钱趁桨牙。”[21]明清两代,长江流域的鲥鱼的名气更是盛极一时。明代于慎行《赐鲜鲥鱼》对此亦有诗云:“六月鲥鱼带雪寒,三千里路到长安。”在一段时间内,江苏一带的鲥鱼甚至是长期作为皇家的贡品,故鲥鱼的珍贵在明清时期可见一斑。
在珠江三角洲,流传着“春鳊秋鲤夏三黎”的俗语。入夏即洄游产卵的鲥鱼,正是其脂厚味美的时候。明代彭大翼的《山堂肆考》中有“鲥鱼味美在皮鳞之交,故食不去鳞”句。古人认为鲥鱼的美味正是位于皮鳞之交的脂肪。番禺及南海等地的人们,会将保留鳞片的鲥鱼进行蒸食。这样即尽可能保留鲥鱼的脂肪,使鲥鱼吃起来的味道更加鲜美。另据屈大均《买鱼词》记载:“两日羚羊峡上居,鲥鱼下酒不曾虚。”[22]由此观之,鲥鱼在广府地区是古人十分热衷的一道下酒菜。
广府地区对鱼类的食用,还有着比较强的季节性。正如《道光新会县志》载:“产三江村外,四时皆有得。苦瓜调之,更佳其味,不亚于顺德甘竹滩所产云。”[15]在夏季炎热的岭南,广府地区的人们通常选择将鲥鱼与苦瓜一同进行焖煮。苦瓜作为夏令的时蔬,味甘苦而性凉。其不仅很好地吸收鲥鱼的鲜味,还能祛除鲥鱼身上所带的泥腥味。当苦瓜的清甘与鲥鱼的肥美完美地结合起来,它也由此成为当地一道夏令时节的特色佳肴。
鱼脍,则是今人所食之生鱼片,这亦是广府地区食鱼的一种常见方法。在制作生鱼片所用的鱼类中,以鲥鱼与嘉鱼为最上品。清代李调元的《南越笔记》记载:“粤俗嗜鱼生,以鲈、以鲤、以鰽白、以黄鱼、以青鲚、以雪魿、以鲩为上,鲩又以白鲩为上。以初出水泼刺者,去其皮刺,洗其血腥,细脍之以为生,红肌白理,轻可吹起,薄如蝉翼,两两相比,沃以老醪,和以椒芷,入口冰融,至甘旨矣。而鲥与嘉鱼尤美。”[22]文中详细描述了生鱼片的制作过程,指出生鱼片不仅具有极佳的口感,同时还兼具如艺术品的审美价值。此外,广府地区的古人在食用生鱼片时,喜欢配以辣椒、香芷调制而成的老酒,从而起到去腥提鲜的效果。
(三)鲥鱼与广府文化
鲥鱼入诗,始于宋代,盛于明清。伴随着时代的发展,鲥鱼作为诗歌意象的文化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王安石、何景明、屈大均等历史文化名人,均为鲥鱼作过诗。其中,珠江鲥鱼以其肉质鲜美的特点,成为广府诗人笔下寄托情感的存在。而广州竹枝词作为广府文化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对岭南地区的风土人情,以及特有物产亦是多有记述和描摹。
在明末清初之际,岭南因特殊的地理位置,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文人志士。屈大均,字翁山,广东番禺人。他在清初影响颇大,与梁佩兰、陈恭尹并称“岭南三大家”。珠江鲥鱼是岭南特有的风味,屈大均对此专以《荡舟海目山下取鲥鱼为脍》为名而写下一组七言绝句:
(其一)
雨过苍苍海目开,早潮未落晚潮催。
鲥鱼不少樱桃颊,与客朝朝作鲙来。
(其二)
烂鳞粉颊满渔船,煮用涓涓海目泉。
海目山人不可见,中流一啸寄僵川。
(其三)
羚羊峡口嘉鱼美,不若鲥鱼海目鲜。
黄颊切来纷似雪,绿尊倾去更如泉。
(其四)
刮镬鸣时春雪消,鲥鱼争上九江潮。
自携鲙具过渔父,双桨如飞不用招。[22]
该组绝句,共有四首。海目山位于南海县西南一百里的九江海中,其一是说明诗人在雨后捕捞鲥鱼,且所捕的鲥鱼多为樱桃颊。屈大均另在《广东新语》提到,“鲥以樱桃颊为上,黄颊、铁颊次之,烂鳞粉颊为下。”[9]其二则表达诗人对收获满船鲥鱼的喜悦,并直接采用清澈的海目山水烹煮鲥鱼。其三则指出诗人对海目山的鲥鱼十分喜爱,并已沉浸于鱼脍配美酒的欢畅之中。其四的“刮镬”为鸟鸣之意,古人凡捕捞鲥鱼,以刮镬鸣为信号。诗中更是以“双桨如飞不用招”的夸张描述,反映诗人对品尝珍馐美味的迫切之感。四首绝句在内容上各有偏重,互为补充,而文人墨客垂钓间的闲适之情亦在这组七言绝句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竹枝词则是唐代流传于巴蜀一带的诗歌体裁,后经刘禹锡、白居易等的推广而逐渐遍及全国。那么,广州竹枝词,又有“岭南竹枝词、珠江竹枝词、番禺竹枝词”等名称。竹枝词虽多出自民间,但却为众多的文人所喜爱。清中叶以后,岭南地区已将竹枝词运用得十分广泛,出现了专咏一地、一事甚至是一物的竹枝词。如专咏顺德甘竹滩所产鲥鱼的竹枝词,据清代罗天尺的《五山志林》记载:“尺案:甘滩更有嘉鱼,味鲜美类鲮,而玉鳞不下杨柳湾。陈学士璋《岭南竹枝》有云:‘羚羊甘竹嘉鱼出,七寸鳞鲜佐晚餐。寄与诗人评水族,阿谁匹美是河豚。’”[19]这首竹枝词运用了对比的手法,突出甘竹滩所产鲥鱼的品质。另有屈大均为了咏颂甘竹滩所产鲥鱼的品质,亦曾作诗二首:“甘滩最好是鲥鱼,海目山前味不如。丝网肯教鳞片损,玉盘那得脍香余。”又云:“滩下肥过滩上鱼,罨中泼刺泝流初。冰鳞触损烹无及,玉筯殷勤食有余。”[9]屈诗二首也表达了自己对于甘竹滩所产鲥鱼的鲜美的倍加推崇。然无论是陈学士璋的《岭南竹枝》,还是屈诗二首,文人群体的食脍之乐、钓捕之趣,背后同样透露其闲适淡雅的处世态度。
五、余论
鲥鱼自元代已被广府先民所食用,至明清仍于广府地区分布较广。明清广府地区鲥鱼的应用价值更是被充分挖掘,兼具药用与食用价值,让广府先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得到满足。而在长期的认识与利用之中,广府地区亦形成了一套与之相关的捕鱼技艺。此外,鲥鱼渗入广府先民日常生活的同时,文人群体更是将其作为诗词中的一种意象加以使用。这不仅呈现了屈大均等一批岭南本土作家注重自然的生态书写,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广府地区的社会风貌。时至今日,由于鲥鱼资源已近乎灭绝,以明清广府地区鲥鱼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希冀可以对今日的鱼类资源保护起到些许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周远富,若愚点教.尔雅[M].北京:中华书局,2020.
[2](宋)陆佃撰.尔雅新义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3](宋)戴侗撰,党怀兴,刘斌点教.六书故[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宋)司马光等编.类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明)李时珍撰,刘永山主编.本草纲目[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6](清)吴震方撰.岭南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元)陈大震,吕桂孙纂修.(大德)南海志[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8](明)黄省曾等著.养鱼经:外十种[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9](清)屈大均撰.广东新语(全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王云五主编.蟹谱及其他二种[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11](明)戴璟修,张岳纂.(嘉靖)广东通志初稿[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12](清)张嗣衍修,沈廷芳纂.(乾隆)广州府志[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13](清)潘尚楫修,邓士宪等纂.(道光)南海县志[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14](清)彭人杰修,范文安,黄时沛纂.(嘉庆)东莞县志[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15](清)林星章修,黄培芳等纂.(道光)新会县志[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16]林书颜.广东鲥鱼及其渔业志[J].岭南农刊,1935,
(2).
[17]长江水产资源调查小组编辑.长江鲥鱼调查研究[M].长江水产资源调查小组,1977.
[18](清)李福泰修,史澄,何若泰纂.(同治)番禺县志[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19](清)吴绮等撰,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20](清)赵学敏撰,刘从明校注.本草纲目拾遗[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7.
[21]朱东润选注.梅尧臣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22]陈永正主编,吕永光,苏展鸿副主编.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
王思昊,男,福建福州人,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