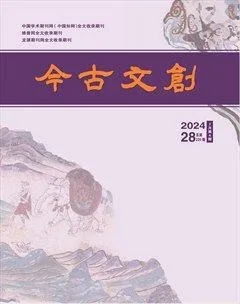对方以智语言学训诂认识的研究
2024-07-31唐琳

【摘要】本文从《通雅》卷四十一草类植物篇的植物词概况、训诂内容、训诂方法、训诂术语几个方面展开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通雅》草类植物篇的训诂特点,从中窥见方以智语言学训诂认识的科学性及其影响后世训诂研究的学术基础。
【关键词】《通雅》;方以智;语言学训诂;草类植物词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8-011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8.036
基金项目:湖北民族大学2024年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对方以智语言学训诂认识的研究——以《通雅》卷四十一为例”(项目编号:MYK2024018)成果。
明清之际,方以智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中产生了有别于传统的、科学的训诂认识,其《通雅》不同于《尔雅》《释名》等服务于经学、解经通义的传统训诂著作,他有意识地摆脱经学附庸,以语言解释为旨归,训诂对象不局限于经,在经学训诂传统之下形成了语言学训诂认识,显现出超前的语言学史观,这是中国训诂学史上的一大进步。
一、草类植物篇的植物词概况
《通雅》卷四十一草类植物篇,共51个词条,约占《通雅》植物篇词条总数的25%。通过对这些词的词群排列、历史来源分布等情况进行描写和说明,可以呈现出《通雅》草类植物篇植物词的大致面貌。
(一)词群情况
根据词群中的词与词之间的意义关系,可将词群分为“类义词群”“同义词群”和“上下位词词群”三种类型。
1.类义词群
“类义词群”指的是具有共同上位词的意义上相近的一组词,其成员在意义上有联系。邢福义先生指出,“类义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类义词是指属于同一语义范畴、表示同类概念或意义,而没有上下义、同义或反义关系的一组词[1]。本文依照邢福义先生狭义的类义词观点确定类义词群。例如:“曰蔚,曰繁,曰艾,曰萧,曰藾,曰茵陈,曰夏枯草、九牛草,皆蒿类。”“蔚,繁,艾,萧,藾,茵陈,夏枯草,九牛草”,它们的所指不同,并非一物,但都属于蒿之一种,是类义关系。
2.同义词群
“同义词群”是具有相同的理性意义的一组词,也就是说这些词的所指相同。例如:“蕙则薰也。《本草》:‘麻叶,方茎,赤花,黑实。’陈藏器曰:‘即零陵香也。’”“蕙、薰、零陵香”所指相同,三者是同义关系。“木生者曰木兰,又名林兰,杜兰,非元美所谓玉兰也。”“木兰、林兰、杜兰”所指相同,三者是同义关系。“萝摩,即羊婆奶,白环藤也。”“萝摩、羊婆奶、白环藤”所指相同,三者是同义关系。
3.上下位词词群
“上下位词词群”指的是该词群里的词之间是上位词与下位词关系的一组词。所谓上位词,是词义体现了一个上位概念或种概念的词;而下位词是词义体现了一个下位概念或属概念的词。因而上位词与下位词的关系,实质上是上位概念与下位概念的关系,是概念上的种属关系[2]。例如:“凡称幽兰,即黄山谷之所名兰華也。凡称兰 之兰,即今省头香。”方以智认为:“萝摩、雀瓢亦名芄兰,瞿麦名大兰,狼牙曰支兰,石斛、山梔皆曰林兰,石苇曰石兰,白菖蒲曰溪荪,弘景以为兰孙,蒲芦曰野兰,白茅曰兰根,麦冬曰珍珠兰,兰固芳草之通名也。”因此,“兰花”是“幽兰”一类的上位词,“省头香”是“兰 之兰”的上位词。
(二)历史来源分布情况
“研究先秦词汇要读《尔雅》,研究汉魏词汇要读《广雅》,如果要研究唐宋元明词汇,则不可不读《通雅》。”[3]《通雅》解释了很多从唐至明的词汇,但《通雅》卷四十一草类植物词的考释材料没有局限于唐宋之间,而是引用了不同时代的例子,这说明方以智在词义考证时注意到了词汇历史来源的不同,这些草类词出现的历史时期不会晚于文献产生时间。借助中华经典古籍库进行检索统计,大致考察《通雅》卷四十一草类词目前已知的历史来源,并依照方一新先生的汉语史分期主张,将现代汉语之前的汉语史分为上古、中古和近代三个时期。上古期是先秦、秦汉;西汉是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演变的过渡阶段;中古期是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初唐、中唐是中古汉语向近代汉语演变的过渡阶段;近代汉语时期是晚唐五代以后。[4]通过考察,得出《通雅》卷四十一51条草类植物词的已知历史来源分布情况如下:
1.先秦汉语时期
卷四十一见于先秦时期的草类词共22例,约占《通雅》卷四十一51条草类植物词的43%。这些词是:兰、蕙、木兰、萝卜、蒿、藚、莎、葍、活莌、寇脱、薯蓣、杜若、旨苕、莠葽、鷄冠、诸虑、鬰金香、杬、萱、泺贯衆、芝、 、耳。
2.西汉过渡期
见于西汉过渡期的草类词共6例,占《通雅》卷四十一51条草类植物词的12%。即:燕支、酸浆、昌羊、荍蚍、大苦、橐吾。
3.中古汉语时期
见于中古汉语时期的草类词共13例,约占《通雅》卷四十一51条草类植物词的25%。这些词是:蘄、屠苏、芪母、薄荷、百灵草、莨菪、夏枯草、青葙、菴闾、虎掌、蚤休、野葛、鬼目。
4.初中唐过渡期
见于初中唐过渡期的草类词共5例,约占《通雅》卷四十一51条草类植物词的10%。这些词是:石龙蒭、押不卢、鹤虱、黄独、由跋。
5.近代汉语时期
为便于统计,在方一新先生主张的基础上将近代汉语时期的界定截至明末。《通雅》卷四十一见于近代汉语时期的草类词共9例,约占草类植物词的18%。这些词是:天棘、透山根、海藤花、缠枝牡丹、席箕、䕭麻、拒霜、白幷、㜑妇。
二、训诂内容与训诂方法
(一)训诂内容
从方以智对草类词的训释与考证内容可以看出,他对有的字的读音做了解释,对有的词义做了解释,考证了某些词源,重视对语言发展变化理据问题的分析,指出了前人的某些错误。
1.注明读音
方以智常使用直音法、反切法等方式先注明读音,再释义。例如:“《春官》:‘駹车雚蔽。’雚即萑,音丸。细苇席也。”方以智注音后再释义,“雚”在此处的读音和词义与“萑”相同,皆音“丸”,“细苇席”的意思。“芹,渠巾切,古作蕲,水草也。”方以智用反切法为“芹”注音,“芹,渠巾切”,并指出“芹”就是古代的“蕲”,“蕲”,渠之切,二者读音相近。
2.考证词义
方以智在训诂过程中使用了丰富的语言材料,考证众多文献材料及方言等,在对语言材料进行分析与比较的基础上做解释,具有重要的语言学参考价值。“纒枝牡丹……即《尔雅》之蕧盜庚也。”方以智先对“纒枝牡丹”是何种植物做了解释,然后列举了匠人对其的称呼、旧名、今称以及在《尔雅》中的名称。纒枝牡丹就是旋葍鼓子花之千叶者,也是旋花、旋葍、旋覆花、蕧盜庚。“鬼目非一……今草子粘衣者,亦非一种。”鬼目,其所指在不同文献、不同方言区都不同,方以智列举了《尔雅》《广志》《东观按图》《吴普本草》《开山图》等文献,涉及到江东、交趾、辽东、襄平、湖南、江北等不同地区对“鬼目”的认识。
3.探求语源
《通雅》草类植物篇体现了方以智对语源的认识,结合大量语言材料与客观事实探求语源。例如:“白幷、㜑妇,即百部也……古人不善状物,如钩吻,实蔓生,似柿叶,而乃云似黄精,此类不少。”方以智通过考证发现,“白幷、㜑妇、百部”为同一物,“白幷、㜑妇”都与“百部”存在音转关系。白,并母铎部。幷,帮母耕部。百,帮母铎部。部,并母之部。白百准双声,铎部同韵。幷部准双声,耕之旁对转。
4.匡正谬误
《通雅·卷八·释诂》言:“智按:古人形相似,则随笔用之”“慕古太甚,虽古之败笔、讹文,皆谨奉之若神功。”[5]方氏能辩证地看待古人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出现的疏漏谬误,对有争议的观点,他通过文献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详加考证,指出前人的错误认识。“天棘,天虋冬也……今《纲目》亦增天棘、万嵗藤。”王仲正、杜甫认为天棘蔓青丝,髙秀实认为天棘就是天门冬,王元之认为天棘舞金丝,冷斋认为天门冬是颠棘,而不是天棘。针对不同说法,方以智对天门冬的外形以及南人对其种植情况做了考察,然后做出判断:蔓青丝正是天门冬,并通过《本草纲目》加以佐证这一观点。由此推翻了王元之、冷斋的观点。
(二)训诂方法
《通雅》草类植物篇以“草类植物词”为基本训释单位,冲破了以词证经,以经证词的局限,具有开放的研究视野与明确的语言史观,把传统经学训诂方法运用得更加科学。
1.因声求义的运用
因声求义是一种利用语音线索来明假借、系同源、考证古书词义的办法。[6]
“䕭麻即荨麻……以爓音瓒,其土音耳。宋子京益部方物记有燖麻赞。”方以智引用了《本草图经》《墨庄漫录》对“䕭”的记录,以语音为线索,由“䕭,音爓。䕭,音瓒。又以爓音瓒,其土音耳”得出“䕭,音爓”,与“荨”同音。又引用李时珍对“荨”的注解,证明了“䕭”“荨”之间是假借关系。
2.比较互证的运用
“存中以苦躭为酸浆,升菴以灯笼草为酸浆……灯笼草结果,曰红姑娘,乃红瓜囊之讹。”不同的人对“酸浆”有不同的解释,方以智把沈括、杨慎、李时珍以及《尔雅》《茹草编》提到的关于“酸浆”的不同的说法归纳到一起,相互比较,指出“酸浆”的所指及不同名称。
3.方言佐证的运用
“大苦,黄药也……此如闽越之木芙蓉数丈,两广之茄不枯,陕边之枸杞合抱,不足异也。”针对“大苦”一词的解释,方以智首先就对郭璞的看法表示质疑,引用《梦溪笔谈》《尔雅》《开宝本草》《说文解字》中关于“大苦”“甘草”的记载,推翻郭璞的观点,并引用李时珍和《后山谈丛》提到的四川、交趾、闽、越、两广、陜等不同方言地区关于“苦药”“黄药”“甘草”等植物的称呼、生长情况,佐证自己的观点,得出“大苦”就是“黄药”。
三、训诂术语与训诂特点
(一)训诂术语
《通雅》卷四十一草类植物词训诂术语主要有“即”类,“则”类,“乃”类,“作”类,“谓之、曰、名、为”类,“类”类,以及无特殊标记词类(某,某也)。其中,“即、则、乃”都可翻译成现代汉语的“是、就是”,“作”可翻译成现代汉语的“写作”,一般用来说明不同写法。“谓之、曰、名、为”可翻译成现代汉语的“叫、叫做、当作”,这些训话术语通常放在解释内容之前。“类”一般用来说明类别、种属关系,“某,某也”这一训诂术语无特殊标记词,直陈其义。
“即”类,14例,例如:“萝摩,即羊婆奶,白环藤也。杜若,即高良姜。”“则”类,共1例。“蕙则薰也。”“乃”类,共2例。“缠枝牡丹,乃旋葍鼓子花之千叶者也。”“诸虑乃葛藟。”“作”类,共3例。例如:“燕支,今作胭脂,古通焉支、阏氏、燕脂,字书因作 。”“谓之、曰、名、为”类,共14例。例如:“木生者曰木兰,又名林兰,杜兰。”“存中以苦躭为酸浆,升菴以灯笼草为酸浆。酸浆,葴也。”“昌羊谓之䒢,一曰尧韭。”“类”类,共2例。例如:“押不卢,盖活鹿草之类也。”“某,某也”,共11例。例如:“天棘,天虋冬也。”
(二)训诂特点
1.实事求是,无征不信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方以智做过中肯的评价:“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虽其中千虑一失,或所不免,而穷源溯委,词必有证,在明代考证家中,可谓卓然独立者矣。”[7]从前文对训诂内容、训诂方法的分析中,不难看出方以智在训诂过程中“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训诂特点。在正文中他引用了大量文献材料与前人的观点,相互比较,对存疑的观点进行考证,指出错误,若证据不足便提出质疑。《通雅》卷四十一共出现“误矣”14处,“讹为”“讹也”6处,“疑”1处。
2.以证为主,以释为辅
从前文训诂术语可以看出,方以智采用多种训诂方式训释草类词,训诂术语前后都是植物名词。正文从植物名称、生长习性、功效用法等方面进行考证,针对单字的具体释义相对较少,注重在“考证”的基础上解释语言。总体看来,具有“以证为主,以释为辅”的训诂特点。其考证材料相当丰富,具体如下。
朝代 文献 人物
先秦 《诗经》《山海经》《楚辞》《吕氏春秋》《夏小正》 周公、孔子、曾子
汉 《仓颉篇》《〈毛诗传〉笺》《淮南万毕术》《说文解字》《上林赋》《淮南子》《甘泉赋》《别录》《神农本经》《急就章》《韩诗》《后汉书·皇甫规传》《急就章》 刘向、司马相如、张揖、郑玄、华佗、毛亨、马融、扬雄
三国 《广雅》《魏略》《与韦仲将书》《南州异物志》 李胜、应璩、王褒、韦昭、孙皓、王全
晋 《郁金颂》 傅咸、左思、嵇含、吕忱、杨孚
南北朝 萧子云、顾野王、王筠、陶弘景、王融、郭文恭、元恪
隋唐 《千金方》《卢氏杂说》《北史·西域传》《唐本草》《干禄字书》《酉阳杂俎》《续集》《唐书》《除䕭草》 杜甫、孙思邈、陈藏器、孙愐、李贺、段成式、安禄山、成汭
五代十国 《日华子本草》《食性本草》 徐铉、徐锴、陈士良
宋 《尔雅注疏》《梦溪笔谈》《冷斋夜话》《墨庄漫录》《益部方物记》《游宦纪闻》《塞上诗》《唐诗纪事》《癸辛杂志》《类篇·益部方物记》《补笔谈》《本草图经》《太平广记》《枫窗小牍》《开宝本草》《后山谈丛》《墨客挥犀》 郑渔仲、郑樵、冯嗣宗、高茂华、王禹偁、陆佃、王安石、沈括、范仲淹、邢昺、赞宁、张咏、赵頵、黄庭坚、张邦基、宋祁、赵彦卫、戴侗、罗愿
元 《异域志》 朱震亨
明 《本草纲目》《吴普本草》《茹草编》《余冬序录》《土宿真君本草》《焦氏笔乘》《本草蒙筌》《庶物异名疏》《塞上曲》《大明一统志》《函史》 李时珍、徐渭、陈嘉谟、王世贞、王慎中、杨慎、郎仁宝、赵宧光、梅膺祚、秦韬玉、邝露、邓元锡、何孟春、刘袤
四、结语
本文通过具体的例子,呈现出《通雅》卷四十一草类植物词的训诂情况:训诂内容丰富,训诂材料广博,训诂方法科学,没有局限于解经,而是将语言作为主要训诂对象,对语言发展的过程做历史的考据。关于明清之际传统经学训诂向语言学训诂转向的问题,陶玲《论方以智经学训诂向语言学训诂之转向》已从训诂对象、训诂目的、训诂内容、训诂材料与方法等方面做过相关论述,但17世纪传统经学训诂土壤里语言学训诂的萌芽与发展的具体情况以及方以智在语言学训诂认识上的具体成就等具体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邢福义,汪国胜.现代汉语[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重排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4]方一新.从中古词汇的特点看汉语史的分期[J].汉语史学报,2004,(1):178-184.
[5]黄德宽,诸伟奇.方以智全书·第六册·通雅[M].合肥:黄山书社,2019.
[6]王宁.训诂学(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7](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
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