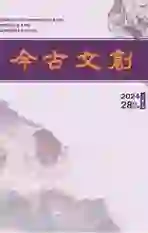《自然辩证法》中自然观走向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进路及其启示
2024-07-31刘世宇
【摘要】恩格斯通过对以往自然观的扬弃以及对近代自然科学成果的总结,以整体性视角在《自然辩证法》中构建出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自然观,完善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为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共产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哲学保证。通过对《自然辩证法》中自然观走向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进路进行深入梳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生态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8-0084-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8.026
近代以来,随着环境污染、能源紧张、生态危机等环境状况的出现,生态环境问题随之成了一项重要的学术议题。生态问题是否必然发生?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人类能否克服生态问题?当代克服生态问题困难的根源又是什么?怎样克服生态问题?这些成了当代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而上述问题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自然观,正是以“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为核心,在扬弃以往自然观、总结近代自然科学成果、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的基础上构建出先进的、科学的、革命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所以,对《自然辩证法》中自然观走向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进路进行深入梳理,对解决上述生态问题、推动共产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大意义。
一、先进且科学的辩证自然观
《自然辩证法》中的自然观并非是恩格斯为显示与众不同的个人价值而论述的特立独行的空谈,而是以解决当时社会背景下哲学和科学的困境为目的,在扬弃以往自然观并总结近代科学成果的基础上的先进且科学的辩证自然观。因此,《自然辩证法》中自然观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是保障其先进性和科学性的前提。
(一)《自然辩证法》中自然观产生的社会背景
随着工业革命的持续发展,资产阶级制度下的大工业生产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另一方面加深了自然、人、社会三者之间的对立。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凭借着在英国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下获得的大量真实具体的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前后人们的生活环境的对比,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工人阶级身体和心理上造成的迫害。由此可见,加深人与自然之间对立的原因应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1]。
巴黎公社失败后,一方面,受到沉重打击的资产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地位,不但在物质层面上加强对无产阶级的迫害,而且鼓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产生出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在精神层面上企图蒙蔽和瓦解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种种行为不仅对无产阶级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同时也搅乱了当时科学界的思想。由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的散布,让打破了宗教神学“存在之链”的近代科学产生出返回神秘主义的倾向,导致当时很多的科学成果出现了“短暂有效”的局面,造成了哲学上和科学上的双重困境。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为准备新一轮的革命积蓄力量,急需在思想上和理论上武装自己。无产阶级革命需要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马克思已经将辩证法成功运用于社会领域,为了不使马克思的辩证法留下遗憾,成为“半截子”的辩证法,就需要在总结自然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将辩证法引入自然界[2]。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的自然观正是为解决当时科学和哲学上的双重困境、完善并丰富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而产生的。
(二)《自然辩证法》中自然观产生的理论渊源
古希腊朴素自然观将自然看作统一变化的整体,虽然是臆测性、不彻底的自然观,但凭着天才般的直觉,认为“整个自然界……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逝中,处于不断地流动中,处于不断运动和变化中”[3],使辨证自然观的存在成为可能。康德的星云假说,虽然最终没有彻底地冲出神学的桎梏,但描绘出生成着和消逝着的自然图景,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3],使辨证自然观在理性思维中的存在成为可能,突破了牛顿力学统治下的“僵化的自然观”。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个方面全面地论述了他丰富的辩证自然观体系,但黑格尔将观念和理念作为理论的出发点,是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辩证自然观。虽然“黑格尔将辩证法神秘化了,但这并不影响他第一个全面、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3],因此恩格斯将黑格尔颠倒的自然观翻转过来,找到其合理内核,将其作为唯物辩证自然观的理论基石。
18世纪下半叶开始,自然科学从原来的搜集材料阶段进入综合整理概括阶段,“现代自然科学——它同希腊人的天才直觉和阿拉伯人的零散的无联系的研究比较起来,是唯一可以称得上科学的自然科学”[3],天文学和力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了现实世界的不断运动和普遍联系;物理学和化学的相继突破,揭示了事物的不断变化发展以及事物之间的相互转化;随着能量守恒定律、细胞学说和生物进化论的问世,进一步证明了物质不灭性以及事物的永恒发展,填补了过去有机界与无机界无法转化的空白。恩格斯正是在扬弃以往自然观,结合近代科学成果的总结的基础上,确立了一种物质不灭且转化的、普遍联系的、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新的自然观。这种新的自然观虽然并非绝对不可置疑,但与其他自然观相比,因其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社会背景,从整体性、普遍性、长远性上看,以压倒性优势证明了这种新的自然观是最先进且最科学的自然观。
二、“人与自然辩证统一”为核心的辩证自然观
如同处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一样,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存在两个方面:“人与自然之间,究竟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与“人能否正确认识自然”的问题。恩格斯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正是《自然辩证法》中自然观的核心内容。虽然《自然辩证法》中没有明确提出生态问题,生态问题也并非当时的主要矛盾,但因其核心内容中包含着人、社会、自然之间的交互关系,所以恩格斯的辩证自然观中显示出了明显的生态意蕴,是解决生态问题的前奏。
(一)自然对于人的先在性
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人本身的存在还是人之为人的存在都是有必要条件的,如果失去这些条件,人将不会存在。由于这些必要条件并非全部是由人类创造的,所以从时间的层面上来看,自然必然先于人而存在。恩格斯认为,在人类产生前,自然就按照其自身规律永恒的运动变化着,物质内部和物质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转化,在不断生成和消逝中演化,星系、星球、环境、植物、动物、人类乃至人类的社会都是按照自然本身的规律转化产生出来的。不仅人产生于自然,人的物质活动同样依赖自然,自然界为劳动提供了材料,劳动再把材料转化为财富。可见,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3]。
人独有的意识是人之为人的特征,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同样依赖于自然。恩格斯对将意识当作大脑产生的特殊物质的庸俗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这是因为意识是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映像,把意识等同于物质忽略了意识的主观性,导致留给了唯心主义反击的空间。在恩格斯看来,意识是人类在劳动中通过分工协作、语言产生、营养摄取等条件下,人类的大脑、器官、肢体得以进化而逐渐产生和发展的,因此人和大脑的存在只是意识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环节之一,意识的“物质性”应归于自然的不断演化而不是人和大脑的存在与功能自身。综上所述,自然界是容纳了所有生物物种的整体,人及其全部的历史都是其中一环[4]。
(二)人对于自然的能动性与受动性
由于自然是一个整体的辩证系统,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相互影响的,因此任何事物的自身变化发展也会反作用于自然使其发生改变。恩格斯认为,生命的出现,使事物的变化与发展具有了计划性,即使在没有细胞出现的地方,也存在着萌芽形式的计划性。但动物仅仅通过自身的存在来改变自然界,而人则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去支配自然界[3]。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正是通过劳动实践在自然打上人类的烙印,通过不断地征服自然的同时使自然服务人类,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
但是,人属于自然却不等同于自然,故此人与自然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共性与差异随着人与自然不断地运动和发展转化为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矛盾运动中的相互吸引、排斥、转化决定了人改变后的自然必然反作用于人自身。人的目的也不等于自然,二者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导致了被人类改变后的自然对人类的反作用会产生同时存在符合人类目的与不符合人类目的的结果。如果人的目的只考虑自身利益却不考虑对自然的影响而一味不断地征服自然,在得到符合人类目的结果的同时,其中不符合人类目的的结果同样会通过量变产生质变,对人类造成显著的伤害。所以,“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3]
然而人类面对自然的报复并非无能为力。人通过劳动与自然连接,由于人与自然遵循同一个自然规律,使人的主观意识中包含了客观的自然规律。科学是人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方式,科学的不断发展让主观意识变得越来越客观;技术作为有效改造世界的手段,技术的不断发展使人改造自然并加强自身,不断地在广度和深度上扩大人与自然接触的范围。所以恩格斯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会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越来越认识到人类生产行为对自然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会感觉并认识到人类自身和自然的一致,达到精神和物质、灵魂和肉体、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3]。人类正是在通过不断扩展加深“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这种正确认识”基础上的劳动实践中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解,避免了自然的“报复”。
三、革命性的辩证自然观
与过去的文明相比,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虽然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扩展加深了“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正确认识。但因其制度本身以追求利润和剩余价值最大化为根本目标,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使其劳动实践不能有效地建立在“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正确认识之上。可见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具有的反生态性是近代以来克服生态问题困难的根源,对其制度正确的批判并非是像动物之间单纯的为私利而产生的争斗,而是人类为有效解决生态问题的必经之路。《自然辩证法》中的自然观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的正确批判,显示出这种新的自然观是革命性的辩证自然观。
(一)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机制的反生态性
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机制是使其为追求一定时期内利润最大化而加深人与自然对立的决定性因素。在这种机制下,如果不在一定时期内追求最大化的利润转化为资本,易导致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市场份额被竞争对手所抢占,进一步影响企业盈利能力,最终使利润下滑、亏损甚至企业倒闭。因此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机制迫使人们不得不优先追求一定时期内的利润的最大化,很大程度上违背了优先追求“人与自然辩证统一”这一有利于解决生态问题的目标,是具有反生态性的市场竞争机制。
一方面,追求一定时期内的利润最大化不完全等同于追求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给人类带来的是整体上、长期的、普遍的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自然因人类对其不合理改造的“报复”要在人类对自然破坏到一定程度上才能从量变发生质变而显现出来,且时间上具有滞后性,只有在对自然的不合理改造达到一定程度、经过一段时间才会出现影响“一定时期内利润的最大化”的现象。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只有在两种追求恰巧一致时或当自然对人类的“报复”阻碍了实现“一定时期内利润的最大化”的目标时,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才将劳动实践建立在“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正确认识”之上。
于是,当人类对自然的不合理改造因没有达到质变的程度,没有转化为对人类的“报复”或因滞后性“报复”没有降临之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业文明为获得充足的资源就会对自然过渡开采,破坏生态平衡。为获得最大的利润过度刺激消费,造成资源浪费。当环保的处理方式的成本高于有害的处理方式时,为节省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就会采用对环境有害的技术和工艺、排放污染物,破坏污染环境。并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导致生态问题从局部地区扩展到全球范围。但人类对自然的不合理改造的影响不会凭空消失,终会随着改造的累加发生质变而“报复”人类,使人类饱受生态破坏的苦果。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
“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实际上就是通过人的劳动实践来实现既满足人类的发展需要,又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目的,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相互的良性影响和共同发展。但资本主义为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采用使劳动实践自身和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分离的生产方式,导致劳动实践和劳动产品不属于劳动者自身,成了不是为了满足劳动者自身发展需要的劳动实践和劳动产品,这种劳动的异化加深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因此,资本主义以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为目的的生产方式是反生态性的生产方式。
由于劳动实践自身与劳动者的异化,资本主义为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采取增加劳动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的方式对劳动者进行剥削和压榨,使劳动者的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伤害。而劳动产品的异化最终会导致劳动产品的生产过剩,造成自然资源的浪费。此外,就连生存环境也转化为劳动产品的形式与劳动者相分离,资产阶级可以生活在相对优质的环境中,而占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只能被迫生活在相对恶劣的环境中。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造成资源浪费、破坏劳动者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体现其反生态性特征的,必然会引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就是对其生产方式反生态性的“报复”。
四、《自然辩证法》中自然观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根据现代科学成果的最新发现,从宏观世界天体之间距离和轨迹的不断改变到微观世界量子之间的相互影响,无不证明着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正确性,使历经百余年的《自然辩证法》至今依旧散发出真理的光芒。但真理不仅仅用来解释世界,关键在于为解决问题来改变世界。因此,生态文明建设是《自然辩证法》中自然观逻辑进路的必然要求,《自然辩证法》中自然观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保证,对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推动创新驱动发展
自然对于人的先在性,决定了人的存在与发展处处依赖自然。首先,人是通过自然的不断演化产生的,且人与自然都遵循着同一个自然规律,因此,顺应自然规律是人类存在的前提。其次,自然为人类的物质活动提供了材料,自然的破坏直接影响着人类物质活动的持续进行,可见保护自然是支撑人类物质文明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最后,人的意识以及精神活动的产生和发展同样依赖于自然,故而人对自然的态度贯穿着人类全部精神活动的始终,对自然正确的态度有利于人类精神文明的持续健康发展,从而有利于人类行动的成功。人的意识正确与否取决于主客观相符合的程度,由于自然是客观的存在,所以尊重自然才是有利于人类发展的正确态度。综上所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生态文明建设中一切行动的前提。
创新可以满足人对于自然受动性与能动性两方面的共同发展要求。从受动性方面的发展要求上看,自然是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没有任何永恒不变的事物。这要求我们要不断坚持创新,只有新的理论才能够符合不断运动变化发展后的自然;从能动性方面的发展要求上看,在以往的发展方式基础上出现了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严峻形势。这要求我们要寻找新的发展方式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正是满足这两方面要求的发展方式,它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手段推动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推动能源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因此,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有利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有利于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二)在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基础上走向共产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但受其制度本身具有的反生态性所影响,致使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将科学技术当作了追求利润与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手段,导致了科学技术的异化进而参与到加深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的过程中去。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凭借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仅增加了对自然资源索取的数量和效率,而且扩大着索取的范围,将索取范围蔓延至全球,不但将高污染高风险的产业转移至其他国家,榨取其他国家劳动力的剩余价值,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发动战争抢夺其他国家的资源。可见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会继续加深。生态危机的出现证明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自然的破坏超过以往的一切文明。为了解决生态问题,就必须超越这种具有反生态性制度的、并随着自身发展不断加深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对立的、对人与自然的破坏程度不断增大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
仅仅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并不代表可以彻底地解决生态问题,只要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存在的矛盾没有真正解决,生态问题就一直会存在。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能使人与自然、人与人相互和解。在共产主义社会,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建立在“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正确认识之上,不仅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双向和解,而且实现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恩格斯认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他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因此,在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基础上走向共产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有效解决生态问题的必然路径。
五、结语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自然观作为一种先进的、科学的、革命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不仅响亮的回答了许多亟须解决的重大生态问题,而且为如何解决生态问题指明了有效路径。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生态保护的加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完善、生态文明教育的普及,无不体现着这种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当代价值,使历经百年的真理至今熠熠生辉。所以,我们应继续对其进行深入地学习和研究,并运用到具体实践中去。
唯心主义过分强调理性的地位,将理性中逻辑的权威置于一切事物之上,这种僵化了的理性使唯心主义具有转化为形而上学的倾向;形而上学的产生归根结底源自人类为逃避现实中的错误和危险,为达到一劳永逸、平静安宁的状态而在心中追求永恒不变的理想。因此形而上学中也包含着唯心主义的元素。然而不将感性和变化运用到实践中去,现实中的问题既不会按照理性中的解决方式消失也无法在变化中得到不变、在消逝中发现永恒。因此要求我们无论在理论中还是实践中,都要摒弃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不崇拜任何事物”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随着对其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这种普遍性的真理必将指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前进,最终建成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杨莉,刘继汉,尹才元.浅论《自然辩证法》中的生态意蕴及现实价值[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34(04):72-77.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4]邓湖川.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自然观及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04):
109-119.
作者简介:
刘世宇,男,辽宁抚顺人,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