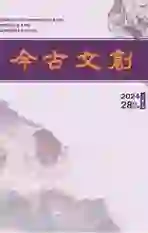青年网络“圈层化” 现象的立体透视与反思纠偏
2024-07-31冉嘉怡
【摘要】青年网络“圈层化”现象是指青年群体在网络场域中因特定兴趣领域形成小团体,并呈现出共同价值观、话语模式和行为规范等现象。本文从青年网络“圈层化”的现实表征出发,基于弗洛姆《逃避自由》的视角,从内在、外在因素两方面对青年网络“圈层化”背后的心理根源和社会动因进行剖析,并从宏观上探讨这一现象的纠偏机制。
【关键词】《逃避自由》;青年;圈层化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8-0079-05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8.025
弗洛姆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综合起来,形成了社会心理学。《逃避自由》是弗洛姆社会心理学的奠基之作。弗洛姆关注的问题是“什么让一个社会群体以相似的方式思考、感受和行动”[1],并在这本著作中给出了答案,这对于剖析当代青年群体网络“圈层化”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近年来,网络上圈层文化在青年人中空前发展,而现实中青年又出现“社恐”“emo”等心理状态,构成了“网络狂欢”与“现实孤单”的鲜明对比。目前,传播学、社会学、教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学界从不同视角出发,结合学科特点展开研究。其中,传播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研究内容多是网络“圈层化”的衍生现象——舆论传播、群体极化等,探究其生成机理、现实困惑和价值引导;教育学和马克思主义学界多致力于解决教育“失语”的问题展开研究。弗洛姆“逃避自由说”关注个人心理的动态过程和社会的动态过程,以人的理性和爱的潜能的自由发展为旨归,为探究青年网络“圈层化”生成的心理根源和社会动因提供理论视阈。因此,本文将基于这一理论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研究青年网络“圈层化”现象。
一、青年网络“圈层化”现象的现实表征
圈层不是网络时代独有的现象。圈层现象自人类社会产生起就存在,在过去的熟人社会中联结圈层成员的主要根据是亲缘和地缘,这种“社会圈子”是“富于地方性的”[2]。在网络的催化下,圈层的覆盖面拓展到虚拟空间中,圈层关系的形成依据由亲疏远近转变为以兴趣爱好为主导。网络的时效性使圈层内部联结更为紧密,圈层文化对青年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凸显。网络“圈层”是指“以兴趣、爱好、利益等为关系构成的网络社群连接”[3]。“圈层化”的“化”则表明这一现象是不断变化的、动态的、渐进的形成过程。因此,要以变化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现象。从当前网络“圈层化”的发展来看,其现实表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现实自由的扩大
网络的匿名性和网络交往的不在场性,给予了青年更多选择、塑造形象、兴趣表达的空间。具体来说:首先,圈层选择自由。对于青年而言,相较于现实社会中社群的复杂性,网络“圈层”的选择是更为自主的。从复杂的现实强联系中剥离,兴趣爱好、价值取向成为青年在网络圈层选择上主要考虑的因素,满足自身需求成为青年在网络圈层选择上的根本目的。青年可以依托个人判断采取行动,“混圈”与否、参与深浅、投入大小都不必受外界强制性因素的控制,青年群体向往的选择自由在此过程中得以充分满足。也正是由于选择的自主性,青年对自己选择的网络圈层有着更高的依赖度与信任感。这种网络圈层选择自由带来的吸引力,成为越来越多青年人主动加入其中的重要原因;其次,形象塑造自由。网络的虚拟数字实践解构着主体自我意识同一性的和谐状态。网络作为现实的延伸,其匿名性可以给青年自由感,允许青年尝试以不同于现实的方式展现自己。青年在其所属的网络圈层中,通过“碎片化”地表现自我,塑造一个理想的数字自我。虚拟世界塑造形象的自主性,同时暗含着真实自我和数字自我的分离;最后,表达兴趣自由。这种因趣缘凝结成的网络圈层往往也是松散的,自发主观因素多、外在行为约束少,圈层内人员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每个人都能在圈内自由表达和交流,成为所属圈层的参与者和建设者。所属圈层文化的单一性给予了青年展现自我的回应和呼声,这让青年主观地认为找到了精神世界的归属。但同时青年也面临着迷失自我的风险与挑战。
(二)圈层内外的分离
文化是多元的,但圈层文化具有独特性和排他性,“小众文化是青年网络圈层形成的前提和基础”[4]。圈层文化的传播和更新只在圈层内部进行,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文化孤岛”的情况,圈层内外出现了分离的样态。具体来说,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从不同网络圈层的隔阂来看,“网络空间本身构成了一个大的场域,其内部又有不同的小场域”[5]。青年往往只关注自己所属“小场域”的动态。因此,圈层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文化壁垒”,不同圈层成员之间难以理解彼此的情感倾向,也难以有共同的兴趣话题。另一方面,从网络与现实的分裂来看,首先是代际沟通的分裂。青年人作为数字原住民,发展出各类网络亚文化,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网络圈层,如“二次元圈”“电竞圈”“饭圈”等。这些网络亚文化的发展与传播离不开网络技术发展的“推波助澜”。但年长一代对于时代技术的革新大多处于被动适应的状态,而老年人更是出现“数字失能”的问题,他们无法把握网络的文化潮流,更不会深入圈层内部。因此,代际沟通的空间和共知的意义内容被压缩。其次是青年群体与现实的分离。长期对网络圈层的沉迷,可能会使青年与现实脱节,甚至产生对现实问题的抵触情绪。
(三)消费主义的膨胀
“社会的变迁导致了人类心理内部的转化。”[6]在泛娱乐化、享乐主义等网络亚文化的耦合驱动下,青年作为“时代最灵敏的晴雨表”[7],他们的消费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转变。商品的使用价值弱化,而商品外在、情感、符号价值的重要性突显。圈层文化打造的消费热点,满足了青年消费的需求变化。一方面,圈层的封闭性加剧消费主义的扩张。攀比心理、炫耀心理等不良消费心理在价值观尚未定型的青年群体中弥散开来。另一方面,圈层青年表达情感和文化认同的方式集中在消费上。青年人散布在网络的各大小圈层中,尽管在圈层的文化基础上各不相同,但是青年表达文化认同的方式却主要集中在消费上,即青年人常说的“氪金”。以典型的“娃圈”为例,青年沉迷于购买和收藏各类玩偶和玩偶的衣服与配饰,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消费“景观”。据一名“娃圈”爱好者坦言,在圈内,最厉害的那些画手和最有钱的一批金主不断推高价格,普通人仍然愿意随波逐流。[8]同样的情况在“饭圈”也处处可见,比如偶像能否出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粉丝“打投” ①的能力。显而易见,消费主义在网络圈层中已靡然成风。某一圈层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越强,其消费能力越强。文化认同在网络圈层中异化为消费主义。
二、青年网络“圈层化”现象的心理根源
青年网络圈层是对现实自由的扩大,出现内外分离的样态以及消费主义的膨胀等现实表征,实质上显示出青年人在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孤独、脱离现实、情感消费等现实困境和倾向。借助弗洛姆“逃避自由说”,可以更加深入地剖析青年网络“圈层化”背后的心理根源。
(一)个体化进程:青年个体孤独的现实处境
圈层的生成从表层看是青年由于各自不同的兴趣而凝结形成的,深入来看实则是青年对现实自由的无所适从,向圈层内寻找安全感。
在弗洛姆看来,人对安全感的需求是一个被动接受到主动寻求的过程。从人的生命历史来看,婴儿独立于母体的标志是联结母子的脐带被割断,但这只是粗浅意义上的独立。人在成长早期通过器质性的“始发纽带”与外界相连,这个生命的安全区使其获得了安全感和归属感,找到了“生命的根”[9]15。在“始发纽带”的作用下,一切都是确定的,人不会有孤独和疑虑,并且会得到归属感,但自我意识的缺失,会使其以一个群体、社会或部落的一分子,而非作为一个人去认识自己。因此弗洛姆总结道,“这些始发纽带屏蔽了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理性及批判能力发展的绊脚石”[9]22。
一旦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就会出现“首次自由行为”[9]22,和谐和安全的状态被打破,开始与原始群体分离,人变成了“个人”,自我的力量得到彰显,原始的安全纽带也因此断裂。在自我意识还未萌芽的时期,人在“始发纽带”的庇佑下,没有所谓的自由和独立,但是却能获得安全和归属;在自我意识萌芽并增长的时期,人渴望摆脱“始发纽带”的束缚,获得独立自主的权利。
青年在摆脱“始发纽带”的过程中,进入个体化进程,但个体化进程是具有两面性的,造成了青年“自由却孤独”的现状。弗洛姆剖析了个体化进程的辩证特征,一方面是“肉体、情感和精神上越发强壮,各方面的强度和活动都在增加”,即“自我力量的增长”;另一方面是“孤独日益加深”。[9]18在成长早期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我意识增强,“达到断绝始发纽带的程度越高,渴望自由与独立的愿望就越强烈 ”[9]18。认识个体化进程的辩证特征是理解人渴望自由的愿望的前提。
因此,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在青少年阶段,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萌芽并不断增长,对社会和世界的认识增强,积蓄了彻底割断“始发纽带”的力量,开始谋求自由和独立。伴随着身心的不断成长和发展,其出现了矛盾心理,一面渴望得到自身的独立和外界的尊重,抗拒并且想挣脱外界的管束,一面又离不开父母,渴望被对方理解和关怀。但是由于受到社会变革,青年一代和年长一代的社会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此父母们在很大程度上难以真正地理解青年们的兴趣和需求。因此,青年们开始向虚拟世界寻求安全感和归属感,众多趣味相投的青年聚集于网络圈层中,构建起了一个庞大的乌托邦的世界。
(二)受虐倾向:青年寻找新的安全和归属
弗洛姆在第五章分析了逃避自由心理机制的不同的表现形式,指出受虐倾向是权威主义性格的一个方面,受虐倾向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中,一种表现形式是,个人过分地俯视自我,贬低和轻视自我,这种贬低自我的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孤独和不安全感;另一种表现形式是通过依附权威,放弃个人的完整性,这一权威在外在形式上表现为某一机构、某个人、某个国家等具有凝聚力的整体力量。当个人发现自己“孤独一人面对一个被异化了的敌对世界”,于是开始“寻求某人或某物,将自己与之相连,他再也无法忍受他自己的个人自我,疯狂地企图除掉它,通过除掉这个负担——自我,重新感到安全”[9]100。个人想要除掉自我,从本质上来讲,是要除掉自由的负担。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分析了现代人这种异化的生活状态,“靠别人恩典为生的人,把自己看成一个从属的存在物”[10]。由此便找到了“继发纽带”——受虐纽带,试图重新获得安全。
弗洛姆又指出,继发纽带根本不同于始发纽带。始发纽带能让个人知道真正的归属,是真正的安全;而继发纽带是一种逃避。人在个人自我状态下,却未能实现自由,由此生发孤独与无能为力感。因此试图在继发纽带下寻求安全感,可能是一种自我安慰的心理,主观上感觉到安全,但从“根本上仍是一个淹没在自我之中苦苦挣扎的一个无力的原子”[9]104。
青年们以原子的状态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生活中,在享受个人自我状态的同时,也饱受着从传统共同体中脱离出来而产生的精神孤独和存在焦虑,因此产生了在网络中寻找自我认同和保持存在的需要。青年人依附于网络圈层的表现,实质上是由于自身的孤独和不安全感而试图使自己成为自身以外的网络圈层的一部分,成为网络圈层的参与者、管理者,使自己不再是一个现实中的孤独的自我,而是一个获得了新的安全和尊严的自我。但现实与网络的割裂感,如果长期得不到弥合,青年们根本不能将自我从这种孤独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仍然扮演着“无力的原子”的角色。
(三)迎合倾向:青年逐渐向圈内趋同
弗洛姆梳理了逃避机制的三种表现形式,他认为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机械趋同,即迎合倾向。这是为大多数现代人所采用的一种方式。机械趋同是指,由于惧怕孤立,害怕对我们的生命、自由及舒适的更直接威胁,我们与别人的期望和要求保持一致。[9]132伪活动取代思想、感觉和愿望的原始活动,最终导致伪自我取代原始自我。[9]135我们可以看到,饭圈、二次元圈、电竞圈等各种娱乐性的网络圈层充斥着虚拟世界,并在网络平台资本的支配下蓬勃生发。青年人融入网络圈层的出发点本是去寻求个人兴趣所带来的精神愉悦感,但网络圈层的封闭性和圈层内容的同质性,会使青年忽视外界环境批判的声音,无法看清事物的真实本质。因此,即使圈层内出现了错误的倾向,圈层成员也会不由自主地去迎合圈层内的潮流,久而久之,价值观得不到主流文化的滋养逐渐扭曲。以饭圈为例,每个偶像在微博上都有或多或少的支持者,这些支持者们为了吹捧自己的偶像,经常出现粉丝群体引战、广场狂欢,为了黑而黑所谓的竞争对手或合作对象,恶意p图,传播黑图,编造谣言,使其陷入从天而降的污名中,无法脱身。粉丝群体中不乏不服从之流,为了维护自己在圈层内所塑造的形象,迎合圈内的任务,也会加入一场场的纷争中,成为群体引战中的一分子。
三、青年网络“圈层化”现象的社会动因
弗洛姆在从人的生命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现代人的性格结构之后,又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剖析了社会进程对于个人性格塑造的影响。而“人的性格结构不但决定了人的思想和感觉,而且还决定了其行为”[9]189。
(一)平台资本的宰制
弗洛姆认为,社会进程通过决定人的生活模式,即与他人及劳动的关系,塑造了他的性格结构。[9]68除了有青年群体自身特征的因素外,现代社会的发展也为“圈层”的生成提供了滋养环境。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智能手机的普及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用户行为发生了质的变化。流量经济大行其道,吸引了一众资本注入互联网的浪潮中。平台资本利用算法推荐机制将用户分流,为用户搭建了一个“信息茧房”,网络用户收到越来越多能满足兴趣的同质化内容。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当代青年与互联网的联系,无疑是最为紧密的。因此,青年人的个体孤独是其向圈层逃避的内在原因,资本宰制与算法技术是催生圈层形成不可缺乏的社会条件。内外因素的合力作用为青年群体打造了一个个性化的信息世界,当青年们在圈层中发表看法时,迎来的几乎都是同类回响,造成了“回音室效应”。
(二)数字劳动的隐蔽
弗洛姆肯定了资本主义把人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指出,人隐蔽地成为实现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目的的劳动者。人的命运便是促进经济制度的进步,帮助积累资本,这并非为了自己的幸福或得救,而把它当做目的本身,人成了巨大经济机器上的一个齿轮。[9]73个人臣服于经济目的,成为实现它的一种手段。[9]74在泛娱乐化的时代,体量不一、各不相同的圈层内嵌了使资本积累的数字劳动。以饭圈为例,在娱乐明星的微博评论区,以互动次数为标准区分铁粉、金粉、钻粉;在明星的超话中,同样以每日签到、发帖量、评论量等为标准确定超话等级,级别越高难度越大。如果在某一天超话断签,需要通过充值VIP获得补签卡,否则就难以升级。在资本的运作下,青年粉丝对偶像的迷恋被捆绑到日复一日的数字劳动中,青年与圈层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三)消费景观的建构
弗洛姆批判了现代广告对人的批判思维能力的弱化。他指出,大部分现在广告并不诉诸理性,而是情感,像其他任何一种催眠暗示一样。他先着力在情感上征服对方,然后再让他们在理智上投降。广告宣传根本与商品的质量无关,像电影一样具有白日梦的特点,能满足顾客的某种需求,但同时增加了他们渺小感与无能为力感。[9]85“谁懂得了令群体想象力深刻的艺术,谁就掌握了驾驭他们的艺术。”[11]在网络圈层中的青年们无一不是某一类商品的潜在消费者。这些商品的宣传海报或宣传广告,从根本上脱离了使用者对于商品使用价值的诉求。而是通过高价聘请流量明星做代言人,通过圈层的力量促进消费。又或者是,通过科技的手段赋予虚拟的动漫人物,以人的特性创设梦幻的情境促进消费。在圈层中消费景观的建构使青年对人的迷恋有了物化的实体。
四、青年网络“圈层化”现象的引导纠偏
青年网络圈层化的生成既受青年群体内在性格结构的影响,也受到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网络圈层的封闭性,加深了圈内文化对青年群体的影响。文化的好坏,影响着青年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如果长期沉浸于某一种文化中,青年可能主动或被动地排斥主流文化,无法与外界正常交流,自以为是、作茧自缚,严重危害其成长。因此,需要对青年网络圈层化现象加以规训。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在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与《爱的艺术》中略窥一二。
(一)注重爱的非对象性
弗洛姆认为人们对自由的肯定来源于人们爱的能力。这里的“爱”不是对某个特殊人的关系,而是一种态度、一种决定。爱是肯定所爱之人是根本人性的化身,爱一个人也意味着爱人类。如果只爱某一个人,“对其他同胞漠不关心,那么这不是真正的爱,而是共生性的依附,或是扩大了的自我主义”[12]57。青年网络圈层的运作模式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实质上是一种共生性的依附,又或说是一种群体自我主义。从某种程度上说,圈层因不同的兴趣而分门别类,这既是个性的彰显,也是个性的丧失。一方面,圈层为青年提供了彰显个性和纾解孤独的入口;另一方面,圈层创造了一个“小世界”,“参加者为了使自己属于这一组人而失去了大部分个性”[12]16。因此,真正地寻求自由是获得真正的爱的能力,即,由爱一人而“爱所有人,爱这个世界,爱生活”[12]57,又或者说是获得积极生活的态度。
(二)回到现实的创造性劳动
创造性劳动是青年自我实现的现实途径。弗洛姆认为实现积极自由需要我们“自发地在爱与劳动中与世界相连”[9]92。这告诫广大青年,要用自发劳动联结世界。首先,自发劳动意味着劳动要与人的类本质相符合。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由于使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13]56,也就是说,劳动要有益于身心成长,凡被资本裹挟与诱导的,要以资本规定的数字劳动表现自我的不能被称为自发劳动。其次,回到现实世界中。青年作为“现实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135。青年要实现积极自由最终要回到现实世界中,因此,要注重判断现实世界和网络场域的必要性与非必要性、根本性与附生性,以免在网络中失去自我,陷入更深层次的虚无与孤独中。
(三)积极实现自我超越
自由和超越往往是密不可分的,自由意味着自发地实现自我,而超越意味着质变,到达实现自我的彼岸,是自我实现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弗洛姆认为,人类所真正追求的是积极自由——自由地发展,而非消极意义上的自由。追求自由是个体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也是文化进步的必然结果。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辩实际是质与量之辩。因此,弗洛姆提出:“自由不仅仅是个量的问题,而且是个质的问题,我们不但要保存和扩大传统的自由,而且要赢得一种新自由,它能使我们认识到属于自己的个人自我,可以使我们对这个自我及生活充满信心。”[9]70也就是说,一方面,青年要保有自我思考、自我选择、接受结果的传统自由;另一方面,青年要培养远见与格局,有面对人生困惑的智慧和能力,超越一切既定关系的束缚,不逃避、不依附,认识自己、成为自己,达成自我“质”的飞跃。
总之,“逃避自由-顺应群体-成为工具-疯狂失控-走向毁灭,这不仅是社会理论的逻辑演绎,更是人类历史的真实展现”[14]。青年从独立自我到顺应网络圈层群体,在多重势力的交织影响下,存在着摆脱良性发展、走向疯狂失控的隐患。面对网络圈层的现实困境,青年要关注现实世界,在爱与劳动中实现积极自由。
注释:
①“打投”指的是“打榜”+“投票”,在一些选秀成团真人秀节目中,票数最高的几位选手可以“成团出道”。通常是粉丝被拉入一个群以后,用手机不断为明星投票。
参考文献:
[1]赖纳·丰克,王琦琪.弗洛姆《逃避自由》一书的出版及其意义[J].国外理论动态,2021,(03):56-62.
[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6-7.
[3]涂凌波,郑石,蔡雨.构建美美与共的网络文化景观[N].光明日报,2020-12-04(11).
[4]罗琳.青年网络“圈层化”的时代特征、生成机制与风险防控[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2,41(03):75-83.
[5]刘胜枝.值得关注的95后群体文化圈层化、封闭化现象[J].人民论坛,2020,(Z2):131-133.
[6](德)韩炳哲.倦怠社会[M].王一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65.
[7]习近平: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EB/OL].http://www.qstheory.cn/2019-04/29/c_1124432366.htm,2019-04-29.
[8]从“绘圈”到“娃圈”都“圈钱”[EB/OL].http://zjnews.china.com.cn/jrzj/2021-11-09/311159.html,2021-11-09.
[9](美)艾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M].刘林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1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09.
[11](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群体心理研究[M].张源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63
[12](美)艾·弗洛姆.爱的艺术[M].李健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1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4]甘绍平.对“逃避自由”的伦理审视[J].道德与文明,2019,(04):11-20.
作者简介:
冉嘉怡,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