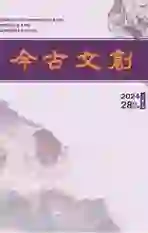恢复本心何以可能?
2024-07-31任远东
【摘要】王阳明之思想以心为本,谓心即理,理即良知。人心本有至善之体,在未动之时无善无恶,在动之时有善有恶。若因既往之习气或私欲而遮蔽本心,则不能辨别善恶而生邪念、作恶行。故欲恢复本心之至善,则须祛除习气和私欲之遮蔽。王阳明于《抚谕贼巢》一文中,以慈悲之心劝诫贼寇,示以去恶向善之法。此文与《传习录》中王阳明对弟子之教诲相合,其间可以探寻到王阳明为善去恶的修身功夫和至善心体为一贯的修证体系。
【关键词】本心;善;恶;诚意;良知
【中图分类号】B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8-005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8.018
基金项目:贵阳学院校级研究生课题基金《清代刘沅〈俗言〉研究》(项目编号:GYU-YJS[2021]-31)。
《抚谕贼巢》是王阳明在平定漳州叛乱后,准备继续进攻乐昌、龙川的山贼时,写给他们的劝降信。这封信深刻地表达了王阳明对那些不得已而逃入山林的叛乱者的同情和怜悯,以及他对他们归顺朝廷的诚恳和期待。这封信一出,黄金巢、卢珂等山贼首领纷纷带领部下投降,及时回头是岸。这封信不仅展示了王阳明人性本善的哲学思想,也体现了王阳明对人性向善的信念和力量。
本文以王阳明的《抚谕贼巢》为基础,想要进入王阳明的哲学境界,探究他的学问的精髓。并且试图跳出王阳明的视角,参考哲学的大传统,以求客观公正地理解王阳明所探讨的哲学问题。因此,本文采用体证法来分析。体证法强调客观的分析态度而非主观的武断,即对王阳明的学问持有一种“同情的理解”的态度。这种体证法包括知和行两个方面的内容。从知的方面来说,让人能够设身处地地体察古人的人生经历,体会他们的真情实感;从行的方面来说,让人能够汲取深刻的教训,作为今人立身处世的警戒。这种体证法不是一种纯理论的研究方法,而是一种“知行合一”的实践意义上的方法论。王阳明去除心中恶念的功夫可以帮助人消除私欲和习气的遮蔽,这对于当下诱惑比古代更多的时代来说,恢复本心之善更有研究意义。
本文根据这封檄文,并参考《传习录》中王阳明对弟子的教导,来探究人心之恶的由来和去除恶念向善之道。本文分三节论述:第一节结合《抚谕贼巢》中所说的叛乱者和《传习录》中的教言,来探究恶是由于本心偏离而产生;第二节分析《抚谕贼巢》中王阳明帮助叛乱者恢复本心之善的策略;第三节借用王阳明“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之教言,来探究为什么消除心中之恶难于登天,普通人又该如何消除心中之恶,恢复心之至善本体。
一、恶之缘起与本心的偏离
在《传习录》中有这样一段话:“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为善,有为不善?先生曰:‘恶人之心,失其本体。’”此言明示人心的本体是理,理即是良知。天理良知人皆具之。由此可见人性本善,亦可知恶之所由来。王阳明四句教云:“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人心本有至善之体,在未动之时无善无恶,在动之时有善有恶。人能以天理良知审察善恶,此乃人皆固有之能力。若失其本体,则本心被遮蔽而不能辨别善恶。
“失其本体”非谓至善之本体消失,乃是至善之本体被杂然之私欲所遮蔽。恶人心中本有至善之本体,良知被其私欲所蒙蔽,不能觉察善恶之分,遂堕为恶人。王阳明所讨伐之乐昌、龙川贼寇,即是此类丧失良知天理之人。然则此等贼寇何以丧失本心之良知天理,而成为恶人。王阳明于檄文中推测曰:“其间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为官府所迫,或是为大户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误入其中,后遂不敢出。”此等人成为贼寇之因,即在于其内心升起错误或邪恶之念头。
王阳明于《传习录》中曰:“善恶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动气便是恶。”人本然之心性固为至善,然心中包含善恶两种念头,自心发出之念头未必皆为善,抑或为恶。如《尚书》所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人心不可靠,发出之心念并非皆可去恶从善,有不确定性。邪恶之事即是不循天理、乱发心念、乱作为、违背道义、偏离正道等等。此邪恶非但指道德上之邪恶,亦指对见识或知识过分追求满足之恶,或曰人不良习性之恶,如贪淫好色等。此等邪恶行为、邪恶念头之来源,王阳明以欲望和习气解之。
当心至善本体被诸般邪念、欲望所遮蔽时,王阳明谓之“意之动”或“气之动”。此二者实系自邪恶产生之不同角度言之。意者心念之发动,气者邪恶产生后之现象。心念与现象所表达者皆同一邪恶。王阳明对“意之动”所产生之邪恶又有一说,借《中庸》中道法则以解释之。心念发动皆须符合中道,即中正平和,无“过”无“不及”。若违背中道法则,则心念发动不能保持中正平和,出现“过”或“不及”者,则为邪恶矣。是故心念发动保持中道则为善,违背中道、偏离中道则为邪恶。邪恶即是对善偏离。亦言善有界限,超越界限即为邪恶矣。此等贼寇身上之邪恶即在于心念发动处产生。当其见财物而心升欲得之念头,则无可厚非。但若其心进而升起欲以不正当方式获得财物,则为“过”矣,是过分发用心念,违背中庸之道,邪恶即产生。此不正当获取财物的念头一升,则为其邪恶念头之发动,若又将此邪恶念头付诸行动,则为邪恶行为之产生。无论因财物占有欲而生出过分之念头,或因地主官府之逼迫而生出邪恶之念头,并使此念实现于行动,无论何种原因皆是作恶。作恶日久则会形成习气,习气遮蔽本心,渐渐沦为恶人。
二、恢复本心之方
人心之本体即理,理者良知。然后天种种缘故,人心至善之本体被遮蔽而不能辨别善恶,遂堕为恶人而祸乱天下。当务之急为探寻恢复本心,去恶为善之方。王阳明于《抚谕贼巢》一文中,以慈悲之心劝诫贼寇,示以恢复至善心体之方。
(一)比拟的方法
人皆厌恶邪恶之事。即使是作奸犯科之徒,不愿遭受邪恶之害。王阳明在檄文中说:“人之所共耻者,莫过于身被为盗贼之名”。盗贼乃邪恶之名,若有人以此称呼之,则其内心必感耻辱,不愿承担此名。《大学》云:“如好好色,恶恶臭”。邪恶之事,如同恶臭之气,令人生理反感,情感厌弃。若邪恶之事降临己身,人们便会立刻产生厌恶之心,驱使行为进行躲避。王阳明以此为据,运用比拟的手法,让贼寇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若他们是普通百姓,被贼寇们烧杀抢掠,他们是否甘心受此劫掠?若他们自己的钱财被夺走,房屋被焚毁,妻女被侮辱,他们是否甘心忍受此事?这些贼寇们若遭此厄运,心中必然升起极大的怨恨,必定想要报复那些毁了自己美好生活的人。这正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自己不愿遭受邪恶之事,就不应该对别人做出邪恶之事。王阳明就是利用这一比拟的方法,唤起贼寇们心中的良知,使他们及时回头。
比拟的方法虽然能够触动贼寇们心中的良知,让他们感受到自己行为的邪恶和可耻,但有一些穷凶极恶之徒,心灵已经被彻底黑暗所笼罩,不再分辨善恶是非,不畏惧他人的报复,他们胆大妄为。这种方法对于这一类人可能无济于事。
(二)譬喻的方法
如果运用比拟之法未能使贼寇回头,王阳明随后又运用第二种方法。此法乃以譬喻之法激发贼寇心中潜藏久远的孝心与敬畏心。此譬喻以朝廷为父母,以贼寇与百姓为子女。人自幼依附于父母之怀,受父母之教。父母为使子女知错改过之意,或斥责或惩戒之。是以父母之威严之像立于子女之心。当子女欲行不义之事时,若念及父母之威严,则内心生敬畏之情,或可止于未然。若不义之事已成,则念及父母之形象,则内心生愧疚之念,思及自己将使父母忧伤,将受父母之责罚,则亦生改过之意。以此畏惧与孝顺父母之心感化贼寇,则或可使其弃恶从善。
(三)恫吓的方法
若譬喻之法未能使贼寇悔过,则又运用第三种方法。此法乃以恫吓之法唤醒贼寇心中之良知。檄文中言若贼寇固执于恶而不肯改过,则朝廷必将剿灭之,并勉励其勿存侥幸之心。朝廷能够剿灭贼寇者,以其得天理良知之助。天理良知者,人皆固有之,能以之辨别善恶,而自然远恶而近善。朝廷乃善人群体之代表,保护善人之利益。朝廷讨贼之举,为了维护善人之生命财产不受贼寇之侵害。是以朝廷必得向善之人之大力支持,向善之人必不断地为朝廷提供援助,朝廷之兵力物资必不断地得到增补。而贼寇一方乃人所憎恶者,人人唾弃者,无人肯为之助。贼寇乃以一己之力与天下之善人相抗。故两方之力量相差甚远。王阳明于檄文中指出朝廷必能剿灭贼巢,乃为了恫吓那些心存侥幸而执迷于恶者。此种恫吓必使贼寇明白自己若不改过,则必无好结果。他们内心必生生死危机之感,想到破贼巢后将无处容身,便对朝廷所代表之善势力生敬畏之心。此时所生之敬畏心,较之幼时因过错而受父母惩戒时所生者更甚。甚至内心无力抵抗。此时他们内心之良知或可除去遮蔽,重见光明。如是则有可能使其投降改过。
三、恢复本心之难
《抚谕贼巢》以至诚感化为旨趣,劝导贼寇回归良知本体。果见效验:不少贼寇感悟而弃恶从善,并率众投降;然亦有一部分贼寇不为所动,仍旧负隅顽抗,终为王阳明先生所剿灭。此中缘由何在?王阳明先生多年后行军途中,有感于此,遂传下一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此言何意?须知破山中贼非易事。在王阳明先生之前,朝廷已派出诸多大将剿贼,皆以失败告终。王阳明先生之所以能够成功,乃因其已得道成圣,祛除心中之习气与私欲,无论行军打仗或朝廷为官,皆能凭借良知做出正当之选择。是以王阳明先生为善势力之代表,能够以源源不断之力量,去剿灭山中之贼寇。而人皆有良知,能分辨善恶,本能趋善避恶。若良知被恶之习气所熏染,被遮蔽而不显,便不能知善知恶,成为恶人矣。杀恶人易,而恶之习气难除也。他人之恶习气非王阳明先生所能剿灭,惟有自己努力祛除心中之贼,方可回归良知本体。已堕恶道之人难以体察心中之贼,故破心中之贼难。
(一)善习的形成
王阳明说:“习性已成,难更改动。”人心念发动行为是习性形成之始。心念有善恶之分,行为亦有善恶之分。故习性有善恶之分。人发出善心念,则行善事。善事给人成就感或满足感,则人再发善心念。如人见劫匪抢人,则制服劫匪送警局。媒体报道此事,则人获赞赏。人欢喜赞赏,则立志帮人行善。由此可见,心念与行为相互促进,时间累积,则形成强大势能。势能如雪球滚大,则习性成善。想成善习性不易。非但需立志,且需持续行善。意志不坚,则懈怠一日,则势能消散,则前功尽弃。想成善习性还需良师益友监督指导,需积极向善生活圈渲染。如是,则内心至善本体彰显,则得滋养之力,则习性成善。
(二)恶习的形成
人多数情况下受血气私欲之影响好逸恶劳,善习难养成。资质优且自制力强者,自律不辍,摆脱血气私欲之影响,日久方可成善习。恶习易形成,与善习同理而更甚。前文论恶非仅邪恶,偏离中庸亦恶。私欲、心念、行为过分者皆恶。过分私欲生恶心,恶习由恶心起,恶心生恶行。若恶行不被发现或指责,则心中侥幸。如小偷初次偷盗,心中紧张而得财物,良知发用而后悔。良知与侥幸交锋,心念再不偷盗。及至无钱用时,忆初次不劳而获,则再欲偷盗。良知虽告之不可,侥幸则推之继行,心念下次再改。如是往复,则偷盗成习惯,良知被遮蔽。偷盗久矣,则内心无波动,至善本体虽存,良知难唤醒,弃恶从善难矣。偷盗已成本能,见他人财物则自然入己口袋。若一日觉察己之错误欲改变,则困难重重。盖偷盗之种已种于心田,即遭法律制裁,渐生悔改之心,但日后见珍贵财物则仍欲占有之,心田侥幸之心种再起,故重蹈覆辙矣。恶习既成,则扭转之需千百倍之努力方可实现。恶习扭转后方始养成善习之第一步,善习养成难,扭转恶习而成善习亦更难,故破心中之贼难。
(三)何以破心中贼
破心中之贼难于上青天,逆转恶习艰于登天。初生之善念,恶习之势能所压,如蝼蚁之力不及振臂。稍不留神,则善念沉没于恶习之海,无以自拔。因此,欲行善事,必先顺从良知之指引,审察心念与行为之是非,如《大学》云:“如好好色,如恶恶臭。”盗贼之所以窃取他人之财物,非无良知之警惕,而是被私欲之贪婪所蒙蔽,不肯诚心听从良知之发用。欲除心中之贼,必须真诚地面对良知之发用,不可欺瞒自己本心。其次,依循正道之步骤,可以消除心中之贼,培养善行之习惯,成为善人。
欲剿灭习气之贼,仍须借助良机。良机在于作恶后惭愧之心升起之时。惭愧者,良知未泯之表也。若能抓住此机,立志改过自新,则破心贼之第一步也。盖人心皆有至善本体,若能汲取其力量,则可滋养善念,抗衡恶习。然而至善本体何在?在于未染尘埃之童年时期也。回想童年时光,无忧无虑,不为世俗所累,心中无恶习遮蔽;再思考恶习何时形成?如何发展?则可防微杜渐,从源头遏制恶行。由有意而无意,由恶而善,则心贼可灭矣。寻至善本体者一难也;得良师益友者二难也。需跳出舒适圈,远离恶友邪朋。同气相求,既染恶习,则交友亦多恶习者。继续与之往来,则恶习势能增大,相互影响,则无益于培养善种。若能遇到良师益友,则可得其善熏陶,更易寻回至善本体,滋养心田中之善种,使之茁壮成长,直至能与恶念抗争。王阳明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难在作恶后惭愧时能否寻回至善本体;难在寻回至善本体后能否得良师益友之辅助;难在得良师益友后能否改变生活环境;难在改变生活环境后能否坚持不懈地修炼自己。《抚谕贼巢》一文,即王阳明以良师之身,助贼寇寻回至善本体,比拟、恫吓、劝导、感化,使黄金巢、卢珂等率众来投,及时脱离恶习之圈子,向善去恶。此文可谓助人破心贼之典范。
四、结语
夫欲行善事,必先顺从良知之指引,审察心念与行为之是非。在王阳明之哲学语境中,恶之层次较善之层次为低,恶乃在意念发动处所生,无本体之根源。故人不可凭意识心思考,意识心虽能思维,而容易生恶,其根源在于人以个体之意识心思考,自己则与天地万物成二元对立。而心中之至善本体能与天地万物相感通,不受一人一念所限,自然无他者与我之分别,故万物一体。是以王阳明悟道后,常以良知发用于官场与战场中如鱼得水也。若如常人一般以意识心发用,个体身心受一身一念之限,必受血气私欲之牵引,生成习气,逐渐偏离中正平和,遂遮蔽本心中之良知,迈错步,做错事,渐渐沦为恶人。总之,阳明心学对恶之论及恢复本心之功夫,涉及道德本体之确立与社会责任之担当。基于《抚谕贼巢》,我们实际探索出王阳明构建之本体与功夫为一贯之修正体系。在探索过程中可得出结论:人心之本体为至善,为永恒;而恶人之形成是因私欲与习气之一时遮蔽。因此恶人得到相应契机,掌握方法亦可转恶为善,重放良知之光。
参考文献:
[1]陆永胜译注.传习录[M].北京:中华书局,2021:81.
[2]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3]龚晓康.“恶”之缘起、明觉与去除——以王阳明“四句教”为中心的考察[J].哲学研究,2019,(7):77-86.
[4]姚军波.从诚意到致知:王阳明晚年教法之变[J].西安航空学院学报,2023,(2):65-70.
[5]詹良水,王飞.王阳明军事思想新探——以《武经七书评》为中心[J].孙子研究,2023,(1):54-65.
作者简介:
任远东,男,汉族,吉林长春人,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儒家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