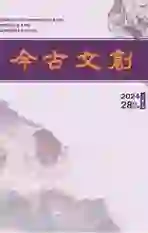伍尔夫双性同体理论下对文学创作的再思考
2024-07-31瞿敏玟
【摘要】不同于传统的生物学和心理学概念,弗吉尼亚·伍尔夫从文学创作的视域进一步对“双性同体”理论进行了阐发。作为一种文艺创作心态和美学风格,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头脑需要同时具备男性与女性两种力量的思考,并且保持一种超越男女两性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创作心境。“双性同体”理论视角下的文学创作,取消性别对立,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了解构;摒弃性别偏见,追求非个人化的写作状态;也为女性摆脱作者性别身份焦虑的困境,做出了不懈抗争;最后强调了对体验的追求,在体验中重建文学创作的新感受力。
【关键词】女性主义;双性同体;文学创作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8-005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8.017
基金项目:2024年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埃莱娜·西苏‘他者双性同体’观研究”(项目编号:2024XKT1865)阶段性成果。
一、取消对立——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
“逻各斯”(Logos)一词最早经由赫拉克利特被引入希腊哲学中,象征着世界一切的规律,万事万物变化的尺度和准则,后通常被解释为“理性”“概念”“本质”等含义。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对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到黑格尔和列维-斯特劳斯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做出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论断。德里达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存在着重视言语而贬低文字的倾向,在场的语言是建立本体论、目的论从而达到客观真理的根源,因而也是一种“言语中心主义”,同时也建立起一正一反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但二元对立并不意味着二者的平等并置,而是从价值论上、逻辑上等方面,一个支配着另一个。正如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所言:“一些二元对立如意义/形式、灵魂/肉体、直觉/表现、字面义/比喻义、自然/文化、理智/情感、肯定/否定等等,其间高一等的命题是从属于逻各斯,所以是一种高级呈现,反之,低一等的命题则标示了一种堕落。逻各斯中心主义故此设定第一命题的居先地位,参照与第一命题的关系来看第二命题,认为它是先者的繁化、否定、显形或瓦解。” ①在逻各斯话语体系下发展起来的社会,不断追寻文学作品背后的内容意义,文学与意识形态挂钩,也导致了以性别为对立的作家创作。女性在“菲勒斯社会”中,始终是从属于男性的第二性,在文学创作中也常以他者身份出现。而通过对这种等级秩序和二元对立统一逻辑的揭露和解构,女性主义试图瓦解和颠倒长久以来的父权传统,提出一种新的整合思维。弗吉尼亚·伍尔夫扬弃了文化意义上的“双性同体”形象,从自身的写作经验出发,将“双性同体”引入艺术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理想状态,使得性别因素反而退居其次。
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一书中,伍尔夫设想头脑中的两性应该与肉体的两性相对应,而两性达到和谐状态则需要摆脱头脑中固有的单一性别观念,对于作家更是如此。虽然柯勒律治早在《桌边文谈》中发出了“伟大的头脑是双性同体”的见解,但伍尔夫指出,柯勒律治只是从创作角度出发,强调男性作家要对女性气质有所吸收,本质上仍是菲勒斯社会下的二元对立思维。而伍尔夫认为任何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都需要摒弃性别的偏见,“必须是男性化的女人,或是女性化的男人” ②,最终在精神上达到“人格的双性化”。荣格从心理学上集体无意识的角度揭示了男女心理的双性特质:“正如男人是由女性成分补偿的那样,女性也受男性成分的补充。” ③男性潜意识中存在的女性气质被称作阿尼玛原型,对应着爱洛斯;女性潜意识中存在的男性气质被称作阿尼姆斯原型,对应着逻各斯。每个性别其实都存在着两种气质,只是在不同的性别中各自的气质分别占据了上风,而“双性同体”的头脑正是应当充分挖掘了潜意识中的另一半性别气质。将逻各斯与爱洛斯结合,理性与感性充分融合,对两种生命形态进行融合和升华,作家才能够形成一种整体统一的思维方式,从而取消二元对立的创作偏见,以文字解构以逻各斯为中心的文学创作,最终冲破父权制语言的牢房。
二、摒弃偏见——对非个人化写作状态的追求
18世纪以前女性的生活以家庭事务为核心,她们在经济上依靠男性,活动场所十分有限。即使是伍尔夫自身所处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也仍是一个以男性居多的知识分子团体。只是随着19世纪下半叶妇女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女性逐渐开始走出家庭的樊笼,伍尔夫也引领了其所在的文化圈,使其充满了女性主义的光辉。
伍尔夫指出,女性想要从事写作,则必须杀死“屋子里的天使”,并且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和一年五百镑的收入。在此之前,女性写作举步维艰,她们将受到男性作家的讽刺告诫与经济压力的双重压迫。所以物质本身并不发挥作用,但是经济上的独立却能够带来心灵上的自由。19世纪伟大的女小说家——简·奥斯丁、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和乔治·艾略特等,一方面正是实现了精神世界的相对自由,才能够创作出不同于男性作家的文学作品;但另一方面也由于其女性作家的身份,被排除在许多场所和人生经验之外,人生阅历的缺乏使得创作形式局限于自传小说,不公正的社会待遇也使女性创作充满了个人情感的宣泄。
伍尔夫在柯勒律治观点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扬弃,将女性也纳入文学创作的对象,实则是使得文学创作不再囿于性别的桎梏,进入非个人化的写作状态。所以“双性同体”的理想创作状态虽然要求女性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但同时也要求女性走出客厅,深入到外部世界,去了解外部世界和异性领域,将注意力集中于人类共同命运和非个人化的事物之上。在创作时,不再刻意强调自己的生理性别,而是将个人化的体验转化为非个人化的经验,摒弃性别偏见的同时,也抛弃社会强加于女性身上的责任和义务,真正回归“人”的主体地位,以“双性同体”的头脑进行关照人类命运的艺术创作。
“双性同体”对非个人化写作的追求还体现在是一种具有交往意识的交往行为,不仅应与同时代的世界交往,还应与跨时代的世界有所关联。伍尔夫在确立女性创作主体的同时,也肯定了读者等其他主体的主体性。“双性同体”的头脑中男性意识与女性意识共同存在,然而两种意识的差异并未被磨灭,也并没有哪种意识得到高扬,而是作家在通过阐述自己思路形成的过程中进行了非个人化创作,以创作主体的身份展开与接受主体相互理解的交往,促使接受主体形成自己的理解和判断。这样创作下的文本也是具有生命力的主体,即使具有其内在的矛盾性,正如伍尔夫一方面否定作家按照自己的性别进行创作,另一方面却也始终要求女性成为自己,但她也没有试图解释矛盾的原因,而是将这种矛盾展露于文本中,呈现在接受主体面前,使得不同主体的思想在文本中平等对话,形成积极主动的互动交流。
三、摆脱困境——对作者性别身份焦虑的抗争
哈罗德·布鲁姆曾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出发,对诗人与诗人之间的创作关系及其影响进行了研究,提出著名的“影响的焦虑”理论,指出焦虑的承受者通常是后辈的作家,担心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自己而是前辈。这样的“前后辈”关系同样也被敏锐的女性主义者注意到。尽管该理论对作者身份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价值,但桑德拉·吉尔伯特与苏珊·古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指出,该理论所呈现出的男性色彩和父权中心思想仍十分明显,理论文本的研究对象多为男性与男性之间,女性作家却在其中处于尴尬和空缺的位置。
桑德拉·吉尔伯特与苏珊·古芭进一步借用布鲁姆的理论,提出女性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新的性别困境——作者身份焦虑。“一位男性诗人所感受到的‘影响的焦虑’,到了一位女性诗人那里,就会更多地为‘作者身份的焦虑’所取代——这种‘作者身份的焦虑’表现的是一种强烈的恐惧感,即女性诗人担心自己无法进行创造,担心由于自己绝不可能成为一位‘前辈’,因此,写作的行为只能孤立她,并最终将她毁灭。” ④作者身份的焦虑源自女性作家在男权社会中的亚文化处境,她们对权威的无意识恐惧,逐渐演变成为创作时超越自我的情感障碍。即使女性终于开始创作,社会现实文化对女性的约束和规范仍然影响着其创作力。
文学从起源便被打上父权的烙印,德里达这样描述诗歌的创作以及诗与诗人的关系:“这意味着一种劳作,一种分娩,一个通过诞生诗人的缓慢妊娠,而诗人乃是诗之父。” ⑤即使诗的诞生被喻为分娩、妊娠,但是诗人却仍是诗之父,诗歌中的父权阴影挥之不去。诗人与诗之间原本存在的母性关系,却被迫指向父性的特征,创造力也因此被定性为自然属性下的男性性征。无法选择的固有生理性别,成了影响女性作家通往文学之源的阻碍,而只能通过父权诗歌来抵达。
对此做出反抗的女性作家,针对现实文化的不满,塑造了“疯女人”等系列区别于父性特征的文学形象进入文本,使得女性气质得以在文学中彰显,从而形成女性文学的特色。但是正如现实中张扬的女性气质的遭遇,女性作家所构建的具有女性气质的文学形象在文学中同样会被边缘化对待。
而“双性同体”的创作头脑中,构建起一种新型的两性格局,女性气质在与男性气质融合的过程中得到正视并加以正确利用,两性气质在融合中彼此区分,从而分别得到保留和展现。因此在重建或复原母性传统时,女性作家可以通过不同视角的选择来表达话语甚至重建性别,而避免在文字中流露出对男性审美的趋附,以及刻意摈弃自身的女性气质。此时的女性正作为“双性同体”的文学主体而存在,无论是从作品中推断前辈的创作意识,还是构建属于自身的一套文学系统,都重新拥有了“作者身份”,能够超越传统社会性别的限制。女性话语在文学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和公认,女性作家才能够缓解内心的恐惧和焦虑,从而释放其想象力。
四、强调体验——对新感受力的恢复
正如前文所言,每个性别身上都同时存在着阿尼玛与阿尼姆斯两种气质,生理性别是先天决定的,而社会性别却是后天规训而成。“双性同体”的创作头脑要求两种气质在创作的过程中得到充分融合,然而人是社会中的人,自诞生之初便受社会性别的限制,而想要打破这种限制,便需要在体验中感受差异,最终在差异中体会两性的融合。
以伍尔夫创作的双性同体人物奥兰多为例,奥兰多的一生不断经历着形体上的变化,其显著特征就在于服装,服装的选择似乎就暗示着奥兰多以何种社会性别面世。但无论是以何种生理性别存在,奥兰多的身上始终保持着两性气质的展露。即使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男性时,奥兰多的举手投足间也会不经意地展现出男性气质之外的“女性意识”。而当奥兰多最终成为传统意义上的生理女性时,由于她曾分别以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身份面对世界,她经历了两种不同的性别遭遇,这种独特的经历使其对性别气质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即使最终以女性的性别角色存在,她也并未刻意压抑自己原初作为男性所获得的经验,而是在体验中确证了“双性同体”的自我身份。所以在伍尔夫的笔下,此时的奥兰多才能够创作出最为伟大的文学作品。
苏珊·桑塔格曾在《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中提出一种“新感受力”,她认为:“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从来就不只是(或甚至主要不是)某些思想或道德情感的表达。它首要地是一个更新我们的意识和感受力、改变(不论这种改变如何轻微)滋养一切特定的思想和情感的那种腐殖质的构成的物品。” ⑥桑塔格强调了伟大艺术的作用在于唤醒人的新感受力,那么艺术创作本身同样需要具备这种新感受力,因为艺术的价值不在于对其结果、思想内容的阐释中,而是应当直接体验其透明状态。文学本身是开放的,文学创作也应当是开放的,所以只有在不断的体验中,感受两性气质的差异和融合,在无限接近“双性同体”的创作意识中,恢复文学创作的新感受力,最终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作。
五、结语
伍尔夫所提出的“双性同体”理论,更多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描述了作家在创作时理应具备的理想人格状态。其对男女两性气质融合的强调,既是对菲勒斯社会下“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的解构,也为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新的思路。在追求非个人化的写作状态的同时,女性作家也得以摆脱作者性别焦虑,重新确立其作者身份。而只有在体验中恢复文学创作的新感受力,才能打破社会的规训,真正创作出更新意识和感受力的作品。
注释:
①(美)乔纳森·卡勒著,陆扬译:《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②(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著,吴晓雷译:《一间自己的房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5页。
③(瑞士)C·G·荣格著,杨韶刚译:《伊雍:自性现象学研究》,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17页。
④(美)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著,杨莉馨译:《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3-64页。
⑤(法)雅克·德里达著,张宁译:《书写与差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6页。
⑥(美)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反对阐释》,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页。
参考文献:
[1](美)乔纳森·卡勒.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M].陆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法)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3](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4](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M].吴晓雷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5](美)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M].杨莉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6](瑞士)C·G·荣格.伊雍:自性现象学研究[M].杨韶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
[7]吕洪灵. 《奥兰多》中的时代精神及双性同体思想[J].外国文学研究,2002,(01):61-65+172.
[8]吕洪灵.双性同体的重新认识:批评·理论·方法[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3):122-127.
[9]沈潇.女作家性别身份焦虑问题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8.
[10]张婷玉.弗吉尼亚·伍尔夫“双性同体”理论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9.
作者简介:
瞿敏玟,女,汉族,江苏苏州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理论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