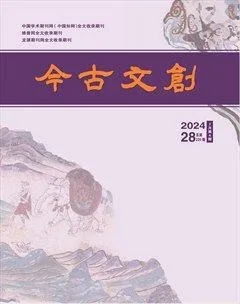“边缘书写‘边缘’”
2024-07-31敬琼尧
【摘要】随着20世纪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与机器的结合成为预见后人类时代的重要标志。在科幻文学中,人类主体被拆解、重构,形成赛博格、人工智能等人机交互的后人类模式。在此基础上,复杂的社会议题与科幻相结合的叙述形式,得到众多少数族裔等作家的青睐。作为非裔美国科幻作家,塞缪尔·R·德拉尼在其小说《巴别-17》与《新星》中,表达了后人类语境下对技术嵌入身体的反思以及对于身体与思维/信息阐释人类主体性的衡量。在此过程中,德拉尼以跨越阶层、种族、性别与技术的实践,探索拥有交叉身份经验的边缘群体实现自我解救的可能性,拓展中心之外的少数空间,丰富了科幻文学的表达范式。
【关键词】塞缪尔·R·德拉尼;《巴别-17》;《新星》;后人类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8-002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8.008
一、引言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诸多社会议题交错不清的美国历史背景之下,“去人类中心化”的后现代思考在哲学、文学、政治甚至技术层面等诸多领域得到大量的阐发。传统人文主义建构出的规则化、典范化的“人之标准”在此时开始受到了极大的质疑与挑战,有关“他者”和“少数”的差异性叙说在后人类理论探讨中逐渐形成一股无法被忽视的力量。
文学领域的“后人类”,自诞生开始,就既被主流的科幻叙事所需要,也成了他者们面对未来,叙事可行的重要叙写路径。这是由于在“科幻”独特的未来愿景中,原有人类各种“边缘”的固有关系在想象中有了被颠覆的可能。面对现实中边缘化的他者所面临的困境,作家们可以在赛博格的视域下,展开“何以为人”的后人类探讨。在赛博格空间中,技术层面对“人”之定义的流动性、混合性的范畴所做出的更大胆的尝试,也为“少数”们面向未来、寻求自我解放的可能性提供了逻辑自洽的理论基础,进而在“人”与“非人”的界限中抒发自身现实的边缘身份。无论是在《巴别-17》还是《新星》中,德拉尼都富有前瞻性地描绘了后人类生存形式的多重类型。单就其科幻作品中体现的仿生人、人工智能、虚拟人等意象而言,这两部作品可被视为德拉尼在面对六十年代末期,社会与政治运动中流行风潮的快速反应,将身体的赛博化置入复杂社会议题的讨论,边缘群体的经验在对未来的观照和展望中成功得到延存和叙写。
二、后人类身体的多重表达
对后人类语境的探讨,不仅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考,更是对人类身体观念、灵与肉二元思维的审视以及后人类主体边界的重建。在科幻语境中,对后人类生存问题及身体观念的关注促使科幻叙事与后人类美学联袂而行,也为探讨后人类时代身份认同问题呈现新的面向。[1]学者诺伯特·维纳在20世纪50年代所提出的控制论思想,将身体的界限观念引入人类的视野。身体的具身化与离身化表达继而成为探讨人类对技术/技术异化充满希冀或隐忧的重要形式。身体的界限是区分人与机器的重要维度,其中思维/信息作为人机交互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很难与主体分离,否则可能违背后人类主义与自由人本主义对认知的关注。
控制论即是赛博格的理论原型。德拉尼则在《巴别-17》中分别刻画了三种类型的赛博格形式,机械化身体、人形机器以及人机交互的人类。哈拉维认为,在通信科学和现代生物学的基础上,将世界编译为一种共同语言时,所有异质性都能被分解、重新组装、投资并交换。[2]凯瑟琳·海勒在其后人类理论论述中,从技术层面提出了电子机械与有机生命体的融合,如使用心脏起搏器、人造关节、药物注射系统等实现技术的治疗作用。[3]赛博格无疑超越了阿西莫夫所设计的“机器人三大定律”对机器人世界的伦理凝视,德拉尼在20世纪60年代赛博格的先声势潮中对于有机体和机械体的相互嵌合提供了具体的应用场景,因为在打破身心二元后,二者结合的不同目的、不同程度,都会对人类主体边界的重构带来不同的影响。
在小说《巴别-17》中,跟随瑞德探寻Babel-17真相的队员耳朵、眼睛、鼻子,作为人体器官从主体中分离并物化成人类得力的辅助机械。有机的物质器官在此成为信息模式的感知载体,对于未来的人类而言,这是允许存在的可靠形式之一,德拉尼在太空歌剧的图景中生动地描摹了未来人类借助机械能量超越肉体极限的可能性,人类完全进入了后人类阶段。
后人类的表现形式可以是技术进入身体的嵌合体;亦可是拥有超越人类计算能力的人工智能。其主体将身体建构为思想/信息,是物质-信息的独立实体,某种意义上是对自由人本主义的延续。那么,在后人类中的赛博格语境之下,承载思维/信息的肉身是否依然需要,抑或思维/信息与身体分离是否具备可能性,成为包括德拉尼在内的科幻作家们表达后人类思想时关注的重要议题。赛博格化的人类将会面临怎样的际遇?尽管生物器官超越了原本的生物学意义,但如同“机器人三大定律”中对“机器人”和“人类”关系的悲观隐喻一般,德拉尼在《巴别-17》中严格地将被机械化的肢体器官局限于人类的帮手范畴,是外在于人类的“技术辅助”,而并非人类与赛博格之下人之造物的相互塑造,因而也无法视为传统的“人”与动物在人类历史中互生的未来投射。
TW-55间谍是由维尔男爵运用基因编程、荷尔蒙激素催化等手段将婴儿在短短六个月内迅速培养成的十六岁的“人形机器”。维尔男爵向瑞德承认,“那个美丽的脑袋里没有任何东西,甚至类似于‘超我’”。[4]即使是在人机深度结合的全新“人”之生命体中,此时的德拉尼依然坚持思维/意识无法在赛博格化的生命系统中独立形成,即主体意识形态不能在人工的身体建构或成长过程中被剥夺、改写,否则重塑的身体只能被视为冰冷的机器而非能被赋权的赛博格人类。
而小说中的Babel-17身为未来技术之下诞生的控制论产物,能够解译任何语言系统,正如历史中的巴别塔一般具有合通性的效能。对于布彻而言,思维并未完全从身体中分离,而是被隐藏和限制在脑部的特定区域。正如海勒所言,赛博格的后人类主体作为各种异质成分的混合,能够持续不断地建构自己的边界。[5]布彻在语言系统置换之后,拥有了重新思考身份、经历以及个体价值的机会,成为区别于TW-55以及耳朵、眼睛、鼻子这类赛博格非人的关键,也呈现了德拉尼所理解的人与机器的边界,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在面对新兴的“赛博格”理论浪潮时,对技术之于人类的普遍焦虑。
《巴别塔-17》中,德拉尼已经通过技术路径,让人类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对自身赛博格化后的拓展性进行书写。而随着人造智能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在身体赛博化的未来中,机器终会进化为身体与思维进行交互的不可或缺的亲密组件。然而身体操控与替代是否会招致主体思维/信息的消失,形成对人类的威胁?技术并非只会与人类的“中心”与“标准”的本质对抗或融合,“边缘”与“少数”会与传统的“人之定义”一起迈向未来。那么,能够混淆“人”之界限的技术到底是后者“去中心化”的机遇,抑或是全人类的灾难,甚至最终会招致“人类世”的终结?德拉尼在《新星》中为这样的考量赋予了新的语境。
三、后人类身体的超越性
德拉尼反复强调人类的主体性是拟人化的元素所无法替代的,他也并非否定人机结合的稳定性,更旨在人机交互甚至共生的过程中坚持人类对技术的驾驭,继而有效规避技术异化的倾向。人机交互的确颠覆了传统生物学意义上人类的概念,在德拉尼的笔下也成了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未来生存模式。然而,相比子权中心的白人群体,小说《新星》中的混血角色可能更需要机体的植入获得健康以及力量,这并非试图改变其主体的思维或者性格,而是通过改造才能获得最基本的权利。如代号为“老鼠”的吉卜赛人角色声带的受损与他天生的神经一致性缺陷有关。这种神经一致性指在大脑底部存在一个类似人类模版的神经簇,其完整性与否直接影响控制身体的整个神经系统,他十分需要“机体”的植入获得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没有插座就意味着可以从事的工作不多。”[6]德拉尼在对于人类的赛博格想象中,让技术为人类赋能,进而为与机器进行完美交互后的人类赋予权力,如同现实中凌驾于少数与他者的特定性别、财富甚至种族元素等等。小说中的吉卜赛人作为身体没有插座的普通人类被视为异类,不断受到追捕、猎杀,驱逐出城市。艺术家卡廷对此向同为吉卜赛人的老鼠解释道:“因为人们愚蠢、狭隘,害怕任何与自己有所不同的东西。”[6]
直至德拉尼书写未来异星吉卜赛人跌宕的生存际遇,我们才能在“太空歌剧”与“赛博格”的重重包裹之下窥得其少数族裔身份的经验和现实观照。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现实,即便是轰轰烈烈的政治文化运动中,性别、肤色、口音、财富、受教育程度等差异依旧能够成为划分阶层或界定群体差异的完美借口,甚至形成了一种影响至今的反“政治正确”风潮。德拉尼将“赛博格”化视为一种利用想象超越现实以后,又影射残酷现实的白人特权,在文中更描述其为“虚假的星际互联”以及“缺乏文化传统的社会”,即是彼时美国现实中传统“人文主义”的“特权化”尚未崩塌、反而被赛博格强化的未来景象。
即便如此,对于身处赛博空间的《新星》少数群体而言,人机的深度交合依然是一次自我解救的契机。作为吉卜赛人的老鼠不得不适应普遍设定的生存模式,在18岁时终于获得了身体插座。这意味着他拥有了得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也避免面临与同胞相似的悲惨命运。小说的结尾,身为权力者的女性露比选择自杀,和作为少数族裔的老鼠获得神经插座的民族性“背叛”,让二者在面对技术革命后的赛博格权力话语结构所做出的截然不同的选择极具矛盾与张力,同时也为德拉尼在两部小说中既承启传统,又观照少数族裔未来的独特写作模式给出了叙事实证。
“少数群体”或许需要接受权力者的赋权模式,首先进入权力者的空间,这是德拉尼所秉持族裔自我解救的方式。德拉尼在小说中塑造诸多艺术家、罪犯,精神病患者等边缘身份角色的活动空间也就此成立。艺术家与罪犯有许多相似性,他们“共同推动了社会的改变”。[7]作为吉卜赛人的老鼠是一名音乐家,他通过使用一种特殊的乐器能够制造全息影像,为人们提供娱乐,也能以此作为武器。
就此,德拉尼在《新星》中为少数和边缘在赛博格的异星未来中赋予了如下的语境:优先拥有神经插座的“赛博格”特权人类是现实中白人至上主义的投射,他们依旧占据着通往未来的绝对优势,因为财富、话语、地位诸多特权的他们可以率先探索人机交合中后人类的发展方向。从这个角度来看,德拉尼并不乐观,因为32世纪的未来也可能是当下社会的如实复刻,但他也并未放弃愿景,因为唯一裂变可能性,也孕育在技术与后人类的超现实隐喻中。尽管老鼠被其族人视为“背叛者”,但在卡廷看来,老鼠是克拉克时代冲突后的产物,他是卡廷一直在寻找的“有历史意义与人性的主题”。老鼠精心保留了几个世纪以来的物品,具备平衡外部世界的概念与内部世界的知识的能力,即便新星在故事的结尾发生裂变,卡廷也坚信老鼠的存在能使其成为解决克拉克时代遗留问题的希望。被视为异类的吉卜赛人保留着最原始的生存方式,更有可能建构民族记忆与身份,进而保留整个华而不实的未来星际社会最为缺乏的边缘文化传统,甚至有能力颠覆未来的整个政治文化和权力系统。
哈拉维预测,赛博格将成为20世纪晚期人类的普遍表现形式。[8]无论是无机物的意识编码或是有机体的机械化,重新书写历史故事的重要契机已经出现。长期以来受困于各种少数身份范畴限制的他者们,在接受了与特权阶级相同的技术改造后,全新的生命形态下,原有的性别、年龄、阶级和种族关系存在被打破的可能性。老鼠也就此成了德拉尼在小说中最具典型的投射,因为此时的他与老鼠一般做出了最符合历史和现实的“妥协”。而《巴别-17》《新星》之后,在成名的德拉尼科幻实验的未来图景中,有色人种与白人将会彻底打破原有的绝对二元对立的极端,而技术/技术异化也绝非隔绝人类与非人类的单一阈限。
四、结论
作为德拉尼“赛博格”的先驱作品,《巴别-17》与《新星》是德拉尼在面对后人类等逐步风靡的技术性政治、文化语境之下,对于“少数”和“边缘”是否能够成为传统人文主义强有力的挑战所展现出的谨慎和顾虑。超能的科技力量与人的自然性状融合在彼时引发了德拉尼的不安,因为其既能够为少数族群提供自我解救的契机,也会在“技术异化”的普遍焦虑中加深“少数”和“边缘”既有的多重身份问题的矛盾。但毫无疑问的是,《巴别-17》和《新星》较显“传统”的实验性探索,让德拉尼坚定了利用科幻去描绘未来各种“乌托邦”和“恶托邦”场景的写作诉求,让少数群体的未来愿景可被触碰,也让他本人成了20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初期在各类语境和潮流中不可被忽视的非裔科幻文学作家之一。
参考文献:
[1]王宇坤.后人类语境与文艺理论新动向[J].南京社会科学,2022,(01):133.
[2]Haraway,D.“A Cyborg Manifesto:Science, Technology,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n Simians,Cyborgs 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C].Routledge,1991:164.
[3]凯瑟琳·海尔斯.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M].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52.
[4]Delany,Samuel R.Babel-17[M].Vintage,2002:84.
[5]凯瑟琳·海尔斯.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M].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5.
[6]Delany,Samuel R.Nova[M].Vintage,2002:91.
[7]Cornis-Pope,M.An Interview with Samuel Delany[J].Blackbird Archive,2003,(02):3.
[8]Haraway,D.“A Cyborg Manifesto:Science, Technology,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n Simians,Cyborgs 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C].Routledge,1991:149-150.
作者简介:
敬琼尧,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