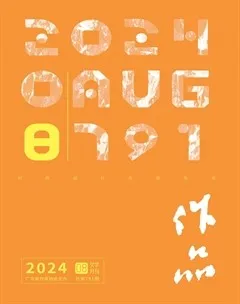重构全球化时代的青年主体(评论)
2024-07-31蔡岩峣
在全球资本主义或曰晚期资本主义的语境中,一切艺术品的生产,包括人类的日常生活,都被编码进了资本主义的数字系统,进行精密运算、快速传播和大量贩卖,世界在光滑且安静的光纤轨道上运行。这种幻梦,这种被资本主义所强加进人类主体的虚幻意识,是导致文学写作“同质化”的根本原因。不仅在经验,甚至在形式上,今天的文学写作也纷纷“同质化”了。而我们必须承认,是因为先有了一种总体性的,占绝对统制力的资本主义文化现实,才导致了文学的虚构被破坏。正如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所做的定义那样,是因为某种“主导性文化逻辑”或者“支配性价值规范”的观念,我们才能对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真正差异做出评估。但吊诡的是,现实的晚期资本主义发展却没有像詹姆逊所预言的那样,加速文学创作的“后现代化”,至少在中国文学的语境里,在“90后”作家的写作当中,这种情况没有普遍性发生。历史似乎朝着人类所不能预料的另一条小径曲折蜿蜒地前行。但詹姆逊给予我们的启示仍在于,我们已不能将小说视为内部肌质完满的自足体,而必须与现实的文化语境相结合,才能读解出其中真正的意义。
首先这种意义在最高的层面应该是一种“破坏”,“破坏”意味着创造,它应该深入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内部表达不满,揭示出这种逻辑的悖论性、不可能性和压迫的真实。其次是“补充”,以差异化和个性化的文学创造补充前辈大师们开创的艺术谱系,以具有创新性的典型人物形象,增补可能颠覆这一文化逻辑的革命性力量。最后的层面则是“反映”,在看似拥有完整叙事结构,也能调动读者情绪的一篇篇“故事”中,小说写作所表达的不过是对已经被压平的资本主义现实的认同,这种写作相较于机械现实主义的“反映论”其实并没有高明多少。马晓康最近发表在《作品》杂志的六篇小说,已经初步具备了上述文化分析的价值,这些小说多多少少地暴露了作者对现实文化逻辑的“不满”。即使在叙述语言和叙事技巧上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但能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介入全球化时代青年主体的建构这一写作主题中来,仍让我觉得十分意外和惊喜。
一、“新打工”经验与差异性
从题材和内容的角度来看,马晓康的这六篇小说可以被轻易地接续到“打工文学”与“留学生文学”的双重谱系进行观察。所谓的“打工文学”(以一种极不周延的定义),主要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描写中国南方省份青年迁徙入东部经济特区特别是深圳、东莞等地“打工”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不仅集中性地描写了特区经济崛起的过程,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内工人劳动的情况,也深刻摹写了当地“打工青年”们的精神现实。同时,这种文学以一种极富同情心和感染力的情感叙述,极大程度地发挥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力量。马晓康的《不要乱喊乱叫》《马歇尔顿抹刀》与《父亲的谎言》三篇小说,延续了以个人劳动书写为主要内容的题材传统,且这种尝试在今天的青年小说家群体中并不多见。与传统的“打工文学”相区别,马晓康将小说的场景安排在海外。这一尝试也至少体现出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直接的变化,即从以“70后”“80后”作家为主体的“打工文学”,到“90后”作家的写作,“打工”的内容已随作家的代际更迭发生了新的转换。二是从国内经济特区到海外发达国家,内容指涉的转移,也深刻表征着中国经济对全球化经济参与程度的日益加深。
这两种变化实际紧密地关联于21世纪“全球化”进程本身。所谓“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轮新的“帝国主义”的扩张,这是能够写出重要作品的文学方向。从马晓康发表的这几篇小说来看,他对于这一问题显然已经开始了自觉的认识和研究。他幸运地从本能出发进行写作,以身边的人和事及他自己的海外打工经历作为最直接的取材来源。但随后开始逐步地在思想层面,将海外“打工”经验上升为自身写作的问题意识。虽然对比我熟悉的一些国内“打工文学”作品,马晓康的小说还没有达到后者的现实复杂性、层次感,以及极高的生命情感熔铸与批判性,但客观地来看,作为一名青年写作者,马晓康已经展现出了极高的潜力。他的《不要乱喊乱叫》这篇小说,无论以何种方式衡量,都无疑是一篇杰作。这篇小说既揭示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劳资关系的紧张,又以“后殖民”的视角,透辟地写出了海外华人劳工群体与西方工人及华人群体内部复杂的情感关系。这种情感关系的实质是冷漠与同情的交织。同时,在这篇小说的结尾,马晓康又以同样具有强烈情感倾向的笔法,写出了“打工”过程中“手掌被钉子钻入”的伦理关切。这种“情感共同体意识”鲜明地体现出了作家的人道主义悲悯精神。
借用王逢振的观点,“全球化”的核心是“同一性”而非“差异性”。在以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资本为主要特点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中,自治的各国市场和生产区域被纳入了某种单一的范畴,民族国家的边界开始消失,世界各国被迫统一到一种新的全球劳动分工中。因此“全球化”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标准化现象,被迫进入到世界制度,且这种情况似乎不可逆转。但与王逢振的分析相对应,在看似标准化、同一性的“全球化”体系中,实则又蕴含着深刻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说是同一性的一体两面,在“同一性”抹平、覆盖、压抑了“差异性”的现实之后,正是文学将这种“差异”再次揭露出来。仍然以《不要乱喊乱叫》这篇小说为例,华人木工队领队老秋手下掌管着十几名“黑户”,其中既有马来西亚华裔也有大陆华人。而被老秋解救出来的工人小罗,曾在一个种族歧视非常严重的澳洲农场主那里打工,每周存下来的钱只有30刀,到了新工地以后,小罗被本地工人嘲笑,处境再度糟糕。小罗的这种身份、地位的尴尬与游移,正是上述全球化体系中“差异性”的鲜明表征。同理,在老秋手底下的马来西亚工人和大陆工人等,肯定也都存在着相似的区别困境。在“全球化”看似同一的生产体系里,文化、族裔、身份、语言等“非阶级”因素,同样制造着劳动关系内部的焦虑和紧张,而这些“紧张”是文学超越于社会科学所更擅长捕捉到的。
进一步辩证地看,马晓康作为深度参与了小说中劳动场景的“青年工人”,他的小说的真实性或还在于他并不以“压迫—反压迫”的单一结构组织小说里的人物关系。他笔下的“我”与当地的外国工人之间互骂“Panda”与“Donkey”。《爱吹牛的吉米》一篇中,寄宿的中国青年“宋润理”和“马晓康”甚至主动去帮一位外国老房东“追”女友。这种颠倒与混融消除着读者对“全球化”想象的某些常规、刻板印象。它以一种文学性的视角深入了“全球化”现实的内部。从这个角度说,与其称2010年前后提出的,以反映广东等地“打工”现象新变的文学为“新打工文学”,不如称这种在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内,中国工人的“海外劳动”为真正的“新打工文学”。因为据我所知,这样的作品其实还有不少。
二、脱域个体与青年主体
与马晓康小说相关的另一条文学谱系是“留学生文学”。同样以一种极不周延的定义,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留学生文学”主要指20世纪80、90年代,以描写海外青年留学生群体为主的一类作品。其中最有名的如小楂的小说《丛林下的冰河》、苏炜的散文集《远行人》等。200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专门出版了“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收集整理这一类作品。20世纪80年代的“留学生文学”主要的书写对象是留学生,到了90年代,由于“留学生文学”引发了中国读者对“异国风景”的热捧,又催生出了一系列如《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海外移民的奋斗传奇。到了90年代后期,大量对这种商战传奇、奋斗故事的粗劣模仿,渐渐解构了“留学生文学”这一概念的合法性。客观地来看,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早期的“留学生文学”顺应了中国“改革开放”开眼看世界的心态,“留学生文学”的作者与读者也都沉浸于一种中西方文化优劣对比的“新启蒙”心境。这一时期的中国读者对“异国风景”的热捧,多少可以看成是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在中国造成的心理“应激”。当时间来到21世纪,伴随越来越多的国人走出国门,加之互联网的普及,这种“应激”的症状也就相应地消失了。
不过问题最重要的地方不在于此,不在于上述心理“应激”症状的波动消替,而在于一种更为内部的文学心理机制,一种有关国家和个人主体“青年想象”的生成与消失。这种“青年想象”所依凭的主要对象,就是对“青年主体”的书写、塑造和“争夺”。作为最早走出国门的一批人,“留学生—青年”恰恰表征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对和接受外部世界的心态,也因此小楂笔下的主人公“我”的困惑,正是作为一个年轻的“改革开放”中国知识青年主体的困惑。“国家—知识青年(留学生)—个人”被同构进了同一个主体,“知识青年(留学生)”的人生道路选择,也极大程度地代表了国家面对“全球化”现实的应对,与中国青年发展的道路希冀。“知识青年(留学生)”在异国遭受的个人危机,同时对应于一个重新“开放”的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遭遇。自“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一直不断地通过塑造“青年主体”来表达理想主义的激情,并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这已经成为文学研究中的某种常识。但在中国深度裹挟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今天,我们如何面对新的话语场域与话语对象,塑造符合当下时代,并对青年读者具有感召力的主体形象,已经成为一个严肃且深刻的话题。
我的观点是应尽快摆脱“脱域个体”的重复书写,而努力给青年主体的塑造注入更多的能动力量。“脱域”的概念来自安东尼·吉登斯,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体制中,通过某种符号和共识的建立,人们可以轻易地认同并自由地传播信息。比如“货币”作为一种“象征标志”就是脱域的。货币虽然没有使用价值,但因为大家都认可它,它即能在社会的经济运行中扮演一般等价物角色。同理,“专家系统”作为一种社会认可的公共范畴,由它制定的规则、发出的行为也不必被所有人认可即能被普遍地接受。我以为,在今天作为一种文学表达的主要话语,“青年”这一概念也是脱域的。与“青年”相关的其他概念如“青年写作”“90后写作”“00后写作”等亦复如是。它们共同地塑造着一种关于“青年”的滥用和通约,把许多毫无相干的写作纷纷地等同起来。我把其中某些看似各有特色、各具经验的“脱域”青年个体,称之为一种“弥漫性虚无”的个体。它们虽然五光十色、五彩缤纷但却是脆弱、被动、景观化且易逝的主体。
仍以马晓康的这六篇小说为例,《我认识的郑义》这篇小说讲述了澳洲留学生群体中的“传奇”人物郑义,他如何以符号化的存在保护了华人留学生群体不被外国人欺负;《陌生人》一篇则讲述了海外留学生阿天、阿翔、艾米莉与“我”如何在酒吧从认识到搭讪再到打得火热的全过程,而最后“我”与阿天在第二天形同陌路。这些小说虽然也提供了作者的个人经验和“异国风景”,但我认为如果将故事的场景更换为中国的上海或山东,情况不会发生太大变化。这就是“脱域个体”的堆叠,是大量“青年写作”的故事化重复。而反观《不要乱喊乱叫》《父亲的谎言》这样的小说,其中的情节、人物却与现实环境紧密扣连,不能游移。因为只有在海外,只有身处于“后殖民”的语境中,“我”对小罗的关怀、斯考特对老杨的同情才能够成立。它无法在另外一个场景中轻易复现。人物主体的行动也就因此有了更加切实的力量。只有这样,马晓康笔下的“海外青年形象”才能不如它表面所呈现的那样,因为提供了某种异质性景观,而被偶然地嵌入当今与政治强烈关联的“全球化”叙事中。它能提供一种反观与对照,对今天中国的普通青年读者来说,它呈现着某种“域外”身份的建构经验。作为一种困难但新鲜、活泼、能动的青年主体建构,这种“海外青年形象”的书写也就能对当下中国文学经验的“混成”形塑提供更多的价值。
三、“劳动”作为一种精神动力
在给马晓康的这六篇小说写评论时,我再三提到了我对他小说中“劳动”经验的看重。我认为这种“劳动”经验能够给虚无主义盛行的当下青年写作提供某种精神动力。不妨再次回到詹姆逊,这位后现代理论家曾这样定义后现代主义“主体的灭亡”——不假外求、自信自足的资产阶级独立个体的终结。詹姆逊认为,“主体”曾作为古典资本主义和传统核心家庭的中心,具有统摄万事万物的力量。但在今天这样一个由后现代权力(官僚—技术—资本)宰制的时代,主体只能在全球性的经济网络和精神分裂中瓦解。这种瓦解给文学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情感的消逝”,即所谓“表现”“感觉”“感情”等的消逝。与之相伴的,还有作为现代主义核心批评概念的“时间”“记忆”“风格”等语词的终结。作者苦于无法写出感人的小说,读者也苦于难觅精神共鸣的文本。当大家集体性地埋首于自我主体的建构时,蓦然回首却发现,这些建构中的主体正日益地脱离他者,脱离社会,与外部的世界完全隔绝。因此我们不禁要问,今天的文学写作到底要求着什么样的小说?
有关“劳动”的书写,作为一种精神动力,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重要意义想必无须多言,而我今天所提的“劳动”,在根本的精神谱系上也回应着这一传统。它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当下“劳动”语境的调整。在《历史、革命与当代青年的思想构成》一文中,汪晖指出“劳动”这一概念在21世纪语境中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作为一种生产价值的行为,“劳动”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始终为劳动者提供着基本的尊严依据,因此,即便在20世纪现代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阶段,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也能够产生“劳工神圣”这样的口号。但当晚期资本主义兴起,进入21世纪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有相当一部分陷入了仅维持劳动再生产,而不再大量创造价值的窘境。也就是说,这一部分的劳动对于资本主义体系来说无关轻重,劳动者的尊严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抽空。无法满足劳动尊严感获得的青年主体,因此普遍地陷入一种溃败、虚无的精神状态中。汪晖的这一分析显然相当深刻,但当面对这一劳动价值“矮化”“虚无化”的现状时,我认为我们反而需要去写一种作为“真实”的劳动、作为“情感客体”的劳动。我们需要将劳动的过程“书写”为我们仍能与这个世界发生着切实联系的纽带。以我阅读的马晓康的第一篇小说,也是他获得“京师——牛津文学之星”金奖的小说《拉小提琴的砌砖工》为例,最吸引我的恰是吉龙、宋润理、“我”在澳籍教师斯考特的教导下砌砖的场景。他写到,我们把碎裂的墙体敲掉,重新插入钢筋,砌好后灌满混凝土,为了美观还调了白水泥抹墙面,墙面仿佛一层灰白色的砂纸,非常有复古感时,我为他对“劳动”经验的重视、坦白和无畏而内心感喟。
我认为“劳动”在此已不仅仅作为主观和客观之间的连接物,而只提供某种场景构成或经验填充的价值,它上升为了一种精神层面的“情感动力”。这种“情感动力”并不是凭空虚蹈的,它切实地关联着小说里每一个人物背后的现实需求和难言之隐。这些隐情的具体所指当然十分重要,但我更看重的是,马晓康经由“劳动”所表征的文学行动,为青年介入现实提供了一种切实的方法。在人的渺小与现实的蛮横之间,青年的这种真挚“劳动”使人的脆弱性、易折的弱点变得更加纯洁。学者何吉贤曾在《“热情”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情感动力》一文中以丁玲为例,探讨了“热情”如何既是推动个人投身文学,以情感性的叙事或抒情的文学形式表达自我,同时也是建构个人与社会、民族及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这种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他者之间的情感联结,被何吉贤称之为“热力的桥梁”。忽略此一论述的严密推理过程,我认为“劳动”作为一种“切实经验”,能够在虚无的生活和精神的迷雾中重新唤起“热情”,这种情感动力机制使得作家和读者再次在文学的写作与阅读中,获得使命感和尊严。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会矮化和排斥晚期资本主义体系中“劳动”异变后的多种情形,比如我并不会否认大城市里格子间处理电子文档的白领相比砌砖工来说就不是劳动。他们的劳动当然在某种层面上是等价的。我只是说,我更提倡将这种劳动的书写“按”入现实之内,即写出青年主体与现实生活之间活生生的碰撞。在马晓康这里,他巧妙地利用了“身体”作为媒介,这很好地抓握住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痛点。《不要乱喊乱叫》中,当小罗的身体被钉进厕所夹板,手掌被铁钉狠狠钉穿时,小说家无疑构造了一个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讽喻。惯于乱喊乱叫的中国人这一次最终没有喊出来,但在他的“身体”之内已经蕴含了一场新的斗争的可能。意大利哲学家埃斯波西托在《人与物》这本书中做了对“身体”这一概念的精彩的分析,他借用西蒙娜·薇依的观点说明,人的身体中“神圣之处”远非它属于人格的部分,而是它非人格的部分,即身体不属于“物”,当然也不属于“人”,身体是一处现实斗争的场域。我非常认同埃斯波西托的看法,我以为从“身体”出发的写作,可以再次警醒和呈现“劳动”这一行为的神圣性。作为一种精神动力的“劳动”在作家笔下也完全不用是封闭的,它能将更多的内容和对象包罗进来。比如我们就曾听到过这样的新闻,在中东某土豪城市,来自全球欠发达地区的劳工因超时、过量的工作而热死,他们的生命可以同样被归入这一情感召唤机制。文学的书写永远在特殊中提炼一般,发生在中国公民小罗身上的故事,也无疑是全球性的现实。
责编:郑小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