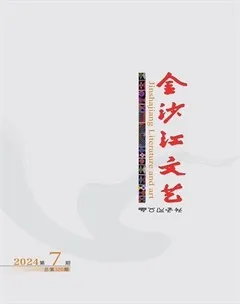华竹,华竹
2024-07-22文芳聪
四周是绵延不绝的山冈,中间是一马平川的平坝,一条河在坝子里流淌,这就是元谋开发最早的坝子——华竹坝。千余年前,这个地方是一个傣族部落的领地。华竹是傣语,意为“高高盘起的发髻”,代指傣族人居住的地方。
元谋开始成为傣族定居的地方,远可到唐代寻其踪迹。在唐王朝支持下逐渐壮大的南诏到天宝末年走完了蜜月期,双方在唐玄宗天宝九年至十三年有三次较大的战斗,史称“天宝之战”,南诏取得胜利,并乘胜北进,于唐肃宗李亨至德元年(756年)占领金沙江北岸的巂州,即以现在西昌邛海为中心的凉山地区,并一直打过大渡河,兵锋直指成都,抢掠“子女玉帛,百里塞道”而还。之后,还有多次争战,各有胜负,直到双方腐朽到无力再战,南诏于902年被大长和取代,唐朝在907年被后梁所灭,中原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傣族先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元谋的。当时的银生百夷人落受南诏统属,被征调到巂州参加征战。随南诏大军北征获胜而还,傣族官兵退出凉山地区,退过金沙江,落籍元谋。这里坝子平坦,河流交汇,气候炎热,符合他们的生活习惯,但是那时叫作毋血水的龙川江两岸还不适合人类居住,他们选择了龙川江支流上更小更便于驾驭的坝子作为族人的生活繁衍之地,这就是华竹坝。他们在这个坝子里聚族而居,在这里静静地生活着、发展着,逐渐强大起来,到南诏被灭后,华竹部已经成为对周边有一定号召力的部落了。
南诏灭国之后到大理国立国之前这一小段时期,洱海地区的上层建筑动荡不已。阅读这段历史,常使人掩卷叹息,偏居云南的地方政权开始走马灯,先是南诏清平官郑买嗣废南诏哀帝舜化贞建立大长和国,历三世二十六年到郑隆。继之剑川节度使杨干贞废掉郑隆,推举赵善政即位,建立大天兴国。十个月后,杨干贞废赵善政自立,建立大义宁国。两年后,杨干贞被其弟杨诏灭掉,改元“大明”,杨诏又被通海段思平所灭。这是一个政局动荡的年代,三十七部就是在政局动荡中走进历史的。
杨诏在位七年后,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联合包括华竹部在内的东方三十七部武装力量西进,灭大义宁国,建立大理国,这是大理国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后,三十七部因为有功而得到优待。华竹部是三十七部之一,而且是地理位置上比较靠近洱海核心区的一个部落。
971年,大理国第五代王段素顺命令宰相段子标和驸马段彦贞等于年初率兵东征,平定叛乱。平叛大军从大理出发,沿着通海城路,一直打到现今的文山州富宁县延众镇,剪除了反叛势力,又回师拓东城,西向讨平了求州等地的武定、元谋、禄劝三邑,接着又讨伐了今云南富源、贵州盘州市的反叛,最后聚集石城(今曲靖城北)。段子标、段彦贞等大理国东征将领在这里与三十七部部落首领刻碑“共约盟誓,务存久长”。
广哀是第一个见于史料的华竹部首领名字:“元谋吾氏始祖景东百夷人,南诏赞普钟六年(757年)奉调北征巂州,后留驻元谋,为部落酋长,九传至广哀”。1254年,忽必烈大军接连破袭大理城、拓东城,大理国末代国王段兴智投降,华竹部首领广哀随后在金马山归附,与云南其他地区一起并入大蒙古国版图。此时元朝尚未建立。到元代至元十六年(1279年)华竹部正式改为元谋县,属武定路和曲州管辖。华竹部部酋广哀回元谋招抚本地夷民恢复生产,动荡的元谋逐步稳定下来,广哀由部酋转而成为元谋县土知县,开启土司制度。
明代,元谋吾氏土司仍是县一级土司,在《滇考》中有确凿记载。《滇考》中把明代云南土司按官阶分为四类二十五家,即知府级别十家、同知级别两家、知州级别十家、知县级别三家。元谋吾氏土司是县一级的土司,等级低,列末位,但毕竟是元明两代统治元谋的土司,不可忽视。
元谋流官首任知县是张元礼,他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到任,一年后病故,之后到弘治七年(1494年)才再次设置流官,百余年间,再无流官到元谋当知县。广哀的后代阿吾,曾在张元礼之前担任元谋土知县,张元礼病故后,他亲赴南京朝觐。这次远途跋涉,沿途的所见所闻和恢宏的明廷大殿,阿吾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无异于一次彻头彻尾的洗脑,这正是明廷所需要的。朝廷见目的已经达到,于是嘉其忠勇,授土知县。就在阿吾回云南的当月,西平候黔国公沐英奉钦旨在昆明为阿吾举行了土官“授职典礼”。土司机构设置为:更资三人,各领从征,听从土司调遣,唯土司之命是从;曲觉三人,分管地方;遮古三人,管理田庄;扯墨一人,统领站班快手;管家十二人,管理租谷徭役。土兵非常设,数目不恒定,不计在内。阿吾之后,他的后代就以“吾”姓为部落首领的家族姓氏开始有序传承。
在靖难之役后,明成祖在边疆民族地区委派流官是明廷改革基层政权的手段之一。当时武定府的和曲、禄劝二州都改设了流官,而在武定管辖之下的元谋县依然实行土官,由阿吾之子吾忠袭位。明代宣德元年(1426年),吾忠去世,他的儿子吾政向登基继位的新皇帝朱瞻基新朝廷贡马,明廷准许他承袭土职。正统八年(1443年),吾起在总督尚书处袭父职。吾起任内在县西一里处建桥以利通行也利于盘诘行人。这件事,《华竹新编》是这样记载的,“其关梁有七。曰望城关,在茶房山东,距县城25里;曰大板桥,在县西一里,土县丞吾起建,后废”这是元谋第一个有名有姓修建的关梁哨卡,距今约600年了。天顺二年(1458年),吾起因病亡故,他的弟弟吾超向朝廷贡马,得奉圣旨,准袭他接任土知县。成化三年(1467年),不是吾超嫡子的吾隆依令披冠带袭。他死以后,于弘治七年(1494年)元谋设流官一员,吾隆的儿子吾大用因此未得袭元谋土知县。七年之后的弘治十四年(1501年),云南抚司又请旨准吾大用承袭其父辈的土官职,但不可以世袭。元谋从这一年开始又实行“土流同置”。二十七年之后的嘉靖六年(1527年),云南发生变故给吾大用的子孙承袭元谋土职提供机遇,而吾大用也确实抓住了这个机遇。原来,这一年寻甸土司安铨、武定土司凤朝文反叛朝廷,斩杀官吏,夺取知府印信,攻围省城昆明。吾大用得令率本地土兵协助朝廷征剿,奋勇平叛获得军功,授职土巡捕,这是他第二次被授职土巡捕。嘉靖九年(1530年),吾大用的儿子吾至先奉钦旨承袭父职,兼理元谋全县事务,再次打破了“不得世袭”的禁令。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流官知县于文蔚打算修建县城,选址在元阳河边的河坝街(今元谋县老城乡政府所在地),一年时间建成土城,可以想象那个一年建成的土城是何等的简陋。二十年后的天启二年(1622年),元谋知县齐以政才把土城改建为砖城,县城城墙总围长一里三分,设四道城门,分别是东面午茶门,西面回龙门,南面丙弄门,北面住雄门,元谋这时有了较成规模的县城。这次筑城在《华竹新编》有记载:“历稽县治三迁而始定丙弄山下,阅三纪而议城,时万历三十一年也”。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武定土司凤朝文的儿子阿克约反叛,攻陷武定、禄劝、元谋等一府三州四县,进而进兵昆明,省城震撼,吾至先的儿子吾孟才再次率元谋土兵与协同官军作战,战争结束后恢复县治。吾孟才后,他儿子吾道南仍然承袭元谋土巡捕。到吾道南的儿子的时候境况更差,因为改设流官力度加大,吾道南的儿子吾必奎袭位时被降为元谋土舍。在元谋改土归流中处置不当,迫使在镇压叛乱中获得军功的吾必奎却走上了反叛的道路,令人唏嘘。吾必奎兵败奔走江外,被斩杀于会川,即今天的会理城内。吾氏家族成员和傣族部族有的不甘屈辱而流落江外,有的改名换姓隐忍于当地,此后,由银生百夷人(景东傣族)演化而来的元谋傣族在元谋土地上消失得干干净净,像被大风吹走一样,只为元谋留下千余个以傣语命名的村落,这恐怕是那些曾经移居此地的银生先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其实,吾必奎才干出众很有威望。在明末清初,吾必奎受云南巡抚沈敬炌、闵洪学调遣,先后率领元谋土司兵参与镇压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叛乱、贵州水西土酋安邦彦叛乱和云南沾益土知州安绍庆、安效良叛乱的镇压,兵锋所及川南和大半个云南,并屡屡取得胜利,保一方平安,在云南历史舞台上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云南巡抚闵洪学当年把吾必奎的战绩上报熹宗朱由校,授吾必奎坐营都司加游击将军衔,这是从三品的武将官衔,是吾氏有史料记录以来获得的最高官阶。
在元谋,留下很多与吾必奎有关的民间故事,其中一个叫“九围大树”的故事被赋予神话色彩,流传甚广,妇孺皆知。
话说吾必奎被剥夺官职赋闲在家,看着衙所外那棵九个人才能合抱的大攀枝花树耸入云霄,心里隐隐有某种想法。这天夜里,吾必奎睡梦中梦见一位高人,这位高人告诉他“明将亡,彼可取而代之”,并传授他点豆成兵之术,说可以作举事之用。吾必奎醒来,连忙吩咐随从,撮芝麻绿豆无数,到僻静处播撒,并用茅草覆盖得严严实实,再洒上神符水,盼望着七天之后能见到奇效。到第六天,举事心切的吾必奎,来到播撒芝麻绿豆处,见不到有什么变化,心想七天期限,到第六天还没有什么动静,怕是不灵验,思来想去,不如干脆翻开茅草看看,翻开茅草一看,只见芝麻、绿豆将都已变成数十万兵,列为战阵,提枪挎刀,但是时间不到,都软弱无力。覆盖的茅草被翻开,这些奇兵异马经太阳一晒,看着看着就枯萎死去了。吾必奎见天机已经泄露,万分懊恼。忧心忡忡的吾必奎,抬眼看看衙所外那棵的九围粗的大树,便爬上大树。说来凑巧,吾必奎爬上大树朝京城一望,正好望见皇帝刚刚起床,正要洗脸。吾必奎一见大喜,连忙拈弓搭箭,瞄准皇帝的头部就是一箭,翎箭向着皇帝飞去,就在箭头离皇帝的脑袋只有一尺远的时候,皇帝一下子弯腰洗脸,“铮”的一声,翎箭射在皇帝前面的玉屏上,箭镞没入玉屏有几寸深,吓得皇帝半晌才回过神来,忙令朝臣查看翎箭,只见箭杆上刻有“吾必奎”三个小字。吾必奎是谁?有大臣回答说是云南元谋的一个土舍。皇帝又令人取出宝镜来对着翎箭飞来的方向一照,发现有棵大树上有个人在向京城窥望,急忙叫人画下像来,随即派兵进剿。围剿官兵来到元谋,砍倒了那棵九围粗的大树,吾必奎无所依靠,他的土兵四处奔逃,不久就被抓住斩首。不料斩首之后的吾必奎倒地之后竟然连头带身遁土而去。官军大惊,忙用草木灰划圈圈住,掘地三尺,又挖出了吾必奎。这一次官军抓住吾必奎后就不让他落地,怕他又遁土而去。不着地的吾必奎就再也不能起死回生了,但是这棵被砍倒的大树当年又发了芽,几年后长有六围粗,算是起死回生了。外地人来到这里,当地人都会指着这棵“六围大树”说,这是“九围大树”的后代。这就是流传在元谋民间的“九围大树”的传说。传说里的“九围大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存在过,但六围大树确实存在,徐霞客在元谋游历时记载:“官庄之北,十里为环州驿,又十里为海闹村,滨溪东岸,即活佛所生处,离寺二十五里。其村有木棉树,大合五六抱。县境木棉树最多,此更为大”。木棉树,元谋本地人称为攀枝花树,海闹村现在的牛街村。元谋坝子攀枝花大树很多,有趣的是好多村子都说“九围大树”的故事发生在自己的村子里。
这是在我老家元谋广为流传的传奇故事,小时候听过无数遍,版本不同,情节却差不多。传奇归传奇,吾必奎是确实存在着的历史人物,在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楚雄人物》一书里,吾必奎位列“楚雄古代人物传”第六位。
元谋历史进入清代,受吾必奎事件牵累,世居于此的华竹人大多亡命江外,大量汉族人涌入元谋,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与当地人融合,共同繁荣发展。康熙元谋知县翁咏榴在他的《元阳赋》里就生动地记录了当时的元谋移民景象:“土成沃壤,人富于财,诗书式榖,风气顿开,荆湘之民间至,九江之众频来”。当时的文人墨客对元谋也称赞有加:“马街为两省通途,每逢街期,百货云集,上达郡城省会,下抵江外巴巫,商多三姚楚景,客尽江右湘湖,所谓滇南都会也。故当时有金马街、银元谋之谣。”其结果必然是留在元谋坝子傣族人改名换姓,逐步汉化,那些傣语地名一直叫到现在。
今天再到华竹,镶嵌在枯黄的群山中的华竹坝子依然碧绿,只是当年莽莽甘蔗林已经全部改种冬早蔬菜,销往全国各地。问及华竹往事,当地人还知晓一些,那是口耳相传的结果,但已经相当模糊。问及华竹坝是否还有傣族,回答说一个都没有了。至于历史的遗物,有帕地村幸存的大钟一口。
责任编辑:李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