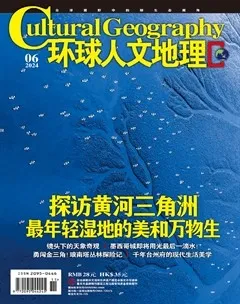那年那月桂花饭
2024-07-21龚学敏
能够把蛋炒饭叫做桂花饭的地方,想必生活里是有一种诗意侍候着,还透着能够对万事万物命名的自信。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有人把蛋炒饭叫做桂花饭了。想想也是,现在的人,凡事就讲直接,讲经济,讲成份。蛋炒饭三字既说了成分,又讲了制作过程,完全是一份简单明了的食物构成说明书。除了像我这样闲得无事的人,似乎已经没人在乎把蛋炒饭叫不叫做桂花饭了。
其实,桂花饭不仅仅是一种对待剩饭的态度,还是人类模仿自然的一种能力,更是把自己融入自然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普遍反映在中国人对餐饮的做法,甚至命名上。可以说,已经成为人类在农耕时期的文化遗产。我们越来越快地走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过去的这种能力也正在减弱。
蛋炒饭有史可查,应该是20世纪70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竹简上有关“卵熇”的记载。专家考证,卵熇是一种用黏米饭加鸡蛋制成的食品。熇字本义为炎势猛烈,这与蛋炒饭的做法倒是相符。又有说法,熇是用微火把汤汁煨干的一种烹饪方法,这似乎与蛋炒饭的炒不符了。专家们怎么讲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像我一样从农村考出来的学生,高考是件关乎命运的大事,自然会记得不少的细节。我参加高考的第一天早上,母亲给我做的就是桂花饭。记得米饭是头天晚上煮饭时特意多抓了一把米剩下的。那个时候,关于早饭的概念,在我们家里,日常是玉米面煮的拌面饭,大米煮的稀饭已是稀罕之物了,再朝大米稀饭往上,真不知道早饭该是什么做的,已经严重超出想象了。所以,高考时吃一碗桂花饭,已是全家人能够想象出的最好的早饭了。并且,能够保证一上午的考试不会因肚子饿而影响成绩。吃完一碗桂花饭,怕关键时候口渴,就用那碗,倒满满一碗的白开水喝下去。
1981年的高考,对一个农村户口的家庭而言,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眼睛高度近视的我,能不能跳出农门,会不会戴着厚厚的眼镜下地去干农活。桂花饭是用家里中等大小的碗盛的,冒了尖。吃完饭后的碗,一粒米都没剩,一丝蛋也没有,干净的碗里只有些零星的油珠,说是油珠,其实,已不能用珠来形容,只是挂在碗壁上的油迹而已。这些油迹比平时的油黄些,想必是蛋黄的缘由。把开水倒进刚吃完饭的碗里,一涮,水面上便是油星。等着凉一些时候,嘴里的饭也嚼着嚼着,咽下去了。这时的水温刚好。一大口温温的水喝进口来,整个口腔像是吃完饭的碗,被这一大口水一涮,把口中的油又搅动起来,在舌头上乱撞出一些不一样的香来。然后,嘴一闭,猛地咽下去。这水也不敢乱喝的。不喝,有油,有盐,又是鸡蛋,又是干饭,肯定要口渴。喝了,又怕到时候要撒尿,浪费时间,耽误天底下最最重要的考试。这纠结,也像是一道颇为复杂的数学题,用现在的词,纠结呀。
现在细想起来,高考时的桂花饭应该是我吃的最后用桂花来形容的蛋炒饭了。因为那个让我第一次知道蛋炒饭有这么一个诗意的名字的人,我的奶奶,就在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几天就走了。从那以后,再没有人给我说这个诗意的名字了。直到世事把我也变俗,只是偶尔地想起,偶尔地心酸一下。我知道,这是我内心深处尚存的一点点未泯。
小时候的县城,究竟哪里有桂花树,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见过,嗅过,确实香。应该是过去的大户人家留下来的,一般的人,哪有闲心种这种树。我依稀有印象的,小时候,家里靠围墙的地方有棵歪来歪去的石榴树。那时候,有院子,或者房前屋后有空地的,种石榴的居多。九寨沟的风景出名之前,在外传播力最强的,便是那首闻名于世的南坪小调《采花》。里面就有“八月间闻着桂哟花香”的唱词。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又听到南坪民歌《盼红军》,调子是老式的,词变了,不是每月都写有。比如八月就没了,从七月的“七月里谷米黄哟金金,造好了米酒等哟红军”直接跳到了九月,“九月里菊花艳哟在怀,红军来了给哟他戴”。想是后来作词的人没有办法把红军的期盼放在与月份有关那一句中,只好再起一句,这样一来,歌词太长,与曲不配,只好少了些月份。知道桂花酒,则是因为毛泽东的诗词有“吴刚捧出桂花酒”。父亲爱喝酒,改革开放后,条件好了些,家中便多了些乱七八糟的酒瓶子。有一个叫做桂花酒的瓷瓶,印象极深,画有吴刚,之所以印象深可能与我小时候喜欢读各类神话书有关。直到有一天,奶奶说要炒个桂花饭,我才把诗里的桂花和能吃的饭放在一块想了。
米饭须是沥米饭。把米倒进水已经沸了的锅里,煮过心,用瓢舀进竹编的筲箕,滤出米汤,然后,又把煮过心的米倒进锅里蒸,直到水慢慢地干了,米香出来,饭就熟了。这样煮的饭,米是一粒粒的散着。小时候,大家都吃完了,就等你一个人吃完后才洗碗时,大人就会骂,你在数米吗?这个数米就是指这样煮出来的饭,是可以一粒粒地数。当天的米饭还是有些软,放一夜,弹性刚好。本是稀罕的吃食,有一碗在灶房里就那样放着,都会让人惦记出不一样的香味的,何况用油、用蛋来炒。锅要大,现在城里人小厨房里的锅完全炒不出桂花状来。先把蛋打在一个碗里,放点盐,使劲地搅拌,直到有些蓬松的感觉。蛋先下锅,再把米饭倒进去混在一起炒,这是技术活了。柴火适中,慢慢地弱下去,让油、米、蛋充分地融合。蛋的黄裹在白的米粒上,整个米粒像是一颗颗的桂花。最后,一把切细的葱花撒进锅,一翻,原本的香,再加上这葱香一起来,便起锅了。
说到底,桂花饭就是蛋炒饭,只是有文化的食客们衣食无忧时的遐想而已。历朝历代,中国文人只要吃饱了,总会弄一些这样的词,以示高雅。最甚者,莫过于顶级食客晋惠帝。百姓闹饥荒,无粟米可食,竞相争食草根,树皮。大臣禀报,竟不解地问,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这还是饥馑年代,但凡日子好过一点,兜里有了几个闲钱,便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是登峰造极。衣食不说,就连对烟、酒,茶这类的副食,嗜好的讲究也到了莫名其妙的奢侈地步。就说香烟,作为舶来品的香烟,为了显出其优劣,先从烟叶的产地开始。一是津巴布韦产全世界最好的。二是每匹叶子选中间那部分用来做价格最贵的香烟。三是近年在过滤嘴中配爆珠,珠中有少许名酒,用酒香佐香烟。我曾不止一次对身边的烟友讲过,香型相同的烟,不管价格高低,混在一起,关上灯抽,谁也不能准确分出贵贱。酒和茶同理。这一点,终还是虚荣心害人。
现在炒饭的江湖已被扬州炒饭一统天下,乱七八糟地配些鸡腿肉、火腿肉、干贝、虾仁、鲜笋丁、青豌豆、鸡蛋、葱花等。这扬州炒饭本该是把扬州显得比其他地方富庶的,可效果不好,像个本是貌美的女子,一通胭脂粉,反倒描花了,俗气得很。
直到写这篇文章时,我才向身边的好吃嘴问起桂花饭的说法,朋友告诉我,川西坝子这一块过去也把蛋炒饭叫桂花饭的,再远的地方也有的。九寨沟过去少有水稻,吃米已是奢侈,这名字多半是从富庶的四川内地传去的了。
爷爷是内地人,桂花饭定是他说给奶奶的。然后,到了我这儿。我就不知道它还会流传多久了,因为,人和事已经变得太快了,由不得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