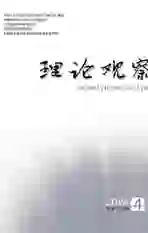网络短视频数字拜物教的表现形式、生成机理及治理路径
2024-07-18蹇俊王贝
摘 要:随着移动互联网络技术的普及和易用性不断提升,网络短视频逐渐替代传统主流媒体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然而,正是由于网络短视频传播媒介的受众广泛性,我们需要关注其中所存在的数字拜物教隐忧。研究发现,网络短视频数字拜物教具有“颠倒性”的表象,即算法崇拜导致的人与数字关系的颠倒,流量崇拜导致的工具与价值关系的颠倒以及信息盲从导致的主观与客观关系的颠倒。究其根源,颠倒表象有其“异化”的内在逻辑,即网络短视频场域中的生产活动的异化,消费行为的异化和意识形态的异化。针对网络短视频数字拜物教的表象及其成因,从长效监管机制,媒介素养教育和全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方面提出治理路径,以此推动网络短视频数字拜物教的“扬弃”进程。
关键词:网络短视频;数字拜物教;意识形态;异化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04 — 0049 — 05
一、问题提出
何为数字拜物教?从“万物皆数”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始,“数”作为一种描述自然、代替自然,乃至成为一种新的自然的隐形规训,逐渐在人类的思想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在人类文明历史的宏观维度上推动了人类理性认知的巨大发展,但是在社会实践过程的微观视角下,数字以及由数字构建的虚拟世界却逐渐成为一种理性认知的壁垒,并且这种虚幻的数字王国披上了一件类似于宗教的神秘外衣,尤其是在数字拜物教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代。徐艳如认为,数字拜物教不仅仅是指人们对于数字符号的主观崇拜,数字拜物教的本质在于人们对于数字符号背后的经济利益以及这种经济利益所蕴含的社会权力的崇拜[1]。吴媚霞、王岩认为,数字拜物教是人们对于数字信息、数字商品和数字资本的崇拜,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主体性逐渐被消解,人们慢慢在虚假的自由和隐匿的奴役中迷失[2]。王维平、汪钊认为,数字技术与资本的资本化应用是数字拜物教产生的前提,而数字霸权则为数字拜物教开辟了空间,数字拜物教就是数字资本拜物教,其典型特点是抽象物对人的统治和支配[3]。网络短视频的数字拜物教问题就是数字拜物教现象在网络短视频这一特定场域中的具体展开。
时至今日,“数字物神”正通过网络短视频的形式降临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在算法和商品编织的世界中逐渐丧失主体性的自觉,进而沦落为自愿服务于资本逻辑的工具人。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10.5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4.4%,其中网络短视频用户规模增长尤为明显,相比于2021年12月增长了2805万,总数达到了9.62亿,占网民整体规模的91.5%[4]。网络短视频受众的广泛性及其数字拜物教的虚幻性使得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批判撕碎锁链上那些虚幻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5]
二、网络短视频数字拜物教的表现形式
“拜物教”一词,最初由马克思用来形容人们对商品、货币、资本等“物神”的盲目崇拜。然而,在数字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数字物神”的普遍性和影响力使得这一比喻的现实性更加强烈,尤其是在网络短视频构建的“数字教会”中,颠倒世界的现象展现得十分突出。如果将网络短视频平台比作主教,那么醉心于流量的视频创作者就扮演着传教士的角色,而沉醉于虚拟世界的用户群体则成为最虔诚的信徒,“数字物神”便是三者顶礼膜拜的共同“信仰”。
(一)网络短视频平台方的算法崇拜:人与数字的颠倒
网络短视频作为一种数字化时代的新型媒介,其核心竞争力源自平台资源的有效整合与精准投送。要确保这一核心竞争力的可持续性,智能推荐算法便成了平台方所依靠的关键技术。但这些算法在方便平台运营的同时,也使人产生了对网络短视频的依赖性以至成为网络短视频平台的附庸。
一是智能推荐算法导致的依赖性问题。相比于传统的搜索引擎需要用户主动搜索才能获得信息反馈而言,网络短视频平台的智能推荐算法更加具有主动性,因为算法能够通过已有的特征库对用户需求进行预测和引导,用户可以最低成本地获取信息。此外,相比于传统纸质媒介,短视频可以通过更为直观的音像视频的形式在解读理解信息上为用户提供了巨大的便利。这些来自媒介的便利在方便人们的同时也在消解人们的主动获取信息、自主思考问题的能力,使得人们对其产生依赖。二是智能推荐算法导致的人的主体性的消解。算法推荐的无微不至不仅仅是让人离不开它,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机器算法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僭越。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关于主奴辩证法的论述那样,看似自由的主人在依靠奴隶劳动过活的过程中因不参与劳动而逐渐丧失主体性,奴隶却因为参与劳动实践而获得了主体性的确证,最终主人反而成为奴隶的附庸[6]。网络短视频场域中的用户与算法的关系未尝不是这种“主奴关系”的当代演绎。从算法辅助决策走向算法代替决策,从算法描述世界走向算法就是世界。一种技术在社会中应用越是广泛、越是具有基础性,其主体性就越强。因此,算法的主体性越强,人的主体性就越弱,而每一个社会成员主体性的消解将会成为社会整体愚昧的起点[7]。算法对于人的主体性的瓦解使得人与数字的颠倒成为现实。在网络短视频平台方看来,现实的具体的人成为抽象的同质化的数字符号。人的丰富性和多元性被数字符号掩盖,人成为平台获取流量的机械性工具。
对于智能算法的崇拜,使得人们沉醉于网络短视频构建的虚幻数字世界中。从满足消遣娱乐的起点走向一种难以抗拒的依赖,再到人的主体性的退让,这种数字化的媒介形式逐渐进化成了人的“社会器官”,最终导致人与数字关系的颠倒。
(二)网络短视频创作者的流量崇拜:工具与价值的颠倒
网络短视频的创作本应以真善美为价值取向,但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流量崇拜的广泛存在使得网络短视频的内容将美好的价值追求工具化,反而将本应服务于价值分享的流量目的化。
无论是普通的短视频生产者还是专业的短视频生产者,在平台分发、审核和激励机制的操控下,以及经济利益的诱导下,都不约而同地将更多的流量作为了自己作品创作的出发点。这一现象主要表现为两大典型的特征。一方面,价值沦为工具的附庸。为了最大可能获取流量,积累经济时代的数字筹码,进而瓜分更多的经济利益,短视频生产者总会利用富有伦理冲击性的热点事件进行迎合大众心理的主观解读,例如按照剧本拍摄的社会事件,捏造的小道消息等等。这些短视频的生产目的并不在于向公众展示客观事实、传达真善美的价值观,而是要利用公众对于真善美的朴素情感来攫取流量,获得利益。另一方面,工具成为价值的主人。一个短视频作品想要表达什么价值观,并不取决于创作者的主观能动性的自由抉择,而是看流量推崇什么,本应作为工具的流量反而获得了一种超越创作者主体性的自主性,这样的现象与马尔库赛所批判的技术理性对于价值理性的瓦解的情形具有一致性。
从短视频生产以流量为目的开始,工具与价值的颠倒就发生了。这种手段与目的的冲突消解的不仅仅是某个网络短视频平台企业的初心和理念,更是对广大网络短视频参与者主体性的瓦解,单向度的人便由此诞生。
(三)网络短视频消费者的信息盲从:主观与客观的颠倒
网络短视频是数字技术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媒介,但由于智能推荐算法对于目标用户的精准推荐,导致人们看到的大多数信息只是人们自己愿意或者喜欢看到的内容,使人们陷入了个性推荐算法编制的信息囚笼。世界著名媒体文化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指出,语言即媒介,媒介即隐喻,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内容[8]。网络短视频以其独特的媒介特点,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造着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其碎片化的,快捷简便的信息传播方式使得人们不得不处于注意力从集中到分散的循环之中,人们深度思考,理性思辨的能力在网络短视频的媒介环境中被消磨殆尽。
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有赖于认识过程在实践中的辩证发展和螺旋式上升。而在网络短视频环境中,人类的认识却被简单直接的感官刺激所束缚,人们需要对于指尖划过的每一个内容做出及时的反应,这样的多任务模式使人的注意力难以集中,长此以往人们从感性向理性飞跃的道路中又多了一层数字栅栏。人们在陶醉于网络短视频带来的快感中,将自己的认知托付于短视频内容,但是没有建立起阻止、隔绝的心理机制。网络短视频基于社交、喜好的推荐不断强化着人们小圈子的回声室效应,这种信息的窄化使人更加难以区分主观与客观。
网络短视频数字拜物教的“颠倒性”在人们认识层面主要表现为主观与客观的颠倒。长期习惯于通过短视频的形式观察世界的人们在感官刺激的娱乐中逐渐丧失了理性思考的习惯。因此,快餐式文化消费使得主观对于客观的僭越成为一种现实。
三、网络短视频数字拜物教的生成机理
网络短视频数字拜物教的“颠倒表象”正是源于其“异化本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劳动异化表现为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者与劳动过程、人同人的类本质、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这些异化又集中表现为一种人与物的关系的“颠倒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这种“颠倒性”称为拜物教。
(一)网络短视频生产活动的异化
相较于传统的车间作业生产模式,网络短视频所构建的数字环境使得生产活动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也模糊了工作与闲暇的界线。资本在网络短视频平台环境中的剩余价值榨取更加普遍化和隐匿化。尤里斯在《互联网中的劳动》中提出,互联网中的社交娱乐活动成了价值生产的活动。普通用户与数据工程师作为生产活动的劳动主体,他们只是作为数字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工具,无法获得自己应有的回报。这种回报对前者是虚幻的感官刺激和可以忽略不计的返利,对后者而言则是维持其生产自身的工资。要理解这样的结果就要回到网络短视频生产活动的异化过程中去。
一是劳动者与自己生产的数据和数据产品相对立,并且受到这些劳动产品的支配和操纵。马克思指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9]。普通用户与数据工程师所生产的数据产品并不属于自己,而且会受到自己劳动成果的支配。这种支配一方面表现为数字资本积累的物质性支配,即“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9]。这种客体对于主体的支配是从异化劳动诞生之时就存在的。另一方面,这种支配在网络短视频有了新的表现,即精准营销,个性化推荐,用户画像等。这些都是基于数据信息,通过算法分析而实现的对于用户的反作用,区别于物质性的支配力量,这种支配是从意识认知层面展开的诱导和操控。至此,数据这种死劳动对于用户和工程师这样的活劳动实现了从物质层面到意识层面的全面支配。
二是用户与工程师在生产数据过程中产生了异化,即劳动者同劳动过程的异化。数据工程师为了换取生活资料所进行劳动的过程是一种机械的,工具化的异己的活动。劳动者在这个过程中是痛苦的,是迫于生计的压力的被动选择。然而,就网络短视频用户而言,这样的生产过程异化却披上了一层极具迷惑性的娱乐外衣,人们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很少感到痛苦和不自由,甚至感到近乎成瘾的快乐,这使得人们对于网络短视频乐此不疲。但是,这样的自由和快乐正如其产生的虚幻的数字基础一样,它们只是资本吮吸人们大量的时间精力的诱饵罢了。因此人们以为的自主性活动成为数据算法操纵下的为数字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性活动,这是网络短视频生产活动异化的新形式。
网络短视频生产活动的异化从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对立性揭示了网络短视频环境中人与数字的颠倒性。人们想要通过网络短视频生产活动的参与来获得一种对象化活动的自我验证。然而,因为劳动的异化,这样的肯定性追求被对立的否定性现实所取代。这使得劳动休闲化的数字时代的人们的生产活动仍然被异化劳动所控制。马克思指出,生产直接也是消费[10]。因此,网络短视频生产活动的异化决定了其消费行为的异化。
(二)网络短视频消费行为的异化
网络短视频的消费行为是指平台消费者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在网络短视频平台中有偿地获取服务或者虚拟商品的行为,这里的“有偿”并不局限于货币与商品的交换。网络短视频消费行为主要可以归纳为隐性消费与显性消费两类。而网络短视频消费行为的异化在于它的隐性消费的欺骗性和显性消费的“胁迫性”,它们彼此联系,相互强化,共同构成了消费行为异化的现实基础。
一是网络短视频隐性消费的欺骗性。网络短视频的隐性消费行为是指平台用户与平台中短视频等数字产品的互动行为,例如浏览、点赞、收藏、转发和评论等等。而网络短视频隐性消费的欺骗性在于其并不是“无偿的”。一方面人们的浏览,用户为了能够获得平台的使用权,不得不让渡自己的隐私信息给平台方;另一方面,用户耗费时间精力产生的大量的数据信息也是为了获得短视频产品消费的让渡内容。因此,从产品交换的本质看,网络短视频的隐性消费并非是“无偿的”。
二是网络短视频显性消费的“胁迫性”。网络短视频的显性消费行为是指平台用户购买平台的虚拟产品,有偿服务等直接体现商品价值让渡的行为。显性消费行为的“胁迫性”区别于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的那种强制性,而是一种无可逃避的虚假需求。马尔库赛认为,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给个人身上的那些需求,是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的永恒化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11]。在网络短视频环境中,人们在消费的同时生产数据,平台利用这些数据对于用户进行引导,进而使人们再次进入下一轮的消费,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为的不是人的本真需求,而是资本的无限扩张。在这样的资本逻辑下,消费从满足人的本真需要的手段异化为了目的和意义本身。随着现代社会数字技术与人们生活的高度融合,这种“胁迫性”更是昭然若揭。
网络短视频的生产活动异化和消费行为异化共同构成了网络短视频数字拜物教的现实基础。在这样的异化基础上,网络短视频数字拜物教的意识形态获得了其坚实的物质根基。网络短视频意识形态的异化使得人们在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上发生了与人的类本质相偏离的问题。
(三)网络短视频意识形态的异化
网络短视频意识形态的异化是其生产活动异化和消费行为异化过程的逻辑结果,也是网络短视频数字拜物教在人们意识层面的最终完成。尼尔波兹曼认为,媒介即认识论,真理只是文化的偏见[12]。媒介并非排除了意识形态的中立存在,媒介即隐喻,媒介在解释世界时,总会选择以一种方式,而不是以另一种方式展开叙事。这体现了媒介本身的意识形态属性。网络短视频对于人们的意识形态的塑造主要表现为对于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影响上。网络短视频通过其碎片化、娱乐化、即时性和消费主义的媒介叙事方式,使得人们逐渐形成了与网络短视频这种媒介形式相适应的认知模式和心理特点。这符合资本将人作为剩余价值生产的工具的异化逻辑,但却不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可持续发展。
一是这种意识形态异化导致了人们形成了虚拟与现实相互颠倒的错误世界观。网络短视频构建的数字世界给人们造成了世界触手可及的假象。然而,正是因为网络短视频所营造的这种随时可及的数字幻象让人们沉沦其中,逐渐不再关注现实世界,充分说明了前文中人与数字的颠倒性关系正是这种颠倒的世界观的产物。正确的世界观是人们作出合理的价值判断的前提条件。
二是网络短视频意识形态对于人的价值观的扭曲在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侵入。人们对于事物的价值判断严重偏离了人的自由意志,并且自觉地将自身的价值取向同资本扩张的逻辑结合起来。人们沉浸在一种扭曲的价值满足当中。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中,指出,处于异化中的人只有放弃自己的私人意识才能成为自己。“自愿”献身于资本增殖的扭曲价值观让人们不再反思生命的真正意义,不再探寻人作为目的性的存在本身。人们沉醉于对于货币财富,物质资源的无止境的贪欲当中。价值倒退成了商品价值,价值观退化成了金钱观。
三是基于这样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人们形成了单调的、机械的、不约而同的人生观。金钱和权力成了人生的终极追求。在网络短视频平台中,大量的炫富内容往往能成为热点,这种机械的人生观正在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的正义。马克思指出,相比于动物的片面生产而言,人的生产本应该是全面的,即除了为了生存的生产,人还会进行彰显人的类本质的生产活动[13]。然而,机械的人生观使得人的活动被限定在了动物性的片面状态之中,从唯物史观的维度看,这种对于财富的单一化追求终究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当然这也孕育着社会形态进化的基础性动力。
网络短视频数字拜物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数字时代的特定产物,其存在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但随着社会制度的进化,它最终会因为失去其物质基础而消亡。在当下,我们之所以能够对此进行批判性的反思,意味着网络短视频数字拜物教的消亡必然性正在走近。
四、网络短视频数字拜物教问题的治理路径
网络短视频数字拜物教是商品拜物教在数字时代的一种新形式。马克思对于拜物教消亡的条件作出了经典的论断,他指出:“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的联合的人的产物,在人的自觉和计划的支配下,才会揭开它神秘的纱布。摆脱资本逻辑,资本支配的生产关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14]因此,面对网络短视频数字拜物教问题,我们既不能因为数字拜物教的异化和颠倒而完全否定其合理性的一面,又不能在数字拜物教的负面影响面前无所作为。基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创举需要我们积极主动地推动对于网络短视频数字拜物教“扬弃”的进程。
(一)监管层面:建立全面的长效监管机制
一是加强对网络短视频平台的算法审察和监督。平台方为了尽可能地追逐商业利益,在算法设计上往往会盲目地迎合资本和市场的需要,从而忽略了应有的社会效益。监管部门需要根据监管对象的技术特点建立专业化审察监管团队,与时俱进地做好监管工作,积极主动应对网络短视频算法可能带来的伦理风险和社会问题。
二是积极发动广大用户群体参与网络短视频的监督。人民的监督是有力且广泛的。在网络短视频中,用户既是平台的消费者,也应当是平台的监督者。当前,网络短视频平台设有投诉、举报和意见反馈的渠道窗口,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用户进行监督提供了便利。但是,这些监督形式基本属于事后监督的模式,而事中、事前的监督则处于缺位状态。平台应当增加设计一种新的机制,使得广大用户群体能够便利地参与到网络短视频监督管理的全过程。
(二)教育层面:开展媒介素养教育
一是从学校的体系化教育方面着手,在不同学段增设适合本学段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当代的学生群体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从小就生长在各种新媒介所建构的数字环境之中。在学校教育中设置媒介素养课程的目的就在于让学生了解媒介发展的历史、媒介的本质和功能等等。只有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学生们的头脑,才能使学生们在未来的媒介环境中保持理性的应对姿态。
二是在社会教育方面,应当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使用灵活多元的教育方式提高普通大众的媒介素养。例如通过社区线下展板、标语等方式,让人们理解网络短视频所展现的虚拟世界同现实社会的区别,倡导人们回归现实世界进行社交活动等等。此外,通过网络短视频平台本身制作节目向人们普及网络短视频的运作规则、算法功能等。这样在大大提高大众对于媒介本身的了解程度的同时也培养了人们的媒介素养。
(三)宣传层面: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网络短视频已经成为大多数公众获取信息,娱乐社交的重要途径。因此,要应对网络短视频数字拜物教的意识形态问题,不能离开网络短视频媒介本身。通过网络短视频全面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需要人们将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内化于心。各大宣传主体应当充分利用网络短视频平台进行贴近人们生活的宣传,例如《人民日报》的侠客岛短视频号紧跟时事,风格轻松幽默,将主流意识形态宣传融入节目之中,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可。另一方面应当大力宣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案例,推动人们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外化于行。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人们在个人层面上持续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并且获得媒介宣传层面的肯定和认可,这便能够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网络短视频意识形态的阵地就会被我们牢牢地占据。
〔参 考 文 献〕
[1]徐艳如.数字拜物教的秘密及其背后的权力机制[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06):105-113.
[2]吴媚霞,王岩.数字资本化与资本数字化的学理考察及其启示[J].思想教育研究,2022(09):75-81.
[3]王维平,汪钊.数字资本拜物教的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J].上海经济研究,2022(11):26-39.
[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J].国家图书馆学刊,2022,31(05):1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
[6][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44.
[7]马乔恩.数字时代注意力经济的多层构境及其批判[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0(03):21-30.
[8][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5.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1.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92.
[11][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6.
[12][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6.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7.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6.
〔责任编辑:侯庆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