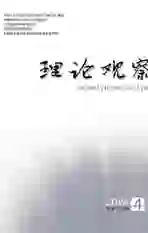弗洛里迪信息伦理思想及抽象层次方法探究
2024-07-18张慧郭佳楠
摘 要:信息和通信技术(ICTs)不仅深刻改变了人类现代生活中的诸多方面,其所引发的众多新的伦理问题也令人深思、亟待解决。然而,这仅仅是第一代信息伦理学的任务。弗洛里迪试图构建第二代信息伦理学,对ICTs引发的伦理学难题背后的哲学框架和概念基础进行深入思考,并通过运用抽象层次法对信息主体自身的知识结构以及所接受的抽象层次进行分析,进而促进认知主体做出新的本体论承诺,使之成为一种全新的伦理学范式。弗洛里迪通过综合“抽象层次”组成框架,对当今信息社会带有基础性的伦理问题进行了规律性探究,一方面从伦理学的研究视角澄清人工代理及其道德责任上的困惑,另一方面是期望能够对信息论理学有更为清晰的认识和更加深入的理解。
关键词:信息伦理;抽象层次;人工智能;信息物;道德;行动
中图分类号:N94-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04 — 0043 — 06
一、信息计算主义者基于信息伦理的基本观点
信息计算主义者关于信息伦理的基本观点主要包括多迪诺·斯诺科维奇(Gordana Dodig-Crnkovic)和詹姆士·穆勒(James Mill)在信息计算主义的框架内定义的伦理问题概念,信息和计算主义的相互关系以及信息伦理可以对道德背景产生更深入的了解,这是将与信息有关的双重本体作为一种结构和计算的过程。
信息伦理提供了分析工具和概念空间,用来阐释在信息物之间动态和控制论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有助于在信息、知识和道德实践之间建立联系,信息计算主义对信息伦理的解释是一种递归的自我可持续性的循环:信息结构自下而上的建构产生了信息自上而下的重新建构(突现),处于最底层的信息元素通过交互影响达到一种集体的状态,这也反过来影响处于底层信息元素的行为。应当强调的是,虽然这种机制存在循环,但是不会产生恶性循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变体,这种变体是在与环境持续交流的。对于信息伦理的解释弗洛里迪认为,本体论应当是信息的,现实的交织物(原型)都是由信息组成的。自然计算的过程就等于信息处理的过程,这种过程是基于一种自然的计算,其中包含了数字和模拟。信息结构和计算结构两个基本的互补概念组成了本体论的两个方面。[1]多迪诺·斯诺科维奇认为,基于物理的规则,信息结构的交互影响,进化以及构建更多复杂的标记,特别是运用世界中的原始信息组成的智能生物机制是用来构建知识和形成决策的。存在于伦理机制中的伦理范式,它们为人类的决策和行为提供了规范,它们可以作为一种在受目标驱动的生物机制中,信息和计算主义结构不断进化的结果。穆勒认为,信息结构构成的复杂系统可以分析不同层次的组织和不同水平的抽取结构,信息伦理是着眼于信息基础层次上的重要伦理方法。[2]
计算主义的信息伦理观点总结起来主要包含以下方面:首先,物理现实的基本本体论存在是信息结构和计算的变化,只有通过信息系统人们才可以认识到自身的存在,才能够通过计算的变化来认识世界的本来面目,这是一种纯粹的本体论观点;其次,一个复杂的物理系统的属性不能单一的来自这个系统组成要素的属性,突显的属性也应当考虑在内,一个系统应当是开放的具有信息交流式的系统;[3]再次,信息结构的变化是有规律的;最后,信息系统的观察者也是这个被观察系统的一部分。信息伦理的定义总是根据信息的自身属性而定的,世界的本事属性是由客观事物组成的,而这些客观事物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也是信息和计算的方式,信息伦理可以说是是一种元伦理。
二、抽象层次(Level of Abstraction)的基本概念
原则上,现实能够在不同层次的水平上进行研究,在以往第一代范式中,人们通过将层次主义(levelism)与自然计算合二为一,成为科学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支撑。然而,在不同学科和不同研究者眼里,任何类的变量的集合都可以组合成一个可观察的“向量(vector)”,每一个类是组成变量类集合的笛卡尔积。例如,对于葡萄酒而言,类的特性可能包括鼻子、长袍、颜色、酸度、水果和长度的类的笛卡尔乘积。[4]最终的结果将是一个单一的、更为复杂的、可观察的信息体。在实践中,由于它要求一个投射符号将向量中可观察到的数值进行过滤,以决定它们是否与从某个具体的抽象层面上形成的某种假设存在关系,因此这样的矢量化是很难实现的。
在此,卢恰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提出了“抽象层次”(LoA)概念来解释“信息体”的类别,并以可观测的方式对“信息体”进行筛选,LoA的关键就是通过对不同层次的组织和阐述层次进行分析:抽象层次是一种技术性和以目标为导向的方法,它代表一个有限但非空的可观测集合。其中观测值没有被赋予任何次序,在一个以其定义为特征的理论中,观测值被认为是信息体的构建模块。当且仅当LoA的所有观测值均为离散时,LoA则被称为离散;否则它被称为混合型。不同的LoA能够适用于不同的目的。例如,当观察一个建筑物的时候,具有抽象层次观念的人应当以建筑学、情感、经济、历史、法律等方面为目标对这个建筑物进行分析,没有“正确的”抽象层次方法可以独立于它所采用的目的,在同样的意义上,也没有正确的工具可以独立于需要被做的工作。[5]就认识论而言,抽象层次的方法取决于不同类的交往,这种交往是处于认知物和研究物之间的,这种类的交往反过来被知识生产的技术本性所定义。从历史上说,研究领域通常会选取在现实中具有代表性的抽象层次,其中显微镜和望远镜,以及在某些科研工具帮助下可见的事物就是它们特定的世界。例如,在显微镜中看不到恒星,在望远镜中看不到原子结构,为什么对于跨越了几个层次的体系而言产生的描述就不是共同的,这些事物都是从最基本的层次开始,跨越了所有的层次到达了一种宏观的状态。对于每一个层级而言,事物出现的属性都是系统组织现象的一种结果,信息和知识之所以不同并不是组成“原料”的差异,而是组织结构的差异。通过研究精细的知识,人们会发现信息,同样的,人们通过信息的眼镜来看世界,只能看到在不同星座上的信息。用精细的分辨仪器来观察人类,一个人只能看到原子,这些原子再一次被称作信息。
每个层次的抽象水平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并且每一个新的层次出现都来源于先前的层次。经典道德论述使用的概念性曲目都是基于人类日常生活经验,信息伦理学家宏拉达龙(Hongladarom)曾经阐述了这样的运动,该运动从信息哲学最大抽象层次来分析个人的信息隐私,他说道:“我们正在从关于每天现实生活的更大特异性的抽象层次上递减,即使我们相信本体是由信息组成的,因为现实可以在越来越精细化和更深的抽象层次上进行描述,因此需要更多的信息,需要去保护个人隐私不被侵犯因为即使信息圈已经成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信息都能够掌握在政治权威的手中。关于信息圈和隐私问题被设计用来证明反自然主义者的一种挑战,这些人强调个体对抗本体的公认可能性,但是这二者并不需要发生冲突。”[6]一些人对抽象层次的方法感到不安,因为他们害怕道德相对主义,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定义抽象层次的方法可以加深我们对范式的理解,一种与自然科学的类比是具有启发性的,物理学拥有关于世界特定模式的抽象的不同层级:从基本的粒子、原子、分子、固态,经典力学和流体动力学,天体物理学到宇宙的水平。[7]一个复杂系统引人瞩目的新领域,这个领域不仅关于组织的现象特定的层级,而且也处理不同层级间的交互,因此,复杂系统就作为一个整体显现的属性出现,这不同于个人属性显现的部分。信息哲学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中发现了相似的复杂结构,信息伦理对道德也是如此。信息伦理成为了一个有前途的研究领域,并且它的实践应用已经非常多了,很确定的是它在以后的数量和重要性上还会有上升的趋势。
三、抽象法(The Method of Abstraction)的阐释
在弗洛里迪的信息模型中,抽象法(LoA)是一种出于某特定的目的而进行系统分析得到的模型结果,它是“知识构成的无穷无尽的来源”;[8]在对现实的探索中,它的意识可以被延伸到无穷无尽的范围,因此,它是一种真正的不可知的联系。这种方法的贡献是,在进一步细化理论之前,需要明确地向LoA/GoA作出承诺。它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优点:
首先,基于LoA作为中介的知识,这种方法能够有助于人们对“间接知识”的意义进行明确的认识。[9]当主体的知识架构发生变化时,它会选取一个新的抽象化的层面,而在这个新的抽象化层面上,这个新的主体的本体论承诺是有意义的,“间接知识”与人的心智或意识联系起来,衍生出思想、指令和概念等意义。
接下来,LoA意味着从一开始就澄清问题的范围(a)所提的问题是否有意义与原则(b)上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范围。在某种意义上,LoA的输入被看成一种正在分析的系统构成,即由数据集合组成;它的输出则是系统的模型,即由信息组成。模型中的信息量随着LoA的变化而变化:较低层次的LoA,具有更高的分辨率或更为精细的颗粒度,其所生成的模型比更高层或更抽象的所生成的模型含有更多的信息量。因此,给定的LoA便能够对从系统中“提取”的信息的种类和数量做出量化承诺。LoA的选择预先确定了能够量化的数据的类型与数量,从而也决定了模型中可能包含的信息。这样,人们必须认识到系统在哪个LoA上得到分析,因为这意味着了解正在开发的模型的范围和限制。
再次,在一个充分的信息社会(信息域)中,确定所采用的LoA能够为因层次漂移而产生歧义、模棱两可和其他谬误提供一种健康的“解药”, 这种解药对处理亚里士多德的“metabasis eis allo genos”(从一个属转移到另一个属)、赖尔的“范畴错误”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悖论”等问题和歧义提供一条可能性路径。[10]
最后,为陈述理论层面LoA,一个理论便能够通过明确的方式澄清其本体论承诺。而这种分析体系被弗洛里迪称为体系—层级—模式—架构(SLMS)模式(参见附图1),在此模式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关于“承诺”与“被承诺”的概念。
如果某理论通过选择特定的LoA完成其本体论承诺,也就意味着该理论对系统的某个特定模型作出承诺。通过采用LoA,该理论决定了什么样的可观测物将在细化模型过程中发挥作用。总之,如果一种理论通过接受 LoA来保证某种物体和它的存在,那么该理论就会向相应的识别做出保证(因为某个模式解释了选定的数据,就意味着相信某个特定的模式)[11],图2总结了这个区别。
在弗洛里迪和桑德斯的《论人工代理的道德》一文中提到,抽象层次法是一种更具主体间性、社会建构性、动态性与灵活性的方法,这种方法既远离内在实在论,又没有陷入外在或形而上学实在论,它旨在“让老相识和新面孔保持某种距离”,从而逐步理解系统本身。[12]在弗洛里迪的信息/计算伦理学中,LoA不仅被用来阐释信息对象的最小内在价值,而且为人工智能哲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临场模型。在每一种情况下,抽象层次方法都被证明为解决信息伦理或哲学问题提供一种灵活且富有成效的方法。
四、基于抽象层次的信息伦理思想
在众多对信息道德误解中一个是与信息物的内在价值有关,这反过来又与对一个范式抽象层次的理解有关。一个常见的误解就是信息伦理会为伦理决策的自动化提供一种机制,然而,在最基础的层次上,信息伦理会首先帮助我们理解基本结构和底层机制,信息伦理与传统的道德方法有关,就如同分子生物学与古典生物学的关系一样。[13]人们不应当期望分子生物学能够回答关于生物世界的所有问题,但是它可以为生物学的其余部分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就如同在其他研究领域,道德方法的多样性仍然是具有同等价值的,并且它预先假定了在理论结构中人们的判断力和相互联系。
信息物具有先验的价值,如果对事物一无所知,人们会选择不去破坏和扭曲信息的结构,而在一个系统更高的层次上,例如人类,人们一定会选择清理他们的邮箱,这当然不是道德问题。弗洛里迪认为,对信息的尊重应当是建立在对自然尊重的基础上,每个人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不应当破坏自然物,但这也不能就断定人们不能改变周围的世界。宏拉达龙发现了弗洛里迪的信息伦理与斯宾诺莎的伦理在伦理自然主义中的相似之处,并且指出得出不同的研究方法也是不可避免的。在日常生活实践的层次上,统一的多样性自然是通过不同的交互所达到的:信息伦理当前情况的转化是概念化一个事物和相同的现实总有不同的方法,它是人们的需求、目标和愿望,这些通常规定了概念化如何完成。然而,当不同群体的人们发生互动,这些系统会向另一个系统看齐,这也许是因为它们已经属于了相同的事实。[14]在对信息伦理的批判性研究中,卡勃罗关注了信息物的内在价值,布里提议将信息伦理从以价值基础导向转变为向以尊重的基础,这是为了让人们接受这样的观点,没有生命的事物也应当获得道德上的尊重,不是因为内在的价值,而是因为它们外在性、工具性和个人的情感价值。[9]然而哈克提出了对信息物关系价值的归因,从而用来区别内在的、关系的和工具的价值。所有的批判性的观点都认为人类应当成为道德关系和利益的联结点,这是信息哲学从一开始构建就避免的。[15]弗洛里迪认为信息哲学就是采用了信息本体论来作为统一所有现实的最小的共同标准。作为一个文明世界的公民,公民仍然是“人类”,公民认知世界的方法也仍然是“人类”的,即使有时人们采用信息结构的基本层次和处理方法,它首先还是尝试去理解一种基本的潜在的机制。即使在未来可预见的人类与人工智能物混杂的世界中,不同的道德结构和描述层次的互动仍然是必要的。
通过关注一个系统基础的层次和重新思考人类自身以及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信息伦理必然在本质上有助于理解在人类与人工智能物组成网络中的道德行为的潜在机制,这些已经被观察到的伦理过程提高了在这系统中的认知分布,这也使得信息哲学的应用成为必然。
五、人工代理及其道德责任
作为实用性的目的来说,自主智能系统的道德责任最好是作为一种监管机制,用以确保渴望的行为。“责任”也被认为是智能系统在某种意义上的“智能”,人们期望一种人工智能系统在行为上可以自己选择什么是道德的,什么不是,就如同以往需要人类来决定的功能。为了证明这些人工道德系统,弗洛里迪采用了抽象层次的方法,并且讨论完全由设计者决定其行为的不同人工代理,并且这些人工代理完全可以自主的学习适应和改变自己的计划。[16]人们得出结论,设计者和其他相关的利益方必须保持对这些人工物的责任,无论它们是多么的自动化。一个具有所谓“自由意志”的人工代理并不比一个处于技术——社会系统的人更加的具有自主性,尽管人类有自主性和自由意志,同时也有一个系统的责任分配,在这些人工代理中构建道德责任的思想并不是意味着把这些替代物排除在技术——社会系统的控制之外。[17]在这种情景下,其中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关于替代物的概念,并不像一些哲学家断言的那样,如果通信技术具有了意识,那么人工代理的道德责任实现就是可能的。
弗洛里迪认为,这种代理可能像细胞自动机一样简单,并且也具有随机访问的存储器,它们可以与环境发生联系,并且运用存储记忆超出同时存在的状态联系,用以简化对环境的表述。[18]作为这种代理的社会成员可以共享信息和知识,这样的代理随着下一个阶段的状态的进入,表现为动态非相关的,这不仅取决于它们之前的状态,而且取决于它们本身的记忆。这些代理的联系可以是本地的,全球的或者是处于中介,系统的进化随着时间不断的发展,它们的行为也可能是单独并行的,因此它们之间的联系也是异步交互的。在信息伦理中加入计算模型就如同在医学诊断工具中加入显微镜,这也许并不会取代医生每天对病人的检查,但是会提供一个非常有益的补充,一个病人的诊断结果自然取决于诊断的方法和仪器。在某种分析层次上,就可以把问题定义成血液中高级的白细胞,在更高的粒度层次上,相同的问题可能作为一种传染病出现,在一个更高的社会层面上,问题可以被定义成一种流行病和卫生保健问题。
弗洛里迪意识到人工代理的伦理涉及到几乎当今社会所有的领域(如他提到的生态、克隆技术、弱势族群、组织机构、医疗、隐私、堕胎、文物价值、政府行为等等),因此,他认为人们不必担心因为抽象层次不同层次的分析而导致产生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答案,例如,一个病人的白细胞过多,可能是传染病的感染,也可能是流感的威胁。[19]人们应当庆幸在每次的分析中终于区分出了一个变量,这些变量也许隐藏在每一次层次抽象之中,是对道德冲突误解的一种根源。换而言之,以信息为中心的信息伦理是对传统道德补充,而不是一种替代。正如弗洛里迪指出的那样,一个可能方法的多元化是对彼此的补充和加强,这就类似于拱门上的石头。
六、结语
任何技术的不确定性和潜在性都会影响人类社会,人们在面对这些技术带来的影响时应当持谨慎的态度。人工智能系统也具有技术的以上两种特性,因此人们要给出相应的预防原则,防止伤害和对无害的举证责任应当是智能系统所承担的责任,就如同一个国家派军队去参加战争,无论是人类还是人工物,它都有责任将军队按照等级组织起来,其中最高的责任控制主体应该处于层级的顶端,但也包括了每一个士兵的责任。信息伦理并不是机器最终的伦理产物,而是关于伦理分析的强大的互补性工具。
弗洛里迪的抽象论阐明了隐藏的假设,简单化对比,增加信息的可信度,从而有助于消除一些模糊的观念。应该说,抽象法是弗洛里迪信息结构实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该方法使信息结构实在论具有了稳固的理论根基,从而使其可以在此基础上为由信息与通信技术引发的终极存在问题提供新的道德框架;另一方面,它也是对康德思想在信息时代的推进和利用,为信息哲学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
〔参 考 文 献〕
[1]Adam, Alison. Delegating and distributing m-
orality: Can we inscribe privacy protection in a machine? [J].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05(7).
[2] Adam, Alison. Ethics for things[J].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08, 10(2).
[3] Himma, Kenneth E. Artificial agency, cons-
ciousness, and the criteria for moral agency: What properties must an artificial agent have to be a moral agent? [J]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09, 11(1).
[4] 阮朝辉.警惕人工智能异化、伪知识泛滥和全民娱乐对人性与文明的危害[J].科技管理研究, 2016(8):262-266.
[5] 玛格丽特·博登. 人工智能的本质与未来[M]. 孙诗惠,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162-163.
[6] Hongladarom, Soraj. Floridi and Spinoza on
global information ethics.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08(10).
[7] Floridi, Luciano. The method of levels of ab-
straction[J]. Minds and Machines, 2008c, 18(3).
[8] Floridi, Luciano. Ethics Information ethics: A reappraisal[J].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08d, (10).
[9] Floridi, Luciano, and J.W. Sanders. 2004a. On the morality of artificial agents. Minds and Machines,2021,14(3).
[10] Floridi, Luciano, and J.W. Sanders. On the morality of artificial agents[J]. In Minds and machines, 2004 (14).
[11] Hansson, Sven Ove. The limits of precauti-
on[J]. Foundations of Science, 1997(2).
[12] Hansson, Sven Ove. Adjusting scientific pr
actices to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J]. Human and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1999(5).
[13]Arkin, Ronald C. Behavior-based robotics[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8:105-110.
[14]雷·库兹韦尔. 奇点临近[M]. 李庆诚, 董振华, 田源,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181.
[15]约翰.马尔科夫. 人工智能简史[M]. 郭雪,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7: 71.
[16]董青岭. 大数据与机器学习: 复杂社会的政治分析[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8: 149.
[17]李海俊. 人工智能与人的发展: 历史生成中的统一[J]. 沈阳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01): 42-47.
[18]张歆悦. 人工智能技术对就业影响效应研究[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9(19): 90-91.
[19]王绍源. 警惕人工智能的伦理缺失[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5-09-10(01).
[20]苏令银. 透视人工智能背后的“算法歧视”[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7-10-10(05).
〔责任编辑:侯庆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