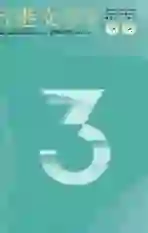觅食记
2024-06-28谢冕
谢冕
饺子记盛
中国人的主食,南方重米,北方重面。这是由于南方多产稻米,北方多产小麦。北方盛产小麦,因此面食的花样层出不穷,眼花缭乱,面条、烙饼、馒头等,其中最主要的是饺子。北方人年节、宴客乃至日常居家,最常见、也最隆重的餐食活动是“包饺子”。包饺子的活动,从和面、揉面、擀面,再到剁馅、调馅,一大套,很是啰唆。南方人对此往往视为畏途。而在北方人那里,特别是在北方的媳妇、婶子手中,却是神奇地“一蹴而就”的日常功夫。我是南方人,原也属于视为畏途一族,因为在北方生活久了,不觉间饺子也成了最爱。
我至今仍不习惯,甚至不喜欢吃馒头,馒头实际上只是一团蓬松的面坨,单调而“乏味”。由于它是发面的,人家取它的优点是松软,我恰恰是因它的“棉花状”而难以吞咽。数十年了,总爱不起来。饺子则不同,外皮是不发酵的实面,吃起来润滑好下口。饺子皮一般不添加什么,近来也有所谓五彩的,用各种蔬菜汁染色,那是特例,并不见佳,倒是单纯的白面好。因为饺子裹着馅,而馅是繁复多彩的。单纯的外皮和复杂的内馅,因反差互补而成了一道美食。北方人很为饺子自豪,自豪到了马可·波罗那里。说是老马把饺子传到了意大利,那里的人学不会,结果把馅放到了外面,就成了后来的比萨饼。此论是真是假,待考。
包饺子是一场让人愉悦欢乐的活动。北方人居家想改善生活了,就说“咱们今天包饺子吃吧”。一说包饺子,就来了精神。物资匮乏的年代,不像如今可以随意上馆子,包饺子就是一件奢华之举。过年过节,亲朋来家,最富亲情的待客之礼,就是包饺子。“包饺子”一声令下,立即兴奋起来,揉面的,和馅的,准备停当,就围坐包起了饺子。边包边说笑,不觉间一切停妥,用笸萝摆放,如花盛开。饺子下锅,热气腾腾,饺子出锅,狼吞虎咽。有情,有趣,有气势。数十年北方生活,享受过数不清的这般热闹,可依然觉得好吃但包起来费事。
我至今不会擀皮,却在北京乡间学会了包。双手一捏,就是一个,迅疾,结实,下锅不破。别人包饺子讲究花样,多少折,怎么折,图好看,玩花的。据说我包的饺子“其貌不扬”,但我很自信。这是包,即制作的环节,而饺子是否好吃,关键却是调馅。调馅的功夫其实蕴含了诸多中国烹调的道理,一是馅中的主客关系,肉和菜是主,葱姜等为辅,要适当;再就是肉和菜的搭配,肉为主,菜为辅,也需适当;就肉而言,就是肥瘦的搭配,一般说来,不能全是精肉,二分瘦,一分肥,比较合理。什么肉,配什么菜,这里有大学问,韭菜配鸡蛋,羊肉配胡萝卜,最家常的是猪肉白菜馅,加些海米,人见人爱。吃饺子,一般人爱蘸醋,而我谢绝,我深信只要馅调得好,无须借助“外援”。
吃饺子讲究薄皮大馅,过去北京街摊上卖的,是用秤称,一两六只。那时面有定量,比较金贵,不能多,想吃大馅也不成。想吃大馅饺子只有自己包。近期北大这边的畅春园超市,有卖大馅饺子的,他卖的是馅,包得越多越挣钱,这就正中消费者的下怀。这家小店只占超市门边一小间,一两张桌子、三五张椅子,现包,现称,现煮,热腾腾出锅上桌。我在这里“宴请”过许多朋友,包括外宾。吃过的无不叫好,说是京城第一。你若不信,可以亲自体验,不远,北大畅春园社区超市一个犄角便是。
北方人吃饺子不仅是享受美食,而且是享受家的温暖。在记忆中,满含着亲情的饺子被替代,甚至等同于家乡、父母。游子离家远了,想家,连带着想起妈妈包的饺子、炊烟的味道,此刻,饺子就是乡愁。即使是身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遇到年节,想家,又不能回,相约若干同样怀乡的朋友一道包饺子,为的是一解乡愁。记得那年在维也纳,短期开会,不是什么怀乡情切,也说不上乡愁,倒是一位奥地利教授的一顿“饺子宴”令我大为感动。
在维也纳,那些奥地利红葡萄酒,那些名目繁多的奶酪、香肠和面包,特别是烟熏三文鱼,这些异邦的美味都令我着迷。可是,接待我的汉学家李夏德却是别出心裁,带我进了维也纳中心区的一条小胡同吃饺子。铺子的名字记得是“老王饺子”。山东人老王开的,小门脸,不加修饰的若干桌椅,设有醋瓶,如同国内规矩。饺子是地道的,热腾腾的饺子上桌,捎带着一小碟大蒜。一切一如国内乡间的小铺。一下勾起了亲切的记忆,浓浓的齐鲁乡音带着胶东半岛的气息。小店只有一个厨师(老王自己),一个收银的,外加一个“跑堂”。那跑堂可是“高大上”,一位在维也纳学音乐的留学生。
李夏德介绍说,这里的饺子本色、地道,是纯粹的中国味道。他经常在这里“宴客”,有时不接待客人,自己也来。这里也常有本地人光顾,那都是一些“中国通”。
二○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此日丁酉腊八
馅饼记俗
在北方,馅饼是一种家常小吃。那年我从南方初到北方,是馅饼留给我关于北方最初的印象。腊月凝冰,冷冽的风无孔不入,夜间街边行走,不免惶乱。恰好路旁一家小馆,灯火依稀,掀开沉重的棉布帘,扑面而来的是冒着油烟的一股热气。但见平底锅里满是热腾腾的冒着油星的馅饼。牛肉大葱、韭菜鸡蛋,皮薄多汁,厚如门钉。外面是天寒地冻,屋里却是春风暖意。刚出锅的馅饼几乎飞溅着油星被端上小桌,就着吃的,可能是一碗炒肝或是一小碗二锅头,呼噜呼噜地几口下去,满身冒汗,寒意顿消,一身暖洋洋。这经历,是我在南方所不曾有的,平易,寻常,有点粗放,却展示一种随意和散淡,家常却充盈着人情味。
我在京城定居数十年,一个地道的南方人慢慢地适应了北方的饮食习惯。其实,北方,尤其是北京的口味,比起南方是粗糙的,远谈不上精致。北京人津津乐道的那些名小吃,灌肠、炒肝、卤煮、大烧饼,以及茄丁打卤面,乃至砂锅居的招牌菜砂锅白肉,等等,说好听些是豪放,而其实,总带着京城大爷满不在乎的、那股大大咧咧的“做派”。至于京城人引为“经典”的艾窝窝、驴打滚等,也无不带着胡同深处的民间土气。在北方市井,吃食是和劳作后的恢复体能相关的活计,几乎与所谓的优雅无关。当然,宫墙内的岁时大宴也许是另一番景象,它与西直门外骆驼祥子的生活竟有天壤之别。
我这里说到的馅饼,应该是京城引车卖浆者流的日常,是一道充满世俗情调的民间风景。基于此,我认定馅饼的“俗”。但这么说,未免对皇皇京城的餐饮业有点不恭,甚至还有失公平。开头我说了馅饼给我热腾腾的民间暖意,是寒冷的北方留给我的美好记忆。记得也是好久以前,一位来自天津的朋友来看我,我俩一时高兴,决心从北大骑车去十三陵,午后出发,来到昌平城,天黑下来,找不到路,又累又饿,也是路边的一家馅饼店“救”了我们。类似的记忆还有卤煮。那年在天桥看演出,也是夜晚,从西郊乘有轨电车赶到剧场,还早,肚子饿了,昏黄的电石灯下,厚达一尺有余的墩板,摊主从冒着热气的汤锅里捞出大肠和猪肺,咔嚓几刀下去,加汤汁,垫底的是几块浸润的火烧。寒风中囫囵吞下,那飘忽的火苗,那冒着热气的汤碗,竟有一种难言的温暖。
时过境迁,京城一天天地变高变大,也变得越来越时尚了。它甚至让初到的美国人惊呼:这不就是纽约吗?北京周边不断“摊大饼”的结果,是连我这样的老北京也找不到北了,何况是当年吃过馅饼的昌平城?别说是我馋得想吃一盘北京地道的焦熘肉片无处可寻,就连当年夜间路边摊子上冒着油星的馅饼,也是茫然不见!而事情有了转机还应当感谢诗人牛汉。前些年牛汉先生住进了小汤山的太阳城公寓,朋友们常去拜望他。老爷子请大家到老年食堂用餐,点的就是城里难得一见的馅饼。
老年公寓的馅饼端上桌,大家齐声叫好。这首先是因为在如今的北京,这道普通的小吃已是罕见之物,众人狭路相逢,不免有如对故人之感。再则,这里的馅饼的确做得好。我不止一次“出席”过牛汉先生的饭局,多半只是简单的几样菜,主食就是一盘刚出锅的馅饼,外加一道北京传统的酸辣汤,均是价廉物美之物。单说那馅饼,的确不同凡响。五花肉馅,肥瘦适当;大葱粗如萝卜,来自山东寿光;大馅薄皮,外焦里润,足有近寸厚度。佐以整颗的生蒜头,一咬一口油,如同路边野店光景。
这里的馅饼引诱了我们,它满足了我们的怀旧心情。此后,我曾带领几位博士生前往踩点、试吃,发现该店不仅质量稳定,馅饼厚度和品位依旧,且厨艺日见精进。我们有点沉迷,开始频繁地光顾。更多的时候不是为看老诗人,是专访—为的是这里的馅饼。久而久之,到太阳城吃馅饼成了一种不定期的师生聚会的缘由,我们谑称之为“太阳城馅饼会”。
面对着京城里的滔滔红尘,灯红酒绿,锦衣玉食,遍地风雅,人们的餐桌从胡同深处纷纷转移到摩天高楼。转移的结果是北京原先的风味顿然消失在时尚之中。那些豪华的食肆,标榜的是什么满汉全席、红楼宴、三国宴,商家们竞相炫奇出招,一会儿是香辣蟹,一会儿是红焖羊肉,变着花样招引食客。中关村一带的白领们的味蕾,被这些追逐时髦的商家弄坏了,他们逐渐地远离了来自乡土的本色吃食。对此世风,也许是“日久生情”吧,某月某日,我们因与馅饼“喜相逢”而突发奇想,为了声张我们的“馅饼情结”,干脆把事情做大:何不就此举行定期的“谢饼大赛”以正“颓风”!
当然,大赛的参与者都是我们这个小小的圈子中人,他们(或她们)大都与北大或中关村有关,属于学界中人,教授或者博士,等等,亦即大体属于“中关村白领”阶层的人。我们的赛事很单纯,就是比赛谁吃得多。分男女组,列冠亚军,一般均是荣誉的,不设奖金或奖品。我们的规则是只吃馅饼,除了佐餐的蒜头(生吃,按北京市井习惯),以及酸辣汤外,不许吃其他食品,包括消食片之类的,否则即为犯规。因为大赛不限人种、国界,所以多半是等到春暖花开时节岛由子自日本回来探亲时举行“大典”。大赛是一件盛事,正所谓“暮春者,春服既成”,女士们此日也都是盛装出席,她们几乎一人一件长款旗袍,婀娜多姿,竟是春光满眼。男士为了参赛,嗜酒者,也都敬畏规矩,不敢沾点滴。
我们取得了成功。首届即出手不凡,男组冠军十二个大馅饼,女组冠军十个大馅饼。一位资深教授,一贯严于饮食,竟然一口气六个下肚,荣获“新秀奖”。教授夫人得知大惊失色,急电询问真伪,结果被告知:不是“假新闻”,惊魂始定。遂成一段文坛佳话。一年一场的赛事,接连举行了七八届,声名远播海内外,闻风报名尚待资质审查者不乏包括北大前校长之类的学界俊彦。燕园、中关村一带,大学及研究院所林立,也是所谓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高端去所,好奇者未免疑惑,如此大雅之地,怎容得俗人俗事这般撒野!答案是,为了“正风俗,知得失”,为了让味觉回到民间的正常,这岂非大雅之举?
写作此文,不时浮现《论语》的《侍坐章》情景,忆及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往事,不觉神往,心中有一种感动。夫子的赞辞鼓舞了我。学人志趣心事,有事关天下兴亡的,也有这样浪漫潇洒的,他的赞辞建立于人生的彻悟中,是深不可究的。有道云:“食、色,性也。”可见饮食一事,雅耶?俗耶?不辩自明。可以明断的是,馅饼者,此非与人之情趣与品性无涉之事也。为写此文,沉吟甚久,篇名原拟“馅饼记雅”,询之“杂家”高远东,东不假思索,决然曰:“还是,‘俗好,更切本意。”文遂成。
二○一九年二月四日至二月五日,岁次戊戌、己亥之交
除夕立春,俗谓“谢交春”,“万年不遇”之遇也。
面条记丰
中国幅员广大,基于气候、地理和物产的差异,饮食习惯南北判然有异,大抵南方重稻米,北方重麦类。我的家乡福建人不会做馒头,也不会包饺子。记得幼时,馒头是山东人营销的,有专门蒸馒头的店,叫山东馍馍,店一般都小,往往供不应求。到北方久了,也发现北方邻居很少做米饭,他们宁可到集市去买现成的面食,而懒于自己做米饭。这种南北差别是明显的。在诸种主食中,能被南北方“通吃”的主食很少,面条似乎是个例外。面条古称汤饼,西晋束皙有《饼赋》,说面条“弱似春绵,白若秋练。气勃郁以扬布,香气散而远遍”。以往都认为面条在汉末方才出现,但考古人员却在青海民和的喇家遗址发现了一碗距今四千年的面条遗存。言者称:“四千年前的那碗面条至今飘香。”(王仁湘:《四千年前的那碗面条至今飘香》,《光明日报》,2018年8月18日。)
我到过中国的很多地方,到处都有面条,而且都能造出自己的风味来。那时我无心,没有想到日后做饮食方面的文章,于是名目繁多且风味各异的面条,吃了也就是一声赞叹,没有留下文字记载,渐渐地记忆模糊了。如今提笔,犹记在遵义夜摊上吃过的一碗面条,口感和用料都非常特殊,留下的印象只记得面条是褐色的,其余一切全忘了。其实,这类谈饮食的文字多半是记叙的,例如用料、形制、火候、汤汁,以及佐料、口感,等等,均应当时静观而默记于心,日后写起来就容易得多,抒情或发挥倒在其次。
尽管如此,大略的记忆还是有的。例如山西的面食品种最多(据说多达二百余种),当年造访三晋大地,从太原一路南行,榆次、平遥、介休、洪洞、曲沃,直抵晋陕交界的风陵渡,都是黄河遥远的涛声与面条的诱人香气一路相伴。山西面条的原料以及造型、宽窄、粗细、名目繁多的各项浇头都让人眼花缭乱:剔尖、揪片、拨鱼、猫耳朵、饸饹、莜面栲栳—当然,为首的应当是名满天下的刀削面了。边走边吃,不禁惊叹山西的面食文化与地面古迹遗存同样地堪称海内之最。
遗憾的是,因为行色匆匆,这些面食多半只能在宾馆的餐厅吃,而餐厅的口味大家都有经验,多半是被一律化了,当然与民间,特别是街边小摊上的本色相差甚远。后来北大校园专门设立面馆,各个窗口有数十种来自全国各地的面条同时开放,这对我像是一种补偿。我在北大面馆吃到兰州的牛肉拉面、上海的阳春面、宜宾的燃面、四川的担担面,等等。因为商家来自全国各地,都带来各自的“看家本领”,诸路诸侯各显神通,面条的水准均是高的。进入北大面馆,因为名目繁多,往往东张西望,无所适从。但我多半会在饱赏众家之后最后选定一碗刀削面。
北大面馆的这款刀削面,一大海碗,至少三两,只需五元(小碗约有二两,为四元)。这碗面条在外边没有二十元下不来,因为是在校园内,免税,而且有补贴。分量足、价格便宜倒在其次,主要是地道。午餐或晚餐,排队买刀削面的队伍最长,但即使如此,学生们还是耐心地选择这个窗口。刀削面的重点是在面条的筋道上,厨师变戏法似的旋转着用快刀削面团,面片如雪花般纷纷飘落锅中,几番加水,翻滚数道而成,有劲。面条从滚烫的汤锅里捞出,紧接着就是一勺带着红烧肉丁勾芡的浓汤浇头,端上桌,碗底闪着诱人的红光。冬天,外边严寒,屋内,手捧面碗,热气腾腾。
这是刀削面,劲道,有嚼头,浇头滑润而霸气,代表着北方特有的坚韧和强悍。而南方的面条则是另一番景象,其代表作应当是在苏州。苏州的面条品种也是多多,浇头多达百余种,细面有若龙须,其特点是细腻、精致、绵软而爽。其著者有朱鸿兴焖肉面、陆长兴爆鱼面、斜塘老街裕兴记三虾面等。单说这三虾面,是一种拌面,虾仁、虾籽、虾黄为主浇头,上桌时,一碗干面、一碗三虾浇头、一碗青菜、一碗蘑菇炒笋、一碗清汤。很贵,很高端,但却供不应求,要预约,每年只卖两个月。
在苏州吃面,食客和店家都很精细,进门一声交代,那边就唱歌般地唱出了一长串:三两鳝丝面,龙须细面,清汤,重青,重浇,过桥!把食客的要求一一都清楚交代了。那店家,很快回应,汤是清澈见底的,面条纹丝不乱,码成“鲫鱼背”,上面漂着绿叶青丝。据说枫镇同得兴的大肉面非常出名,汤宽汤紧,重青免青,都能吃出一片清风明月,吃成与苏绣、碧螺春和苏州园林一样的风雅来。到苏州吃一碗地道的面条,是一种温柔的体验。我多次访问苏州,但却没有在苏州名店就餐的机会。倒是在上海南京路的小弄堂里,有吃一碗苏州焖肉面的经历。面端上来,清汤见底,一块焖肉约占三分之一的碗面,汤上撒着小葱花,色彩艳丽,特别是那块焖肉,色鲜红,酱香油亮而糯。面碗周边陈列小盘的各色浇头,如花盛开。
面条在中国可谓遍地开花,遍布南北西东:兰州牛肉拉面、新疆拉条子、武汉热干面、苏州奥灶面、上海阳春面、四川担担面,还有福州的线面,丝丝不断,下锅不糊,可汤可炒,可称极品。也许不应漏了京城,北京拿得出手的也就打卤面和炸酱面两种。就是这老两样,在现今的京城也是难有正宗的货色。单说那打卤面的卤,肉和鸡蛋,鸡蛋打成蛋花,金黄色浮在暗红发亮的卤汁上边,黄花、木耳,加上传统的鹿角菜,就成了。鹿角菜在北京打卤面里,犹如芽菜在四川担担面里一样,看似配角,却是万不可缺。普通面食,但看有无这配角,由此可辨真伪。
我历年漫游各地,每到一地,总要问津当地的面食。曾经在号称“美食之都”的成都,多日住在宾馆,天天面对刻板乏味的饭食,连一碗普通的担担面都不见,直至离去,可谓怨恨至极。那年在重庆也是如此,宾馆吃食,千篇一律,于心不甘,决心“造反”。私下约了二三好友,找一家面馆,一碗重庆小面,三元钱,豪华一点,再加一碗“豌炸”,也不过数元。大喜,大呼,这才算到了重庆!
二○一九年二月九日,己亥正月初五于北京
烧麦记雅
中国面食中的许多品种都与日常生活紧密关联,面条、包子、饺子都是平常家居不可或缺的主食,犹如南方人依赖米饭一样,北方居民依赖这些面食。北方的面食品种繁多,大抵也都是常见,其中只有烧麦很少出现在平时的餐桌上。平常人家可以说,今天咱们包饺子吧,动手就是,很是平常。提及烧麦,总有隆重之感。就是说,在诸多面食中,烧麦的身份有点特殊。单看名字,它就不俗。古时烧麦称“稍梅”,亦称“烧梅”,名字中有“梅”,就雅多了。据称,也有称“稍美”的,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读音,就更美了。一种小吃,有这么多的好名字相伴,的确不寻常。烧麦的历史没有面条那么久远,大约盛起于明、清年间,北京出现烧麦是乾隆三年,浮山县王瑞福在前门外鲜鱼口开浮山烧麦铺。
由此引出了乾隆吃烧麦的“都一处”的故事。
烧麦有馅,但不同于包子和饺子将馅完全包裹起来,烧麦的部分内馅是外露的,它上端不封口。和饺子一样,烧麦的馅有多种,随地域习惯而定。但不论什么馅,一律都不封口,有意露出顶端。这好比女子知道自己美丽,总是半遮半掩,有意无意地展示她的美。所以,同样是一种面食,烧麦的身价不同凡响,首先就是由于它的特殊造型。在中国品种繁多的面食中,唯有烧麦用得上“如花似玉”的赞辞。它的优雅犹如一位风姿绰约的女子,主体部分丰满,中间紧缩如细腰,上端皱褶处突然绽放,如含苞待放的鲜花,又如花团锦簇的头饰。一只初出笼屉的烧麦,内馅透过薄得透明的皮儿,白里透红,洁白晶莹,鲜亮而性感,诱发的岂止是食欲!
烧麦南北都有,无论南方和北方,爱美的主人总把烧麦捏成一朵花。它的整体造型除了花的联想,更像是一只饱满的石榴,怎么看都是美的化身。在中国北方,面食是主食,面条、馒头、饺子,甚至窝窝头,称呼都不讲究,也不避俗。但是,说到烧麦,人们却一下子矜持起来了。烧麦几乎不涉家常,多半出现在酒楼歌肆的宴席过后,作为喜庆的收尾,几道精致的点心上桌,其中就有风情万种的烧麦。这烧麦的确不负众望,她总是花团锦簇、仪态万端地出场,赢得一片掌声。烧麦的品种很多,风味各呈其异,但从造型到命名都高雅而美丽:菊花烧麦,裹馅上笼前特意撒上金黄的蛋花碎末,状如秋菊盛开;翡翠烧麦,它的主馅是菠菜(或其他青菜),外加虾仁、火腿、鸡蛋黄等,透明,呈翡翠色,见于扬州富春茶社;另有一种桃花烧麦,核桃仁、白糖、桂花为馅,香甜惹人喜爱。
烧麦是面食中的一种,它的用料和内馅与普通面食并无太多差别,无非是用的面粉(也有用薯粉打粉皮的),一般是生面粉加水揉搓,也有用烫面的,擀皮儿,稍薄。说到烧麦的内馅,的确用料考究,虾仁、海参、鸡蛋、香菇、鲜笋、各种肉糜。三鲜烧麦、四喜烧麦,都是因用料而得名。记得幼时在家乡吃到一个品种,皱褶部分花团锦簇,五彩缤纷,几种不同的内馅仿佛是刻意分隔置放的,精致得令人痴迷,不忍动筷。烧麦到了南方,开始与南方的稻米联姻,糯米馅的烧麦多出自南方江浙一带。糯米烧麦一般常用蒸熟的糯米加相关的馅料调制而成,糯米松软,取其软糯而不烂熟,佐料是讲究的,酱油、盐、胡椒、酒以及少量的糖。
在福建平潭,因为是海岛地区,它的烧麦以海鲜为主,蟹黄、虾仁、紫菜、鲜肉,薯类的淀粉打底,因为皮儿是透明的,表里互显,五彩交映,鲜丽夺目。这一道烧麦可谓富贵尊荣,显示了南方特有的细腻丰盈。前年在遥远的宁夏银川,为着访问贺兰山下的葡萄园,主人张秉合安排我们入住银川的同福酒店。为我们洗尘的有一个丰盛的清真宴。张总点了当地最有名的菜肴,从手抓羊羔肉、葱烧海参、葱爆羊肉,到凉拌苦苦菜、凉拌沙葱、玫瑰饼和黑豆酸奶。特别是宾馆的笼蒸羊肉烧麦,冒着热气上桌,精心用香料腌制过的纯羊肉丁,其状婀娜,弱不禁风,招人怜爱。烧麦通明而有汤汁,吃时先吸汤汁,若南方的汤包,鲜美不可言状。这道银川烧麦,一下子改变了我对宾馆菜肴的成见,我为此得出结论:北方的烧麦同样可登极品。我们在银川数日,都选定同福酒店,而且餐餐必点银川烧麦,直至出发去机场的饯别宴。难以忘怀的同福酒店,我创造了一口气吞食八个烧麦犹不尽兴的纪录。
现在轮到北京迷住乾隆皇帝的那个“都一处”了。它的名气很大,我曾慕名前往,可惜没有留下佳好印象。那一天上桌的烧麦,不温不热,皮是硬的,淡而少油。其实,越是老字号,越应兢兢业业,百年如一才是。对此,我的评语是:名实难副。
二○一九年二月十九日,己亥元宵于昌平北七家
春饼记鲜
有一段时间,我很迷恋北京街头摊子上的煎饼馃子。所谓摊子,大体是架子车运载着简单的饼铛子,下面支一个简单的炉子,玉米面、面粉、绿豆粉混成的稀面浆,经过饼铛上加温,摊成薄饼,打上一个鸡蛋,摊平,翻个个,用刷子刷上酱料,要辣椒?就再加一刷。最后一道工序,是裹上一个油炸薄脆,撒上香菜碎末,成了。北京街边卖的煎饼馃子,每份四元,现在涨价了,六元。那时我总找机会在路边蹭上一个,边走边吃,很是惬意。时间久了,顿觉那刷子的确欠雅,就疏远了。这道街边美食,不是我此刻要说的春饼,但是那卷着吃的吃法,倒让我想起春饼。
春饼是春天的庆祝和记忆。民间吃春饼的习俗,缘起于迎春。它的历史久远,可以追溯到晋,而盛于唐,东晋叫春盘,唐谓之五辛盘。宋代宫廷有芥菜迎春饼之举,饼置于盘中,翠缕红丝,金鸡玉燕,备极精美。明史记载,立春之时,无贵贱皆嚼萝卜,名曰咬春,当日互相宴请吃春饼合菜。所谓春饼合菜,《关中记》说,“立春日做春饼,以春蒿、黄韭、蓼芽包之”。冬末春初,许多植物的嫩芽忍耐不住,心急,破土而出。这情景恰似是春天的序曲,诱引人们打开封闭的柴门,来到乍暖还寒的野外,踩春、咬春、打春、吃春饼,迎接春的消息。民间习俗,春饼的内馅多以应时的春蔬韭黄、菠菜黄、绿豆芽加姜丝、粉丝、肉丝混合而成,这习俗代表着内心的喜悦,是一种迎接春天的庄严的仪式,一直延宕至今。
春饼的食材以面粉为主,有外加米粉、豆粉或玉米面为原料的,大抵是因地、因俗而异。山东的煎饼也是春饼一族,煎饼裹大葱,天下闻名,它的用材除了上述米面而外,亦有小米和高粱的。山东人吃煎饼裹大葱,加黄酱,充满霸气和豪气。山东煎饼宽大,直径可达一米,要用特大的饼铛烙制,大气磅礴,一派齐鲁气象。烙饼折叠数层如布帛,坚韧劲道,贮存数月不坏。那年我清晨空腹徒步登泰山,行至中天门小憩,一卷煎饼大葱鼓舞我爬越令人生畏的十八盘,寸步维艰地直抵南天门,攀上了玉皇顶,正是煎饼之功。家乡福建饮食偏甜,怕辣,我的生啖大葱大蒜的习惯,是年轻时在军中学会的,我当年的部队是来自胶东的子弟兵组成,他们的饮食习惯影响了我。
春饼在宫中染上了皇家气象,在北方总带着壮阔平原的苍茫之气,而在温柔缱绻的南方,当然拥有了南国软糯的风格。在老家福州,旧时年节也吃春饼,主要用材是韭菜和绿豆芽,姜切成细丝,加上泡软的山东粉丝(闽地称“山东粉”)。春饼皮是外买的,馅是加工过并炒熟的。餐桌上,一家人围坐,现卷现吃。福州的春饼皮为何要外买?因为它工艺特殊,要求高,一般家庭不具备制作条件。春饼皮有专店供应,简单的铺子,在门外支起炉灶,饼铛微火加温,厨师右手不断地上下凌空抖动经过揉搓的面团,面团往下熨帖饼铛,一粘,瞬间即起,留下一片云彩般的、透明如薄纸的春饼皮,厨师再以左手掀动那薄如蝉翼的作品,一张张摞好,称斤出售,上了家庭的餐桌。
福州人迎春包春饼,总是到这样的专门店铺买春饼皮。那年我访问遥远的沙捞越,那里有座城市叫古晋,是最早的福州移民开发的,有“新福州”之称。这称呼使我想起纽约、新德里或新西兰,都带着最初移民的色彩。沙捞越古晋聚居了几代的福州乡亲,他们把做鱼丸、肉燕的工艺搬到了那里,也搬来了做春饼皮的饼铛和一套制作工艺,祖代相传。古晋街头,乡音盈耳,汉字商标满眼皆是。走在街上,吃着福州的光饼,吃着现包现吃的韭菜、豆芽、姜丝和肉丝裹就的春饼,仿佛是回到了万里之外的家乡福州。
春饼有多种吃法,包着吃的,炸着吃的,蒸着吃的,唯独福州春饼只能现场卷着吃,绿色白色相间的内馅,透过春饼的薄皮,仿佛就是“咬着”乍暖还寒的早春原野,要的就是那种新鲜的感觉、喜悦的感觉、和春天拥抱的感觉。记得我曾把这种感受告知诗人舒婷,她的回应却是对于福州春饼的“不屑”—在福建,厦门人往往瞧不起省城,总觉得福州“土”:厦门的粽子比福州好吃,厦门的春饼也无一例外地比福州强。舒婷向我炫耀她那里的春饼的内馅由多达十多种的材料构成,“福州太单调”。而我哂之。
这涉及相当复杂的饮食美学问题。窃以为,食有繁简二道,繁简各呈其趣。一般说来,闽南厦门、泉州一带,气候温湿,阳光充足,作物丰盈,食品之作偏于细腻繁复。举例说,被我称为“天下第一粽”的泉州肉粽,就是一种“繁”的极致。当年我在泉州华侨大学任教,慕名前往泉州城里最老的肉粽小店—记得是在钟楼附近,一家外观很不起眼的小店面,其间摆着简陋的几张桌椅,顾客盈门。香叶包裹的枕头形肉粽上桌,粽叶打开,香气扑鼻,外加一碗精致的薯粉制作的牛肉羹陪伴。那肉粽的内馅有极品豪华的阵容:五花肉、咸肉、虾仁、干贝、皮蛋、板栗、莲子、芋头(油炸过的)、芸豆、香菇,佐料也是五彩缤纷:沙茶酱、蛙油、酱油、蒜蓉汁。相形之下,母亲包的福州粽子却显得寒碜,重碱,有时加花生,更多的,是裸粽。多半是蘸着糖吃。
行文至此,公平而论,泉州肉粽是经典的豪华,而福州粽子却保持了本色。依稀记得当年母亲用蒲绳包粽子时拼力而为的那股“狠劲”,结实、厚重,凸显的就是一个字:鲜!鲜明的,鲜艳的,鲜丽的,春天的鲜!福州的粽子如是,福州的春饼亦如是。
二○一九年二月十九日,己亥元宵
此日京城小雪,俗云“正月十五雪打灯”,此之谓也。
包子记精
记得那年在扬州,正好赶上烟花三月时节。瘦西湖上雨丝风片,乱花迷眼。我们的画舫穿越于依依柳丝之间,春风拂面,莺啼在耳,挚友为伴,心绪畅怡。弃舟登岸,于五亭桥上,遥观远处熙春台殿影,隐约于二十四桥重荫之中,恍若仙境。那日我们行走于长堤春柳,访大明寺,谒史公祠,甚是尽兴。唯以未尝远近闻名之富春包子为憾。询之游客,得知每日上午九时,有专船载现蒸的富春包子于平山堂筵客。
翌日早起,抵平山堂,迎候。九时正点,一小舟穿越柳烟迤逦而来,大喜。平山堂这边有专门茶肆迎客。几张木质桌椅,上面备有碗碟和蘸料。坐定,冒着热气的笼屉从小船被抬了下来。赶早而来的食客安静地等待开单。记得当年要了一屉的三丁包子,另加若干普通的肉包子。肉馅有繁简,表现在个头上,五丁肉包堪称超级豪华版,个头大,皱褶多,内馅依稀可见,近于透明。因为是学生,不多钱,没敢要五丁馅的。已很满足了,毕竟是在别有风味的地方,吃别有风味的包子。扬州古称“销金之地”,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即是。这里歌楼酒肆,钗光鬓影,春风十里,觥筹歌吹。堪与此种盖世奢华媲美而骄能自立者,除了瘦西湖,可能就是名扬天下的貌俗实雅的富春包子了。
富春包子讲究荤素搭配,除鸡丁、肉丁等,必不可少的是鲜笋丁,构成鲜、香、脆、嫩的组合,以盐正位,以甜提鲜,皮薄多汁,构成清鲜与甘甜、蓬松与柔韧、脆嫩与绵软交映互补的味觉效果。说到富春包子的笋丁,引起我的一番回忆。我与扬州大学叶橹教授是老朋友,我们在学术上没有论争,却在“扬州狮子头是否应放荸荠丁”的问题上有过激烈的“论辩”。叶橹受难时被发配到高邮劳改,他认高邮为他的第二故乡。也许是爱屋及乌,他更加确认,高邮总是世上“最好”,包括高邮的狮子头也比扬州好。“扬州狮子头放荸荠丁,高邮就不放,高邮全肉。”我称赞过江都人民饭店的狮子头:六分肥,四分瘦,特别是加了荸荠丁,软糯中又有脆感,很是适口。叶兄不以为然:“肉馅加别物,是过去穷,不能用全肉,才加了别物。”
其实,扬州狮子头之所以能艳压群芳,肉馅加荸荠丁确是神妙之笔。这点叶橹不懂。我常感慨中国菜犹如中药的配伍与组方,一个方子,有主有伍。落实到狮子头,荸荠丁虽不是“主”,却是精彩的“伍”。厨师在没有荸荠的季节,笋丁、藕丁亦可替代,要的还是软糯中的那种脆劲。这点北方人不明白,也学不到,他们喜欢在四喜丸子中用土豆丁,这就叫“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叶先生以穷富代审美来论狮子头食材之主配,其谬大矣!
话扯远了,还是回来讲包子。和饺子一样,中国的包子也是南北竞秀,花开遍地。我的见闻有限,大抵而言,北方口重,近咸,南方口轻,偏甜。那年偕同李陀、刘心武、孔捷生等访闽,记得郭风先生亲抵义序机场迎接我们。宾馆的早餐有福州包子迎客,李陀一咬,愤愤然,拒吃:“这是什么包子?哪有肉包子放糖的!”他是东北人,少见多怪,不免偏颇。殊不知,长江往南,遍地皆是“甜蜜蜜”,而以无锡为最。就包子而论,广州的叉烧包可谓国中佳品,肥瘦兼半的叉烧肉,加上浓糯的汤汁,其口味咸甜谐和,想仿也仿不来的。当然还有如今满街头的杭州小笼包,六元钱一屉,一屉十个,一个一口吞,甚妙。
据说,包子的豪华版更有胜于富春包子的,那就是江苏靖江的蟹黄汤包。蟹黄乃是味中极品,以蟹黄做馅可谓奢华之至。靖江地偏,我尚未到过,难以评说。倒是在南京鸡鸣寺品尝过蟹黄汤包,也许失去地利,也许旅中匆促,印象倒是平平,并不“震撼”。但愿有机会实地“考察”一番。名声大的,还有上海生煎。顾名思义,生煎不同于一般的气蒸,有油煎的焦香,馅鲜嫩,皮焦脆,风味独特。
说到上海的煎包子,不免联想到乌鲁木齐的烤包子。新疆的小吃从馕到手抓饭,我都喜欢,但最爱却是烤包子。每到新疆,首选非它莫属。乌鲁木齐烤包子用的是巨大的圆形土烤炉,烤炉的内厢均是泥巴,羊肉大葱馅,好像是半发酵的面皮,往炉壁一贴,不多久,香气就飘出来了。外皮是酥脆的,肉馅是嫩滑的,又有烤馕和孜然的芬香,极佳。新疆烤包子凝聚着西北边疆特殊的文化风貌,以无可替代的、独特的风格丰富了千姿百态的中华烹调。
天山南北,大河上下,大地生长的小麦和稻谷创造了悠久的农耕文明,遍地开花结果的包子,以面食的一种代表的是中华文化的绵远精深。也许此刻我们最不能忘的是享誉海内外的天津狗不理。“狗不理”这名字有点俗,也有点野,但却象征着文明的一端。据说狗不理包子的主人大名高贵友,小名狗子,原籍武清杨村,1858年在天津开德聚号包子铺。生意做火了,忙不过来,顾客怨狗子不理人,包子被谑称“狗不理”。津门诙谐,雅号沿用至今,犹如京片子的“大裤衩”之不胫而走。
这篇文字的标题是一个“精”字,其意在表明代表中国餐饮的精彩之笔乃是貌不惊人、随处可见的包子。中国包子的精妙之处在它的一系列工艺的“精”:揉面,调馅,蒸,煎,烘,烤,关键则是最后一道工序—通过包子的“包”显示出它的审美性。就造型而言,天津狗不理的皱褶是十五褶到十八褶,上屉或下屉的瞬间,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柔柔的、怯怯的、一朵含苞待放的白菊花!有传言说,扬州三丁包子的皱褶可以多达二十四褶,代表二十四节气。这就叫精彩绝伦。
但不论如何,我依然心仪于半个世纪前平山堂的那顿“野餐”。清晨,薄雾,一舟破雾欸乃而至,山水顷间泛出耀眼的绿。我们以素朴的、民俗的、充满乡情的方式,等待、期许、接纳、相逢。这情景,如今已被那些豪华、时尚、奢侈所替代。当日的那份情趣、朴素的桌椅、简单的碗碟、冒着热气的笼屉,如今是永远地消失了。怅惘中,依稀记得的还是那梦一般的此景、此情。
二○一九年四月十七日,于昌平北七家
馄饨记柔
中国面食中除了面条是可汤可干的吃法外,全程和汤而吃的,可能唯有馄饨。带汤吃馄饨是常态,也有油炸着吃的,那是偶见。所以,说馄饨不能不说馄饨的汤,那是鱼水不可分的。鱼因水而活,馄饨因汤而活。馄饨在四川叫抄手,红油抄手是成都街头一绝,汤汁是红通通、火辣辣的,辣椒油、花椒油、胡椒面,全来。但是,四川抄手的底汤是鸡汤和猪骨熬制,却是不假。那年在成都,晨起遛街,商铺未开张,但店家早已收拾好几只鸡,熬汤待用。因为是亲眼所见,所以相信四川抄手的鸡汤是真货。但是成都以外,号称鸡汤的,真伪就难辨了。大体而言,总是代以味精、香醋诸物搪塞。
馄饨是面食中的小家碧玉,用得上一个“细”字来形容。它的特点是体积小,细弱的小,不似饺子馒头的大格局。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厦门鼓浪屿轮渡码头,有当地妇女街边用担挑小炉灶现煮小馄饨。当时一元钱可买一百只小馄饨,摊主用手拨拉计数,一五一十,极其精细。那馄饨小如林间落花,浮沉水中,鲜虾肉馅,白中透出红晕,美不可言。一元钱可数一百只,每只一分钱,其小可知。论及性价比,放在今天,当然是不可思议的。重要的是那份小巧精致,来自闽南女性柔弱之手,绝对是巧手细活,世所罕见。别说价钱便宜,那份精致,喻为绝响,亦不为过。
在北京吃馄饨,有叫百年老字号的,位于京城某繁华区,平日门庭若市。我曾慕名前往。紫菜虾皮香菜为汤,稀汤寡水,皮厚馅小,状如煮饺,确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数十年居京师,总共只问津一次,不想再去。倒是有一年在海淀黄庄,偶见新开小铺,专卖馄饨,去了多次还想去。那馄饨包成圆形,薄而透明的馄饨皮裹着,汤中散开,状若一朵朵绣球花,极美。细查,发现不似是包捏的,更像是薄皮如丝粘裹而成的,可见其制作之精细。记得那小铺取名“黄鹤楼”,也许竟是来自江汉平原的店家?可惜却是昙花一现,很快就消失了,而我总是惦记着。
馄饨在福建多地叫扁肉。特别有名的沙县小吃中,我每次总是点扁肉加拌面,二者是鸳鸯搭档,可谓绝配。沙县的拌面加碱,韧而柔,主要是拌料特殊,用的是花生酱。拌料置底,捞出的热面置上,另撒葱花于上,顾客自行搅拌。至于扁肉,一般馄饨肉馅是切肉或剁肉,而以沙县为代表的扁肉是打肉,即用木槌在墩板上不断敲打成肉泥。这样的肉馅口感特殊,柔韧之中有一种脆感。更重要的是它的汤清澈见底,上面漂着青绿的葱花,清而雅。一盘拌面、一碗馄饨,堪称世上最佳。
在我的家乡福州,扁肉的称呼又多了个“燕”字,叫扁肉燕。这主要是因为它的面皮用料特别,面粉、薯粉加上猪瘦肉,也是人工拼力敲打,摊成透明的薄皮,而后切成菱形小块,再包肉馅。因为扁肉燕的燕皮也是肉制品,谐称“肉包肉”。扁肉燕的馅除了精选鲜肉,必不可少的是捣碎的虾干,以及芹菜碎末和荸荠丁,鲜脆,味道是综合的,很特殊。扁肉燕名字雅致,也许是状如飞燕,也许是“宴”的谐音,它是福州的一张饮食名片,代表着闽都悠久的文化。
馄饨在广东叫云吞,这名字也很雅,云吞者,云吞月,云遮月之谓也。记得郭沫若当年曾为厦门南普陀素斋一道菜取名“半月沉江”,成为文坛佳话。可见菜名中也应有诗,菜因诗得名,也因诗而远播。“半月沉江”是,“云吞月”也是。粤菜的精致华美堪居举国之首,其他各菜系虽各有其长,但只能列名于后。而云吞是不曾列名于粤菜中的,云吞充其量不过是一道小吃而已。但广东的云吞实在不可小觑。至少在我,宁可不吃粤菜的烤乳猪、烧鹅仔,也不会轻易放弃一碗三鲜馄饨面。
有一段时间我在香港做研究,住在湾仔半山区。我总找机会步行下山,在铜锣湾街头找一家馄饨店坐下来,美美地吃一碗地道的三鲜馄饨面。吃着吃着就上了瘾,以后总找借口一再问津。从湾仔、铜锣湾,一直吃到油麻地、旺角,甚至是尖沙咀的小巷,我都能找到我情有独钟的馄饨面。我发现所有的小铺都能煮就一碗让人忍不住叫好的、地道的馄饨面:细长又柔韧的碱面,清汤,虾仁鲜肉和菜蔬,最让人迷恋的是馄饨馅中竟然包着一只鲜脆的大虾仁。
香港商家不欺客。几乎所有的店家,只要是做鲜虾馄饨的,都包着这样的大虾仁,不变样。前些日子重访香港,住在旺角,还是“怀旧”,特意过海找到我常常光顾的那家铜锣湾小店。人多,在门外排队,领号进门。食客几乎都是当地街区的居民,他们不仅是回头客,而且是常客。与之攀谈,均对小铺的馄饨赞不绝口:本色,地道,价钱公道。从沙县扁肉到香港馄饨,从火辣辣的龙抄手到家乡福州温情的扁肉燕,这道貌不惊人的中国面食,因为它的小巧玲珑,因为它的“美貌如花”,吸引了多少人的念想和期盼!
史载,早先的馄饨和水饺是不分的,二者的区分是在唐朝。“独立”之后的馄饨,自动走更加细腻精巧的路线,而与水饺判然有别:水饺逐渐成为一种主食,而馄饨依旧是茶余饭后的“随从”。在中国南部,皖南那边还保留了二者不分的“混沌”状态,那里的水饺是带汤吃的,近似馄饨的吃法。远近闻名的上海菜肉馄饨,不仅个头大得惊人,简直就是一盆带汤的饺子!一贯精细小巧的上海人,为什么会欣赏这个傻大粗的菜肉馄饨?摇头,不可解。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于昌平北七家
馒头记粗
馒头是非常简单的一种面食。发面,揉搓,切块,而后上笼屉蒸。除了酵母,或些许碱,不须任何添加。馒头不注重形态,或长方,或半圆,亦有“开花”的。一般的馒头不咸、不甜、无馅,因此,馒头又是最单一的一种主食。在北方的广袤地区,家家户户的女主人,都是制作馒头的能手。和馒头最亲近的吃食,是兄弟排行,也叫“头”,是窝窝头。窝窝头的主料是玉米面,与馒头略有不同,但制作简单却是一致的。馒头、窝窝头,名字都很俗,也都很野,就像北方人家为给孩子添寿,叫“狗剩”一样。而馒头在南方却是稀罕之物,南方人不会做馒头。在家乡福州,街上卖的馒头都是山东人做的,我们把馒头叫馍馍。如此简单的面食,家乡的妇女不会做。
在过去饥荒年月,能吃上一顿白面馒头就像是过年一般,穷人家平日是吃不上的。窝窝头也差不多,是纯粮食不掺野菜的,能吃到也算奢侈了。在北方,我常听人说,现在过上好日子了,不吃掺和面了,吃的是纯粮食了。可见生活的改善,首先体现在馒头、窝窝头这对“难兄难弟”上。在北方,馒头是富裕的象征,是穷人的最亲。时代变了,观念也随着变,如今人们讲健身、环保、绿色什么的,别说馒头,就连窝窝头也跟着吃香了—粗粮居然上了豪华酒宴,也颇得时尚人士的欢心。而在我,每逢众人争食粗粮薯类这场面,就觉得是“趋世”,多半总是“婉拒”。
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北方,可是从来都很拒绝馒头,更拒绝窝窝头。南方人的胃有点“娇气”,吃不惯这一类吃食的“硬气”。福建近水,饮食多汤类,一道正宗的闽菜,汤类占了多半,日常家居,早晚两顿稀粥。在北方几十年的历练,我总是没法适应这两“头”兄弟。就像北方人吃不惯米饭,说“吃了等于没吃”,总觉得吃不饱。他们说,馒头“经饿顶饱”。南方人的感觉却完全不同,我吃馒头总是困难,像嘴里塞了一团棉花,总咽不下去。也许是娇惯了,忘了艰苦岁月,吃着过去过年才有的纯粮食,却硬是“味同嚼蜡”。
即使如此,这道面食在我这里也留有温馨的记忆。很遥远了,那是七十年前的旧事,我随着隆隆的炮车行进在夏季的风雨中,炎热,汗湿,炮车卷起的泥浆沾满军装。部队日夜兼程,向着南方尚待解放的城市。那年我十七岁,步枪,一百发子弹,瘦弱的身子挎着沉重的子弹袋—那袋子是绿色布缝成,现在已见不到了。这是左肩,我的右肩也挎着一条袋子,那是白色布缝制的。这袋子装着晒干的馒头片,斜挎在我的右肩。数百里急行军,没有时间停步做饭,这是我们的军粮。行军中途,传令就餐,这就是当日的口粮,清水,就咸菜。后来上了海岛,挖坑道。日夜三班倒,军情危急,顾不得埋锅做饭,日常所食,也还是馒头干。艰苦岁月的记忆,很暖心,顿然消除了我与馒头的隔膜。我们不能忘记这性命交关的恩人挚友。
诸多的面食品种中,馒头最简约,也最低调,它无须任何装饰,它的使命就是充饥,喂饱人的肚子。吃馒头不需要排场,陪同它的,一碟咸菜足够了。一个馒头、一碟盐疙瘩,再加上一碗玉米碴子,此乃最佳的搭配。北方乡间,冬日暖阳,墙根屋檐有太阳处,馒头、玉米碴子粥、咸菜疙瘩,老人们围坐,呼啦吸溜,酣畅快意,也是人生一景。
我写过烧麦的雅,写过馄饨的柔,形容过它们如小家碧玉,描写过它们身姿婀娜,如花似玉。烧麦,还有馄饨,它们有自己的一份矜持和温柔,应当是女性的。而生长于北方大地的馒头,吸取了燕赵大地或齐鲁山间的豪气,粗放、刚强、一派带着林间响箭的气势。女子亲手揉捏,凭空地增强了男儿建功立业的胆气雄心。馒头到底是北方的、阳刚的,当然更是男性的。
二○一九年五月一日凌晨,于昌平北七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