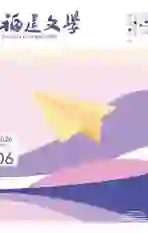默笺
2024-06-18严熙泽
严熙泽
堂姐大我六岁,是个哑巴,她原先也会说话。五岁那年的冬天,失足落水挨了冻,后来喉咙就只能“嘶嘶”的了,吃了多少药也不见好。突然有一天,就完全说不出话来了。我不曾听见过堂姐的声音,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堂姐已经哑了许多年。
开始把堂姐唤作“堂姐”的那一年,我七岁,她十三岁。初夏,大人正在农忙,也是小孩最疯的时候。那天,我在外面野完了,快到饭点便往家赶。隐约瞧见旁边一道垄上,三四个和我一般大的小孩,正追着前面一个人。他们笑着、嚷嚷着,时不时扔着土块,被追赶的人不及躲闪,倒下去捂着脚起不来了。
当时,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胆气,跳下垄就穿过田往对面跑。那块田还没有收,比我人还高的麦子把脸刮得生疼。到了旁边垄上,几个小孩早就跑远了。穿碎花布衣裳的她歪坐着,低头掸着灰。
我现在仍记得见堂姐的第一面。我问她“你怎么了”,她抬起头没有说话;我以为她听见了,便又问“你怎么了”,她还是不说话,然后手在衣服上擦了擦,从兜里掏出纸,还有一支头上有橡皮的铅笔。我有些恼火,心想我为你穿过这么一大片田,划了多少血印子,你怎么就一声不吭?却见她在纸上写些什么。
“他们叫我哑巴。”她写道。我接过了递来的纸和笔,她用手势示意我往下写。
“什么是哑巴?”我歪歪扭扭写了几个字,“哑”字我还不认识,是照着描的。
“不会说话。”
“你是吗?”
“我是。”
就这样,我认识了堂姐。
那天,我看着她沿田垄一瘸一拐回了家。她家是那头一方小小的院子,我勉强能瞧见。到了以后,似乎见她还朝我挥了挥手。
晚上,扒饭的时候,我和母亲说:“今天在田里遇见了个哑巴,女的。”
“哑巴?”母亲有些诧异。
“哪个哑巴?”她接着问,然后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
“噢,她呀。”
之后,母亲便与我讲了堂姐的事。母亲说,堂姐可以算是这附近十里八乡的小美人,即便咱们村在镇上比较偏远,也即便堂姐那时也就十三岁,还没有完全长开。用母亲的话讲,“偌大的镇上,没见过谁家有这么俊的姑娘。”堂姐还分外聪明,母亲说,别人教绣花、打毛衣,她一看就会,都不用上手示范的。
“可惜,是个哑巴。”
“唉!”我装作大人一般,叹了口气。
“你来的什么劲?按辈分,你得叫她堂姐。”母亲说。
“她爸是你爸的远房堂兄,出五服了,祖上几代坟还是挨着的。”她接着补充。
“她爸在哪?”我问。
“和你爸一样。”
后来我才知道,堂姐的父亲和我父亲都在外地。我父亲原先在村小教书,后来发的工资越来越少,为了养家糊口,便出去做小买卖。她的父亲在工地,推沙子、拉砖头,做的是力气活,一年也回不来几次。所以,她常被大小孩子欺负。堂姐虽大我六岁,但并不比我高多少,还很瘦弱,加上又是个哑巴,在田里被扔泥巴早就习以为常了。这也间接导致了她孤僻的性格,好在那会儿她已认识不少字,从镇上买来的画本、小说都能看懂,也并不需要有那么些朋友。
我第一次去堂姐家借纸笔,是那年的三个月后的秋天,我在村小上一年级的第四天。当时我不肯上学,非要晚一年八岁再上,母亲却觉得早上一年早一年出来,硬是给我报上了名。那几天我还在闹脾气,总有意无意地丢三落四,不是忘带本子就是忘带笔,有一天还忘带了书包。前三天,连着被老师在走廊上罚站,他说再这样我就要叫家长了。
然而第四天走到半路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只背了个空壳书包,连课本都没带。回去拿已经来不及了,直接去学校又肯定不行,便想着到哪儿找些纸笔应付一下。
堂姐家就在我上学的必经之路上。自从第一次见面后,我在外面野的时候,又见过她几次。但她自然是不可能与别人主动打招呼的,我也不会。谁又想让玩伴瞧见,自己与一个哑巴主动打招呼呢。所以,那时我与堂姐远没有熟到可以借东西的地步。只是突然想到,她总随身带着纸笔,家里应该会有不少。
这样想着,我硬着头皮来到堂姐家门前。她家的院子不大,但门却很高,与一圈低矮的围墙不太相称。我敲了敲门,没人应。又加紧敲了几下,有人开门了。堂姐瞧见是我,先是有些迟疑,估计没认出来。然后顿了顿,可能想起了三个月前认识的那个小男孩,便把我让进了门。
家里就她一人。堂姐拿了杯子,要给我倒水。我估摸时间不早,上学要迟到了,便赶紧摆摆手。把书包从肩上卸下来,打开来指了指,示意里面什么也没有。堂姐像是明白了什么,转身跑去灶房,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两个糙面烧饼。
我有些急,这样怎么叫聪明呢,这么笨!突然瞧见桌上摆着几张纸和一支笔,便赶紧拽过来,画了好久,写了五个字。
“借我纸和笔。”
她拿起我写的瞧了瞧,捂嘴笑了,转身进了屋。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我写的“笔”字那竖弯钩画反了方向,十分滑稽。
堂姐拿出来一本崭新的本子、一支削好的铅笔,放进了书包。把两个糙面烧饼也一道装了,然后扣上了扣。我顾不上谢她,抹了一把汗,飞一般跑出门去。这才想起来有些没礼貌,便转头喊了声:“堂姐,谢谢!”
这是我第一次叫她堂姐,隐约瞧见她笑了笑。难道听懂了?我一边往学校跑,一边想着。突然一拍脑袋:堂姐是哑巴,母亲又没说她聋,怎么会听不见呢。但那一天在垄上,她为什么要让我写字?这个问题我没有再问过她,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渐渐有了自己的猜测。大概堂姐的性格比较孤僻,用手势示意自己听得见并且要别人讲话,这本身就很滑稽,像是把她的缺陷又强调了一次。“我虽然不会说话,但能听见”,远不如用纸笔沟通来得方便和体面。
我现在依然觉得,那始终是个正常人看来不太合理的习惯。但是,命运却让她这个习惯变得合理,甚至更加纯熟了。堂姐虽不聋,但她认识了一个又哑又聋的瘸子,那人后来成为我的堂姐夫。
我在村里上完小学后,接着在镇上读了初中,三年后又考上了县中。小学五年里,我隔三岔五地去堂姐那里借纸笔,也渐渐养成了和她写字沟通的习惯。堂姐的字很秀气,虽然她只在特殊学校上过两年学,倒是比我这个正规学校出来的字要好看。堂姐的字也写得飞快,而且她很有条理,分析问题的时候,一二三四、清清楚楚,比不少正常人看得还明白。
初中三年,我在镇里住校,便不常回家了。但每次一回来,在家里放下东西,就往堂姐那跑,与她“聊聊”学校里的情况,还有镇上的新奇事。这时候,堂姐的字便写得更快了,她两眼放着光,问这问那。每次,堂姐总要与我“聊”上很久。她的朋友实在太少了,我算是为数不多的其中一个。
高中的第一个周末,我照例回家点个卯,就去了堂姐那里,一进门就见她一人在桌前出神。她见我来了,默默写了行字递给我。
“我要结婚了,十一,记得来。”
我很是诧异,虽然那几年我已不常回家,但也并没有听堂姐自己或者我母亲提到过这事,她突然就要嫁人了。正想着,堂姐把那张纸又抽回来,接着写。
“羡慕你,能上大学。”
这句话让我很惭愧。我的成绩并不好,初中三年都是磕磕绊绊的,中考超常发挥才考上了县中,还只是个普通班。能不能考上大学,能上什么样的大学,对当时的我来说,都是个未知数。
后来,我与堂姐又“聊”了一会儿,大概明白了些情况。
那个男人虽是隔壁村的,但是与我家、堂姐家都不远,在两个村子交界的地方。他比堂姐大三岁,算是同龄人。他一出生就是聋的,后来怎么也学不会说话。更不幸的是,小时候吃了镇卫生所发的丸子,大家都没事,他却开始腿疼,然后就有些瘸了。镇上来的医生说,这是小儿麻痹症,至于与丸子有没有关系,也说不清楚。不过,听说他父母后来去镇上、县里都跑过闹过,最终赔了一笔钱。他父亲靠这个在镇上开了间杂货铺。
其实,堂姐夫家的条件还算不错。他长得也周正,就是聋哑、有些瘸。当时,堂姐已经二十出头,仍找不到婆家,谁家又想娶一个哑巴媳妇呢。但那个岁数的姑娘,在村里已经很大了,再拖下去可能真就嫁不出去了。当时,堂姐夫虽然家里条件说得过去,但由于残疾的原因,也怎么都讨不到媳妇。后来有人给两家牵了线,双方父母见了几次,合计合计,便将他俩的婚事定了。
堂姐和我“说”,她父亲在外面本就挣不了多少钱,岁数大了更加找不到活。她母亲估计也是看上了他家的条件。
“人家在镇上开了铺子,还盖了三四间砖房,你还要哪样?”堂姐一字一句,在纸上“复述”着她母亲的话,末了还画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你想嫁吗?”我见她有些不太情愿。
“我能选吗?”堂姐这几个字写得很潦草。给我看后,立刻拿橡皮用力擦去了。我猜她是怕家里人见到,不想留下痕迹。
后来,我再见到堂姐的时候,是在堂姐夫家院子里办的婚礼上。那天我从县里回来,没赶得上接亲,直接去了镇上。堂姐夫家的砖房确实气派,院子也大,杂货铺就在院里一角,有个窗对着外边。他家一共摆了六桌,我找到母亲坐的那一桌,在第二排的左手边。母亲怨我怎么才来,是不是赶车误了点。她告诉我,堂姐夫家说院子不够大,过几天去村里还要再摆酒席,请乡亲们热闹热闹,再散散糖。
我抬眼向前,堂姐也正往我这边看,见我来了,微微点了点头。她和堂姐夫都是一身红,还戴上了耳环和镯子,堂姐夫拄着手杖,气色也不错。要是大家都不会讲话、都听不见该有多好,我当时这么想着。外表看,堂姐和堂姐夫还是很般配的。
拜堂、酒席之后,我拿出一张红纸,上面写了“祝堂姐、堂姐夫百年好合、早生贵子”,递给了他们。份子钱母亲已经出过,这个算是我的。堂姐冲我笑笑,堂姐夫也动了动嘴,像是“谢谢”的口型。然后他们便转身进了屋。
堂姐就这样找到了另一半。堂姐夫的父亲把铺子和院子给了小两口,自己回村里了。堂姐夫一个人操持生意,明码标价、不讨价还价,倒也省了不少麻烦,把账算好写在纸上就行。堂姐在家里忙家务,另外再做点针线活,帮人缝缝扣子、补补衣服。
后来我又去过几次他们家。堂姐已经结婚,也不便常去。桌上、橱上、床上,甚至厨房的灶台上,哪里都是纸笔,比堂姐原先家里的还要多。一个聋一个哑,这是他们唯一的沟通方式。原先堂姐夫认识的字不多,还写得歪歪扭扭,后来也渐渐有模有样了起来。
有一次我去看堂姐,堂姐夫出门进货去了。堂姐倒了两杯水,在我那杯里,特地冲上了铺子里卖的橘子粉。我与她“聊”了一会儿。
“日子还行?”
“还行。”
“对你咋样?”
“不错。”
“挺好。”
“我和他能说话、能听见,就更好了。”
堂姐突然的这一句话,让我有些默然,但又有些欣慰。堂姐以前时常写“我要是能说话就好了”,现在已将聋哑的堂姐夫放进她的思虑之中了。
上天终于眷顾了他们一次。婚后第二年底,堂姐和堂姐夫的孩子出生了,是个不聋不哑、健康漂亮的女孩。堂姐夫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还找了个老妈子带孩子,减轻点堂姐的负担。
堂姐和我“说”,听到我侄女第一声喊“爸爸妈妈”的时候,她实在是忍不住哭了。堂姐夫也明白了什么,边哭边笑。后来侄女稍大了些,和我说:“堂舅,我爸爸妈妈不会说话,他们从不吵架,有事情都是写字!”我摸摸她的头,想着,你爸妈可真想好好吵一次架啊。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市医院做了医生。堂姐和堂姐夫还在老家镇上,他们的女儿也从小学开始,上了初中、高中,然后是大学,日子眼见是越来越好了。这些年,我娶妻生子,父母也搬来城里住,去镇上越来越少了。再加上大家都有了手机,沟通起来更加方便,所以我去堂姐那里每年也就一两次了。
前些天正在上班,突然来了个电话,我接通了。
“你好,请问哪位?”
“堂舅,昨天给你发消息你也不回。”
“当时在忙,真不好意思。”
“我刚在网上看到,现在有声带修复手术了,我妈还能治吗?”
“这我得问问,我们这边可能还做不了,去大城市才行。”
“谢谢堂舅。”
“先别和你妈讲,等有准信了我再告诉你。”
“知道。”
挂了电话后,我去找有关科室的同事问了问。他们的意思是,目前声带修复手术还处于起步阶段,只在一些顶尖的大医院才能做,效果也因人而异,并且存在风险。更何况,堂姐已经哑了三十多年,当时怎么哑的原因也不清楚,又胡乱吃了不少药,能发声的希望非常渺茫。同事还委婉地表示,目前做这种手术的,大部分是靠嗓子吃饭的歌手、主持人,他们负担得起高昂的手术费。
堂姐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村妇女,就算去大城市医院,满足手术条件了,但花了一大笔路费、手术费后,也很有可能人财两空。我后来又打了个电话,和侄女说了情况。听完后,她沉默许久,说要和她妈再商量一下。
第二天一早七点多,我正在食堂吃早饭,手机“叮咚、叮咚”收到了两条消息,应该是堂姐。这些年,发短信的人已不是很多。但堂姐说那些上网的东西她学不会,短信也发习惯了,所以仍用着这种略显过时的沟通方法。
“堂弟,谢谢关心。那事你侄女昨天和我讲了,我也仔细想了想,还是要给你回个信。我现在不想治,我们家好不容易走到今天,孩子也快大学毕业了。”
“以后孩子用钱的地方多着呢,我现在治是拖累她。你也说了,不一定治得好,那花冤枉钱干啥?这么多年,我不也过来了。”
因为短信字数有上限,所以堂姐总是能省则省,尽量把几件事压在一条短信里说完。并且,没有重要的事,她也不会给我发短信。像这样分成两条发很是少见。
我读了几遍堂姐的短信,有些沉默。虽然我也觉得,这其实是他们家最理性、最明智的选择,但是这样想,对于哑了三十多年、刚看到点希望的堂姐来说,又显得那么不近人情。
我编辑好了短信,“好的,等技术成熟了再看,我相信总能治的。”刚准备发送,“叮咚”一声,堂姐的又一条消息来了。
“就算治,也先治默笺她爸,我不要紧的。”
“默笺”是堂姐和堂姐夫给我侄女取的名字。堂姐想出来并征得堂姐夫同意后,他们一起去给孩子上了户口。
当时,双方的老人都反对,这名字不符合辈分,难听又难写。那天,我正好去他们家串门。房间有些凌乱,估计又是不欢而散。堂姐坐在床沿啜泣,堂姐夫抚着她的背,侄女在旁边小床上睡着。
抬头见我来了,他们有些尴尬,赶紧用手势招呼我坐。我看见地上有张皱巴巴的纸,便捡了起来。
“默笺。”
“好。”
无声而有力的沟通,是他们早已习惯的默契。
责任编辑韦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