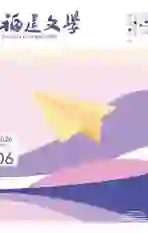会飞的男人
2024-06-18邝立新
邝立新
玻璃幕墙外依旧是熟悉的风景。蜿蜒起伏的街巷,白墙灰瓦的楼房,遒劲苍郁的法国梧桐,流动的汽车与行人。几座造型奇特的高楼拔地而起,显得有些突兀。透过高楼之间的缝隙,隐约望见一汪淡蓝色的湖水,湖面游弋着几艘黄色鸭子船。湖后面是云雾缭绕的黛色山峰,山顶似有白色球形物体缓缓转动。
伟雄在这幢高楼东北角房间待了近十年,日复一日地写稿子。坐在工位上心烦意乱时,他便起身走到玻璃幕墙前,活动身体,看看远处的风景。外面的风景没有多少变化,他的身体却在机械而固定的劳作中变得衰老,腰颈疼痛,眼睛酸涩。他把头伸出窗外,吸入外面的新鲜空气。他甚至要控制自己想要飞翔的冲动,这种冲动不知从何而来。说来难以置信,他和阿辉是在这种情况下相遇的。
那天他像往常一样站在窗前,看见几根绳子在外面晃荡。每隔两三个月,大楼物业会安排蜘蛛人清洗外墙。他看到这些悬挂在空中的人,那股莫名冲动愈加难以遏制。这时,一个人影沿绳子缓缓降下,挡住他的视线。他看着眼前的蜘蛛人,感觉眼熟,却想不起来到底是谁。过了几秒钟,他的脑子忽然闪过一个名字。他大声地喊“阿辉、阿辉”。但隔着30毫米厚的钢化玻璃,外面的人对他的呼喊浑然不觉。他试着招手,窗外的人似乎注意到他的动作,没有加以回应。也许阿辉早已习惯别人的围观或好奇。他用沾了水的短柄拖把擦拭外墙玻璃,水滴从玻璃上滑落,清晨的阳光透过玻璃进入房间,映在伟雄因为兴奋而略微变形的脸上。
几个小时后,他终于在地面见到全身被汗水打湿的阿辉。在他的记忆里,阿辉似乎没有长高多少,但身材更加健壮敦实,皮肤黝黑。阿辉显然也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伟雄,他腼腆地笑着,露出白皙牙齿。他跟工友介绍,这是他小时候最好的伙伴,在这座大楼里上班,大学生、白领。同样晒得黝黑的工友们投来羡慕眼光,一位头发稀疏的老哥说:“你们长得还蛮像,不会是失散多年的兄弟吧!”一群蜘蛛人晃动汗津津的头颅笑起来。伟雄约阿辉晚上一起吃饭,好好聊聊。
伟雄回到办公室,神情仍有些恍惚。他与阿辉在镇上的老家门对着门,幼年就在一起玩,童年时光如影随形,不知道在一起干了多少坏事。直到他上高中,阿辉出去打工,两人的联系才渐渐稀少。他们最近一次见面,应该是十年前,他在文星镇上见到阿辉,两人相约到宗祠贴对联、放鞭炮,跪在祖宗牌位前烧纸、磕头。这些年他回去少,阿辉也四处闯荡,为生活奔波。前不久他听父母说起,阿辉也在这座城市工作。他本想找机会见个面,却屡屡被手上文稿耽搁。
那份名为《摩天大楼记》的稿子从年初开始动笔,倏忽间已过去小半年,修修改改不知多少次。如果没有意外,还会继续改下去。他打开邮箱,看到一封标注为红色字体的邮件,里面写着修改意见:“内容基本都有,但感情略显不足,请继续修改。”交稿时间是三天之后。稿件主要论述摩天大楼曾是城市文明和现代工业的象征,但也存在诸多问题,未来该如何发展等。改到如今这种程度,他已经没有任何想法,只盼能早日交稿。他觉得自己受到的折磨就像《死屋手记》里的囚犯,被强迫着把一桶水从一只桶倒进另一只桶,然后再从另一只桶倒回原先的桶里,如此循环。写稿子本身并没有那么痛苦,只是找不到任何意义,他甚至从未见过用这份稿子的人。所有的指令都通过冷冰冰的邮件下达,所有的回复也都是邮件。他忽然想到,与蜘蛛人阿辉的交谈,或能解决“感情略显不足”的问题。
时值6月傍晚,夕阳沉入地平线,天空从青灰变幻成绯红。白日棱角分明的建筑,此刻也变得柔和起来。树身斑驳的梧桐矗立在马路两侧,行人从树下匆匆走过,仿佛想刻意逃离什么。他钻进一辆白色网约车,车上弥漫烟草与汗水的气味,司机神色漠然。他走进清江路那家烧烤店时,发现阿辉已经在里面等他。
店里人不多,他们找了靠窗户的位置坐下。多年不见,加上生活经历迥异,两人一时间不知该从何说起。阿辉抓起一把毛豆,一颗颗剥开塞进嘴里。他的手指极为灵巧,剥起来速度奇快,像动物园里剥花生的猴子。这是伟雄经常光顾的烧烤店,店面不大,生意很火,去晚了还没座位。圆头圆脑的老板看到他来,身体微微前倾,满脸堆笑跟他打招呼。扫码下单不久,一份份吱吱冒油的羊肉、羊排、羊腰、凤爪端了上来。两杯冰镇啤酒进入体内,两人才找到共同话题。
他问阿辉怎么会做起这份工作。阿辉说他之前在广东那边的工厂,但加班太多,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也就四五千元,便出来跟着别人做事。他做过网吧管理员、摩的司机、贩卖手机的黄牛党,还干过地产中介、快递小哥,几乎干遍了他能干的工作。后来也是这边朋友介绍,说高空作业赚钱多,还是日结,不用加班,他便努力考取高空作业证,进入这个行业。伟雄说:“你们收入还不错吧?”阿辉说:“都是拿命换的,不像你们坐在办公室里吹空调、敲键盘就能挣钱,多好。”伟雄笑着说:“其实也没那么轻松,至少没你想的那么轻松。”
伟雄不想多谈论自己的工作,只是大概告诉阿辉,他在一家智能写作公司工作,为客户提供文稿起草服务,有政府官员、企业高管,也有高校教授。说起以前在文星镇的日子,两人都有些唏嘘。镇上当年很热闹,大街小巷里都有许多小孩,孩子之间拉帮结派,为了莫名其妙的事情打架。那个当年带他们玩的大哥,几年前意外去世,留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其他的小伙伴,也失去联系。他和阿辉如果不是机缘巧合,也不会在这里碰面。他们举起啤酒杯,仰头一饮而尽。
伟雄问阿辉:“你们爬那么高害不害怕?”阿辉说:“开始当然也怕,干得多就习惯了。”相比流水线上的工作,阿辉说他更愿意在户外,人在半空,视野开阔。在不同的高楼作业,就像在城市里飞来飞去。所以他更愿意被人称作飞鸟,而不是蜘蛛人。哦,飞鸟,倒是个不错的意象,或许可以写到稿子里。如果把蜘蛛人比喻为飞鸟,那么摩天大楼就是参天大树。城市里高矮不一的建筑,就像森林里高高低低的树木、灌木和草丛。人们就是生活在其间的动物,水泥森林的统治者、劳作者。说是统治,似乎有点高估自己。阿辉见他陷入沉思,便举起啤酒杯,再次碰撞。
他回过神来,突然对阿辉说:“下次你能带我去体验空中作业吗?”阿辉愣了一下才回复:“去看看可以,但不能随便上去,要先把高空作业证考出来。”阿辉说:“你不会想干这个活儿吧?这挣的是辛苦钱,哪有你在办公室待着好。”伟雄也说不清他为什么想去高处,也许他的前世是一只飞鸟,却困在牢笼之中。
烧烤店里人多起来。人们说话的声音在狭小空间里回荡,香烟白雾与炭火烟尘交织在一起,店里变得嘈杂起来。伟雄喝下三大杯啤酒后,头也有些沉重。他们结账出来,看见路边停着许多车,有人扶着电线杆呕吐,有人坐在马路边抽烟、喝啤酒。夜晚气温降下来,甚至透着一股凉意。“那改天再约?关于摩天大楼,还有事情想请教。”伟雄说。阿辉点点头,挥手跟他告别,身影没入暗淡街巷。
妻子对他的晚归并没有抱怨。她已习惯伟雄没日没夜加班,反而对他偶尔正常时间回家感到意外。他们住在一套三居室房子,收拾得很干净。妻子几乎把所有的热情和精力都花在清洁上。她每天都要把家里清扫一遍,每个月都要洗一次床单、被套,顽固地用手洗衣服。地板偶尔出现的灰尘、毛发、污渍,都会让她抓狂。他对此不太理解,他总觉得除了清洁和卫生,生活中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家中唯一无法清理的区域,位于落地玻璃窗的外面。客厅朝西这片区域视野开阔,透过玻璃可以看到波光粼粼的浩荡江面。经年日久,窗外蒙了一层黑灰,还有白色的鸟粪,昔日明亮的玻璃变得雾蒙蒙。保洁阿姨尝试用磁吸式清洁器来清理,但很难擦洗干净。伟雄说或许他可以爬到外面试试,妻子白了他一眼,说你以为你会飞啊。有一回,她不知从哪儿看到擦玻璃机器人,让他买回来试试看。他看价格要五六千元,有些犹豫。今晚,妻子再次跟他提起这件事。他想到白天的经历,随口说也许可以让阿辉帮忙。他跟妻子解释阿辉是谁,做什么工作。
妻子得到他的承诺,神色缓和许多,很快发出轻微的鼾声。他躺在床上,腰肩部位隐隐作痛,翻来覆去难以入睡,尚未完成的稿子涌上心头。人工智能撰写的初稿提供许多素材:高达828米的迪拜哈利法塔是世界第一高楼,如今已成为世界知名的旅游观光胜地。上海中心以632米的高度,居世界摩天大楼第二高度。沙特麦加皇家钟楼饭店也超过600米。在广州、深圳、北京、天津、台北等中国城市,还有许多超过500米的摩天大楼,都是当地有名的地标性建筑。摩天大楼的运营和管理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作,电梯、消防、清洁、供水、安保都是艰巨挑战,寿命到期后的处理也是一项难题。他把这些资料都用上去,标题也用心打磨,邮件所说的“感情略显不足”是什么意思?谁对摩天大楼有感情?是那些城市的管理者、规划者,还是在大楼里工作的人们,或依赖大楼生活的安保、清洁工人?不同角色的人对摩天大楼有不同情感,或许可以从多个维度来论证。
他迷迷糊糊想着这些事,自己仿佛来到大楼外立面。微风徐徐,阳光刺眼,他似乎克服了重力,从地上腾空而起,在空中升降自如,就像城市森林的飞鸟。他看到大楼里那些终日忙碌的年轻人,他们眼神专注地盯着电脑屏幕。他心里忽然生出同情,他们也许会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但始终只是流水线上一颗随时被替代的螺丝钉。一颗螺丝钉损毁,很快有新的螺丝钉补上来。他们就是墨盒、纸张或键盘、鼠标之类的耗材。恍惚间,他似乎又回到格子间的固定座位上,他看到悬挂在空中的人明明就是阿辉,并不是他自己。他本想呼喊阿辉,却说不出话来。
阿辉一开始下意识拒绝他的请求。他说清洁公司有明文规定,不准员工在外接私活。伟雄说这不是私活,是朋友之间帮忙,而且他在妻子面前有承诺。阿辉只好应承下来。好在楼房本身并不高,对于阿辉而言不难,他让伟雄在上面看好,不要让楼房边缘部分磨损绳子。他侧身从楼顶下去,带着擦洗工具降到伟雄家外面,用短柄拖把和特制洗涤剂将那些陈年污垢一一冲洗干净。同一单元的人看见蜘蛛人在外面作业,也纷纷上来询问情况,想请阿辉帮他们也清理一番。
妻子看到透亮的玻璃窗,紧蹙的眉头舒展开来。她热切地挽留阿辉吃饭,说你们俩是发小,多年不见,又帮我们解决难题,无论如何不能走。阿辉看着伟雄,他自然附和妻子的意见。阿辉只好留下来。他坐在客厅时,跟伟雄聊起这套房子。伟雄说,这是他和妻子三年前买的,花了大几百万,耗光他们所有的存款(包括父母的资助),并为此背上沉重的房贷。还好房子本身在升值,让他们心里稍微好过些。阿辉说你们好歹还能在这边安家,他是没办法也没想法,以后只能回老家县城买一套。伟雄说他也不想活得这么辛苦,整日受折磨还不能有任何想法。
阿辉离开后,妻子细致清理一遍地面,还用消毒液浸泡刚刚用过的碗筷。伟雄看着她做这些,没有说什么。他习惯了妻子对洁净的执着,她也许并非嫌弃别人,只是心里过不了那个坎,仿佛活在一尘不染的环境中,她才是安全的、安心的。他自己不也是如此吗?很多事情都是心中有执念,放不下,看不开。
改过的稿子发送过去,一段时间没有任何回音。在他的工作经历中,这也是寻常的事情。事实上他对于稿子的用途并不了解,许多他呕心沥血写出来的东西,最终不知去向。公司审稿人是比较神秘的存在,跟他都是邮件沟通。审稿人不会跟写稿人解释为什么要这样改,也不会告诉他们客户满意与否。等到写稿人快要遗忘,审稿人突然给你发邮件说稍加调整就可交稿。伟雄后来分析,公司或许根据形势做出预判,提前选定主题,研究起草,一遍遍修改,作为储备稿件。待客户提出这方面需求时,把对应的稿子找出来。这篇《摩天大楼记》估计也是如此。
他暂时把这件事放在一边。待在格子间无所事事时,他跟阿辉联系,能否到他的工地上观摩。阿辉说这两天就有一趟活儿,作业地点是本市地标银河大厦,有兴趣可以来看看。他当然知道那幢建筑,他在玻璃幕墙前曾无数次眺望,甚至幻想过有一天会爬上去,那是一座300多米的超高层建筑,矗立于城市中央。他反复观看过那部名为《徒手攀岩》的电影。亚历克斯·霍诺德为了攀登美国加州约塞米蒂国家公园酋长岩绝壁,借助绳索上千次练习、规划路线,最终徒手爬至顶点。亚历克斯登顶后对自己说:“我没有向任何一项东西妥协。是的,包括爱情和生命。”这句话对伟雄触动很大。他问自己能够为热爱的事情放弃什么。他也说不清楚。即便是做出一点点改变,似乎都很艰难。
空中作业没有伟雄想象的那么浪漫。他站在银河大厦天台,望着深渊般的地面,头皮一阵阵发麻,腿脚控制不住颤抖,但忍不住想试试。阿辉他们似乎见怪不怪,按照常规套路固定绳索,系上安全带。等安全措施检查到位,只听见一声令下,七八个蜘蛛人从楼顶翻身下去。他望着一根根晃动的绳索,天台上空无一人,心里也没有着落,后来干脆坐高速电梯来到一楼。他看见阿辉他们悬在空中,一层层清洗,一层层下降。近中午1点,蜘蛛人陆续返回地面。
中午照例吃清洁公司提供的盒饭。阿辉提前交代过,盒饭多送一份。伟雄像他们一样,坐在台阶上,手捧温热的塑料饭盒,埋头吃起来。这是一份咖喱牛肉饭,配了青菜、酸豆角和紫菜蛋汤。伟雄许久不吃盒饭,尤其在户外吃,别有一番滋味。大楼的饭菜有一种恒久不变的气质,不同食材能做出完全相似的味道。
吃罢,那位头发稀疏的老哥掏出香烟,给每人发了一支。伟雄推辞说自己不会。老哥笑嘻嘻说:“试一下嘛,你想跟着我们做这个事情,不抽烟哪行?”阿辉此时已经喷出白色烟雾,对他点点头。伟雄便也不再推辞,把香烟接过来点上。他之前也抽烟,婚后妻子有意见,他便下决心戒掉。老哥问他为啥要跟着他们,好好的写字楼不待。伟雄说自己在写一篇关于摩天大楼的文章,想要了解情况。一起干活的兄弟,听到伟雄这个目的,纷纷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他。
他们无一例外是冲着日薪600—800元的待遇来的,但各有各的目的,有的是攒钱回家盖房娶媳妇,有的是为子女挣学费,也有的创业失败来赚钱还债的。但没有一个是因为喜欢这个来干的,阿辉当然也不是。他们每天干活前,都会祈祷自己平平安安,活着回来,就像下井的煤矿工人——尽管这种事故发生的概率并不高。他们跟幕墙里面的人通常不交流,也没有办法交流,但有时会看到一些不该看到的东西。他们什么也不会说、更不能录下来,这是他们的职业操守。摩天大楼是他们赖以为生的土地、森林、矿场,也是随时可能夺去他们生命的炼狱。
他不太好意思说,如果他有一天从事这个工作,可能是因为喜欢这种挑战和刺激。他不会为了钱冒生命危险,但在城市森林里“飞翔”的想法让他兴奋,他已经很久没有体验到这种兴奋。他甚至感觉到背部骨骼挤压、皮肤瘙痒,似乎正生发出什么东西。那是冷冰冰的邮件和文稿无法给他的,也是十几年陈设不变的办公室格子间和一成不变的餐食无法给他的。也许邮件那头的意见是对的,他对这份工作没有多少热情,几乎无法避免地出现“感情略显不足”的问题。
几天后,他收到新的邮件。审稿人给出的意见是:“新的稿件重点讲述摩天大楼与人的关系,摩天大楼由人建造,供人使用,也因此衍生出新的职业,包括你说的蜘蛛人、管道工、安全员等。摩天大楼离不开人,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可以在这方面继续深挖,尤其是城市森林与飞鸟的概念。”至于如何“深挖”,邮件并没有明确的说法。他靠在人体工学椅上,望着窗外那片湛蓝天空,思绪陷入茫然之中。审稿人的意见往往大而笼统,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却不知从何下手。
邮件要求的交稿时间是两天后。他想了半天写不出一个字,只好先收拾东西回家。他到这里工作十年,除了往返于公司和家,对这座城市谈不上多熟悉。那些外地人眼里的风景名胜,他也没怎么去过。稿子写到深夜,身心俱疲,只想着早点回家、洗澡睡觉。有一次,他加班到深夜两点多,经过老城墙下面小公园时,发现里面竟然熙熙攘攘挤着许多人。他们用LED灯照明,上面摆放着许多新老物件,有人蹲在地摊前讨价还价。后来他才知道这是鬼市。难道深夜出来摆地摊也能挣钱糊口?也许对那些生活要求不高的人,的确是够了。今天回家还算早,公园里只有几个跳广场舞的老太。那些人真如鬼魅一般,深夜出动,天亮便隐身。他有几次故意加班到凌晨,就是为了去逛鬼市,尽管也没什么想买。
他推开门时,妻子正俯身清洁地面。看到伟雄迈腿进来,妻子用略显夸张的语气提醒他地还没拖完,千万别进来。他只好倚在门口,掏出手机刷了起来。他看到阿辉发来的信息,说他们公司最近业务繁忙,想招聘一批蜘蛛人,问他有没有兴趣。阿辉又发来一条,说只是开个玩笑哈,你不可能来干这个活儿。伟雄回复说:你把具体信息告诉我,我会尽快回复你。他好几次想跟妻子说工作的事,但话到嘴边又有些迟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阿辉这条信息,他似乎下了决心。
妻子的反应没有出乎他的意料。她盯着伟雄:“你不要开玩笑,工作稳定或赚钱多少还是其次,你确定能干这个活儿?”伟雄说:“应该可以,刚开始有点害怕,多干几趟习惯就好了。”妻子确定他不是开玩笑,厉声道:“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在办公室里写稿子有什么不好?非得去干这种体力活,还是高危行业。”“可是我真的不想写,一点意思也没有。”“有什么工作是有意思的?在家里拖地、洗衣服有意思吗?我不是天天得做。”“可是,我们应该有选择自己职业的自由。”“是不是你那个老乡对你说什么?可我们还有高昂的房贷……”
他最初对写东西是有兴趣的。他在大学时读了大半个图书馆的书,经常写东西发在QQ空间和各种论坛上。正因为不想虚掷自己的天赋,他才选择进入写作公司。他曾经是这家公司最有才华也最勤奋的员工,起草过许多重量级、有影响力的稿件,尽管这些稿件并没有署他的名字。但时间渐渐消磨他的锋芒和热情,他一遍又一遍改那些不知所云的文章,仿佛在服一场没有期限的劳役,又像套着眼罩原地转圈的驴,直至耗尽所有的心力。写作成为纯粹的谋生手段、与绩效指标挂钩后,写文章曾带给他的快乐和成就感消磨殆尽。而摩天大楼就站在那里,触手可及,只要克服心中恐惧,用自己的手和脚,就能一座座攻克它们。
身边的女人不再发出声音,他却毫无睡意。文稿、格子间、摩天大楼、飞鸟、蜘蛛,这些词语在他脑子里交织纠缠。他换了无数种睡姿,却无济于事。不知晚上几点,他从床上爬起来。他穿上衣服,悄无声息走到客厅。他在沙发上呆坐一会儿,看见暗夜中仍有几许亮光。他走出家门,走到街上。街上空无一人,只有昏暗的路灯和飒飒作响的行道树。几只野猫窜入草丛之中,不见了踪影。他快步往前走,身上渐渐有了汗,身体微微发热。他摆动双臂,慢慢跑了起来。他跑过大桥、跑过城墙、跑过街巷,跑过人影憧憧的鬼市,跑过霓虹闪烁的高楼。他也不知道要跑到哪里,他只是想跑,仿佛只有跑动起来,身体才真正属于他。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他把精力投入文稿修改中。不管有多少想法,这是一项不得不完成的任务。人与摩天大楼是什么样的关系?他认为或许可以把摩天大楼看成一个人,一个人造的巨人。人们建造它、膜拜它,又使用它、消费它。飞鸟离不开大树,大树也离不开飞鸟,彼此是一种共生共存关系。高楼是权力的展示,是权力者意志的外化,是垂直的社会等级秩序,对人的存在构成某种压迫感。他想在下一稿里,把这层意思表达进去,用一种更诗意、更感性的表达。
写稿间隙,他会起身到窗前看看远处的风景。外面的风景没有多少变化,近处的楼房、街巷、行人、车辆,远处的湖泊、山峰、摩天大楼,还有山上的白色球形物体。他十分好奇那缓缓转动的白色物体,到底是什么东西,有一天他或许能爬上去看看,等忙完这篇稿子吧。阿辉见他不是开玩笑,帮他报好名,让他过两天来面试,到时有一个现场考核。公司那边阿辉会帮忙打好招呼,只要身体素质合格、没有恐高症,一般都能通过,关键自己要想好。其实伟雄也没有完全想好,他唯一能确定的是,未来十年,他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他总要为自己做点什么,或许不需要征得她同意吧。“可是,我们应该有选择自己职业的自由……”
修改过的稿子提交上去,他同时在邮件里委婉地表达辞职的意向。这一次倒是很快有回复,审稿人希望他慎重考虑,如果对薪酬不满意,也可提出他的想法,只要在公司承受范围内都可以考虑。邮件还回顾这些年他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说公司在人工智能写作领域已经领先业内,未来有上市的打算,希望他能留下来,也许有机会成为公司合伙人,实现财富自由,如何如何。但他始终没有接到电话,也没有人跟他面谈。他忽然想到,邮件那头与他交流的“审稿人”也许是人工智能,这在技术上完全能做到。想想这十年,除了偶尔露面的老板和极为精简的行政人员,他所接触到的同事都是他这样的文字工。也许所谓审稿不过是机器学习并不断迭代给出的意见。他们日夜加班,不过为机器写作提供大数据训练样本。迟早有一天,他们都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他盯着白色的电脑屏幕,仿佛看到一串串代码在流动,代码后面是一副狰狞面孔。他死死地按住电源键,直到屏幕突然变黑。他倒在人体工程学椅子上,闭上眼睛,抱紧双臂,大口大口地呼吸。房间里灯光忽明忽暗,一道闪电划破夜空,雷声在耳边炸响,大雨浇灌而下。
考核在一幢11层的高楼举行。身上系了保险绳,下面铺了厚厚的气垫。阿辉跟他说,技术本身并没那么复杂,最重要的是克服恐惧,把自己想象成一只鸟,离开地面,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有七八位跟他一起参加考核的人,其中两个迟迟不敢下去,好不容易爬下去,在空中大声呼喊救命,最后被工作人员强行降至地面。他从天台下去的时候,竟然还有点兴奋。那些在脑子里预演无数次的场景,终于变成现实。6月的热风拂过他的身体,阳光照在他脸上。他呼吸着温热的空气,听见心脏怦怦跳动着。他控制着绳子一点点下降,完成规定动作。
妻子嘱咐他有空去跑步、游泳或撸铁,不要老是坐在电脑前写东西,久坐伤身。那天以后,他喜欢上夜跑,晚上的街道空旷静谧,夜晚的人们面目模糊,风也有一种别样的气味。跑动起来时也能稍微缓解背部莫名的疼痛,那些疼痛和瘙痒时时折磨着他,以至于睡觉也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是他固定的跑步时间。妻子说,为什么要深夜跑,早点起来锻炼不好吗?说归说,也没有明确反对。他们之间除了必要的沟通,真正能待在一起说话的时间很少。伟雄觉得这样也挺好,很多事情他不想解释,也解释不清,这样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吵。
他向写作公司请了几天假,邮件回复让他好好考虑。他想给自己一点缓冲,也许能做出更明智的选择。他按照老时间出门,坐地铁到清洁公司体验生活。他没有实质性任务,只是帮阿辉做些辅助性工作,检查安全绳、传送水桶、拖把、处理突发状况等。这份工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浪漫,更多的是重复的机械性劳动。最大的挑战是不同高楼外立面千差万别,有的清理起来极为困难,甚至有一定危险。但只要按照规程操作,一般都没问题。打听下来,收入跟他在写作公司差不多,但加班比以前少许多。他因此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这也不是坏事。
妻子打来电话时,他正在银河大厦天台做准备工作。她不知从哪里得知他最近没去写作公司上班。她在电话里气呼呼地说,为什么辞职这么大的事情都不跟她商量,眼里还有没有她,是不是不想跟她过了,又问他现在做什么工作,是不是假装出门上班。他说自己没有辞职,不过休几天假,等晚上回去再跟她好好解释。妻子仍喋喋不休地抱怨,他应付几句便挂断电话,继续手上的工作。
公司本来把这趟活儿派给阿辉,阿辉把“实习生”伟雄也带上。他知道伟雄对这幢楼向往已久,上次来参观时就跟他说过,希望有一天能上去。伟雄在这边工作几个月后,对摩天大楼有了更感性的认识,如果现在让他写那篇稿子,或许能写得更好。他见过极尽奢华的总统套房,里面所有的物品都是金灿灿的,连浴缸表面都镀了一层金,那张大床足足有四五米宽。他也见过保洁阿姨待在狭窄的布草间里啃馒头,边上塞满她捡的塑料瓶、纸盒。他见过环境优雅、应有尽有的自助餐厅,坐在里面的人吃着美味的食物,远眺整座城市的风景。他也见过热气腾腾的后厨,赤裸上身的厨师在里面挥动锅铲,汗水混入饭菜之中。这些看似殊异的风景,只是摩天大楼的一墙之隔。手指间绳索滑动,进入另一个世界。
从百米高空俯瞰这座城市,有一种睥睨人间的感觉。那蜂巢般的楼房、蝼蚁般的人群、火柴盒大小的汽车,与他毫不相干。他体会到阿辉说的“飞鸟”。是的,他们的工作更像是自由的飞鸟,在城市上空翱翔,而不是蜘蛛。他讨厌那黑乎乎毛茸茸长着八条腿的昆虫。可是他该如何面对妻子的质问呢?说自己受不了写作公司压抑的氛围?说他向往户外相对自由的环境?妻子不可能理解的,就像他也无法理解妻子为什么对清洁和卫生这件事如此执拗,执拗到变态的地步。
渐渐地,他的意识遁入虚空之际,身体却变得轻盈起来。他睁开眼睛,看到这座熟悉的城市,看到层层叠叠的房屋、缓缓流动的汽车,以及远处淡蓝色的湖泊与黛色山峰。银河大厦玻璃幕墙上映出一个熟悉人影,人影像一只飞鸟在空中滑翔。他转过头去,看到自己身后竟然挥动着一对翅膀,表面覆着一层光滑的灰白色羽毛。他试着挥动翅膀,身体也随之前行、上升。仍在摩天大楼外立面工作的蜘蛛人阿辉,看到他的同伴猛地掉落又莫名飞升起来,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
他向阿辉挥手告别,向这座城市告别,也向过往的生活告别。风吹过他的脸庞,吹拂他的头发,也托举着他的身体。一只体型巨大的苍鹭向他俯冲过来,他转动翅膀来了一个漂亮的转身,与那只苍鹭擦身而过。经过短暂的练习,他对翅膀的控制更加自如,甚至可以在空中回转、悬停。他用力挥动翅膀,越过那汪湖水,向着城外山峰的方向飞去,他距离山上的白色物体越来越近,甚至能看清上面蛛网般的天线。他心心念念想爬上去一探究竟的东西,原来是一部军用雷达。
伟雄站在玻璃幕墙前,望着远处的风景。外面的风景没有多少变化,他的心境大抵也如此。血色般的夕阳铺陈在大地上,整座城市笼罩在暮色将至的苍茫中,远处的山峰和白色球形物体渐渐隐去。几个蜘蛛人从楼上缓缓降落,遮挡住他的视线。其中一个看着有些眼熟,他想了许久,却想不起到底是谁。他叹了一口气,重新回到格子间的座位上,打开那篇名为《摩天大楼记》的稿件。
责任编辑林东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