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姥姥
2024-06-11覃冰
覃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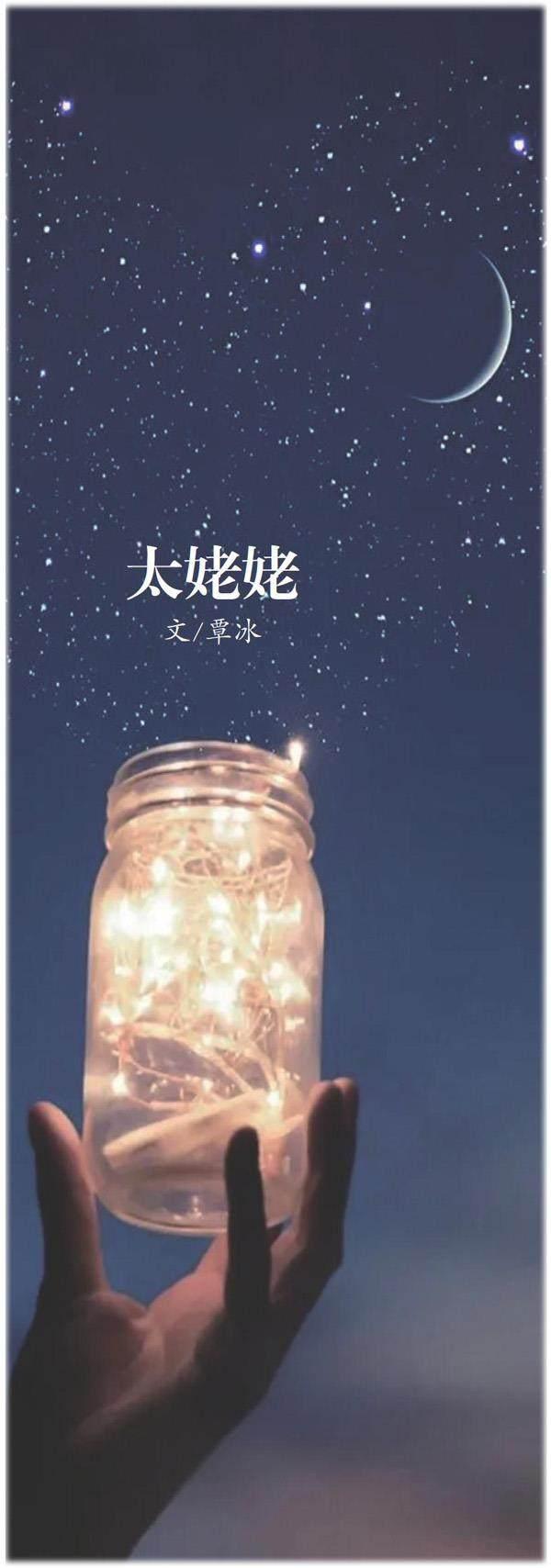
太姥姥是个“抱小姐”。她从小缠足,一双三寸金莲,鲜少沾泥,即便偶尔拄着拐杖下地走几步,也像只被烫脚的虾米,极为痛苦迟缓。太姥姥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像普通人那样能跑、能跳、能出门,而不是坐在门槛上望了一辈子的山,却一步都没走近过。
太姥姥一生没吃过农活的苦,却受够了裹脚的罪。为了避免悲剧重复上演,她坐在厅堂里,一根拐杖把地面杵出数个深坑,说若是谁再让家中子孙裹脚,现在就把她绑到牛身上,她宁愿去犁田,也不想做个废人。太姥姥的明理,让家中的女孩从外婆那辈起,相继逃过了被裹挟的一生。
母亲出生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人人都在温饱线上挣扎,更遑论我们这些山里人家。我的故乡在河池环江,那个九分石头一分土的地方,摧残人们命运的不仅是恶劣的自然环境,还有艰难的生存条件。一个六口之家,三个孩子、两个大人,外加一个进出都要抱着的老人,母亲童年的苦难可想而知。
那时,外公是家里的天,上山下地全得依仗着他。没办法,太姥姥身边离不开人,必须要外婆贴身照顾着吃喝拉撒。母亲作为家中长女,从小就得帮着做家务和照看自己的两个弟弟。可即便如此,重男轻女的外公依旧认为这碗水迟早要泼出去,往里面多添一滴都是浪费。对母亲动辄骂,恼即打。
村里人的俚语,有时粗鄙得难以用语言去解释,却总能精准地囊括进某些器官,让人羞愤欲死。
母亲不知道为此暗自哭了多少回。外婆性子软,看着孩子一身伤痕,能做的也只是流着泪给她抹药,不敢贸然去挑衅家中顶梁柱的权威。毕竟外公一撂挑子,这天就塌了。
太姥姥也跟着难过,攥紧母亲的手,反复地说:“儿啊,别哭,这不是你的错。”
可错的是谁呢?太姥姥也说不清。母亲只能自己寻找答案。
吹着山里的风,母亲把自己长成了草。外公打她骂她,她就弯腰,把身体俯到泥里去,等着下次再站起来。可她的一生就只能这样了吗?母亲充满了迷茫。直到有天她从在村里任教的老师口中听到了一句话:知识改变命运。母亲才终于找到了生长的方向,她要求知、想上学。
不料,比知识先来一步的是灾荒。那个时期,母亲的两个弟弟接连死去。一个饿死,一个为了填肚子把枇杷籽吞了下去,生生噎死。太姥姥哭瞎了双眼,外公受了极大刺激,纵使母亲也饿得只剩下个枯瘦的身体顶着一个巨大的脑袋,仍旧变本加厉地责难于她。一时间,乌云有如华盖,笼罩四野。
待到整个社会大环境有所好转,村中的学校在1967年再度响起读书声,母亲早已过了上学的年龄。
母亲渴望着知识,就像干涸的田,不分昼夜地渴望甘霖。为了听老师讲课,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劈柴烧水喂猪做饭,待到把一切都打理好之后,外公出门干活,她就悄悄到教室外蹲守。
课堂上,老师读一句,母亲就蹲在墙根下跟着念一句。那声音大到连老师都无法忽视,找上门来。
老师说,母亲是他见过最好学的女孩,迫切地恳请外公松口,让她上学。外公一斧子劈在地上,说女孩读书没用,只要会做饭干活和生孩子就够了。
见外公态度强硬,老师也急,呛声道:“你不让她读书,以后生了孩子能数得清楚有几个吗?”
外公恼羞成怒,操起地上刚劈的柴追着老师跑。
老师是个聪明人,边勾着外公往各家里躲边嚷嚷,说外公欺负知识分子,看不起知识分子就是对党和国家的政策有意见。
村里人呼啦啦全被老师喊了出来,外公顶着一个“大帽子”,骑虎难下,这才终于松口,让母亲跟着上了初中。
彼时恰逢小舅舅出生。為了读书,母亲在自己还是个孩子的年纪,就背着另一个嗷嗷待哺的孩童,披星戴月地干活,见缝插针地学习,不仅恶补了小学的课程,还赶上了中学的进度。可母亲的聪慧与上进并不能打动外公,听闻母亲还想读高中进而考大学,外公的大戏又开场了,家里的东西每天随着他的叫骂乒乓作响。因为读高中就意味着要到县城里住校,既要花钱,家里又少了一个劳动力,这笔账就像他胸中那口怒气一样难平。
即便母亲什么都没说,太姥姥也没看到,但仅凭每天醒来枕边摸到的潮气,她也能算得出母亲又哭了多久。在外公刚扔完杯子的饭桌上,太姥姥摸索着,脱下腕上的玉镯,让外公拿去当掉,换成学费给母亲上学。其实那镯子成色并不好,却是这个贫困家庭里最昂贵的家传之物。外公噤了声,不敢收。母亲也不同意,她决定靠自己挣学费。
当时恰逢村里修水渠,母亲报了名到生产队挑沙。挑沙的都是成年人,每人一担挑上百斤不等的沙石,从山里的石场到田头的工地,不停往返。忙活一整天纵使能挣满十个工分也才能抵算两三毛钱。可就是这一丁点儿的增补,宛如乌云里裂进来的曙光,让母亲看到了希望。
为了凑钱读书,母亲每天仅睡两三个小时,早早把家务做完就到生产队报到,从凌晨干到天黑,一趟趟地赶。有时候母亲在半夜里回到家,累得只想倒头就睡,却发现鞋子早已脱不下来,脚板上不断被磨出的血泡,早已将脚掌和鞋底整个黏到了一起。
就这样,母亲咬着牙,硬是靠着在生产队加班加点地挑沙,或是翻山越岭把村里的瓜果挑到县城卖,凑出了学费。她的双脚,也在肩上不断被压实的重量中,越长越大。
过去住校读书,除了学费还要按时往学校上交米粮,作为生活必需。给了米,外公就拒绝再给母亲任何费用,并勒令母亲每周都要回家帮忙干活。
长年的困苦早将母亲的性子磨得无比坚韧。没有生活费,她就靠着交给学校的粮食换米饭,然后每周回家炒一罐酸菜或是黄豆带去学校配饭。有时候天气热,带去的菜坏了,她就用开水泡白饭,饥一顿饱一顿地读完了高中。
县城到家乡那十几里的山路见证过母亲的汗水,那些长满了倒刺的荆棘,曾在母亲义无反顾的踩踏下呻吟,也曾为了母亲的徒劳无功而呐喊。
母亲的大学录取通知,被外公撕碎扔进了火塘。
那时,摆在母亲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嫁人生子,围着锅边灶台转;二是参加工作。
在读书这件事上,母亲说她很难原谅外公。甚至好几次,她走在这条山路的时候,都委屈得想要从山上跳下去。
母亲说这话时,我和她正坐在外婆家和县城必经的山坳处小憩。这座高达数十米的山,岭上怪石嶙峋,崖下杂草丛生。每次攀爬我都手脚并用,心中发怵。
“那后来呢……”我问得有些小心翼翼,因为母亲的神情过于悲伤,风一吹,就碎了一眼的光。
一切幸有太姥姥。在母亲被迫离家到别的乡镇工作那晚,外婆悄悄塞给了她两双鞋。那是两双自制的布鞋,蓝色的面,黑色的底,上面的针脚大部分歪歪扭扭,不甚美观,却十分结实。
太姥姥并不知道母亲想要读的高中和大学是什么,但是她能感受得到母亲想要离开大山的渴求。所以,她打算为母亲做几双鞋,让母亲能走更远的路,去更多的地方。虽然很早就开始准备,可是因为瞎了眼,做得慢,只能摸索着一天缝一点儿。最后鞋没做完,太姥姥就走了,外婆便接了手,继续缝制。
“你们太姥姥是我这辈子最尊敬的人。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我。”母亲把我抱在膝上,脱下我脚上的凉鞋,一点点拭净我踩到坑里的泥。
我只在外婆家的厅堂上见过太姥姥的画像,黑色的头巾,黑色的交领衣,看起来和村里寻常老人没什么两样。可母亲手上的热度,让我开始有点儿想她。
(摘自2023年第12期《海外文摘·文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