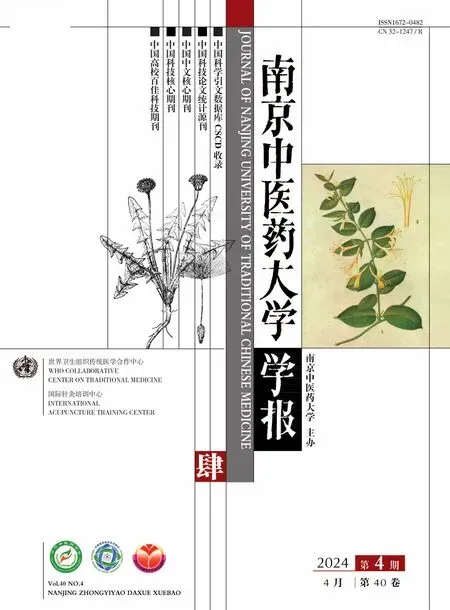《伤寒论》临证价值刍议
2024-06-10马俊杰周春祥
马俊杰,周春祥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伤寒论》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对临证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此书经过历代研究者不断传承发展,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术理论体系。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诸多问题亦随之而来,如对《伤寒论》临证价值认识不全面、疫病诊治重温病轻伤寒、经典理论如何与时俱进地应对当代疾病及如何合理构建经方运用规范体系等,为此学术界产生了不少争论。争论是学术发展的必由阶段,但是《伤寒论》研究首先需要明确此书的学术价值,在寻求发展变革的同时,须遵守经典自身发展规律,不可盲目一改了之。
1 《伤寒论》为百病立法,治伤寒亦治杂病
关于《伤寒杂病论》,历代有不少医家认为《伤寒论》偏于治外感,而《金匮要略》则偏于治杂病,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伤寒论》之名源自王叔和,是其整理张仲景部分散落之书而成,并非自行分类而成,只因此部分内容与外感之疾密切相关,大多为外感风寒及其所引起的诸多传变之疾,故而取名为《伤寒论》,书中不仅记载外感,涉及杂病者亦甚多。就《伤寒论》六经病篇幅而言,虽太阳病篇所占居半,然其中所论外感病仅冰山一角,绝大多数内容皆针对杂病,更何况其他病篇。
同时《伤寒论》不仅为伤寒而设,亦为杂病而立,如柯琴言:“自王叔和编次,伤寒、杂病分为两书,于本论削去杂病。然论中杂病,留而未去者尚多,是叔和有《伤寒论》之专名,终不失伤寒杂病合论之根蒂也……世谓治伤寒,即能治杂病,岂知仲景《杂病论》,即在《伤寒论》中。且伤寒中又最多杂病夹杂其间,故伤寒与杂病合论,则伤寒、杂病之症治井然。今伤寒与杂病分门,而头绪不清,必将以杂病混伤寒而妄治之矣。”[1]157方有执亦言:“论病以辨明伤寒,非谓论伤寒一病也。”[2]
再者《伤寒论》虽无杂病之名,却有杂病之实,其中太阳病变证比比皆是,如变为热证、虚证、结胸证、脏结证及痞证等,此实则可作为杂病的辨治法则,而且书中各病篇中诸多方证,如苓桂术甘汤证、茯苓甘草汤证、五苓散证、小青龙汤证、黄连汤证、五泻心汤证、吴茱萸汤证、真武汤证、当归四逆汤证及白头翁汤证等,皆为杂病常见证候[3]。
此外,《伤寒论》虽未明确提出各种辨证法之名,但涉及的辨治思路众多,有八纲辨证、脏腑经络辨证、气血阴阳辨证等多种辨证方法的体现,如三阴三阳、六经传变与八纲之阴阳、表里密切相关,又如六经的脏腑属性有脏腑经络辨证之意,再如张仲景通过患者小便通利与否来判断病邪在气分、血分则是气血阴阳辨证的思路。当然《伤寒论》最具特色的是六经辨证,其传承于《黄帝内经》“六经”理论,同时又创造出与其不同的六经辨证法则[4],后世医家在《伤寒论》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诸多辨证方法,皆是对仲景学说的发展。
需说明的是,《伤寒论》六经之名源自《黄帝内经》却又与之有所区别,其并非仅是经络的概念,而更多是与经络相关的六类疾病。即以《伤寒论》特有的辨证思路确诊各种疾病的六经属性,以此给予相应的治疗方药,正如程应旄所言:“张仲景之六经,是设六经以赅尽众病。”[5]柯琴亦言:“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之节制。”[1]158所以笔者认为,《伤寒论》是以论治伤寒疾病切入,阐述外感病的证治及传变规律,不仅是治疗伤寒的专著,更是杂病的临证应用法则。
2 疫病诊治重温病轻伤寒,实则寒温相互羽翼
近年来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以下简称“新冠病毒感染”)肆虐,温病学思想又被学术界重视,伤寒之名因“寒”而被部分医家认为是感受风寒所生之疾,与温热之疾有异,故在疫病诊治时易被忽视。其实此“寒”亦可为“邪”之义,正如《难经》五十八难“伤寒有五”之广义伤寒,其不仅包括风寒之疾,亦涉及温病之疾。东汉末年,连年战乱,加之天灾,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故外感寒证者居多,然《伤寒论》并非仅有寒证,张仲景亦有对温热之疾的记载,如书中第6条云:“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时瘈疭;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6]25
然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张仲景所遇外感风寒患者居多,故其对疏散风热法的记载有所欠缺。温病学理论是在《伤寒论》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弥补了《伤寒论》对外感风热病治疗的不足,看似寒温对立,实则羽翼伤寒,可作为外感温热病证治思路的补充。如同样针对表证,《伤寒论》多以疏散风寒治疗为主,其中麻桂剂为首选方药,而温病学则多从风热论治,以银翘、桑菊之剂为代表,虽寒温治法有异,然解表达邪的思路一脉相承[7]。此外,《伤寒论》中诸多病证如太阴湿证、阳明实证、少阴热化证、厥阴动风证及热盛动血证等的辨证规律被广泛运用于温病学中,为叶天士卫气营血辨证及吴鞠通三焦辨证的理论源泉。正如秦伯未所言:“温病学是伤寒的发展,二者结合,寒温一统。”[8]故我们不能割裂伤寒与温病的关系,而应该以动态的眼光去看待寒温之间的演变发展,即温病传承伤寒又发展伤寒,同时两者相互羽翼。实际临证时六经辨证亦可与温病学诸辨证方法相互结合,以新冠病毒感染为例,六经辨证贯穿疾病的辨治始终,同时可参考温病学派的多种辨证方法,俞根初在《重订通俗伤寒论》中提出:“以六经钤百病,为确定之总诀,以三焦赅疫证,为变通之捷诀。”[9]具体临证时可将新冠病理因素提取后,综合运用六经辨证、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等多种辨证方法,并找出相对应的用药思路。笔者前期亦针对新冠病毒感染疾病的不同阶段,根据患者具体病证运用不同的中医辨治思路,同时在用药时亦灵活变通,不可拘泥,常伤寒方、温病方并用[10]。
3 经典研究可借鉴西医思维,应对疾病须以中为基
目前学术界有观点认为中医要借鉴现代医学知识,变革经典理论,使其适应当代疾病的诊治。如有学者试图将中医宏观思维与西医的微观思维相结合,提出“态靶结合”理论,认为“态”是反映疾病的“状态”“动态”及“态势”,外还蕴含了审因和防果的内涵,而“靶”则借用了现代医学“靶点”的概念,包含病靶(特定疾病本身)、症靶(患者异常症状或体征)、标靶(现代理化指标、影像学检查),是最突出的客观指标[11]。
笔者认为这样的认识方式对中西医结合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此“态”的定义其实并未脱离张仲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6]27的窠臼,而且“态”与“靶”的结合亦往往涉及经验因素,即需在一定临证经验下的结合,而不可拘泥。以针对桥本氏甲状腺炎患者为例,B超显示甲状腺弥漫性增生,从六经辨证而言,往往多见少阳枢机不利。此外,其中部分患者抽血检查可能显示甲状腺功能亢进,常有甲状腺激素(T3、T4、FT3、FT4)水平升高,促甲状腺激素(TSH)水平下降,中医病机为肝火上炎者居多,而部分患者则可能显示甲状腺功能减退,其甲状腺激素及促甲状腺激素水平变化与甲亢者相反,中医临床表现多见阳虚湿困之证,此时中西医之间可相互参考。但是必须在辨证的前提下,而不可以直接等同。
亦有观点认为可在中医思维模式下用中医药术语重新定义西医疾病,如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以下简称“非典”)命名为“肺毒疫”[12],将新冠病毒感染命名为“寒湿疫”[12]。此外,亦有观点认为中医亦可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研究手段,全面把握疾病的发展规律[12]。这种思维方式立足中医根本,以古法理论认知现代医学疾病,古为今用,具有一定创新性。
然上述观点亦有不足之处:其一,《伤寒论》以辨治外感病切入,阐述了邪气侵袭肌表及肺脏,再逐渐往里传变的完整过程,为系统的疫病理论体系,非典、新冠病毒感染发病过程亦不离六经,故是否有必要重命名?甚至笔者认为此可能会影响对疾病的全面认识;其二, 非典在临床上亦有“寒湿疫”的情况,新冠病毒感染同样与肺部感邪密切相关,故将非典命名“肺毒疫”,将新冠病毒感染命名“寒湿疫”尚缺乏针对性;其三,基于现代医学检查、检验指标的疾病诊断、分期,与中医病机并非相互对应,故不可视其为中医理论的突破;其四,中医理论确实要与时俱进,但是应当是在统一理论体系下的创新,如温病学说,虽表述方式与《伤寒论》有所不同,然理论体系却一脉相承,是对《伤寒论》学术思想的补充发展。
总之,中医经典研究首先要尊重经典条文本身,并结合临床实际,以具体病证及疗效为依据,在实践中还原及理解《伤寒论》的临证要旨。同时要融合多种研究方法,取多家之长,亦可适当参考现代医学知识,并结合医者的个人临床经验,中西医之间可相互协助,但是并非一味以此释彼,更不是以此代彼。
4 经方运用重方药略理法,亟待构建规范体系
关于经方,有广义经方与狭义之经方之分。广义经方即经验用方,可上溯至神农、扁鹊仓公时代,再经张仲景时代逐渐成熟,当然亦包括后世医家临证所创造之相关验方[13]。而狭义之经方则主要指仲景《伤寒杂病论》所载方药,其组方严谨而不失灵活,被后世称为方书之祖[14]。经方是千年来学术优胜劣汰的结果,是历史的选择,理论上经方可治诸病,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经方在部分疾病中效如桴鼓,然而有些疾病却优势不足,甚至缺乏可重复性,故亟待以疗效为准绳梳理经方优势病种,并制定相关临床运用规范。
经方为中医经典方、规范方、标准方的代词[15],其配伍强调原方及原量或原比例,同时加减、合方思路缜密,在《伤寒杂病论》中,常加减一药即成新方,所以有观点认为经方是中医人工智能化的突破口,未来可围绕首辨六经归属、次辨病机方证及预测病传规律的智能化临床辨治路径实施[16]。笔者团队亦尝试运用计算机技术,面向临床需求进行《伤寒论》知识挖掘及知识体系构建,这样对经典的智能化探索具有创新性,对中医临证有一定参考价值。
伴随经方的临床运用,方证、药证之说随之而来。其中方证之名始于孙思邈《千金翼方》:“今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须有检讨,仓卒易知。”[17]是对《伤寒论》方证思想的总结。柯琴《伤寒来苏集》采用“以方名证,以证名篇”的编撰原则:“仲景之方,因症而设,非因经而设。见此症便与此方,是仲景活法。”[1]182而药证之名则与朱肱密切相关,其在《类证活人书》中提出:“所谓药证者,药方前有证也。”[18]喻嘉言在《寓意草》中亦言:“故治病必先识病,识病然后议药,药者所以胜病者也。”[19]构建了患者脉证与具体药物之间的桥梁,比方证思想更为直接快捷。方证、药证常被认为是经方运用的重要指导原则,即有是证用是方(药)。
然而笔者认为方证、药证可启迪医者临床直觉思维,但不能成为经方运用的唯一规范,现代经方运用不可局限于方证、药证,如此并不严谨。如《伤寒论》中同样针对瘀热互结,可选用桃核承气汤、抵当汤及抵当丸治疗,又如同样是少阳阳明合病,有小柴胡汤证、大柴胡汤证、柴胡加芒硝汤证,甚至大承气汤证。此涉及证候及经方用量的问题,显然并非简单的“有是证用是方(药)”可一概而论[20]。方证相应并非“一方一证”,亦非“一证一方”,而是理法方药与证之间的广义相应[21],包括药物剂量、配伍比例、剂型、煎服法等分别与病证相应[22],而不可简单的某方与某证相应。
同时经方运用时,不仅要研读含方药的条文,非方药部分亦同样重要,要通过此类条文凝练《伤寒论》中的理法思路,以此指导相关方药临证的灵活运用。如《伤寒论》259条针对太阴发黄证,仅提出“于寒湿中求之”[6]80,然并未出具方药,但是医者可以根据张仲景的用药思路,运用茵陈蒿、干姜、茯苓及甘草等药温阳健脾,利胆退黄。又如《伤寒论》209条[6]72、238条[6]77及251条[6]79皆有言之大便“初头硬,后必溏”,书中亦未提出相关治疗方药,但根据原文“不可攻之,攻之必胀满不能食也”[6]72,“攻之必溏”[6]79,医者推知此处有脾虚的病机,故临证遇到此类病证要注意固护脾阳,可根据具体情况选用理中汤、半夏泻心汤,甚至是乌梅丸等方治疗。
再者,面对同一病患,临证时百医常出百方,并且可能皆有疗效,此并非处方错误,只因用药切入点不同。如针对脾虚湿困导致的腹满患者,医者选方用药有以温阳健脾为主,又有以理气化湿为主,然调治数周皆有疗效。经方须在张仲景理法指导下运用,此临证之根本法度,有时甚至遵理法而易方药,皆为仲景活法的体现,目前人工智能尚不可取代。
所以,计算机算法难以全面模拟六经病的辨治规律,只能为经方运用提供借鉴而不可拘泥。并且诸多医者在临证时,遵仲景之旨,师其法而不拘泥其方,同样屡起沉疴,故经方智能化运用还须强调以人为本的综合辨治模式。[23]当然,随着计算机算法的逐渐发展,未来人工智能或许可从《伤寒论》理法思想角度进行深入探索。
总之,经方蕴含精妙的配伍规律,有着深层次的理法思路,临证不是简单统一用方施药,而是要统一理法思路,谨遵仲景理法,万变不离其宗,探索理法方药相融合的经典辨治模式,构建和而不同的经方运用规范体系。
5 结语
历代医家皆将《伤寒论》视为临证之圭臬,不仅针对伤寒疾病,对杂病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在面对当代疾病时,如何将传统经典理论与现代疾病相结合,开辟古今融合的经典辨治模式,是当代经典研究者面对的重要课题。笔者提出鼓励经典创新但必须坚持中医思维,古为今用,西为中用。此外,《伤寒论》所蕴含的理法方药思路是其临床价值的根本,然而现在不少医家在研究过程中只重方药,而忽略理法,不能全面认识此书的学术价值,实属经典研究之憾事,故学术界须在理法前提下构建和而不同的经方运用规范体系,以此探索理法方药融合的经典研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