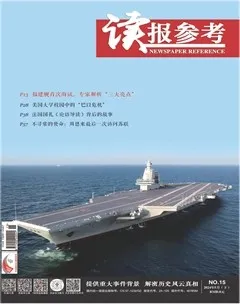一个美国学者的中国养老院观察
2024-05-29
2013年秋天,云南昆明的一家私营养老院里,老人们好奇地打量着一位特别的闯入者——一位年轻的美国女性,拿着自己的问题本,被院长介绍给大家。她用生涩的普通话四处提问:“你结婚了吗?”“你是不是城市移民?”“你为什么住进养老院?”
她叫葛玫(Rose K.Keimig),当时是耶鲁大学医学人类学博士候选人。但在那时,她想关心一些更普遍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养老——第一批主动住进养老院的中国老人,他们是谁,过着怎样的生活,衰老到底意味着什么……她的调查最后变成了一本书,《谁住进了养老院》,在2023年出版。以下是葛玫的口述——
一
我第一次去玉山养老院是2011年。当时中国有一个领域正在经历巨大变革,那就是养老——当人们老了,谁来照顾他们?
我的理解中,原来在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家人会照顾你,但现在情况显然已经不同。在过去,“三无老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的60周岁以上公民)会被送到公立养老院,但是我想找的是第一批选择私人养老院、主动寻求养老服务的人,他们往往有子女,有收入。
玉山养老院是一家很寻常的私人养老院。大概有300个床位,當时每个床位每月收费2100元左右,刚好是昆明养老金的平均数。正因为收费不高,它吸引了更多住户,平常总是满员。我的导师建议我就选择这里,这样,我就可以了解一个普通的养老机构,而非那些“模范养老院”。非常幸运的是,玉山养老院老人们很欢迎我,对我很友好。这段时间里,我一共记录了对玉山养老院的60次访问。
在这里,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们为什么会住进来?
对老人们来说,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他们有保全面子的压力。但总的来说,我发现,老人们进入养老院,可能并不总是被动的,有些人是主动选择。
我印象很深的是80多岁的张爷爷。他本来和女儿一起住。但是有一次,女儿和丈夫要出去两周,就商量要把张爷爷怎么办。张爷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他主动说,给他找一家养老院比较好。张爷爷告诉我,他主动选择这样做,第一,是“想要解放孩子们”;第二,正因为是他坚持要住养老院,女儿不会因此觉得自己不孝。我确信,在养老院里,至少有一些老人和张爷爷情况相似。他们不再是要求听话、期望回报的父母,恰恰相反,他们会尽量压抑自己的需求,真心盼望子女幸福。
当然也有很多老人向我表达他们的痛苦——他们被迫呆在养老院,有被遗弃的感觉。比如万叔叔,他之前中过风,从第一家养老院出院时,他以为自己会回家,但是车直接开到了第二家养老院门口,他就一直呆在了这里,两年了,女儿再没出现过。
我也和一些子女交谈过。比起父母,子女们其实不那么愿意和我交谈。他们会解释说,自己把父母送到养老院,是因为养老院更安全,父母在家里可能会摔倒或者突然发病,甚至有人会自杀。子女们会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二
养老院的资源有限,通常会体现在某些地方——比如气味。在玉山,你会闻到(没来得及处理和清洁的)尿味,也会闻到油漆味,因为养老院的房子就是重新利用的老建筑。
空间也是一种有限资源,必须不断“争取和捍卫”。很多地方都是上锁的。每层楼的大门都上了锁,防止老人走失;高楼层的走廊也是用栏杆封住的;窗户平常也是锁住的。在玉山,每间房一般住2-4位老人,上下铺的床,下铺住人,上铺堆放物品。房间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也就是说,下铺是老人们仅有的私人空间。
我在昆明的那年,大概有三次,有老人问我:“能不能买来安眠药,偷偷捎进养老院?”我的回应是倾听,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在养老院里,自杀和安乐死是寻常的话题。玉山的很多老人都有慢性疾病,比如中风,这些疾病会随着时间缓慢发展,但不会终结。可是治疗疼痛的药物(如阿片类和抗抑郁剂等药物)受到严格监管,养老院基本没有。没有缓解的希望,对许多老人而言,生命等同于痛苦,“活得越久,痛苦得越久”。
科学界也越来越关注“慢性生存”,它与“健康生存”相对,不仅仅指人们带病生存,也意味着生命本身的不良状态。
总的来说,在昆明一年,肯定不足以让我说,“哦,我已经经历(了解)过了”。但有些事情让我感到惊讶,我本来以为,这一代老人会觉得,自己值得更多照护——因为他们为了给子女、孙辈和整个国家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曾牺牲了很多。但我低估了他们,低估了他们一生中经历的创伤和动荡,以及这些经历又是如何改变了他们的期望。他们总是接受一切,展现出韧性。
(摘自《作家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