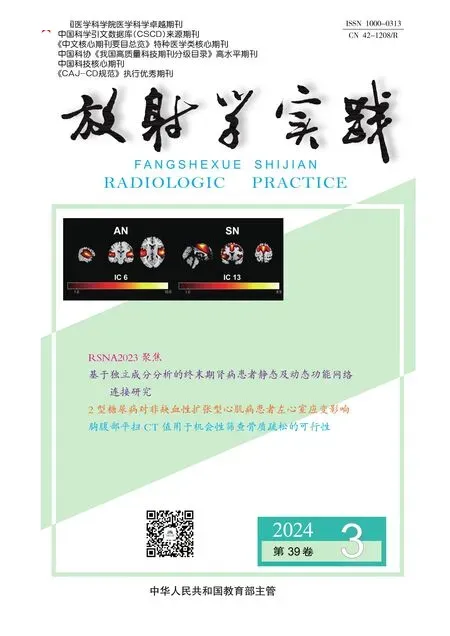CMR参数及相关纹理分析预测肥厚型心肌病患者主要心脏不良事件研究进展
2024-05-29郑月马运婷沙立辉赵晓莹赵新湘
郑月,马运婷,沙立辉,赵晓莹,赵新湘
肥厚型心肌病(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HCM)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心肌病,是35岁以下成人心脏猝死(sudden cardiac death,SCD)最常见的原因[1]。据2021年《Lancet》发布的HCM临床管理指南,全球人口中,HCM发病率约为0.2%~0.5%[2]。在我国,经年龄、性别校正后的患病率为万分之八,估计我国成人HCM患者超过100万[1]。HCM的特点为左室壁厚度增加,不能用异常负荷解释(如高血压或主动脉瓣狭窄)[2]。HCM常累及室间隔,表现为室壁非对称性增厚,心腔缩小,其病理特征为心肌细胞肥大和间质纤维化。HCM患者轻者可无任何症状,重者可出现劳力性呼吸困难、晕厥、心力衰竭甚至SCD。目前已出现多种方式治疗HCM,如药物治疗(常用为β受体阻滞剂或钙离子拮抗剂)、介入手术(经皮室间隔消融术)、外科手术(室间隔心肌切除术)以及植入式心率转复除颤器 (implantable cardioverter defibrillator,ICD)植入治疗,但上述方式无一能彻底治愈HCM。HCM患者远期预后仍不理想,其根本原因是主要心脏不良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ac events,MACE)的高发生率及缺乏准确的指标对MACE的发生风险进行评估。本文就目前国内外有关心脏磁共振(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CMR)参数及相关纹理分析预测MACE发生风险的研究进行综述,旨在对HCM的危险分层提供一定的建议和参考,从而及时干预并改善预后。
HCM经典SCD危险分层指南
MACE主要包括:SCD、植入ICD、恶性心律失常、栓塞性卒中、植入心脏起搏器、心衰、心脏移植等。SCD是HCM患者最严重的后果,而植入ICD是目前减少SCD风险最有效的措施。因此,临床上需要评估SCD的发生风险,进一步评估、指导ICD的应用。目前,对HCM患者SCD危险分层指南有2014年欧洲心脏病学会(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ESC)提出的5年HCM Risk-SCD风险模型和2020年美国心脏病学会/美国心脏协会(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CC/AHA)提出的7种SCD临床危险因素[3-4]。两者共同纳入的主要危险因素包括:SCD家族史、最大室壁厚度≥30 mm、非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不明原因的晕厥。此外, ESC指南将年龄、左房内径、左室流出道梗阻、运动血压反应纳入SCD风险评估,而 ACC/AHA指南将左室收缩功能障碍、左室心尖室壁瘤、(延迟钆强化质量/左室质量)%>15%纳入风险评估。由于两种指南评估的主要危险因素不全相同,会导致同一患者SCD风险等级存在差异。且最近的一项包含784例HCM的大样本研究表明[5],ESC提出的5年HCM Risk-SCD风险模型敏感性较低,而ACC/AHA提出的SCD风险分层的7种临床因素的特异性较低。因此,现有的SCD风险分层指南不能很好的预测远期发生MACE的概率,临床医生制定正确的治疗策略仍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CMR获得的心脏结构、组织特征参数与MACE
1.常规电影序列
既往研究发现,左房内径[6]、最大室壁厚度[7]和左室心尖室壁瘤[8]已确定为HCM患者预后不良的的危险因素,并已纳入SCD危险分层[3-4]。近年来,有关右房室、二尖瓣环平面收缩偏移(mitral annular plane systolic excursions,MAPSE)、三尖瓣环平面收缩期偏移(tricuspid annular plane systolic excursions,TAPSE)与HCM预后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成果。Doesch等[9]将HCM患者分为房颤组(包括最初诊断时出现房颤和随访期间出现房颤)和窦性心率组,与健康对照组相比,窦性心率组MAPSE减少,而房颤组则TAPSE减少和右心房扩张。受试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显示,TAPSE、右心房直径和MAPSE对存在房颤风险的患者有良好的预测能力,提示可作为HCM患者发生房颤风险的标志物。Dong等[10]研究发现,与无严重右心室肥厚的HCM患者相比,合并严重右心室肥厚的患者有更严重的临床症状和更高的纽约心脏病协会(New York Heart Association,NYHA) 心功能分级,并且有更差的临床随访结果。Zhang等[11]对893例HCM进行随访研究,并将存在右心室肥厚、梗阻或延迟强化之一定为右心室受累,发现右心室受累是HCM患者心血管死亡、全因死亡、心衰相关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2.钆延迟强化
心肌纤维化是HCM的病理特征之一,也是发生心律失常甚至SCD的重要病理基础。根据不同病因及病理特征改变,心肌纤维化分为替代性纤维化、反应性纤维化和浸润性纤维化。HCM是替代性纤维化的常见疾病之一,其原因可能与小血管缺血导致心肌细胞死亡并最终以间质纤维增生修复有关,也有研究提到可能与细胞外基质蛋白的过度沉积有关[12]。心脏磁共振延迟钆强化(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late gadolinium enhancement,CMR-LGE)是检测心肌纤维化的有效手段。HCM患者中LGE的平均报告率为65%,但可能存在于高达86%的患者中[13]。研究证实,CMR-LGE检测的心肌纤维化是HCM患者不良预后的独立预测因子。Doesch等[14]利用5年HCM Risk-SCD模型对149例患者进行风险评估发现,LGE%≥20%的患者有很高的MACE发生率,而LGE%<20%的患者,尽管SCD风险评分≥6%(高危),但MACE发生率很低。不同类型的心肌病存在一定的LGE分布特征,HCM患者心肌强化区域常位于肥厚节段的心肌中层,以室间隔和右室插入点多见,表现为点状、片状或团状强化。基于此,Li等[15]对HCM患者LGE强化位置和预后关系进行研究,发现LGE位于室间隔外的患者的全因死亡率、心血管死亡率、心脏移植和SCD显著高于LGE位于室间隔的患者,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LGE位于室间隔外是预后不良的独立预测指标。以上研究显示,LGE的存在、程度及分布位置是独立于常规危险因素的重要预测指标,可为HCM患者MACE风险评估提供一定的增量价值。
3.心肌应变
CMR特征追踪(cardiovascular magnetic resonance feature tracking,CMR-FT) 技术基于常规电影序列,可以自动追踪心动周期中心内膜及心外膜上体素的相对运动与位移,评价心肌在张力作用下的形变能力。与左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相比,CMR-FT可以评价局部心肌的运动及舒张早期功能的变化,对于射血分数保留的HCM患者心功能的评价亦具有明显的优势。通过CMR-FT反应的心肌应变和HCM患者预后有一定的关系。Negri等[16]研究发现,在所有的应变参数中,整体纵向应变(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GLS)是HCM患者终点事件的独立预测因子,将GLS添加到其常规包含临床、影像危险因子的预测模型中,其C-统计量从0.48升至0.65。与GLS相关的峰值舒张期应变率(peak diastolic strain rate,PDSR)也是预测HCM患者不良结局的一种新的、易于获得的标志物,有利于风险分层[17]。另一项研究显示,整体径向收缩期应变率值<1.4/s和整体径向舒张期应变率值≥1.38/s与随访时的临床事件独立相关[18]。心肌纤维化是引起心肌运动异常的重要原因之一,且CMR-FT检测心肌运动功能的改变非常敏感,因此具有间接反应纤维化的价值。有研究者将HCM随机分为训练组和验证组,发现CMR-FT衍生的节段周向应变(segmental circumferential strain,SCS)可将两组中有无LGE鉴别出来,原因可能是HCM心肌纤维化通常位于心肌中层,而周向应变主要由心肌中部的心肌周纤维产生[19]。另一项研究显示,室间隔的GLS和梗阻型HCM组织学上的心肌纤维化及室性心律失常独立相关[20]。因此,不管是心肌运动还是心肌纤维化,CMR-FT都能很准确地监测HCM患者的疾病进展,为预后评价提供参考。
4.T1-mapping、ECV
HCM患者中局灶和弥漫性心肌纤维化常共同存在。LGE对局灶性纤维化敏感,在弥漫性心肌纤维化中,由于缺乏对比,其诊断效能不佳。纵向弛豫时间定量(T1-mapping)技术无需以正常心肌作为对比,可测得一定场强下的心肌T1值,反映弥漫纤维化过程中的不良心肌组织重构。按照是否注入对比剂可测得初始T1(Native T1)值和增强后T1(Enhanced T1)值,但Enhanced T1值易受多种因素(如给药剂量、延迟强化时间等)影响,其稳定性和可重复性逊色于Native T1值,因此临床诊断工作时多使用Native T1值[21]。测得Native T1值和Enhanced T1值后结合红细胞压积,可计算得到细胞外容积(extracellular volume,ECV)。HCM患者中,Native T1值和ECV值较正常人升高,值越大,提示心肌纤维化越重,且Native T1值和ECV值检测的纤维化与组织学上的纤维化有良好的对应关系[22-24]。此外,Native T1值和ECV值还与心肌肥厚相关,并可将HCM与常见的引起左室心肌肥厚的疾病鉴别开,如心肌淀粉样变性、高血压心脏病等。近年来,Native T1值和ECV值也越来越多地用于预后评价。有研究者发现,整体Native T1值与MACE独立相关,T1-mapping作为一种新的SCD风险分层生物标志物,有潜力成为当前SCD风险评估指南的补充[25]。Li等[26]研究显示,ECV是评价HCM不良预后的强有力指标,且ECV每增加3%,主要终点发生的风险将增加1.374倍。另一项研究显示,当平均ECV值>27%时,HCM患者发生室性心律失常的风险增加2倍,从而更易发生猝死[27]。Native T1值升高与心肌收缩功能受损有密切关系,而ECV与舒张功能障碍相关,提示可通过监测两者值的改变为心功能评价提供信息[22,27]。
5.T2-mapping、T2*-mapping和T2 BOLD
心肌水肿是HCM早期的病理特征,T2WI序列上信号强度可以反映由于微循环功能障碍导致的心肌水肿改变[28]。高T2信号与标志心肌损伤的高敏心肌肌钙蛋白T(hs-cTnT)相关,提示在影像上高T2信号可作为心肌损伤的标志物[29]。一项多中心研究显示,伴有高T2信号的HCM患者SCD风险分层更有可能位于中高危,且SCD预计发生率比无高T2信号的患者高1.5倍,但高T2信号相关的混杂因素较多,其单独预测能力较低[30]。T2-mapping能定量测得不同心肌节段的T2值,可以更准确、更直观地反映心肌和间质水含量的变化。T2值越大,心肌细胞水肿越严重。T2-mapping可在心脏形态和功能改变之前,定量发现异常的心肌组织重构,有利于HCM的早期诊断[28]。但有关T2值大小与预后的研究,尚未见文献报道,其原因也可能是相关混杂因素较多,研究设计存在一定难度。
T2*-mapping是另一项表征心肌组织特征的技术,反映组织本身及主磁场不均匀导致的横向磁化强度矢量的衰减,称为T2*弛豫时间或T2*值。HCM患者由于微循环障碍,氧合血红蛋白减少,脱氧血红蛋白增加,脱氧血红蛋白具有顺磁性,从而降低T2*值。T2*降低可提示心肌缺血和心肌纤维化,并与心律失常具有一定的相关性[31-32]。新近出现的T2*血氧水平依赖(blood oxygen level dependent,BOLD)MRI技术,可用于心肌的氧合评价,该值降低提示灌注不足,并与纤维化形成相关,不利于HCM患者预后[13,33]。
基于CMR图像获得的纹理特征与MACE
心脏正常的收缩及舒张功能依赖于心肌细胞的数量、形态及排列顺序。HCM患者心肌细胞肥大、畸形,心肌纤维排列紊乱,从而显示出一定的异质性。CMR作为常见的一种生物医学成像方式,包含了反应疾病特定过程和状态的信息,但传统的图像分析方式无法识别、量化。近年来,基于MR图像的纹理特征分析已成为研究热点,在肿瘤领域的应用价值已经得到验证。纹理分析可以通过一定的算法从图像中提取信息,呈现为定量的放射学特征,反映人眼无法识别的微小改变,从而提高诊断效能和预测价值。
1.基于电影序列的纹理特征分析
常规电影序列提供心脏形态学和功能学特征。纹理分析可将常规的电影图像转换为高维数据,客观、定量地描述组织水平上的心肌形态学特征。基于电影序列的影像组学特征差异有助于区分HCM患者LGE(+)和LGE(-)的心肌,识别无纤维化的患者,减少不必要的钆给药[34]。关于电影序列获取的纹理特征与HCM预后的研究,尚无文献报道。
2.基于LGE的纹理特征分析
传统的LGE通常以量和分布来诊断和预测疾病,纹理分析可提供纤维化的空间异质性信息。Wang等[35]从LGE图像中提取的放射组学特征LBP和Moment可反映瘢痕的异质性,对识别SCD高危的HCM患者具有独立的预测价值。Aquaro等[36]利用LGE纹理分析-色散映射方法,发现整体色散评分(global dispersion score,GDS)>0.86患者预后差于低GDS患者,其GDS>0.86对LGE%>15% HCM患者有附加预测作用,其5年SCD风险从8%上升至34%,多因素分析显示,GDS>0.86是心脏事件的唯一独立预测因子,可以提供比LGE的存在和程度更好的危险分层。 Alis等[37]利用基于机器学习的LGE纹理分析研究HCM患者的室性心律失常发现,k-nearest-neighbors模型预测室性心律失常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可分别达到95.2%和93.0%。
3.基于T1-mapping、T1WI的纹理特征分析
不同心脏疾病之间、心脏疾病与健康人之间的T1值和ECV值可出现重叠,且T1值受设备、场强影响很难确定截断值。因此,通过T1值和ECV值的大小诊断疾病表型有一定的难度。实际用到的T1值多为整体测量的平均值,大量反映疾病特征的信息未被利用。纹理分析允许对T1-mapping图像中像素灰度水平的空间分布进行量化分析,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基于Native T1-mapping的纹理特征分析有利于HCM与其他心脏疾病的检出和分类,且在描述心肌肥厚方面优于传统的Native T1值[38]。此外,通过对Native T1-mapping的纹理分析还能表征HCM与其他心脏疾病不同的纤维化模式[39]。Neisius等[40]对188例疑似或确诊HCM患者研究时,验证了基于Native T1-mapping的纹理特征LRLGE-45°和LBP-22等能够识别所有的LGE(+)患者和37%的LGE(-)患者,可用于筛查识别出避免使用钆剂的患者。
T1WI序列通常用于辅助其他序列对疾病进行诊断。HCM患者心肌纤维化可在T1-mapping和LGE上发现异常,而在T1WI序列上单纯通过视觉观察和主观分析无法识别。纹理分析有利于定量检测心肌组织异常。研究显示,基于T1WI获得的四种纹理特征GLevNonU、WavEnLL、Fraction、 Sum Average在HCM和对照组间有差异,包含单参数GLevNonU的模型被证明是区分HCM患者和对照组的最佳模型,其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91%、93%[41]。基于T1-mapping、T1WI获取的纹理特征是否可以预测HCM不良预后,尚未见文献报道。
4.基于T2WI的纹理特征分析
T2WI序列显示的信号强度差异和阈值设定有关,高于阈值的心肌表现为高信号,而人眼识别高信号是主观的,不是基于组织学发现的。T2-mapping可量化心肌组织的T2值,但需要额外的扫描序列。Amano等[42]研究发现,HCM患者中基于T2WI获得的纹理特征GLevNonU、SumAverg和Energy明显高于对照组,其中GLevNonU是HCM患者和对照组之间的最佳鉴别指标。与HCM肥厚但无T2高信号和LGE的区域相比,T2异常高信号区域的GLevNonU明显较小,而SumAverg、Energy和99%百分位数较大。GLevNonU主要反应灰度的不均匀性,从而反映心肌的异质性,而SumAverg主要反应肥厚区域心肌含水量的变化。因此,基于T2WI序列的纹理分析可以反映HCM组织特征改变,有利于HCM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HCM人群患病率高且存在SCD风险,虽然已有ESC和ACC/AHA指南用于SCD识别,但多项研究指出指南的应用价值有限。目前,CMR参数评价成为临床诊断、治疗参考和预后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CMR图像分析结果已经成为临床决策的参考,可提供心脏形态、结构、功能方面的信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心肌病理生理改变,但其效能有限。基于影像组学的图像纹理分析正在成为一种趋势,可提供更全面、更丰富的信息,提高CMR诊断和预测价值。基于LGE的图像纹理分析特征可以反映瘢痕的异质性,具有较LGE本身更好的预测效能,但仍需要使用对比剂。而HCM多为年轻人发病,随访过程中需要反复使用钆剂,会造成各系统异常钆剂聚集,对身体造成伤害[34,41]。虽然心脏电影、T1-mapping、T1WI、T2WI等序列无需注射对比剂,可进行图像纹理分析,但研究成果还处在HCM诊断、心肌组织特征的识别及表征层面,其预测价值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综上,CMR传统图像分析手段和纹理分析各具优缺点,随着CMR新技术的发展与成熟,两者结合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且将在HCM危险分层和预后评估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