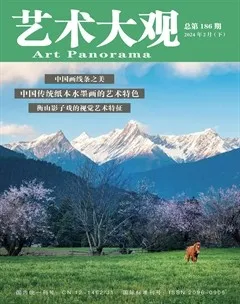20世纪初录音与现代音乐家演奏实践的风格比较
2024-05-28赵淑娴
赵淑娴


摘 要:“演奏实践”这一术语如今越来越受现代学者们的关注,从字面对其进行阐释,在中国古代文学《宋史·理宗纪》中记载:“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1]这里“实践”是指实行;履行,用行动使成为事实。那么“演奏实践”则指演奏家将文本的音乐符号转化为音乐实体的过程。而在西方《新格罗夫音乐词典》(1901)中,阐述该词来自德文“Aufführungspraxis”,而与之相关联的是“诠释”一词,《里曼音乐词典》(Riemnns Musik-Lexikon)中阐释“诠释”一词源自拉丁语“Interpretazione”,具有解释之意,是指演出者将乐谱上的音乐呈现出来。
关键词:录音;演奏实践;风格比较
中图分类号:J6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0905(2024)06-00-03
如上文所述,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演奏实践都需要从音乐文本入手进而转化。而若要追溯音乐乐谱文本则要从古希腊字母符号谱,到中世纪的纽姆谱,再到现代作曲家“精益求精”的乐谱。几个世纪以来,乐谱的标记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录音技术的问世,使得演奏实践研究产生了新的方向。录音技术一劳永逸地将作品归于一个确定的音乐形式上。对于演奏者来说,“二次创作”时所呈现的主观“解释”原则也受到了一些挑战。
本文将对20世纪初至今不同演奏家对于同一作品音乐诠释的不同风格进行探究,进而对20世纪初录音版本和当下现代音乐录音版本的差异作浅显之谈。
一、20世纪初的录音技术发展环境
爱迪生的锡纸留声机(1877)开启了声音复制的时代,为表演实践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新型资料。在20世纪初的声学录音(acoustic recording)技术发展下,录音室的环境非常简陋,其与音乐家曾经所熟悉的,宽敞明亮的音乐厅相差甚远。并且声学录音需要艺术家或演奏者在固定的录音设备前表演,限制了他们的移动和表演的自由度,从而导致演奏者无法完全展现音乐作品的表现力和舞台魅力。与此同时,由于当时声学录音技术限制,声学录音无法准确地捕捉音乐的细节和动态范围,导致录音总体质量相对较差。这使得当时的音乐录音师无法客观地完全还原演奏者及艺术家的音乐表现和真实感受,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音乐的传达和欣赏效果。在时间方面,由于当时声学录音设备使用脆弱的介质,无法实现长时间的连续录制。录音需要频繁更换介质,增加了录制过程的复杂性和成本,这限制了音乐录音的持续性和连贯性。以上种种问题都反映了20世纪初声学录音技术下客观存在的限制性,使得听众从录下的声音中根本無法得知录音室里音乐作品中的任何声学特点。因此,在录音技术还不成熟的20世纪初,大多数音乐家对录音表现出一定的不适应性。例如,拉赫玛尼诺夫曾发表过“憎恶麦克风”或者“恐惧红色信号灯”之类的言论。[2]但于此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初的声学录音技术仍然具有历史意义,为当时的音乐记录和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并为后来的录音技术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二、音乐作品介绍
《Scherzo NO.1 in B minor,Op.20》这首作品是肖邦得知华沙爆发反沙俄武装起义之后而作的,因此在音乐中涌现与迸发了从未有过的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舒曼曾评价此作品:“既然连玩笑都披上了黑纱,那么庄严又该穿什么服装呢?”[3]的确,尽管这是一首谐谑曲,但在整首作品中充斥的是绝望与悲愤。接下来笔者将对利奥波德·戈多夫斯基(Leopold Godowsky)、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Vladimir Horowitz)、郎朗三者的录音版本进行比较。
三、《Scherzo No.1 in B minor,Op.20》三个录音版本的分析
三个录音版本的具体信息见表1所示。
(一)演奏家个性特征
由于个性气质、生活经验、社会环境、审美理念等差异,不同的演奏家形成了独特而赋有个性化的音乐风格。他们的音乐表演通过音乐独有的形式——音响,展现出独特的表现力。作为艺术表现的主体,他们对旋律、节奏、速度、和声等音乐表现要素的处理方式各异。同时,又融入了个人的审美经验与艺术观念,从而使其音乐蕴含了更深层的个人意义。本文在分析不同演奏家的录音时,发现不同演奏家的个性特征对音乐诠释的风格有着巨大影响。
在录音技术刚刚兴起的时代,大多数的音乐家对录音抱有“厌烦”情绪。比如,斯特拉文斯基在写给朋友的信件中,他抱怨录音过程没完没了地重复带来折磨神经的体验,而同时代的很多演奏家也深有同感。但对于戈多夫斯基这位追求完美而易于紧张的人来说,即便是在音乐厅演奏,也会有着某种程度的拘束。腼腆和拘谨的性格特征影响了他的演奏效果,同时,在弹奏的力度上他也不会用力过猛,始终保持着一种文雅的风度。
霍洛维茨的音乐演奏极富个人色彩,以至于任何听过他演奏的人都能轻易地将他的音乐创作与其他演奏家的演奏区分开来。他十分善于使用断奏,短促而扎实的音乐表现手法,也是霍洛维茨演奏作品时的一大特点。他的琴音灵动剔透,其左手运用了特殊击键方式使其音乐充满一定冲击力与独特性。
中国演奏家郎朗的演奏风格以极具个性化的表现力而被大家熟知,他性格的自信、乐观、洒脱,导致其音乐风格的豪放张扬,也因此而受到广大音乐爱好者的喜爱。
(二)版本时长及特点
从宏观速度布局来看,最引人注目的是戈多夫斯基版本(总用时716”),他的演奏整体偏快,特别是他对于尾声的处理,听感上略显仓促。相对而言,郎朗的演奏(总用时947”)更加具有音乐的方向性。他将情感处理得更加细腻、抒情,并且演奏速度较为缓慢。通过丰富的表情语言和身体动作完美地展现了音乐作为一种可观赏艺术的视觉盛宴。他的演奏时长较长,作品中呈现出的个性化元素也最为丰富。此外,霍洛维茨(总用时828”)在第一乐段的a部分的演奏用时最多,用时47秒。在这版录音中,他用了一种反常的慢速来演奏,听感上极具个人色彩。
(三)演奏手法的对比
本曲的引子部分是两个完全不协调的和弦,宛如两个巨大的惊叹号,为整个曲子创造出了一丝紧张不安的氛围。戈多夫斯基演奏引子时,较为中规中矩,且有急促与“草率”之意;霍洛维茨演奏引子时,将音乐从强音(ff)过渡到更强的音(sf),力度对比鲜明,使得音响连贯而又紧凑。郎朗演奏的节奏最为自由,两个和弦的“惊叹号”变成了一问一答。乐句的衔接间带有部分的渐慢或突强,同时通过节奏的加紧或收放,增强了音乐的动态性特征。在呈示部,郎朗演奏速度很快,旋律不断攀升,爆发力极强。戈多夫斯基发展同样激烈。然而霍洛维茨演奏呈示部时呈现出格外严谨的结构模式,引子部分的颗粒性较强,力度对比富有戏剧性。戈多夫斯基和霍洛维茨均强调了左手和弦的进行,并且重音的处理十分精巧。而郎朗自由热情的演奏风格赋予了这首谐谑曲新的生命。
从74小节开始,整体的音乐变得惶恐不安,戈多夫斯基的演奏贯彻了其一开始的急促风格,好似要将情绪推向最高点。高低声部、三个八分音符所组成的旋律线形成了一种对峙的效果,而主旋律则隐藏在高音部的最高音中,使其音乐力不断凝聚上升,后又慢慢回落。而霍洛维茨的演奏并没有一度地追求音乐的速度,而是在音与音之间设计一些意料之外的休止与停顿。音符的演奏变得灵动纯粹,少了些紧凑感,突出左手的重音演奏,与戈多夫斯基的版本形成了鲜明对比。而郎朗则以他华丽的演奏方式和超高技艺,将半踏板以及颤音踏板(Flutter Pedal)灵活地混合应用。
肖邦在展开部旋律的写作时模仿了对巴赫复音音乐的不同声部间的模仿,使一个声部产生了两种不同的音响。右手高音部看似只有一个声部,但事实上大指为旋律,小指为伴奏,演奏者必须把音色区分出来,让右手表现出两个声部的效果。[4]这一部分,演奏最为突出的是霍洛维茨,中声部的持续音自始至终都存在。
尾声部分的情绪迸发将音乐推向顶峰,不断出现的fff力度符号将一个个强烈而尖锐的和弦奏响连续重复了九次。在“con brio”的指引下,音乐以活力积极的方式下行,然后以半音阶的上行作为终结,宛如狂风一般,以辉煌的姿态结束了整个曲子。然而在本曲最后八小节的六个和弦的演奏,戈多夫斯基弹奏得相当急促,频繁运用缓急重音的手法,给人们的听觉带来了明显的伸缩变化。相比之下,霍洛维茨和郎朗演绎的音符节奏与时值则比较严谨,更偏于标准化。
(四)弹性速度的分析
“弹性速度”(Tempo Rubato),原文的意思为“被夺去的时间”(Stolen Time)。《牛津简明音乐词典》解释为:“一种演奏方面的现象,在一个短时间内不顾及严格的拍子,在某个音符或某些音符中夺取的时间在后面给以补偿[5]。”根据音乐的进行适当增減速度,从而使得音乐更加自由,具有歌唱性。也就是这种弹性速度,让演奏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酌情处理乐句之间的紧密联系。戈多夫斯基的rubato处理在乐句演奏的划分上,似乎并未按照谱面的演奏标记,将两个乐句的划分变为一个长句。在装饰音部分,似乎更倾向于古典风格的演奏风格。而霍洛斯茨的处理相较于其他两位较为快速,中声部的旋律的演奏最为突出,旋律不断地高扬,直至最高音?G,随即突然渐慢。装饰音的处理的延迟演奏,突出了情感的表达。而郎朗总体偏于抒情缓慢,有一种渐入云层之感,与前段的摇篮曲形成呼应。这一部分装饰音的弹奏,郎朗处理得较为自由,出现了一些左右手的错置对位。
不同作曲家对于rubato的处理有所不同,慢—渐快—推向高点,使音响效果富有张力。而有些演奏家“倾囊诉说”,缓缓道来。由此说明,音乐是感性的产物,每个人有自己的认知处理方式。
(五)音色处理的分析
由于戈多夫斯基版本录音为20世纪初,当时录音技术不够成熟,同时录音师要求演奏家需要极度克制音响的强弱对比,从而导致戈多夫斯基录音版本的音色层次感和强弱对比不够鲜明。而在霍洛维茨和郎朗的录音中,对比明显,高音音色较为清脆,而低音音色则更为厚实和深沉。在三位演奏家的表演中,霍洛维茨在音色的特殊处理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处理最弱音时,他甚至能使其弱到你几乎无法听清,但又在微弱中显现出来。这需要出色的键盘控制力。可以说在音色的控制程度上,霍洛维茨是无人能超越的。
四、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肖邦《Scherzo No.1 in B minor,Op.20》作品不同录音版本的聆听,分析从20世纪初至今,三位具有跨时代代表性意义作曲家的音乐诠释,进而对20世纪初录音版本和当下音乐录音版本的差异作浅显之谈。在戈多夫斯基的录音中能够听见较多的匆忙的短音符和过多点缀的节奏,从而在听觉感知上总会产生一些认为演奏处理缺乏控制的“错觉”。而这些在其后霍洛维茨和郎朗的版本中都得到了明显的克制。在旋律方面,如装饰音的弹奏,会以轻巧快速的方式弹奏。而当代的演奏家则更加偏向于弹性速度的演绎。杨健老师总结20世纪初的音乐时说:“在20世纪初,那些被称为缓急重音或不均衡的节奏等传统演奏,似乎更像是一种古老的叙述方式,当代的听众习惯渐渐无法十分清楚地解读其中的表现含义。”[6]对于20世纪初录音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对当代演奏风格中的精确性、规范性倾向特征进行反思,从而也为未来的演奏实践领域产生了全新的视野。
参考文献:
[1]刘绪义.周敦颐的为官之道[J].刊授党校,2016(04):66.
[2]杨健.录音技术对20世纪西方音乐表演风格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0(04):48-54.
[3]李琦.“披着黑纱的玩笑”——肖邦《b小调谐谑曲》Op.20研究[J].音乐时空,2016(07):63-64.
[4]谢承峯.漫游黑白键:西方钢琴作品解析与诠释[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8.
[5]谢承峯.论弹性速度的广义概念与应用[J].艺术评论,2015(08):94-96.
[6]杨健.20世纪西方器乐演奏风格的结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基于计算机可视化音响参数分析的研究结果概述[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8(03):104-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