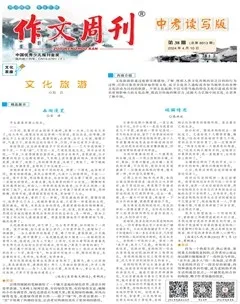文化旅游
2024-05-26刘兵
刘兵
内容介绍
文化旅游指通过旅游实现感知、了解、体察人类文化具体内容之目的的行为过程,泛指以鉴赏异国异地传统文化、追寻文化名人遗踪或参加当地举办的各种文化活动为目的的旅游。开展文化旅游,不仅可将当地的特色文化打造成具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提高目的地的吸引力,还能大力弘扬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
精品展示
西湖漫笔
◎宗 璞
平生最喜欢游山逛水。
……
六月间,我第四次去到西子湖畔,距第一次来,已经有九年了。这九年间,我竟没有说过西湖一句好话。发议论说,论秀媚,西湖比不上长湖天真自然,楚楚有致;论宏伟,比不上太湖,烟霞万顷,气象万千,好在到过的名湖不多,不然,不知还有多少谬论。
奇怪得很,这次却有着迥乎不同的印象……几天中我领略了两个字,一个是“绿”,只凭这一点,已使我流连忘返。雨中去访灵隐,一下車,只觉得绿意扑面而来。道旁古木参天,苍翠欲滴,似乎飘着的雨丝儿也都是绿的,飞来峰上层层叠叠的树木,有的绿得发黑,深极了,浓极了;有的绿得发蓝,浅极了,亮极了。峰下蜿蜒的小径,布满青苔,直绿到了石头缝里……
西湖胜景很多,各处有不同的好处,即便一个绿色,也各有不同。黄龙洞绿得幽,屏风山绿得野,九溪十八涧绿得闲。不能一一去说。漫步苏堤,两边都是湖水,远水如烟,近水着了微雨,也泛起一层银灰的颜色。走着走着,忽见路旁的树十分古怪,一棵棵树身虽然离得较远,却给人一种莽莽苍苍的感觉,似乎是从树梢一直绿到了地下。走近看时,原来是树身上布满了绿茸茸的青苔,那样鲜嫩,那样可爱,使得绿荫荫的苏堤,更加绿了几分。
在花港观鱼,看到了又一种绿。那是满地的新荷,圆圆的绿叶,或亭亭立于水上,或婉转靠在水面,只觉得一种蓬勃的生机,跳跃满池。绿色,本来是生命的颜色,我最爱看初春的杨柳嫩枝,那样鲜,那样亮……荷叶,则要持重一些,初夏,则更成熟一些,但那透过活泼的绿色表现出来的茁壮的生命力,是一样的。再加上叶面上的水珠儿滴溜溜滚着,简直好像满池荷叶都要裙袂飞扬,翩然起舞了。
从花港乘船而回,雨已停了。远山青中带紫,如同凝住了一段云霞。波平如镜,船儿在水面上滑行,只有桨声欸乃,愈增加了一湖幽静。一会儿摇船的姑娘歇了桨,喝了杯茶,靠在船舷,只见她向水中一摸,顺手便带上一条欢蹦乱跳的大鲤鱼……同船的朋友看得入迷,连连说,这怎么可能?上岸时,又回头看那在浓重暮色中变得无边无际的白茫茫的湖水,惊叹道:“真是个神奇的湖!”
我们整个的国家,不是也可以说是神奇的么?我这次来领略到的另一个字,就是“变”。和全国任何地方一样,隔些时候去,总会看到变化,变得快,变得好,变得神奇。
更何况西湖连性情也变得活泼热闹了,星期天,游人泛舟湖上,真是满湖的笑,满湖的歌!两三人寻幽访韵固然好,许多人畅谈畅游也极佳……每个人在公余之暇,来休息身心,享山水之乐。这热闹,不更千百倍地有意思么?
(选自《名家散文精选》,有删改)
●赏读
宗璞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铺天盖地的绿色世界:道旁古树苍翠欲滴,飞来峰上绿树层叠,有的绿得发黑,有的绿得发蓝;蜿蜒的小径布满青苔,绿色直渗进石头缝儿里;黄龙涧绿得幽幽,屏风山绿得苍苍,花港绿得清新自然……除了“绿”外,作者还紧扣一个“变”字展现了西湖的变化,让读者对西湖的美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瑞丽情思
◎高洪波
云南的边陲小城瑞丽,一直让我念念不忘。为什么呢?一是因为我曾经在几十年前,在瑞丽一带有过将近一百天的采访活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二是我原来所在的炮兵团,在十几年前整建制地变成驻防瑞丽的边防团,这对我来说好比娘家整体搬家,所以瑞丽带给我诸多的牵挂。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只赭黑色的水罐,这是一只陶土烧制的水罐,古朴、笨拙。无数次搬家,这水罐一直是我的珍藏,不为别的,就因为这里面盛满了一位傣家老妈妈的情意,像米酒一样,时间愈久愈醇厚。
记得上世纪70年代中期,告别云南边陲的瑞丽县、途经怒江大吊桥时,由于是边防站,乘客要下车接受检查。我当时只是抱着这只水罐。边防站的战友们感到奇怪,过去一看,哦,是一罐大叶炒青茶,再端详一下这古朴的水罐,便微笑着递给了我。
我与傣家老妈妈的相识,是在边陲的一座傣家寨子里。当时我以现役军人的身份陪同两位云南作家深入生活,办创作讲习班。
在瑞丽,我首先结识的是老妈妈的女儿,一位有着标准北京口音的县广播站播音员。从这位傣族播音员口中,我才知道她们一家一直生活在北京,几年前才和妈妈一起回到故乡瑞丽。我是北京人,老妈妈一听我的口音,就有一种“亲不亲,故乡人”之感。老妈妈出生在这里。抗战时期,老妈妈同一位在这里修筑临时机场的青年工程师相恋。老妈妈跟随这位工程师来到北京,近几年才回到阔别许久的故乡。
老妈妈领我穿过长满含羞草的草地,站在滚滚的瑞丽江畔远眺对岸的异国风光。她在竹楼四周种满鲜花,无比自豪地展示着自己育花的本领。她对房前屋后的花草十分上心,用细细的竹竿编成鸟笼似的篱笆。老妈妈的花大多是本地田野常见的,如夜来香、栀子花、含羞草,以及热带地区常见的蛇皮兰等花草,老妈妈让这些绿色的植物环绕、装点着自己的生活。
临分别时,傣族老妈妈挖出一捆蛇皮兰,又递给我十几棵常青藤,嘱咐道:“这些东西在瑞丽不值几个钱,带到北京可就珍贵了,你一定要保护好。”转身又抱来一只赭黑色的陶器,说:“这是大妈从缅甸买的,过瑞丽江时累得我好苦,我一直抱着它,生怕在船上跌碎了。”
水罐就这样到了我的手里,以一种古朴的韵味,赠我以绵邈的情思。
之后,我再没有机会返回瑞丽看望这位老人。
然而这位老妈妈却一直记挂着我。我曾收到过当年同行的一位作家的来信,他再一次走访瑞丽的时候,得知老妈妈至今没有忘记多年前造访过她的北京口音的军人。从来信中,我才知道老妈妈的老伴从北京回到瑞丽后不久便去世了,现在她孤身一人,守着那幢竹楼,竹楼四周种植了许多甘蔗,生活得还不错。
我多么盼望能在一个明丽的夏日,重新踏上那绿荫遮蔽的乡间小道,寻找边陲甘蔗林中翠绿色的竹楼,向那给予我温暖与母爱的傣家老妈妈一诉衷肠啊!那条小路,想必是鲜花依然艳丽、栀子花的清香依然醉人心脾吧?
(选自《人民日报》2022年1月12日,有删改)
●赏读
因为一个热爱生活、热心善良、重情重义的傣族老妈妈,让作者对云南这座边陲小城瑞丽多了一份怀念与牵挂。“亲不亲,故乡人”的一见如故,让作者与老妈妈开启了一段美好的相遇:四周种满花草的竹楼,成为老妈妈平淡生活的最佳装点;一只赭黑色的古朴的陶器,赠予作者绵邈的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