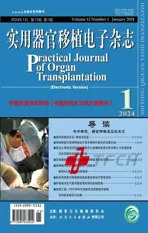肾移植适应证的变迁
2024-05-26赵杰窦古枫薛武军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肾移植科天津300000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脏病医院肾移植科陕西西安7006
赵杰,窦古枫,薛武军(.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肾移植科,天津 300000;.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脏病医院肾移植科,陕西 西安 7006)
肾移植是终末期肾脏疾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患者有效治疗方法[1-2]。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随着血管吻合技术、免疫学、免疫抑制药物、器官保存等技术的不断发展,移植物和患者的生存率有了显著改善。肾移植的适应证也在随着这些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发生变化。但肾移植仍然面临供体短缺、慢性排斥反应、原发病复发等导致远期预后不佳的问题,临床上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回顾了肾移植适应证的变迁,并提出未来的策略以解决当前患者和移植界面临的问题。
各种肾脏疾病引起的ESRD,或者肾小球滤过率小于15 ml/min, 均为肾移植的适应证。常见的疾病包括:肾小球肾炎,如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膜性肾病、IgA 肾病、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等;遗传性疾病,如Alport 综合征、多囊肾、肾髓质囊性变等;代谢性疾病,如糖尿病肾病、原发性高草酸尿症、Fabry 病、肾淀粉样变等;系统性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肾炎、溶血性尿毒综合征等;先天性畸形,如马蹄肾、先天性肾发育不良等。随着血型抗体滴度测定技术、高分辨组织配型技术、基因检测技术、流式交叉配型淋巴细胞毒检测技术、新型免疫抑制剂的不断发展,肾移植手术逐步成为常规手术,具有成熟的手术方案和治疗流程。同时,肾移植的适应证随着科学技术更新、供体选择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
1 老年及儿童肾移植
1.1 双 肾 移 植(dual kidney transplant , DKT):由于医学伦理问题,年轻供体将优先分配给年龄相仿的受者。而老年供肾的质量下降,肾单位减少,单个肾脏不能满足受体代谢需要,并且存在远期预后不良的风险。这导致老年受者可接受移植的机会窗非常窄,面临较高的病死率。供肾短缺及老年慢性肾衰竭患者数量逐年增加,双肾移植将成为此类人群得到救治的有效途径之一,这也是对于老年患者行肾移植适应证的一种扩大。而如何评估老年供肾质量和如何进行受者匹配至关重要。1999 年,Remuzzi 等[3]提出了基于移植前活检的评分系统,用于选择DKT 的肾脏,他们报道的24 例DKT 中,6 个月时患者和移植肾存活率为100%。目前临床常用的双肾移植供体标准:临床标准主要是供者年龄 和eGFR,年 龄>60 岁、30 ml/min <eGFR <60 ml/min 时可评估采用DKT[4-5];组织病理学标准是根据活检病理(包括肾小球硬化、肾小管萎缩、间质纤维化、动脉狭窄)综合评分:评分0 ~ 3 分者可行单肾移植,4 ~ 6 分行DKT,评分≥7 分则弃用肾脏[3]。对于DKT 的最佳受者存在争论。由于大多数DKT 涉及高龄供者,因此许多作者建议行供受者年龄匹配。一是功能有限的肾单位质量能够满足代谢需求低的老年受者,而且根据预期寿命,老年供肾给老年受者符合伦理要求。此外,由于老年受者排斥反应发生风险低,较低剂量的钙调磷酸酶抑制剂能减少肾单位损伤[6]。双肾移植增加了边缘肾的使用,使一些老年尿毒症患者得以获得手术的机会,改善了生活质量和远期预后。
1.2 儿 童 肾 移 植(pediatric kidney transplantation,PKT):历史上儿童肾移植发展缓慢,主要原因为儿童长期透析充满了与透析通路、营养、生长、骨骼疾病以及发育和神经认知延迟相关的问题[7-8]。其次为儿童肾移植手术外科技术难,血栓发生率高[9],并且存在对肾衰竭儿童进行积极治疗的获益与风险的伦理争议,以及儿童死亡供者严重缺乏等原因,最初儿童被认为是肾移植的禁忌证。随着透析技术以及移植技术的不断发展,儿童肾移植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已经没有年龄限制,一般选择在1 ~ 18岁[10],且普遍认为儿童早期行肾移植手术对其生长及发育是有益的,尽管术后需要使用包括类固醇激素在内的免疫抑制剂。这得益于大量临床经验的总结,可以逐步减量激素,甚至完全停药,最大程度上减少激素对儿童生长发育以及认知障碍风险的影响。最初的儿童移植受者存在严重感染导致无法接受的高病死率,而谨慎且较弱的免疫抑制常导致无法接受的高排斥反应发生率,而现代免疫抑制已降低了这一发生率,尤其是他克莫司等新型免疫抑制剂的问世,在排斥反应发生率和病死率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降低。如今,感染仍然是儿童移植后死亡的主要原因[11],且许多感染因子具有致癌性,这显著增加儿童移植受者罹患癌症的终生风险。如EB 病毒可能引起移植后淋巴组织增殖性疾病。尽管问题仍然存在,但迄今取得的进展有望在未来为需要肾移植的儿童患者带来更多希望。
2 病毒性感染与肾移植
2.1 乙肝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s,HBsAg)阳性〔HBsAg(+)〕肾移植:既往认为,尿毒症患者合并HBsAg(+)和HBV-DNA(+)行肾移植手术是不可行的,因为这将面临严重的乙肝病毒暴发性复制,甚至引起急性肝脏衰竭而危及生命。但随着抗乙肝病毒药物-核苷酸类似物的出现,此类患者行肾移植手术成为可能,因为核苷酸类似物可以抑制病毒的复制,使HBV-DNA 处于极低复制水平而达到HBV-DNA(-)。术后继续抗乙肝病毒治疗,使得爆发性肝炎的发生率大大降低。针对此类患者,肾移植术后HBV 感染的监测至关重要。美国移植学会建议在移植后至少12 个月内,每3 个月监测1 次肝酶、HBsAg 和HBV DNA。随后的治疗是基于第1 年期间检测结果的情况[12]。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新型药物的出现使HBsAg(+)供体的使用也在发生着变化。普遍认为HBsAg(+)供肾匹配HBsAg(+)受者是符合医学伦理要求的。但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将HBsAg(+)供者的肾脏移植给HBsAg(-)的受者,并谨慎考虑其风险和获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肾移植的适应证,因为与将潜在受者保留在等待名单中相比,从HBsAg(+)供者移植肾给合适的受者是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选择[13],体现在透析患者的高病死率和严重的心脑血管并发症。而HBsAg(+)供肾肾移植所面临的感染传播风险被证明极少发生。最近的一项研究从HBsAg(+)供者向HBsAg(-)受者进行了83 个活体的肾移植,观察组移植前28%的供者是HBV DNA(+), 24%的受者没有抗-HBs,结果显示,这种治疗提供了良好的移植物和患者存活率,没有过多HBV 传播[14]。原则上,接受HBsAg(+)供肾的受者应具有保护性抗-HBs。一些指南和研究提示,抗-HBs >10 mU/ml 可以起到保护性作用[15-17],且术前进行疫苗接种认为是必要的。另一种预防HBV 经肾移植器官传播的方法是使用抗病毒药物和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human hepatitis B immunoglobulin,HBIG)。HBIG 为高浓度的抗-HBs,其提供被动免疫,目的是作为HBV 的中和抗体[18]。已报道的长期结局结果显示,与没有HBV 标志物的供者相比,经过适当的预防方案,受者的结局良好[19-20]。HBsAg(+)供 者 在 抗-HBs >10 mU/ml的受者中的研究报告显示10 年移植物存活率为84.6%,受者生存率为92.8%[21]。而HBV 感染及爆发性肝炎的发生率是非常低的。总之,HBsAg(+)、HBV-DNA(-)受者行肾移植手术是安全可行的,这归功于抗病毒药物对乙型肝炎病毒的有效控制。在器官短缺的现实条件下,捐赠者HBsAg(+)不应阻止肾脏器官被使用。对于愿意接受此类供者肾脏移植的候选者,还需要一些额外的治疗以及术后严密的监测随访,这同样适用于活体肾移植中。
2.2 丙型肝炎阳性〔HCV-RNA(+)〕肾移植:ESRD 合并HCV-RNA(+)患者行肾移植术在抗病毒药物出现之前是禁忌证。首先是因为肾移植术后的抗排斥治疗会加重HCV-RNA 的复制,造成肝细胞的损害,严重者会出现暴发性肝炎而导致肝衰竭。其次是HCV 的持续性感染会加重肾脏的损伤,加速移植物的丢失,对预后产生不利的影响。还有相关的移植中心由于HCV 监管制度而不愿接受“高危”患者,以及普遍的社会经济支持水平较低等。综上原因,HCV-RNA(+)人群被纳入肾移植等待名单困难重重[22]。HCV-RNA 的清除依赖抗病毒药物的出现。2011 年之前聚乙二醇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治疗12 ~ 24 周是HCV 的标准治疗方案,耐受性差和疗效不一致是它的主要缺点[23]。其病毒根除率为40% ~ 50%,持续病毒学应答(sustained virological response,SVR)率 为70% ~ 80%[24]。第 一 代 直接作用抗病毒(direct-acting antivirals,DAAs)为Telaprevir 和Boceprevir,于2011 年获得批准,疗程较短,可提供显著较高的SVR,但干扰素和利巴韦林仍是疗法的一部分。第二代DAAs 于2013 年出现,索磷布韦迅速取代第一代DAAs,为无干扰素/利巴韦林治疗铺平了道路。目前的DAAs 联合治疗具有良好的耐受性和较高的疗效,为接近100%的患者提供了SVR。这为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ESRD 患者的肾移植带来了光明的前景。有效的HCV 治疗抵消了HCV 感染对移植后结局的负面影响。一项研究估计接受DAAs 治疗的患者病死率降低了57%。在慢性肾脏病患者中,数据提示DAAs 治疗HCV 感染后可改善蛋白尿和肾小球滤过率(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GFR)[25]。另一方面HCV-RNA(+)供肾分配给HCV-RNA(-)受者亦受益于抗病毒药物的出现,在器官短缺的年代,这扩大了供体池,同时器官的合理利用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扩大了肾移植的适应证,因为这让更多的ESRD 患者摆脱了透析。HCV-RNA(+)供肾的病毒传播风险及预后是值得肯定的。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将20 例来自HCVRNA (+)供者的单独肾脏移植到HCV 阴性患者体内,有3 例出现HCV 转阳并接受为期12 周的抗病毒治疗,20 例患者均获得了SVR[26]。另一项纳入11 例肾移植患者的预先试验报告,从移植的中位时间16 d 开始,索磷布韦/维帕他韦治疗12 周后,SVR 为100%[27]。综上所述,HCV-RNA(+)肾移植,无论是受体还是供体都扩大了可移植人群范围,且具有低传播风险和高治愈率。
2.3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阳性〔HIV(+)〕肾移植:HIV 感染是导致ESRD 的原因之一。HIV 感染既往被认为是行肾移植手术的绝对禁忌证,这源于感染者免疫力低下,且可能同时合并多种感染,而肾移植术后的免疫抑制又加重了感染的发生。因此,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患者在发展为尿毒症后只能通过透析来维持生命,但接受透析治疗后的生存率很低。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使HIV(+)患者接受肾移植手术成为可能,这是一种肾移植适应证的扩大。2008 年,南非的医生率先将HIV(+)的供者移植给HIV(+)的受者,最初4 例受者的1 年患者和移植物存活率均为100%[28]。这为HIV 患者行肾移植术带来了希望,随后很多中心都开始进行了此类治疗。Selhorst 等[29]描述了51 例患者的1 年患者生存率和移植物存活率分别为96%和87%,5 年随访显示患者生存率和移植物存活率分别为83.8%和78.7%。从2016 年3 月至2019 年7 月,14 个中心共对75 例HIV(+)受者进行了成人死亡供者肾移植,其中25 例为HIV(+)供者,50 例为HIV(-)供者。在1.7 年的中位随访期后,没有患者死亡,1 年移植物存活率91%,在eGFR、HIV 病毒血症复燃、感染等方面无差异[30]。最近的一篇前瞻性研究显示,其总体移植和HIV 感染结局良好[31]。患者术后在免疫抑制和抗病毒治疗上面临巨大挑战。首先是HIV(+)患者肾移植术后排斥反应发生率较高,而高强度的免疫抑制必然带来机会性感染的风险增加。其次是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和免疫抑制剂之间的相互作用。另外,HIV(+)受者的排斥率约为HIV(-)受者的3 倍[32],原因尚不清楚,但有人提出了两种假设。首先是免疫失调,其次是管理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和免疫抑制剂之间的药物相互作用的挑战[33]。目前普遍认为HIV(+)患者行肾移植术的术前条件需要满足以下3 点:① CD4+T 细胞计数>200 /μl。② 术前接受联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至少6 个月,血浆 HIV-RNA <50 copies/ml。③ 不合并活动性感染。
3 新技术带来了禁忌证的突破
3.1 ABO 血型不相容肾移植(ABO-incompatible kidney transplantation,ABOi-KT):供者和受者之间的ABO 血型不相容一直被认为是肾移植的禁忌证。针对血型抗原A 或B 形成的同种血凝素抗体是引起超急性排斥反应和导致移植失败的原因。1955 年,Hume 等[34]报道了第1 例ABOi-KT 病例,不幸的是,10 例ABOi-KT 的移植肾中有8 例在术后第1 天内丢失。后来,一些散发的ABOi-KT 被描述为不同的结果和总体移植功能不良[35-36]。直到1987年,Alexandre 等[37]描述了26 例成功的ABOi-KT,这些移植采用了活体供者、脾切除和先进的免疫抑制方案。2006 年王毅等[38]在我国首次开展ABOi-KT,成功在A 型血供者和O 型血受者间完成了肾移植,在术后的半年随访期内,未观察到感染、急性排斥反应等并发症。ABOi-KT 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术前处理方案,包括3 个方面:① 降低体内预存ABO 血型抗体滴度水平,主要方法有血浆置换、免疫吸附、二重血液滤过。② 抑制体内ABO 血型抗体反弹,包括采用脾切除术和使用抗CD20 单抗药物,脾切除术现已不被采用,因为大量的研究证明使用利妥昔单抗能达到脾切除的效果[39-40]。③ 调整好受者凝血功能障碍,这源于血浆置换和二重滤过是以白蛋白为替代液,会导致凝血因子丢失、血小板减少,这需要在术前、术中、术后定期检测凝血功能。在采用标准处理方案后大多数同种异体移植功能能保持良好,1 年移植存活率为93.3%,患者生存率为100%[41-42]。为了减少ABOi-KT 术后感染风险,人们在逐渐探索个体化抗体预处理方案,ABOi 免疫适应现象具体机制仍不明确,值得进一步研究。总之,ABO 血型抗体滴度测定技术的出现使ABOi-KT 的成功率大幅提升,术后密切的随访有效地控制了抗体排斥反应的发生,提高了移植物的存活率。
3.2 遗传性或代谢性疾病致肾衰竭的肾移植治疗:最初,由于科学技术的限制,遗传性或代谢性疾病导致的肾功能衰竭常常无法进行治疗,肾移植往往治疗效果较差,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移植物的丢失和患者的死亡。但随着组织病理学、免疫学、遗传学、基因组学等学科技术的发展,遗传性或代谢性疾病的发病机制得到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明确。这使得此类疾病致肾衰竭的肾移植治疗得到了显著的发展。
3.2.1 法布里病(Fabry disease,FD)是一种由GLA基因突变引起的α-半乳糖苷酶完全或部分缺陷所致的罕见x 连锁疾病。这种酶缺陷导致溶酶体糖脂的进行性积累至肾脏而导致肾衰竭。自1967 年首例FD 患者进行肾脏移植手术以来,由于感染并发症和早期移植失败的高发生率,人们对这种方法提出了一些担忧。之后的两项研究显示移植肾的1 年存活率为33%[43],5 年存活率为26%[44],因此,最初不鼓励FD 患者进行肾脏移植。但随着酶替代疗法的出现,移植肾的存活率大大增加。Inderbitzin 等[45]进行了一项回顾性单中心研究,发现肾移植联合酶替代疗法可使移植物5 年生存率为达90%,10 年生存率为66%。
3.2.2 非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atypical hemolytic uremic syndrome,aHUS)是一种罕见的血栓性微血管病。其预后不良,最终进展为终末期肾衰竭。因其特殊的病理生理基础,导致超过一半的aHUS 患者会出现疾病复发和移植物丢失[46],这种临床结果令人难以接受。依库珠单抗有望改变这种情况。通过术前开始使用依库珠单抗并在术后继续使用,初步经验表明,可以避免过多的复发、死亡和移植肾衰竭[47-48]。
3.2.3 Schimke 免疫-骨发育不良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多系统疾病,通常累及免疫系统和肾脏系统,因疾病本身的免疫缺陷常导致严重的感染,肾移植后的免疫抑制是感染风险雪上加霜。但近期的一项研究[49]显示,SIOD 患者同期序贯进行造血干细胞-肾移植能够重建免疫系统并诱导形成免疫耐受,能够完全摆脱免疫抑制剂,这为此类患者开辟了良好的前景。还有很多一直被认为不适合行肾移植术的遗传性或代谢性疾病会随着新的药物或新的方法的研究成功,逐渐成为可能。
3.3 高致敏肾移植:高致敏患者既往为肾移植的禁忌证。抗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抗体和记忆B 细胞和T 细胞形成了一个免疫屏障,与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的风险增加和较差的移植物存活率相关,这对器官移植来说仍然是一个持久且难以逾越的障碍。由于没有移植的可能性,这些患者仍在接受透析,病死率是脱敏后接受移植的致敏患者的2 倍多。脱敏通常用于创造移植HLA不相容肾的机会窗。随着高分辨率配型技术的出现,以及流式交叉配型应用于临床,能够更加精准的知晓HLA 抗体的位点和致敏强度,从而在供体筛选和后续的脱敏治疗上提供指导。目前被广泛认可的脱敏方案是联合使用IVIG、血浆置换和利妥昔单抗的方法。一些研究总结了脱敏的结局,总体良好[50-52]。Montgomery 等[53]报道了利妥昔单抗 +小剂量IVIG方案脱敏的211 例患者长达8 年的随访结果表明,与继续接受透析的患者相比,行肾移植的高致敏患者的死亡风险显著降低。Orandi等[54]的数据还提示,如果在尝试脱敏和移植之前对患者进行适当选择,则可以获得良好的患者和移植物长期生存。尽管取得了进展,但急性和慢性抗体排斥仍然是不相容移植长期成功的一个重大障碍。近年来,新型药物不断问世,如蛋白酶体抑制剂硼替佐米和补体成分C5 抑制剂依库珠单抗等。最近一种名为来源于化脓性链球菌(IdeS)的IgG 降解酶的新型药物被用于脱敏。这种内肽酶具有瞬间选择性地将人IgG 裂解为F(ab')2 和Fc 片段的能力。在美国和瑞典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共有25 例患者在HLA 不相容的肾移植之前接受了ideS 治疗,治疗后6 h 内血清IgG 完全消失,所有患者均转为DSA 阴性[55]。这为高致敏肾移植受者带来了曙光。
4 总 结
肾移植适应证的扩大从某种意义上改变了很多尿毒症患者的结局,使他们能够摆脱透析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更是提高了他们的生存率。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既往被认为是肾移植禁忌的情况逐渐成为适应证,这令人鼓舞。但仍然有很多的障碍包括老年供肾使用普及、PKT 带来的感染和肿瘤风险、ABOi-KT 和高致敏肾移植的远期抗体排斥以及遗传性疾病致全身多系统损伤等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解决,任重而道远。我们寄希望科学技术的再发展能够带来肾移植适应证的再突破,为更多ESRD 患者带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