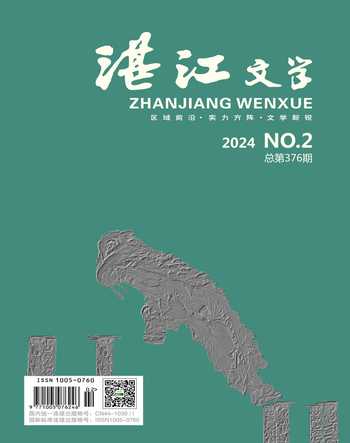巨鲸游向一片月光
2024-05-14黄宝琴
黄宝琴
一
还不到一周岁的时候,我就在洗澡盆里学会了游泳。
那是一个红色的塑料盆,直径大约一名是成年人伸直一只手臂的大小,这些红色塑料盆一个个被立在百货商店的门口,不是被买来做孩子的洗澡盆,就是搁在码头或市场门口,用来放从海底捞起来的各色海鲜。
母亲林焕娣逢人就骄傲地笑着说,我家孩子还没学会走路就先学会了游泳,天生就注定是海的孩子。尽管当时的我听不懂,但总会回以母亲一个灿烂的、带着口水的笑容。父亲李国明从渔排回来,肩上扛着已被太阳晒干的渔网,手里提着滴答滴答正漏着海水的黑色塑料袋,里面是新捕获的鱼。他又一次把鱼扔到我的洗澡盆里,大吼道:“一个女孩子学会游泳有个屁用,你快去做饭,我要饿死了。”
咸腥的海风穿街过巷,让大大小小的鱼儿误以为自己仍在海中,它们在洗澡盆里挣扎,跳跃,想要逃出这个小小的牢笼回归大海。鱼尾巴在空中一次又一次地奋力摆动,甩进奋力想要爬到洗澡盆旁的我的眼睛里。我大哭了起来,父亲明明坐在屋里喝茶,却好像听不见我的哭声,只是按着遥控器,将电视的声音放大。母亲从厨房里跑出来把我抱起,用袖口擦了擦我糊在我眼睛边上的鱼鳞,低头轻轻吹着我的眼角。
“妈妈在这呢,佩德不哭”,混合着呜呼的海风声,那是我一辈子听到过的最动人的音乐,它伴随保护着我变高,长大,成人。
我的洗澡盆在被鱼虾蟹螺等霸占了以后,母亲只能抱着我窝坐在仅半个手臂大小的洗衣盆里洗澡,里面没有多余的伸展空间,就更别提游泳了。长大以后母亲回忆起这件事,嘴角总带着一丝微笑:“你啊,换了个盆洗澡就好像要了你的命似的,总是在那里哇哇大哭,眼泪鼻涕一起流,还经常把自己呛到咳嗽。一咳起来可吓坏我了,一直拍你的后背,很怕你缓不过气来会窒息。”
一天清晨母亲在醒来以后,背起我骑着小电驴,到附近的斜吓沙滩上抱我下海游泳。这仿佛是母亲施的一个魔法,当晚我在洗澡时不再号啕大哭,反而出发咯咯的笑声。从那以后,母亲每天都会早起带我去海边游泳,慢慢地她不再需要抱着我,而是放开我,让我自己在海边畅游。附近的渔民从小看着我游泳长大,他们每次见到我都不喊我的名字,而是喊我“小美人鱼”。
我很喜欢这个称呼,像是某种无形恰巧的关联吧,在我还不认字的时候就喜欢看《美人鱼》这部动画片,认字以来更是一遍遍地读《美人鱼》的童话书,书页边角早就被我翻破了。只是我不喜欢故事的结尾,美人鱼用声音换取人的双腿,最终化为泡沫。为此,她放弃了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声音、鱼尾巴以及大海,只为来到上岸与王子一起生活,那她在某种程度上不就是无法接纳自己吗?
“接纳”这个词自然不是我当时最准确的感受,因为那会我还不懂什么叫接纳,只是含糊地讨厌故事的结尾而已。这种强烈的不满,如今想来是另一层面的共情,父亲也无法接纳我不是男孩这个事实。母亲每次说起这事脸上都带着苦笑:“当时我的肚子尖尖的,见到我的人都是怀的是一个儿子,你爸听得不知道有多高兴,结果生下来的时候医生告诉他你是一个女孩,你爸问了好多次医生是不是搞错了,他生的是明明是一个儿子。”
“可是生下我的人,是妈妈你,又不是爸。”等我明白这个道理,并且能当面跟母亲说出来的时候,她的骨灰已埋葬在港湾边上的墓园里,我的话只能说给吹过的海风听。
二
对游泳产生更大的野心,是某天从幼儿园放学,我回到家打开电视,里面播放着游泳比赛的画面。屏幕里的游泳运动员纵身一跃,便扎进了水里,像一条鱼一样在水里翻腾涌动,水花搅动出流畅又迅速的线条。
太美了,我也要成为一名游泳运动员,我心里默默许愿。
吃晚饭的时候,我将碗里的米饭吃得一干二净,以示我对刚产生的梦想的郑重决心,放下饭碗后我跟父母说:“我想成为一名游泳运动员。”
父亲“啪”地一声放下筷子,瞪了我一眼:“就你还想成为游泳运动员?这山旮旯地方的渔民后代?想要家里拿什么去支持你,有钱还不如去维修渔排呢!”
母亲听后也放下碗筷,望着父亲说话:“李国明,渔民后代为什么就不能成为游泳运动员?佩德从小就喜欢游泳,还没学会走路就先学会游泳,这不是天赋是什么?你告诉我!”
“会游泳跟成为游泳运动员是一个水平的事吗?你也会游泳,我也会游泳,有哪个渔民是不会游泳的?那我们都能成为运动员了咯?”李国明将杯里刚满上的白酒一口喝完,又再倒了一杯,顺手拿起旁边的烟盒,点上一根抽了起来。
“我说过几次了,不要在孩子面前抽烟,吸二手烟有害健康,你怎么都当听不见呢?”林焕娣起身拿起烟盒扔到垃圾桶里,被海风晒得黝黑的脸在白炽灯的照耀下有些发青。
李国明拎起垃圾桶摔在地上,又猛喝了一杯酒:“我也是吸着我爸的二手烟长大的,我的兄弟姐妹也是吸着我爸的二手烟长大的,我们身体有什么问题吗?别整天娇滴滴你的宝贝女儿,乡下人就得吃点苦头长大。”
“好,我话就跟你放在这里了,别整天乡下人乡下人的,乡下人的孩子也能当游泳运动员!”
母亲拉起我的手,牵着我来到码头,夜里的码头没有路灯,只有围栏之上的马路边传来一丝微弱的灯光。今晚没有月亮,星星发出碎碎点点的光亮,可无法照耀近乎墨色的海面,远处的渔排只剩下灰黑色的轮廓,好似只是大海一抹碎屑的影子。
母亲抱着我登上快艇,摸了摸我的头:“现在正是钓墨斗仔(乌贼)的时候,佩德我们去渔排看谁钓得多,好不好?”
我点了点头,听见快艇启动发出腾腾的声音,还有散发出来的浓重机油味。夏夜的海风在快艇的波动下,又多了几分清凉,消解了广东夏日高温的炎热。我伸出舌头舔了舔海风,有一點咸味,像放凉了的白灼海鲜的味道。
渔排被夜晚吞没,失去了光线以后,变得特别薄,仿佛只是漂浮在海面上的一叶轻舟,海风太大或海浪太汹涌,它都能借着这股力气飞向天空。我坐在渔排边上摇摇晃晃地抓着鱼线墨斗仔,越发加重这份可能会飞向天的晕眩感。
没过多久,我偷偷放下鱼竿,去到母亲不久前为我搭建的秋千上,用力往高处荡。眼睛可以看到远处墨色的海水在翻涌起白色的浪花,可以看到天际的星星逐渐被乌云遮住光芒,四周陷入一片似乎死寂的黑里,咸腥的海风味道更是加重了这股死亡气息。我不断用力往上荡,期待着下一秒自己从秋千上跳跃,就能飞入黑夜。
母亲快步走来,打破了这份黑色的死寂,她拉住秋千的绳子,将我抱在怀里:“佩德,你快要吓死妈妈了,妈妈到处找都找不到你。”
温暖的怀抱捂得我那被海风吹得冰冷的脸在发烫,一股热流从心窝直往上蹿,酸涩热辣地化作泪水从眼眶里流出来,滴落渗入母亲的衣服里。母亲拍拍我的背:“妈妈在这呢,佩德别哭,我们不怕,你想成为游泳运动员,妈妈砸锅卖铁也会支持你的。”
长大以后再回过头去细想,我依旧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年仅五岁的小孩会产生如此浓烈的自杀情绪,但深知没有母亲过来抱住我的话,我应该只会以小小的身形坠入海底的月色中,是那么的轻而又那么的沉。
三
林焕娣从不说假话,几天后她便给我报名了一个游泳班,还花了几万块钱买了一辆二手车,每天接送我在学校、游泳馆与家之间往返。
每次我坐在车里都想跟她声感谢,可话在喉咙里就是吐不出来,最后只能以在泳池里加倍的练习来报答她的付出。她坐在观众席上,可以看到我的泳姿,可以看到我游进了电视屏幕里,可却一辈子都没能听到我的一句“谢谢”。
更残酷的是,我越长大,身体就变得越笨重,距离能够获奖、登上颁奖台的秒数也就越远。我从大海里跃入游泳池,又被现实从泳池拉回到了岸上。我發现我这条所谓的“小美人鱼”,只不过是渔民随口封的花名而已,我也并不是真正的海的孩子,仅仅是我母亲的女儿而已。
每次训练结束回到家中,父亲都会在饭桌上喝酒抽烟,母亲为此一次次地跟他激烈争吵,却换不来一丝的变化。呛鼻的烟味与酒气刺入我的鼻腔,我一次次地暗示自己人类在岸上生活是可以自在呼吸,不会因此就搁浅的。
可暗示无法解救真实的生活,也无法拯救我。退队回到家吃的第一顿饭,饭桌上只有咀嚼饭菜的沉默。良久,李国明用被烟熏得蜡黄的手指,捏起一片白灼鱿鱼放到嘴里,吧唧吧唧地搅动,嘴角带着一抹得意的笑:“我就说渔民的后代当不了游泳运动员,你偏不信邪,现在好了,孩子书也读不好,游泳也没泳出一个成绩来。”
林焕娣夹了鸡腿放到我的碗里:“佩德刚回到家,能不能不聊这些有的没的,好好吃饭。”
“什么叫有的没的?”李国明摔下筷子,“为了让她学游泳,让你再生个儿子,你还不乐意,说会耽误她的训练,那你告诉我,她训练出一个什么来?”
“我生不生二胎,是我的选择,跟女儿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不要混为一谈。”
“呵,敢情又是我的不对了是吗?你们两母女一点错都没有,错在命里只能开二手车,永远都开不了法拉利。”
“李国明,佩德她才十九岁,这只是她人生的开始,你自己看看自己说的都是些什么话,怎么就好像她已经过完一辈子似的呢?”林焕娣说话时气有些喘,她一只手扶住桌子,另一只手按着心脏。
“我说得有错吗……”李国明的话音还没落下,林焕娣忽然就往后一倒,身体擦过椅背,跌落到地上。
“妈妈!”我在慌乱中的惊叫,没想到竟然成了最后一次掠过母亲耳朵的呼喊。
母亲被救护车送去医院急救,出殡入葬的整个过程在我的脑海里是一片空白,我无法接受这些无常忽然降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期间每次想起母亲,剩下的只有“急性心肌梗死亡”这个抽象的医学名词,以及她再也无法睁开双眼、永远带着苦痛的遗容。
葬礼过后没多久,李国明娶了一个仅比我大几岁,从外省过来这里打工的女孩。我不知道他们是何时认识,何时确定关系的,也不知道他们彼时确定的又是何种关系,这些都不重要,因为已然都成为了事实。
他们领完证去餐厅庆祝的那个晚上,我独自沿着公路走了将近两公里,来到斜下沙滩。又是一个没有月亮的黑夜,四周只有岸边的路灯与远处渔火,给夜色带来丝微流动的波光,声音都被波光削掉了,只留下海风与海浪的声音。
我脱下衣服,赤裸着身体走入大海中,初秋的水温将我冷冻了起来,我希望自己能如同一块冰块似的下坠。可当我的四肢遇到了水,便条件反射不由地开始划动,滚动的血液抵抗着每次涌过来的冰冷海水,我无法如同想象那般沉下去,只能一直游,游到精疲力尽为止。
月亮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海平线爬起,她银白色的手很长,轻柔地抚摸着海面,伸向被海水包围的我。水波让她的手长满了皱纹,让我想到已经不在人世的母亲,我感觉胸腔一阵滚烫,往上游到了海面,大喊了一声“妈妈”。
追随着那片月光,我赤足而行,带上一身湿淋淋的咸腥海水走回到自己的房间,踏入浴室里洗了一个热水澡。“她才十九岁”这句话,随着水汽漫入我的眼睛,憋在心底已久的眼泪与花洒一起滴落,流进了下水道。我知道它们会一路奔流,在白天的热气下蒸发,失重似的飞向天空,而又在云朵抖了抖后,重新落入大海的怀抱。
这一次躺在床上,我感觉自己终于有了天亮以后,能够睁眼爬起来继续生活的力气。
“谢谢你,妈妈。”
梦里,我坐在渔排的秋千上,一遍又一遍地对着月亮默念道,这是我与月亮之间公开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