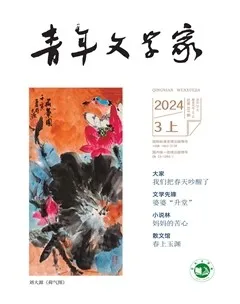破碎的梦,没有酒精的酒
2024-05-13陈世玮
陈世玮
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开始写作的第三代诗人感受到的生存状况与朦胧诗人有了较大不同,位列其中的张枣所作的诗歌不断受到争议,现代人认为张枣被神化,名不副实,可事实上有多少人贬低他就有多少人褒奖他,其作品蕴含的大量东方古典意象、西方诗法结构是被读他作品的人所熟知的特点。而张枣恰如他自己所言那般,写诗的向度上如今无人能超越,塔可夫斯基敏锐的美学嗅觉,让他在电影拍摄当中突破了线性叙事,每一个镜头所包含的语言恰如诗中不断出现的意象,以美的连贯给电影形成一种孤独与幻想交织宿命之感,而这种独具一格的美感在张枣的《镜中》同样能体会到: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面颊温暖、羞涩
低下头,回答着皇帝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
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最近二十年,张枣成为一位炙手可热的诗人。研讨会、诗文集出版、以张枣命名的诗歌奖,各种围绕他展开的活动频频不断。在整个当代诗歌界主流话语权里,张枣是一位大诗人的呼声越来越高。从2010年张枣去世迄今为止,“张枣热”从未冷却过。常常人们神化张枣,张枣也不止一次地说过,“我是个大诗人”“就我写诗的这个向度而言,我可以说,五十年内没有人能赶上来超过我……”五十年没人超过或许听起来是个噱头,但事实上离张枣写出最负盛名的《镜中》也已过去了将近四十年,未来几年是否能出个张枣,没人说得清楚。而这句话的最核心之处在于他强调的是“向度”,而非吹嘘他物。向度,指的是一个判断、评价和确定一个事物的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概念。
张枣在向度的使用上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提及张枣的诗时,人们都喜欢用中国传统诗词的方式去解构和剖析张枣在中国古典文学文本、传统韵律、意境塑造等方面进行的不同程度的借用和化用。回到中国当代诗的历史语境中看,在1980年之后开始写作的第三代诗人的生存状况与朦胧诗人有了很大不同,社会政治压力减轻了很多,取而代之的是外部世界的现代性困境。他创作立足的时代正好在后朦胧诗时期,不仅在新诗的探索上打开了一条通往传统的途径,而且还使他的作品呈现出先锋和反思的姿态。但从中国传统诗词的借鉴角度去评价他的作品似乎又有些片面了,以新批评流派的角度结合张枣的个人情况来看,张枣在20世纪80年代就旅居异国他乡,在德国接触到了很多西方美学与哲学的思想,大学讲学,结婚又离婚,他的诗歌充满着多元化的孤独感与宿命感。
一、塔可夫斯基的《镜子》,破碎的梦
初读这首诗时我联想到了塔可夫斯基的电影《镜子》,一部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剧情电影。无论从剧目上还是电影画面的选取上,张枣的《镜中》都与其有着一定的联系,影片以催眠治疗口吃的男孩的画面开始,坐在篱笆上抽烟注视远方的妇人的背影,舔舐牛奶的黑猫,不断翻动书页的小孩,着火的木屋,一只鸟撞破窗玻璃的一角飞出,桌上滚落的玻璃瓶,下雨中坍塌的房间,镜中母亲的老去,提着行李箱站在风中的医生。电影中的每一帧画面都像是一首流动、跳跃的诗歌。这些浓重的混沌感,灵魂出窍,情绪是受感染的。塔可夫斯基的创作介质是环境,是外界本身。流水、烈火、镜面,氛围澄澈,光影绝佳,情绪却是难以捕捉的。将电影中这些意象的选取和《镜中》对照来看,诗中的意象多为梅花、南山、河岸、骑马等。这些意象都有共同点在于—人能够欣赏美,但美并不都为所有人接受,人们或许会思考为什么这些意象组合排列在一起就是美的了,而单独展示或者与其他意象组合却又不美。这部电影就像窥看他人的记忆,产生了一种耦合感,也产生出了一种割裂感,以虚幻去排斥现实,这些画面都呈现出了一种静思默想的本质,似一场破碎的梦,这些梦构成的整体是从意欲世界中截然分离出来的纯粹表象世界。从本质上讲,它们不与任何实际的价值或用途有关联,同样也与叙事无关,但在思想中有着无穷无尽的指向。
塔可夫斯基在创作这部电影的时候就联系到了柏拉图的床喻说,艺术决不能将概念之间的互动作为终极目的,而是将形象作为具体的物件展現,却沿着神秘的途径延伸到超越精神的地带。“镜子”在传统视角中的意象里多起象征作用,可塔可夫斯基却明确表达了这部电影里的“镜子”不是象征性的物象,那么镜子的含义早就跳脱出了符号层面上男孩与过世奶奶对话渠道的这一媒介。这点在《镜中》里也可以很好地展现,镜中世界里的女子望向“窗外”就是在与镜外世界交流。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隐喻的范式在两位作者的很多作品中都有出现。
日常的镜子可以理解为工匠造的床,是认知能力被意欲操控的体现,而“理想中的床”为这部闭环电影跳脱的非线性叙述,毫无线索的叙述使电影的叙事带有诗意般的美感。电影结尾处在结束叙述的同时也在开始新的叙述,既是在打结,也是在解结的过程,与起始处相联通,呈镜状相通的叙事结构,这也就是将“镜”这个意象融于电影,以及人的理念之中,成为“理念中的床”。这种特殊的电影叙事如同一个巨大的精神旋涡,将观众吸到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时空中。观看这场破碎的梦境时无需在意看不看得懂,因为在此过程中可以感受到精神层面的抽象净化、洗涤,如诗一般干净、纯粹、动人。同时,这在创作时间上也早于《镜中》,这也让人联想到后来张枣在老塔式的电影中摄取到的创作方式。
二、张枣的“镜中世界”
张枣在创作《镜中》时也是站在脱离传统的叙事逻辑,使他的诗充满了无关紧要的叙事特征,此一言,那一句,诗中更多的是物象与物象、场景与场景之间的切换,这与塔可夫斯基的电影风格存在着同源。“一想起后悔的事情”与“梅花落下”两句之间是不是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呢?为什么当“想起后悔的事情”的时候“梅花会落下来”呢?首先从文学话语的角度来看:文学言语层中具有内指性,文学语言不必受到外部现实世界的过多束缚,文学作品构建起来的文学世界有着其内在的规律。此处需仔细品读才可以发现端倪,按照正常逻辑来讲的触物兴怀,应该是先“梅花落了下来”再“想起后悔的事情”,而文中恰恰是以相反的逻辑来叙述的,于是我就推测这个文学世界所在的位置可能是在标题所提到的“镜中”,在镜中世界里,一切事物形式可以是相反的,逻辑可以是相反的,内容也可以是相反的,甚至情感也可以是相反的,就好比“秋雁万里送长风”(原句为“长风万里送秋雁”),以及“上青天难于上蜀道”(原句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样的逻辑。
而与此同理,《镜子》这部电影也不存在客观理性世界中,那套由纯粹理性所制定的范式。影像自身所形成的韵律、节拍,所形成的一种美的同时带痛感的流动,既表现出我们繁忙的思想活动—持续不断的好奇、回忆、想象,也显示了静谧的时刻、聚精会神的时刻,以及聆听噪音缓慢变成旋律的时刻。而《镜子》的叙事结构是完全意识流的、非时序性的。梦境、回忆与想象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张复杂而具体的网,一张关于导演自身、有关导演过去及现在的网。
接下来,由两个“比如”所引出的“危险的事情固然美丽”也是一句逻辑相反的话,按照现实世界的逻辑应该为:“美丽的事情固然危险”,可明明是“后悔”,为什么还要“面颊温暖”,羞涩地回答皇帝?是镜子在等待她,还是她等着望向那面镜子中的世界,镜中世界的“窗外”指向的应该是“镜外世界”了,可一看向“窗外”,镜中世界的“梅花便落满了南山”,梅花并不因为苦寒才芳香,芳香是其自带的;南山也不因梅花而孤寂,使它孤寂的是空间上的距离与时间上的遥思,于是镜中世界的迷离来自镜外世界的不可触碰。而塔可夫斯基同样有着相似的想法,他认为人们欣赏艺术,其目的是找回时间,那被消磨了的、浪费了的,或者尚未体验过的时间。艺术的目的是帮助人们做好准备,以迎接死亡,将孤独之美演绎到让人窒息,但也让人无比自由、释然与超离,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的紧张感也就逐渐消失了。
罗兰·巴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将叙事作品分为了三个描述层:功能层、行动层、叙述层(话语层)。以上部分对叙述层有了初步的认识,但一种功能只有在一个行动者的所有行动中占有主导地位时才具有意义,行动者的全部行动只有被叙述并成为话语的一部分才具有意义。同样,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发现根本无法寻找到电影和诗歌二者中的叙事者,或许有人会说《镜中》和《镜子》的叙事者都是以女性视角展开的,但其实二者的女性视角都不是引导故事发展的主体,在作品中,她们可能扮演着抒情者,镜中的女子抒发着幽怨怅惘之情,《镜子》里细雨中坐在井上的母亲观看大火时抒发的绝望与幻灭。而真正的叙述者绝非二者,二者只是在文学世界里被牵着走的两个客体,镜中世界的“她”作为行动者同时也是抒情者,行动者在镜中游泳、骑马、登梯……可我们发现“她”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由自己决定的,而是由真正的叙述者去把握,真正的叙述者也不是作者本人,而是隐藏在“镜外世界”的未知者(这与庞德的《对镜自怜》相似),叙述者产生了分裂,本诗中的叙述者将叙述焦点始终聚焦于镜中的“她”,叙事者们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站在绝对感性的高地,决定着她们的一举一动,这种叙事者和抒情者的内外存在的割裂感使得二者在风格上别具一格,也传递了一种美学的概念。
三、没有酒精的酒
T.S.艾略特在1928年提到:“論诗,就必须从根本上把它看作诗,而不是别的东西。”如今对诗的批评早已跳出来古典诗歌或现代诗歌这种题材上的强烈区分,此批评如今已经进入了诗作世界、诗意语言、诗意场景中。华兹华斯也在《抒情歌谣集》中提到过:“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一件艺术品本质上是内心世界的外化,是激情支配下的创造,是诗人的感受、思想、情感的共同体现。张枣尝试塑造个人世界来创作诗歌,梅花、皇帝,包括他其他诗中出现的街巷、黄昏、向日葵等意象,都是从他的心灵世界中创作出来的,而他的心灵世界与塔可夫斯基有着一定的同源性,在二者极具脆弱敏感的心灵世界中充满了梦境、情感、灵魂、呓语……
翻阅《诗与宗教》,其中解释道:“何谓心灵?是多愁善感吗?非也。心灵不是指与理性—逻辑的东西相对立的非理性—感情的东西,而是指以身体器官为象征的人的精神中心,也就是说:它是人最内在的活动中心,是人与他者动态性人格关系的出发点,是人整体领悟的精确器官。”看懂,无外乎有两种内涵,其一是终于厘清了非时序叙述中的时序性事件。所谓叙事、情节剧,以及叙事中的时间,都可归为因果律。其二在于“看懂”是当影片完成之后我们明确地获得了价值位置,我们可以对影片做一个不那么道德化的,但是有自我放置的价值评判。醉翁之意不在酒,观赏二者的创作时,如同喝了一杯剔除掉酒精的酒,失去了一些致幻与激情后,却未因二者中缺乏了炙烈的叙事,以及明朗的表达而欣赏不到文学塑造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