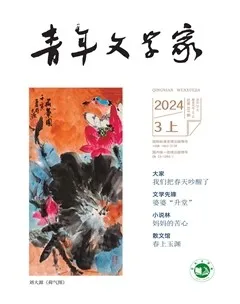摸爬叉
2024-05-13韩清华
韩清华
放了暑假,有了闲暇时间,儿子就让我带他去摸爬叉。
爬叉,学名金蝉,俗称知了龟、知了猴,在我们当地叫爬叉。爬叉含有大量蛋白质,营养丰富,是难得的美味。每年夏天一到傍晚,就有很多人拿起手电,前往树林寻找。之前没有手电,在黑夜里只能靠两只手在树干上触摸,因此被称作摸爬叉。
如今,摸爬叉已成了一个“行业”,一只爬叉可以卖到八九毛钱。据说,今年已经突破一元钱了。听人讲,爬叉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其数量减少了。
隨着天色慢慢变暗,我和儿子出发了。初夏的夜晚,偶尔还能听到几声知了的鸣叫。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城外的大堤,随即把车停靠在路边。我和儿子每人拿了一只强光手电筒,他还特意找了一个盛爬叉的大瓶子。在儿子的想法里,今晚肯定能摸不少。我们在大堤两边寻找了一个多钟头,仅摸到了一只,儿子甚感失望。尽管如此,但他还是准备将它放生。返回途中,我们选择好了放生地点:在宋街最北头儿,路东边刚好有一棵大槐树。儿子从瓶子里倒出那只爬叉,放到树干上,在手电的照射下,它一步步地向上爬去。第二天,我上班路过此处,特意查看了那棵树。果然,在树的高处有一只爬叉的空壳。
如今,爬叉确实有点儿太少了。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我们姐妹仨跟着父亲去摸爬叉的情形。那时,父亲领我们去的是南洼树行子。那里方圆几里地内都是杨树和柳树,棵棵高大茂密。进到那里面,仿佛真的走进了大森林。论环境,南洼树行子自然是知了喜欢待的地方。同样,那儿也成了人们摸爬叉的理想去处。摸爬叉不能像空手捡芝麻一样,多少要准备些工具。我们带的是两个手电、一根竹竿、一只水罐子。
开始行动之前,父亲给我们做了分工:他和我负责用手电照明;妹妹拿竿子,够不着爬到高处的爬叉时,就用竿子;弟弟最小,负责拿罐子,把摸到的爬叉盛到里面。我记得那是一只下地干活儿用的饮水罐,容量不小,足足能装下五百只爬叉。那晚去南洼树行子摸爬叉的人很多,到处晃动着手电光柱,并伴着大人和孩子的说话声。那时的爬叉真不少,一棵大树上往往就能摸到好几只。你过一会儿再转回到同一棵树,可能还会有新的收获。
在身旁抱着罐子的弟弟,见我们都摸到了那么多爬叉,眼馋了,手痒了,直嚷嚷着要与我换换。叫我替他拿罐子,他用手电照。我说:“那怎么行呢?你不知道哪棵树上有,哪棵树上没有!”“不是有手电,我能看不见?”他反问道。“看见了,你也够不着,你个子矮。”我说。“哼,我有竿子!”“来,你用这个照吧!”父亲把他的手电递给了弟弟。不服气的他拿着父亲的手电,开始跑着在树林子里照来照去。这时候,父亲一边抽着烟,一边拎着那只罐子。他跟在我们身后,当起了“勤务兵”。
说来也奇怪,手电在父亲的手里,一只只爬叉被从树上“拿下”。一到弟弟那里,有好久一段时间也没听到他找到爬叉的叫喊声。他又照了一会儿,自知水平有限,只好把手电又归还给了父亲。其实,爬叉这小东西,它的去处是要选择的:有的树下可能多,有的可能少,有的甚至一只也没有,就是这么奇怪。这下弟弟终于死心了,不再闹着要跟我换了。已经晚上九点多了,手电的光渐渐稀少起来,最后一批上树的爬叉也差不多快出完了,该回家了。父亲召集我们,清点收获,足足超过了四百只,收获颇丰。
摸了那么多爬叉,怎么个吃法?还真成了问题。关于吃爬叉,现在最基本的办法就是油炸,或者锅煎。但在那个年代,家庭生活困难,哪有油炸呢?所以,父亲就用煮的办法,把那些爬叉一锅给煮了。外加了些盐,权当作是饭菜了。用筷子夹起一只爬叉,吃在嘴里,肉嘟嘟的,远远比不了煎炸的口感,我们却吃得津津有味,那四百多只爬叉满可以当作几天的口粮。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同样是摸爬叉,同样是领着孩子,只因为时代不同,一个为充饥谋生活,一个为带儿子玩儿。可见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决定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不同。今非昔比,希望明天的生活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