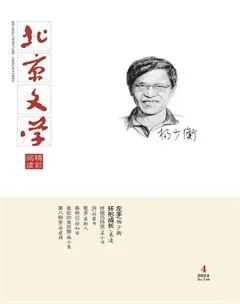笔录
2024-05-09废斯人
小说试图探讨祖母的身心创伤、自我疗治,以及与孙女之间的女性情谊,二人互为镜像,照见对方,也照见自己。那首吟唱的童谣“白鹿白鹿,会识来路?路上行人,知是春横”萦绕耳畔,山林中自由奔跑的白鹿,或许才是一切故事的要旨。
从天河机场去山城还需一个半小时。谢小月坐在大巴上,她疲倦地靠着座椅,侧过头,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她刚从英国伦敦回到武汉,飞机一落地,连家门都没进,父亲就催促她火速赶往老家山城。父亲说,祖母疯了。
十二岁之前,谢小月一直跟着祖母生活在山城。每日清晨,只要不下雨,祖母便会将她从床上唤起来,带她去山上。山腰有一口老井。祖母从老井里打两桶水,带回家去煮饭烧茶。她不喝别处的水,就只喝老井的水。哪怕家里安装了自来水,她还会去山上挑水吃。周边也有几户老人吃水井的水,听他们说,老井里的水通了灵气,吃了没病没灾。谢小月起得早,又要爬山挑水,那时她就想,要是天天都能下雨就好了。
谢小月认为祖母的命真好,做饭、家务都是祖父的事,她大部分时间闲得无事,就打理花草。祖母在院子里种满了月季。夏秋两季,院子里会开满各色的月季花,而祖父会坐在墙角的竹椅上,要么抽烟,要么打瞌睡。
父亲说,祖母太狠心了。
一个月前,祖父因晚期肝癌在医院去世了。那时,谢小月在威斯敏斯特大学组织了一场大型的女权抗议活动,她们准备去一家跨国企业门口抗议,谢小月是负责人,肯定不会临阵脱逃,加之还有两门课程需要答辩。她没有回国奔丧。
那段时间,父亲很沮丧。
祖父被送到省城的三甲医院,在重症病房插上了呼吸机,无论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的时候,一直念叨着祖母的名字。祖母像是知道祖父要死了一样,既不关心他的饮食,又不关心他的病情。父亲打电话跟她讲祖父病情的时候,她也心不在焉地嗯啊几声,不愿多听。这些是其次,关键是祖母一眼都不愿多瞧祖父,怎么劝她,她坚决不去医院探望祖父。她总说她的花需要照料,走不开。花能比人重要?父亲气不过,专门回山城,把祖母硬拉上车,拖到医院,祖母一到医院,直接躺在大厅的地上打滚,不管怎么劝就是不愿意上楼去,父亲见状,也只能作罢,又把祖母送回了山城。
父亲恼火地讲,比起祖父躺在病床上长吁短叹,祖母小日子过得欢快。
那些日子,天一亮,祖母就起床,在屋外打一套太极拳,然后就去山上打一小壶水,刚好能提得动,也够她吃的。菜园里的豆角刚刚成熟,祖母喜欢吃煮豆角,天天要煮一碗豆子。她将豆角剥壳,煮熟,放在碗里,用勺子碾碎,然后拌点糖,一勺勺地吃,吃起来还咂巴嘴。父亲一边劝祖母,毕竟夫妻在一起这么多年,去看一眼身上又不会少一坨肉;一边听着祖母咀嚼食物的声音,越嚼越响,父亲实在受不了,干脆什么都不说了。
父亲回忆道,相比你祖父忙碌了一辈子,从国企退休,你祖母几乎没有工作过,除了几次去邻居家水果摊帮忙,也没挣过什么钱,整日除了吃吃喝喝,就是花花草草。你祖父太温柔了,从未见过他对祖母红过脸、发过脾气。父亲觉得祖母没有理由不去探望生病的祖父。他望着病床上的祖父哼哼唧唧地唤着祖母的名字,心里实在难受,也实在没办法,委屈得都快哭了。父亲气不过,砸了祖母养的几盆绿色月季,他知道绿色月季是贵重的品种,也是祖母的心头所爱。祖母没说话,巴巴地望着父亲砸花。
砸了花,又不能改变什么。直到祖父去世的当晚,祖母都没有去探望过他。祖父抱憾而终。祖父死前还对父亲念叨:你回去问她,喜不喜欢我?
事后,父亲想起祖父临终的这句话。他对谢小月说,祖父都这一把年纪,还看重喜不喜欢、爱不爱的。
错!谢小月斩钉截铁地说,你不懂!谢小月硕士学的心理学,精神分析是她在学校唯一获得了“优秀”的课程。她从父亲对祖母的抱怨中,似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解释。谢小月说,我完全理解祖母的行为,这还是要回到女性的本身,在生活中,女性对男性长期依赖,在即将失去的时候,她们会表現出极度无所谓,一方面在掩饰自己的脆弱,另一方面,在寻求解决的办法:妥协还是僵持。
你懂个屁。父亲打住了谢小月的夸夸其谈。祖母从来不会依赖祖父,她做什么事,都是说做就做,从不问任何人。
大巴连续转了几个急弯,甩得谢小月有些头晕,她拉下帽檐,闭上眼休息。睡意正浓的时候,父亲打来了电话。父亲问她到哪儿了。她也说不出个地名来。
父亲说,你最好把祖母带回省城,去大医院检查一番,她心里有病。
谢小月说,那你太小瞧我了,我可是专门学心理的。
父亲说,你别卖弄,让你回来,是因为你小时候跟祖母住过一段时间,你的话她或许能听,还指望不上你给祖母看病。
谢小月不服气地说,我尽力。
电话里,父亲说话顿了顿,有些话始终没有说出来。大巴驶向山区,信号时有时无,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忙音,谢小月把电话挂断了。她给父亲发了一条短信:你头上的伤好点没有。
祖父办后事的那几天,祖母坚决不露面,她跑到了寺庙里,在伙房里住了几天。祖父出殡前一天,父亲去寺庙接祖母回家。祖母坚决不回。两人吵了起来,父亲硬要把祖母拉回去。祖母正在厨房烧火做饭,气急了,抄起手边的火钳,向父亲扔去,正好砸到了父亲的额头,顿时鲜血直流。父亲还是扯着祖母的手不放,一遍遍地质问她,为什么要做到这么绝,到底为什么?
父亲哭了。祖母没哭。
窗外树影婆娑,谢小月似睡似醒,她似乎看到了祖母站在屋外的院子里,小心地修剪月季的枝叶,突然,她抬起头,望向自己,她眼中的忧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纯粹、热烈的目光。谢小月惊了一下。
院子里烧了一堆火,祖母把祖父的衣服、鞋子、书籍,牙刷、毛巾、杯子,只要祖父用的,统统烧了摔了。她还要把那张睡过的床也烧了。院子里浓烟滚滚,不知谁报了火警,远处响起警报声。
父亲回了一条短信:头上的伤已经好了。
谢小月犹豫了一下,还是发了一条短信出去:你是不是恨祖母?她等了半天,父亲没有回复。
出入山城要经过一座两公里的长坡,从山腰直插入山底,这条不宽的路上挤满了来来往往的车辆。谢小月被停停顿顿的急刹车晃醒了。
到了车站,她提着行李走下了车,十多年没有回到山城,依旧是熟悉的街景:戴着斗笠的妇女坐在街边聊天,跟前摆着豆角和土豆,她们从不叫卖,有人确定买了,她们才从聊天中抽出身来,慵懒地应付。就这样瞎聊一整天,什么也没卖出去,她们也不觉得亏,反正时光总是被打发掉了。有几个小姑娘,沿街蹦蹦跳跳地卖着纸花。谢小月也曾折纸花卖过,她叫住了小姑娘,挑了几枚月季样式的,准备送给祖母。祖母会喜欢吧!
老屋离街道不远,周围几户人家都搬到省城去了,就祖母家敞着大门。谢小月一进大门,就看见祖母躺在中庭的藤椅上,头顶是一棵枫香树。祖母一边闭目养神,一边抱着橘猫,轻轻地爱抚。那猫还活着?谢小月心想:自己离开山城的那年,橘猫已经是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
祖母听见动静,转过头,一脸平静地望着谢小月。她认出谢小月,嘴角露出微笑。谢小月热情地凑上去,抱了抱祖母,还送上了纸花。祖母对亲昵的动作极其抗拒,她用力地把谢小月推开,拿起纸花,仔细端详,念叨:这花没有你小时候折得好,买它做什么?你看,这花褶子都折错了。
谢小月蹲在祖母的跟前,说道,你是晓得的,我小时候卖纸花,也想有人买,可是我折得那么好看,从来都没人买。
祖母说,你那个时候像块木头,一坐就是一上午,一直盘着折纸,邻居们都说你呆,不活跃。
谢小月撒娇地说,我才不呆。
祖母轻轻踢了她一脚,说道,你还是那个样子,站没个站样,坐没个坐样。
谢小月悻悻地站在一旁,瞅着祖母没有更多的话了,她转过头,浏览了一圈院子,到处种的都是月季花。大枝的、小枝的,红色、粉色,最稀奇的是一朵绿色的。谢小月走过去,刚想用指腹触碰绿色花瓣,祖母立马制止了。祖母说,这花本来有四棵,你父亲弄死了三棵,就只剩一棵了。
谢小月听了这话,转过身,刚想要接过话茬。祖母喝了一声说,别扯你父亲,要想在这儿住,那就要和以前一样,少说多做。
谢小月住了嘴,愣愣地望着祖母。祖母站了起来,招手让她过去。她跟祖母来到厨房。祖母指着水桶说,你去山上老井打水吧,我早上打的水只够我喝,你要喝的水,自己去打了喝。
谢小月看了一眼水桶,笑着说,我不渴,你有得喝就行。
祖母瞪了她一眼,那你就回省城吧,还有6点的一班车,别在这儿待了。
谢小月无奈地提起水桶。通往山里的路她很熟悉,沿着青石板拾级而上,走到顶就可看到老井。谢小月有些懊恼,祖母明镜似的人,总能看透她的心思,那些心理沟通技巧完全不奏效。她提了满满一桶井水,从山上下来。这一桶水还挺重的。没做过什么重活的她,胳膊累得要脱臼了。
等谢小月把水提回家,祖母已经做好了晚饭。桌上放着一碗清汤面,没有放辣椒、酱油,只放了一点点盐。谢小月吃不惯,放下了碗筷说,我不饿。
祖母瞟了一眼说,你小时候也是这副模样,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后来饿了几天,猫屎都吃了。
谢小月说,那你能记得我最喜欢吃什么吗?
祖母说,那倒不记得,反正我就爱吃清汤面。
谢小月说,我的口味比较重,喜欢吃小龙虾。
祖母摇头说,千种口味万道菜,还是清汤面最好吃。
眼见祖母说不通,谢小月离开厨房,独自在老屋里晃荡。老屋里的家具都不见了,想必都被祖母的一把火烧了,家里真的没有祖父任何痕迹。祖母在空荡的地方摆上了各色的月季花。
谢小月找了一把折叠椅,靠了上去。从英国飞回来,一路上她没怎么休息,刚闭上眼睛就睡着了。谢小月梦见自己在英国拿着横幅,走在抗议队伍的最前面,那些英国警察虎视眈眈地盯着她。她才不怕任何人的目光,于是恶狠狠地回瞪过去。抗议的人在街上站了几个小时,谢小月坚持不坐,从头到尾都站着,一件事她只要认准了,就会卖命般卖力。她熬了几个通宵制作标语,又长时间站立喊口号,实在太累了。在抗议的人群前,她的身体前后摆动,仿佛天要塌下来一样,果然她中暑晕倒了。等她醒来的时候,老屋的院子一片漆黑。她赶紧看了一眼时间,已经夜里11点了。她发现自己的肩上搭了一件衬衣,肯定是祖母的。
祖母的房门紧闭,想是已经睡下了。
谢小月重新打开院子里的灯,走到大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下来,望着古朴的木门,上面贴一些卡通画,谢小月想到了小时候,那时,祖母还经常给她唱童谣:
白鹿白鹿,会识来路?
路上行人,知是春横。
谢小月不明白童谣的意思,祖母就给她讲。以前,祖母家里是猎户,住在大别山脚下,屋后就是一大片森林。一次,她在森林里玩耍的时候,偶然遇见一只白鹿,那只白鹿长得特别白,又白又亮,身体似乎在发着光,当时祖母震惊地望着白鹿,更让祖母惊喜的是:白鹿能唱童谣。白鹿轻声地哼唱各种各样的童谣,悦耳动听。
这首歌谣就是白鹿唱给祖母听的,祖母再唱给她听。谢小月猛然想到,祖母在小时候一直给她讲白鹿的故事。祖母告诉谢小月,小的时候,白鹿带着她在森林里奔跑,教她辨別枞菇和天牛。等到祖母刚成年的第一天,白鹿带着她走出了森林。那是祖母第一次走出森林,她一直跟树打交道,很少见到那么多的人,看到热闹的集市,又惊喜,又害怕,然而有白鹿在,祖母才稍稍安心。一人一鹿逛街、吃汤圆、玩风车,那一天,她们还喝了果酒,醉醺醺地回了家。
祖母跟谢小月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她徜徉在回忆中,目光变得柔和,语气也很温柔。当时谢小月很好奇白鹿到底长什么样,她拉着祖母的衣袖,问道,那只白鹿长啥样?祖母听了这话,反应特别大,瞬间就苦着脸,吼了她,你管它长什么样!
谢小月憋着泪水。祖母严厉的眼神让她很受伤害,如同白鹿单单只属于祖母,只能由祖母分享。谢小月从那时起就不喜欢白鹿的故事。偏偏祖母每日夜晚都要对她讲白鹿,不管她是否在听,也不管她感受如何,祖母都要全身心地把童谣唱出来,把故事讲出来。这时候,谢小月就特别想父亲,想要离开山城回家。
白鹿的故事反反复复也只讲了个开头,后头是怎么样的,谢小月也不得而知。她盯着祖母房门,门紧紧闭着。她心想,祖母还没睡吧,于是轻声地唱着童谣:白鹿白鹿,会识来路。谢小月歌唱的声音很轻,却被一阵阵微风播洒在屋子的各处,像是有无数个人在轻声歌唱,声音汇聚成流,越来越大,越来越响。祖母扯着嗓子大叫一声,像是撕开了喉咙。房门嘭的一声推开了。祖母披着白色的睡衣站在了门口,风吹起睡衣,她像是一只奓毛的白鹿,气势汹汹地伫立在那里,俯视着谢小月。
祖母从来没有这样过。谢小月吓呆了。
老屋的木板床又硬又霉,谢小月睡不着,在床上翻来滚去,思索着祖母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她拿起手机,翻着与父亲的聊天记录。父亲对祖母是数不尽的抱怨,而这一切都是祖父病倒后发生的。在谢小月的印象里,祖父瘦高个儿,一直都有风湿病,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祖父话少,几乎没跟自己说过什么话,他要么呆坐着一旁,不作声;要么趁着祖母在侍弄花的时候,久久地注视着她的背影。他们俩更是很少说话,如同是两棵树那般静默。
说到树,谢小月脑海里映着一棵枫香树。那日,她在伦敦晕倒后,被人抬到了一边的树阴下。她忽然闻到一股熟悉的香气,微微张开眼,眼前是一棵枫香树,树叶已经黄了,微风起伏,树枝随之摇曳,树叶摩擦,沙沙作响。这时,树上掉下一片叶子,叶子是三角形的。正好落在她的额头上,像是一只鸭掌踩在她的脸上,不仅挡住了她的视线,还弄得额头瘙痒,很不舒服。她想要弄掉树叶,可是身体和脸又动不了,她越想越痒,又是挤眉头,又是咧着嘴,弄了半天,叶子纹丝不动。她大声呼喊帮助,不知为何嗓子却发不出声音。没有办法,她只好强忍住额头的瘙痒,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不知忍了多久,额头终于不痒了,想必她已经忘了痒这种感觉了。这时,谢小月听到了议论声,有人在她身边说话,虽然听不清说了什么,但是有人在她的身边。她本想扭动身体,想想还是算了吧,都已经不痒了。有人发现了她的异状,拿走了脸上的那片叶子,光线重新照在她的眼瞼,她睁开眼,逆着刺眼的光芒,她看到了一个影子,定睛一看,居然是一只白鹿。
谢小月惊醒了,她坐了起来,打量四周,还是老屋,还好是一场梦。窗外天已亮了,谢小月听到祖母起床的动静,她也起了床。祖母昨天歇斯底里的模样,让她有点不敢招惹祖母,她在屋外转了转。她抬头,枫香树还是那般遒劲,新长的翠绿色的叶子,鲜嫩可爱。一院子的月季,能嗅到淡淡的香味,她昨日还没闻到花香,细细寻找,有好几枝初开花的月季,粉粉的,花瓣上还沾了露水。谢小月转了一圈,停在祖母的房前,等着她出来。
祖母忙活好了,推开房门,看都不看谢小月一眼,直接吩咐她到厨房把水桶挑着,去山上打水。谢小月愣了一下,她瞅了一眼祖母。祖母凶了一句,快去!谢小月回过神来,赶紧去了厨房。
这次祖母也跟着上山去了。她拄着拐杖,走几步,歇一歇。
谢小月挑着水桶,她没做过这活儿,不习惯肩挑,扁担常常从肩上滑落,她干脆双手提着。谢小月喘着气说,镇上通了自来水,你不喝自来水吗?
祖母说,不喝。
谢小月说,你这么大年纪,天天来提水,多不安全。
祖母说,与你无关。
谢小月说,万一哪天你提不动了,怎么办?
祖母说,那就不喝水。
谢小月见状,自顾自地说,我觉得井水和自来水的味道没什么区别,自来水都消毒了,还安全一些。
祖母累了,她找了一块大石头坐下休息。谢小月放下水桶,挨着祖母的身边坐了下来。谢小月咬咬牙,还是张了口:好奇怪,我早上做了一个梦。
祖母没搭话。谢小月说,你知道我梦见啥,一只白鹿,纯白色的,跟你给我讲的差不多。
祖母听闻,转过脸,瞪大眼睛,盯着谢小月。
谢小月装作没事人一样,继续说,当时它直愣愣地盯着我,我还吓了一跳,太奇怪了,怎么就梦见白鹿了。
祖母叹了一口气。
谢小月说,你不是小时候讲给我听吗?再给我讲讲呗。
祖母说,不讲了。
谢小月问,为什么?
祖母说,那只白鹿死了。说完,祖母拄起拐杖,站起来,急匆匆往家里走。谢小月莫名其妙地望着祖母的背影,提着水桶,跟在身后。
等她们到了家,一辆破旧三轮车停在了门外,一位戴着草帽的中年男子蹲在墙角抽着烟。他是镇上的花贩子,见着祖母来了,就站了起来。两人都没寒暄。祖母把那人领进院子,直截了当地说,这镇上就你懂花,你看这院里大大小小的花,估个价吧。
那人吐出烟圈,环顾院子一周说,老姐姐,你也知道,我是个小店,你说几盆,我还出得起价,这一院子的花,我可要不起。
谢小月这才明白,祖母要把月季卖了,她本想劝阻,祖母却坚定地说,都拿去吧,你自然晓得有地方卖,放心,钱不会要你许多的,半卖半送,只是得找个老手,也不让这些花受苦。
那人笑了笑说,既然这样,我就按自己的买卖来出价了,老姐姐别嫌弃价格就好。
祖母摆了摆手,让花贩子自己去打理,她走进房间,闩了门。
谢小月坐在院子里,看着那人把花一盆一盆地搬了出去。她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些花都是祖母的心血,祖母到底在闹什么?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解决的,居然要卖花。
谢小月无能为力,她左思右想,还是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父亲也焦头烂额。张嘴就问她,劝得怎么样?
谢小月说,这次回来,祖母明显跟我疏远了。
父亲说,那你打电话来干吗,家里出事了吗?肯定是你祖母又不安生了。
谢小月说,祖母把一院子的花都卖了。
父亲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她要卖就卖吧。
谢小月说,可是这些花她都养了大半辈子了。
父亲说,告诉你吧,这不算什么,她是什么都要卖的,把家也卖了。刚刚,房产中介打了电话过来,根据祖父的遗嘱,确定我对老房子没有继承权。祖母已经把老屋挂牌销售了。
谢小月说,可是她到底为什么?
父亲叹了一口气,唉,说不清,怕是精神问题吧,这次非要把她送到省城医院看病。
谢小月说,是不是祖母和祖父之间发生了什么?
父亲说,有什么呢,五十年的夫妻,有事也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这么多年,都老化了。父亲告诉谢小月,他正在赶回家的路上。父亲气愤地说,再不回去,恐怕连家都没有了!
晚饭是父亲做的,一个清炒豆腐,一个凉拌皮蛋,一个炒黄瓜。饭桌摆在院子里,父亲没有喊祖母。祖母自己上了桌,拿起碗筷就吃了起来。祖母嫌弃父亲煮的饭水放太多了,饭都煮烂了。她尝了一口,吃不下去,便从碗里拨出半碗饭给谢小月。
谢小月见父亲沉着脸,没说话,便笑着说道,我还能再多吃一碗。可是没人理她。
祖母夹了一块豆腐,吧唧着嘴,又说道,豆腐醋放多了。
父亲认为祖母吹毛求疵,恼火了。他放下筷子,说道,你有什么不满的,赶紧都一溜地说完,说完了好吃饭。
祖母说,凉拌皮蛋少了葱,不香。
父亲说,不管香不香,能吃饱就行。
祖母说,有个事我要跟你说。
父亲没抬头,只嗯了一声。
祖母说,房子过些时候就要卖了,钱我留一点,剩余的都捐给庙里,我已经跟山上庵子里的师太说好了,她给我预备了一间屋子,明天我就搬去庵子里住,长久住。你们都不消管我。
谢小月看了一眼父亲,他强忍着怒气,夹了一筷子黄瓜放在祖母的碗里。继续说道,别瞎说,明天跟我去省城看病。
祖母把黄瓜又夹了出来,扔回盘子里又不太好,干脆就夹到谢小月碗里。祖母说,我不是跟你商量,我是通知你。
父亲说,你别犟了。
祖母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气,我决定的事就是拍了板。
父亲说,这次由不得你,捆也要捆去省城。
祖母说,你试一试,反了天了!我要走,你拦得住吗?
父亲摔掉了筷子,气冲冲地说道,你说试,那就试一试,带你去医院看病,是为你好,你以为我愿意讨这份麻烦。
祖母直勾勾地盯着父亲的脸,她大声地说,我没病!
父亲说,有没有病,去医院看了才知道。
祖母气得发抖,她用筷子指着父亲的脸,你这张脸,你这张脸……她突然哭了,双手抹着泪水。
见祖母哭了,父亲的戾气也消失了不少,他像一根木头一样不作声地站在一旁。
祖母转头看了我一眼。她带着哭腔说,你个死丫头,不想知道白鹿是怎么死的吗?你去问他。祖母指了一下父亲。他什么都知道。说完就回了房间。
谢小月盯着父亲。父亲望着祖母房间的灯火,他还是很在乎祖母的。谢小月把父亲拉回椅子上坐着,细声问道,到底是什么事?父亲愤懑地坐了下去,椅子发出吱吱的响声。谢小月催促了他几遍,他才开口。
祖母家有一个姑妈嫁到了本镇,当年祖母才十八,人长得俊俏,跟人学习纺织。那年,祖母趁着中秋来姑妈家过节,在街上游耍的时候,被祖父看中了。祖父二十好几,无所事事,靠在湖里偷鱼挣点钱。祖父追求祖母,祖母视而不见。她有喜欢的人,是山里的猎户,姓白。祖父不知听了谁的诡计,打点了熟人,邀祖母出来逛街吃糕点,在茶水里放了药,祖母失了神志,祖父趁机和她发生了关系。后来祖母怀孕了。祖父以此为由,登上祖母的家门,强行娶了祖母。祖母家还有两個未出阁的妹妹,为了家门声誉,只好闷声吃了这个大亏。
听了这席话,谢小月惊到了。她没想到这事居然发生在祖母身上,怪不得她非要吃自己打的井水,这才能安心!
父亲说,这都是半个世纪之前的事,时间过了这么久,都是一家人,何必再计较这个。
谢小月忽然明白,祖母为何在祖父死了之后才将所有的委屈和不满表达出来,她忍气吞声这么多年,终究是为了父亲,然而父亲并不懂她,也不领情。谢小月质问父亲,这些事是祖母跟你说的?
父亲摇摇头说,前几天,你祖父病危时说的,我不信,打电话向你祖母求证,你祖母听了,越发狂躁了。
谢小月说,所以在得知真相之后,你还是一意孤行,要把祖母送去看病。
父亲说,这是两码事,你祖父与祖母的事是夫妻间的事,过了这么多年,你看看,你祖父为了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他的罪已经赎清了。再说人死为大,你祖父已经不在了,这件事再怎么也应当过去了,再大的怨气也该消了。我问你,不可否认祖母对祖父有感情吧?
谢小月说,你这是胡言乱语。
父亲说,你祖母之所以这么思维混乱,行为怪异,是因为祖父的死让她的精神受了创伤,她需要去看医生。
谢小月生气地蹦了起来,对着父亲吼道,你知道祖母为什么不喜欢你吗?
这句话像是戳中了父亲的软肋,他骤然安静了下来,父亲疑惑地看着谢小月。
谢小月说,你跟祖父长得一模一样。祖母为你做了那么多,你却还要步步紧逼。
父亲听了这话,也跳了起来,大骂说,你个死丫头,你有什么资格对我吼,你没搞清状况,我是为了你祖母好!
谢小月不想多语,她擦了擦泪水,冲出了家门。山城的街道路灯稀疏,灯光昏暗,她漫无目的地走着,想起祖母的種种,不免有些心酸。还有那次在伦敦,她被送进医院之后,她组织的抗议活动也黯然收场。那些被伤害的人又无可奈何地回到了原本的生活中,甚至在某个时刻,继续被命运嘲弄。她心有不甘。
谢小月走累了,坐在马路牙子上,泪水缓缓流下,她想到了祖母在院子里种的月季花,她付出那么多心血,此时被花店廉价贩卖,她住了一辈子的房屋也将被出售,她的一切都没有了。她在脑海里想象:祖母独自站在小院里,孤独又无助。突然,她闻到一股香味,是枫香味,从祖母院子里飘来的。谢小月抬起头,一树的枫香叶闪着金色的光,翻腾着、跳跃着,呈现欣欣向荣的模样。卖花卖房都是祖母的决定,她已经想好了,一切都没有了,还能重来。谢小月那刻或许理解了祖母。她听到了熟悉的歌谣:
白鹿白鹿,会识来路?
路上行人,知是春横。
在灯光与黑夜的交界处,她仿佛看见了一只白鹿,在挣脱泥泞的沼泽,从地上一跃而起,快速奔跑,越过她的头顶,跳跃升空。
第二天一大早,祖母收拾好行李打开房门,谢小月抱着一盆月季花站在门口,那是一盆绿色的月季,谢小月花了三倍价钱从花贩子手中买的。
祖母看着绿色的月季,脸上露出了笑容,她轻轻地抚摸了一下花瓣,然后警惕地冷下脸,环顾四周。
谢小月说,不用担心,父亲走了。我早上把他送到了车站。
祖母拿了一个小包袱往外走,她说,我也要走了,去街上过个早,然后去庵里。
谢小月连忙说,走之前,我们去做一件事吧。
祖母问,什么事?
谢小月说,我们去报个警,写个笔录吧,不管过了多少年,把你的委屈都写在笔录里,这件事算正儿八经地了结了,以后就不用再想它了。
祖母没想到谢小月会这么说,她紧锁的眉头良久才舒展开来。祖母拉起谢小月的手,缓缓地说,以前说你长得像你父亲,仔细看,真不像,你长得俊多了。祖母从小包袱里拿出一枚纸花,纸都泛黄了,花瓣的褶皱却依旧清晰。这是谢小月小时候做的。
作者简介
废斯人,90后,湖北罗田人。小说作品见《人民文学》《花城》《长江文艺》《江南》等刊物,出版小说集《故乡志》《国境线上晴与雨》。曾获屈原文艺奖、湖北文学奖,系中国作协会员、湖北作协签约作家。
责任编辑 丁莉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