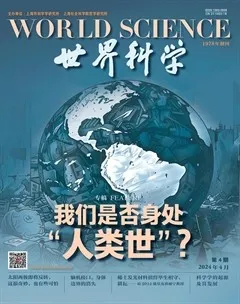脑机接口,身体边界的消失
2024-05-06陶虎邹家俊
陶虎?邹家俊



你身体的边界在哪?有人说,我的皮肤划定了我和世界的边界。
但我们总感觉自己的边界要再大一些,比如当一个陌生人和你的距离小于1米时,你就会感到不适,要是只有半米,你甚至会浑身不自在,此时,你的边界不再是你的皮肤。
再想象一个场景,你正驾驶着自己的爱车下班回家,心里想的是晚饭吃什么,时不时抬眼看看后视镜,确保自己不会和其他车相撞。总会有那么一刻,你觉得车子和自己的身体融为了一体,俗称“人车合一”,此时你的边界又扩展到了整个车子。
上述边界的拓展多是先天或被动的,那我们有可能主动拓展自己身体的边界吗?当然可以。
脑机接口就是这样一种能拓展你物理边界和精神边界的技术。修复退化的感官,延展四肢触达的空间,甚至让电影《阿凡达》中描绘的情境成真,这些都是脑机接口已经或正在实现的事。
边界修复
重建神经连接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来自大脑,即我们的神经系统,这个系统和其他所有身体系统最大的不一样是:它具有可塑性。
什么是可塑性?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小朋友在学会说话前后,他们的大脑就发生了可塑性变化。将 “可塑性”换成脑科学的术语:“Fire together,wire together”。
短短的一个词却几乎包含着人类世界全部的智慧。让我们将上面那句英文表达展开说说。大脑由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构成,后者主要起支持作用,前者才是信息传递的主要载体。神经元的长相很特别,它们有很多触角,帮助它们和周围其他的神经元建立连接,在连接处,信息通过电信号传递。于是,“Fire together,wire together”就可以这样来理解:当神经元A持续并重复地参与诱发神经元B的活动,A和B之间的连接就会被强化。上述表达有两个关键点:一是重复,也就是多次发生;二是要有时间上的先后,即A的活动要发生在B前面。
那么神经可塑性和脑机接口又有什么关系?关系太大了,我們可以借助脑机接口来重塑神经系统。举个例子,很多瘫痪病人大脑中的“指令”神经元和分布在四肢的运动神经元间的连接被切断了。这时,我们可以在病人头上放置电极,实时记录他脑中正在发生的活动。同时,要求病人做运动想象,想象自己要抬起手或脚,一旦监测到这些“想象信号”,立刻刺激信号所对应的肢体,从而模拟肢体接收到了大脑的指令,并行动起来。只要保证每一次指令发生后都有相应的行动,重复足够多次,我们就有希望重建瘫痪病人的神经连接。
在探索大脑奥秘的前沿领域,科学家正致力于开发一种全新的技术——超声神经调控。这项技术利用超声波作为非侵入性的工具,通过精确的频率控制,直接作用于大脑的特定区域。超声波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类似“指挥官”的角色,引导神经元的活动,实现对大脑功能的精细调节。超声神经调控的潜力巨大,它为治疗一系列神经疾病提供了新的希望。例如,它可能有助于减轻帕金森病患者的震颤症状,缓解慢性疼痛,甚至可能对抑郁症的治疗产生积极影响。未来,超声神经调控或许能够成为我们调节大脑状态的有力工具,帮助人们达到更高层次的认知和情感平衡。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对医学具有重要意义,也可能对人类自我理解的深度和广度产生深远影响。
人工耳蜗再来看另一项更为成熟的脑机接口应用——人工耳蜗。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就第一次提出了人工耳蜗的概念。1972年,首个商业化人工耳蜗被植入人体。截至2017年,全世界的人工耳蜗市场达到了13亿美元。
很多听障患者,他们的病灶在内耳,也就是耳蜗,而大脑中负责解读声音的神经元并未发生器质性的病变。于是,治疗这类听障患者的思路就变成——用人工器官取代发生了病变的耳蜗。一般的人工耳蜗至少包括三个部分:声音接收器、声音处理器和听皮层刺激器。声音接收器是一个小型的麦克风,在接收声音后,需要由声音处理器将声波转换成神经系统更为熟悉的电信号,最后再通过植入耳后皮肤下的刺激器刺激听觉皮层,至此,声音重新被大脑感知到。
对瘫痪和听障患者来说,脑机接口技术帮助他们重新找回了身体的边界。
用舌头看清世界“我看见了美丽的景色”,这是一句普通的表达;“我尝到了美丽的景色”,这就变成了一句运用通感修辞的句子。通感,在脑科学领域又被称作联觉,这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现象,即一个感官的刺激引发了另一个感官的感觉或体验。
听觉、视觉、嗅觉和触觉,这些常见的感觉往往对应大脑皮层中特定的区域。一般来说,看到绚丽色彩的那一刻,视觉皮层会“欢呼雀跃”起来,而听皮层和嗅皮层等不会有什么反应。但如果在某一瞬间,绚丽的色彩让你的听皮层也开始“闪烁”,那么你将会感到颜色变得悦耳动听起来,在那一刻,联觉发生了。
现在,借助脑机接口技术,人类可以随时随地创造联觉体验,比如,用舌头看到这个世界。
事实上,美国已经有医疗器械公司推出了成熟的脑机接口产品,帮助盲人用舌头“重见光明”。这类产品再一次借助了神经系统的可塑性:在你的眼前架上一个特殊的眼镜,用来捕捉大千世界的影像,它能“读”出外界图像的大小、深度和角度等信息,这些信息经过一个信号转换器,变成电信号,再借助另一个设备将电信号导向放在舌头上的电极,多次重复上述步骤,你大体上就能“尝”出世界的样子了。
对大多数盲人来说,他们的视觉皮层一直都在,只是鲜少有从视网膜投射过来的视觉信号。将连接眼镜的电极放在他们的舌头上,舌头对应的感觉皮层就会密集地接收到神经电信号,而视觉皮层和舌头对应的感觉皮层又离得不远,“看着”感觉皮层噼里啪啦地放电,总有一些时刻,视觉皮层也会“耐不住性子”地参与其中。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盲人的舌头接收到了电刺激,视觉皮层却对此做出了反应。至此,感觉皮层彻底“侵占”视觉皮层的地盘,更有意思的是,视皮层牢记自己的身份——在大脑中建立对外界图像的认知。也就是说,借助脑机接口技术,盲人朋友们成功地拓展了自己舌头的边界。
边界拓展
第六根手指让我们再问一次那个问题:你身体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来看个经典实验:橡胶手错觉。实验人员让受试者坐在桌前,一只手放在桌上,另一只手放在桌下(最好是受试者目光正前方看不到的位置)。同时,再将一个逼真的橡胶假手放在桌上,重点是要反复调整假手的位置,使其看起来就像是受试者那只放在桌下的手正放在桌上。紧跟着,实验人员用毛刷同时抚摸真手和假手。
现在想象你自己就是受试者,你觉得你能分清自己的真手和假手么?“这我还能分不清么?”想必这是你的第一反应,话别说太早,实验继续进行。
在受试者走神的瞬间,实验人员掏出了一把硕大的榔头,猛地砸向假手。每当这时,受试者们都会惊恐异常。榔头砸下后,有些受试者甚至说自己产生了明显的痛感,不管这些人事后做何解释,他们的恐惧神经元和痛觉神经元不会说谎,它们在榔头砸下前后涌起了剧烈的反应。
也就是说,在那一瞬间,假手也被纳入了身体的边界内。
类似的,我们还可以借助脑机接口控制外骨骼。伦敦大学学院的科学家给受试者准备了一根机械手指,固定在小拇指旁边,接着让受试者学着用脚来控制这根手指,他们大脚趾抠地的力会被转化成这第六根手指张开和闭合的动作。神经系统最“怕”重复,连续训练5天后,大多数受试者就能熟练地使用这根多出来的手指,一些人甚至能完成单手开瓶盖,单手打扑克牌的动作,更有人实现了六根手指弹吉他的壮举。显然,这多出来的一根没血没肉的手指,也被纳入了身体的边界。
世界杯上的钢铁侠前文中我们讨论的几乎都是单向地给大脑输入指令或感觉,这是广义的脑机接口技术的最后一环。更多时候,科学家需要先拿到高质量的脑电信号,再对其进行解码,最后根据解码的结果将人工生成的反馈传回大脑,由此才形成了脑机接口一个完整的闭环。
2014年世界杯落户巴西,巴西裔脑机接口专家米格尔 · 尼科莱利斯(Miguel Nicolelis)誓让家门口的盛会青史留名。在这届世界杯开幕式上,29岁的巴西青年朱利亚诺 · 平托(Juliano Pinto)时隔6年再一次感受到了踢足球的快乐。而这一次,平托穿上了厚重的外骨骼,成为现实版的钢铁侠。
先说第一个环节——脑电采集和解码,借助放在头皮表面的电极,实验员能实时监测平托的脑电活动,这些脑电活动包含着纷繁冗杂的想法和意志。为了让脑电信号和运动想象一一对应,平托完成了成千上万次的训练,努力想象着那几个动作,千万别小看“想象”二字,为了捕捉到“纯净”的脑电信号,平托在想象每个动作时必须心无杂念,也许在想象抬脚动作时,思绪飘飞到马拉多纳(Maradona)的庆祝动作上,就会让这次脑电信号采集功亏一篑。
接下来,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外骨骼控制与感觉反馈。首先将脑电信号转换成清晰的运动指令,指挥外骨骼牵引瘫痪的肢体完成动作。在那之后,平托需要反馈。反馈无比重要,大脑最开始给出的指令不一定精确,需要实时调整,而调整就来自反馈,也就是说,每一个动作的完成都需要大脑与外周感觉神经的多次交互。回到平托身上,开幕式当天绿茵场上草皮的触感,外界的温湿度和最重要的对球的触感,都需要借助外骨骼上附着的传感器传回给平托的大脑。借助外骨骼,平托成功地拓展了自己身体的边界。
现实版“阿凡达”到这里,我们对脑机接口的讨论都局限在自己身体的周围,且操控的机械也相对简单。那我们能否像电影《阿凡达》那样躺在家中,操控千里之外的复杂身体呢?这个构想,米格尔教授用一只名叫伊多亚的猴子实现了。
作为一只猴子,伊多亚更习惯四足行走,但如果把它放在跑步机上,并在它每次直立行走后都给它捧上好吃的水果,那两足行走也完全可以接受。重点来了,在伊多亚行走时,米格尔团队记录了它皮层中几百个神经元的电活动,然后他们对这些电活动进行解码,即找到这些神经元不同的放电模式和行走动作之间的相关性,一旦强相关性被找到,我们就可以借助脑电信号来预测伊多亚的动作。
上述实验,只要猴子配合,全世界大多数电生理实验室都可以完成。米格尔教授显然不满足于此,他想让伊多亚完成一组更具科幻感的动作——用它的皮层脑电控制千里之外一个机器人的运动。
实验开始,伊多亚又一次站上了跑步机,它的右臀、膝盖和脚踝部位都被涂上了荧光颜料,当它移动下肢开始行走时,天花板上的摄影机能捕捉到荧光颜料反射的光。借助这套设备,伊多亚腿部的每一个细微动作都会被准确地记录下来,且能被定量描述,再利用线性回归方程,成百上千个皮层神经元的放电信号就能被转化成伊多亚腿部的三维空间位置的预测值,不断调整线性方程的系数,使得预测值和实际值不断逼近,最后线性方程的系数稳定在某一个特定值,该值的确定标志着解码模型搭建成功。
接下来,伊多亚每一次行走前,脑子里的“意图”都会被精准地转化为运动指令,并被传输给大洋彼岸的另一个机器人。
这里岔开一句,虽然每次伊多亚完成的都是同样的行走动作,但每一次实验的模型都需要调整,甚至重新训练。这是由于神经系统具有简并性,即在大脑中,任何动作或念头的表征,都有远不止一套的“神经元解决方案”。也就是说,即便是完全一致的动作和环境,伊多亚都可能会动用另一套不同的神经元来完成。
回到实验,机器人的运动画面会被传回到伊多亚面前的显示屏上,它脑子里刚一动迈左腿的念头,机器人就会分毫不差地抬起左腿。更神奇的是,借助高速电缆,从伊多亚起心动念到看到机器人开始动作的时间间隔,甚至小于伊多亚控制自己抬腿所需的时间,也许在伊多亚看来,那条机器人的腿比它自己的腿更“听话”。
为了进一步验证伊多亚是否意识到了自己拥有“阿凡达”般的超能力,米格尔团队将它脚下的跑步机关停了,紧跟着,激动人心的时刻出现了,机器人的腿没有随之停下,而是继续平稳地行走着,这意味着,伊多亚正主动地用自己的腦电控制着远方的钢铁之躯。用米格尔的话说,这是“机器人迈出的一小步,灵长类迈出的一大步”。
如此看来,我们身体的边界完全可以拓展到任意电信号能触达的地方。
精神边界的拓展
物理的边界终归是有形的,有形就意味着有边界,但人类的精神世界可以无限大,在扩展精神世界方面,脑机接口技术正在让更科幻的场景成真。
想必你一定有过这样的体验:一个阳光和煦的午后,你拿起一本小说读了起来,再一抬头,天黑了,对,就是那种时间悄然溜走的感觉。脑科学家为这种心无旁骛的状态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心流。
心流是一种美好的状态,同时更是一种做事效率极高的状态,我们能否主动创造它呢?脑机接口正在让这件事成真。
那些正处于心流状态的人的脑电波介于α和θ频段之间——8 Hz左右——我们完全可以借助外部输入来诱发这种特征性的脑电,主动进入心流状态。这是一项非常前沿且极具想象力的技术。
“消耗更少的能量,传递更多的信息”永远是人类世界发展的主轴之一,这与脑机接口的终极图景不谋而合:我们最想连接的不是计算机,而是人,“机”只是一个载体。因此,脑-脑接口也被提上了日程。
你肯定有过怎么都表达不清楚自己意思的时候,有时是表达技巧的问题,但更多时候,是那个意思本身只可意会,难以言传。三体人就不会被这件事困扰,因为他们的思想是透明的,而借助脑-脑接口,我们人类也有希望进入那个信息沟通效率极大提升、误解和尴尬都不复存在的世界。科学家在这件事上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2018年,华盛顿大学的几名研究者成功让三名受试者在仅靠脑电交流的情况下默契地玩起了俄罗斯方块游戏。
更进一步,脑-脑接口可以不是实时的,如果把脑中的电活动上传,或者储存在U盘里,那将会彻底抹去沟通成本。更进一步,我们甚至还可以上传自己的意识,让自己在数字层面实现永生,到那时,个体的物理边界和精神边界将被彻底打破。
回到电极
让我们暂时收束想象力,重新将目光聚焦到器件和脑组织接触的第一界面上——神经电极。它既是各种刺激的发起点,更是脑电信号获取的起点,因此,说电极是脑机接口的钥匙一点也不为过。然而,这把钥匙的材质选择,却关乎着整个系统的安全与效能。传统的金属电极虽然在短期内能够完成任务,但长期来看,它一定会伤害到脆弱的脑组织,从而引发身体的炎症反应。这就像是在精密的钟表中放入了一块粗糙的石子,不仅影响钟表的运转,还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
有人说,进化论是这个地球上最为靠谱的成功学,接触生物组织还要靠生物材料,这是脑虎科技开发蚕丝蛋白电极的发心。蚕丝,这种古老的材料,不仅承载着千年的文化,更以其独特的生物相容性和机械性能,成为开启脑机接口的绝佳“钥匙”。
蚕丝蛋白能够在脑内长期稳定存在而不引起免疫反应。更重要的是,蚕丝蛋白具有可控的降解性,这意味着它能够在完成使命后,逐渐被身体吸收,不留任何痕迹。除了良好的生物相容性,蚕丝蛋白的力学性能更是优异。在实际应用中,蚕丝蛋白电极的植入过程非常温和,这能够减少对血管的损伤,降低出血风险。同时,其柔软的质地也减少了对脑组织的切割伤害。
最后的话
脑机接口技术的飞速发展,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新时代。脑机接口不仅拓展了我们的身体能力,更深化了我们对精神世界的理解。面对这一历史性的机遇,我们应保持谦逊与敬畏之心,谨慎前行,也希望我们能共同见证脑机接口为人类世界开启的美好未来。
本文根据笔者在上海市科学技术普及志愿者協会主办的“ 海上科普论坛” 上的报告撰写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