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史中的古代海外民族记述浅论
2024-04-25王文光李书豪
王文光,李书豪
中国古代的史学是十分发达的,中国正史也称为二十四史,(1)正史主要指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帝王本纪为纲的纪传体史书,这一类史书通常表达了国家意志和民族情感。二十四史是中国历代的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的总称。它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二十四部史书。中国正史用本纪、列传、表、志等统一的体裁编写。二十四史之中,除《史记》是通史之外,其余皆为断代史,还有部分既是断代史,同时又是民族史,例如《辽史》《金史》。此外,也有人把《清史稿》列入,称为二十五史,但是在《清史稿》中关于海外民族的记述已经有了新的视角,具有世界近代化的特征,所以本文不讨论《清史稿》中记载的海外民族。除了记载古代中国各朝疆域内的民族历史,也还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情况,对所认识的海外民族有所记述。从总的趋势来看,古代中国对海外民族的记述经历了一个在空间上不断扩大,内容上不断丰富的过程,表明中国对世界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的认识过程,这是由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深度和广度所决定的。20世纪,中国学术界对古代海外民族的研究在很长时间里大多数是从中西交通史的角度进行,没有把海外民族作为本体进行研究。进入21世纪,开始有学者从民族学的学科角度对海外民族进行研究。2010年高丙中在《西北民族研究》发表了《海外民族志: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路途》,文章认为,中国的人类学要与世界接轨,必须到境外进行民族志研究,才有可能为中国的整个社会科学找到新的发展之路,这是关于学科发展问题的论述,没有涉及古代的海外民族研究;(2)高丙中:《海外民族志: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路途》,《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王建民2013年在《西北民族研究》发表了《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学术史》,文章对“中国古代海外记述传统、20世纪上半期中国学者在海外的实地调查及其著作、中国人类学界海外研究的早期案例、20世纪50年代以后台湾香港学者所作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人类学界的海外民族志研究作了较为系统的爬梳,以求勾勒出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史的总体轮廓,说明每一时期海外民族志发展的特点及研究重点的变化,为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大规模开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平台”。(3)王建民:《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学术史》,《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这是一篇典型的学术史研究论文,但重点不在古代,强调的是民族学人类学现当代的海外民族志研究,而且他们的研究都不以正史作为研究的基本依据,所以这些研究还不能够算是中国古代的海外民族研究。
总的来看,学术界对古代中国的海外民族研究关注是不多的,因此研究中国正史中的海外民族,目的是梳理中国正史关于海外民族的记述、从对海外民族的记述中看中华民族与海外民族交往、交流的基本规律,以求在中国正史中寻找世界民族早期发展历史,丰富世界民族历史的研究,乃至丰富世界历史的相关研究内容。2014年,我们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发表了《二十五史中的海外民族史志与中国的文化边疆、政治边疆》,虽然与海外民族有关,但是重点是讨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边疆和政治边疆问题;(4)王文光:《二十五史中的海外民族史志与中国的文化边疆、政治边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4期。2015年我们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发表了《中国正史中的古代海外民族史志研究》,初步讨论一些海外民族研究的基本问题,深度不够;(5)王文光,曾亮:《中国正史中的古代海外民族史志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2019年我们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发表了《商周时期华夏族的民族观、民族地理观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中涉及一些海外民族研究的内容。(6)李艳峰,王文光:《商周时期华夏族的民族观、民族地理观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目前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入推进,有必要从中国正史中发掘中华民族与海外民族交往、交流的历史,希望我们探索性的研究能够对“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一定的学术贡献。
需要特别说明,在二十四史中提到的海外民族名称,一般而言既指某个国家或者地区,也指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地区的民族。例如大夏,既指大夏国,也指大夏国人,或者指大夏国的民族,我们关于海外民族的研究,就是用后一种意义,即指某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民族。
一、海外与海外民族考释
中国正史中,除了《陈书》《北齐书》没有专门记载民族历史的传记之外,其他的各史都有专门的民族历史传记。但并不是所有的民族传记记载的民族都是中国各个朝代疆域内的民族,那些不在中国疆域内的民族可以称之为海外民族。因此,关于海外民族的讨论首先从“海”字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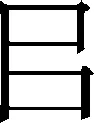
除此之外,先秦时期的文献中还有诸多关于“海”的记载,其中《尚书·禹贡》的记载最多且最为详细:“海、岱惟青州……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贡盐絺,海物惟错……海、岱及淮惟徐州……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厎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9)江灏,钱宗武译注,周秉钧审校:《今古文尚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3页、第74页、第84页、第85页。《尚书·禹贡》是战国时魏国的人士托名大禹的著作,故以《禹贡》名之。这几个地方说到的“海”,指的是黄海;又载:“淮、海惟扬州……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10)江灏,钱宗武译注,周秉钧审校:《今古文尚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6页、第77页。“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迆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11)江灏,钱宗武译注,周秉钧审校:《今古文尚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5页。上述说的“海”,指的是东海,因为古代的“江”专门指长江,长江流入东海;又载:“导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12)江灏,钱宗武译注,周秉钧审校:《今古文尚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3页。这里的“海”,指渤海;又载:“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13)江灏,钱宗武译注,周秉钧审校:《今古文尚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4页。所指为南海。
从《尚书·禹贡》关于海的记载来看,说明只有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生活在靠近“海”的地方,这个“海”就是中华民族分布区东部的渤海、黄海、东海以及东南方的南海。分布在东部的主要是商周时期的鲁国、齐国的华夏民众,《诗经·鲁颂·閟宫》载:“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保有凫绎,遂荒徐宅,至于海邦。”(14)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40页。这里的“海邦”是指鲁国东部的黄海;(15)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原始社会·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26—27页。《尔雅·释地》载:“齐有海隅。”(16)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十三经》下册,徐朝华注译:《尔雅》,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1995年,第56页。说明齐国也是在海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的记载,齐国的北边是渤海。(17)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原始社会·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26—27页。在《汉书·叙传》中还提到了东海和南海:“南越尉佗,自王番禺。攸攸外寓,闽越、东瓯……汉兴柔远,与尔剖符。皆恃其岨,乍臣乍骄,孝武行师,诛灭海隅。”(18)《汉书·叙传下》,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第4268页。闽越、东瓯分布区东部,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的记载是东海,南越的南部是南海。(19)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原始社会·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31—32页。
上述以《尚书·禹贡》为代表的文献对“海”的记载,真实地反映中国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是古代中华民族对中国地理环境基本特征的早期认识,“他们所聚居的这片大地是一块从西向东倾侧的斜坡,高度逐级下降。西部是海拔4 000米以上的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东接横断山脉,地势下降到海拔1 000—2 000米的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其间有塔里木及四川等盆地。再往东是海拔千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和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20)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页。再往东就是西太平洋上中国的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这恰好与《尚书·禹贡》等文献的记载吻合。除了历史与地理文献的记载之外,在先秦时期的神话当中也对“海”有记载。例如《山海经·北山经》载:“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21)黄永年校点:《山海经·北山经第三》,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0页。
很显然,“海”是中华民族认识自己生存空间的一个自然地理概念,诸多的文化概念也就由此推演出来,具体有“四海”“海内”“海外”等与国家疆域、民族分布相关联的概念,这些概念具有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表现了中华民族早期的时空观和民族观。
从《尚书·禹贡》的记载来看,并没有严格意义的四个“海”,那么为什么古人会有“四海”的概念呢?《管子·地数》记载说:“桓公曰:‘地数可得闻乎?’管子对曰:‘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22)戴望校正:《管子校正·地数》,《诸子集成》第5册《管子附校正》,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382页。从这个数据来看,中华民族认为自己居住的地理空间是由东西南北构成的一个四方形,故有“天圆地方”之说,这个四方形大地的周围就是“海”,四方形大地到达“海”以内的空间被称为“四海”,就是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空间。(23)李艳峰,王文光:《商周时期华夏族的民族观、民族地理观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四海”一词当最早出现在《诗经·商颂·玄鸟》中:“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24)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48页。《诗经·商颂·玄鸟》是宋国国君祭祀商高宗武丁时吟唱的诗歌,赞颂武丁中兴时商朝疆域内所有的民族都来朝贡,所以这里的“四海”就是指商朝的疆域。《尚书·禹贡》又载:“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25)江灏,钱宗武译注,周秉钧审校:《今古文尚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8页。从文义来看,这里的“四海”与“海”的纯粹自然属性概念不同,已经具有强烈的人文属性。其他有代表性的记载还有《尚书·大禹谟》:“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26)江灏,钱宗武译注,周秉钧审校:《今古文尚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7页。《尚书·禹贡》:“九泽既陂,四海会同。”(27)江灏,钱宗武译注,周秉钧审校:《今古文尚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7页。《九歌·云中君》载:“览冀州兮有馀,横四海兮焉穷。”(28)聂石樵注:《楚辞新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5页。《史记·五帝本纪》载:“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29)《史记·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第43页。以上所有的“四海”都是指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的疆域,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具有文化和政治意义。
到了汉朝,“四海”一词在很多情况下也是指中国疆域。《史记·高祖本纪》载:“大王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30)《史记·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第379页。本处的“四海”便是汉朝疆域的代名词。强盛的唐朝,也常以“四海”指唐朝的疆域。《新唐书·韩瑗传》载:“陛下富有四海,安于清泰,忽驱逐旧臣,遂不省察乎?”(31)《新唐书·韩瑗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4030页、第4031页。《新唐书·褚遂良传》又载:“汉光武得其雄,起南阳,有四海。”(32)《新唐书·褚遂良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4026页。。《新唐书·长孙无忌传》载:“群臣披荆棘,事陛下。今四海混一,诚不愿违远左右(33)《新唐书·长孙无忌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4019页。”。所谓“四海混一”就是指建立了大一统国家。
综上可知,先秦时期华夏族把自己认知的生存空间叫做“四海”,是天子控制的区域,而“四海”之内的所有民族都是天子的臣民,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天子统治下的臣民就是一个中华民族共同体。因此,“四海”又多了一层含义,把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称为“四海”。《尔雅·释地》记载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34)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十三经》下册,徐朝华注译:《尔雅》,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1995年,第58页。与《尔雅》所记载内容相同的文献还有《论语·颜渊篇》的记载:“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35)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24页、第125页。费孝通曾经这样概括地说:“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广阔的大陆上。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这个地区在古代居民的概念里是人类得以生息的、唯一的一块土地,因而称之为天下,又以为四面环海所以称四海之内。这种概念固然已经过时,但是不会过时的却是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36)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页。
由于“四海”主要指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疆域,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因此在“四海”的基础上产生了“海内”和“海外”两个概念。“海内”指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疆域;“海外”则指古代中国各朝疆域之外的国家和民族的分布区。《诗经·商颂·长发》就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37)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49页。这里的“海外”就是指商朝疆域以外的地方,以后“海外”这个概念就成了中华民族习惯使用的词语,主要指的是古代中国主权实体边疆以外的区域。(38)王文光:《二十五史中的海外民族史志与中国的文化边疆、政治边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4期。那么分布在“海外”的民族就可以称为海外民族。
二、中国正史中的海外民族记述
中国正史中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就有记述海外民族的传统,但是不同历史时期对海外民族的记述因为不同的历史背景,所记述的重点和特点是与差别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多民族中国发展的多样性特征。
(一)汉晋时期编撰正史中的海外民族记述
汉晋时期编撰的正史有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南朝刘宋范晔的南朝梁萧子显《后汉书》、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北齐魏收的《魏书》、南朝萧梁沈约的《宋书》、南朝梁萧子显的《南齐书》等七部正史,其中《史记》是一部通史,其他为断代史,而《魏书》还是鲜卑民族史。
先秦时期,中国人对海外民族的认识是十分模糊的,仅仅在《穆天子传》《山海经》这一类书中可以看到一些对海外民族奇异的记载。汉代,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第一次较为系统的记载了奄蔡国人、大夏国人、身毒国人、安息国人、条支国人等海外民族,开创了对海外民族记载的先河。《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的海外民族虽然较为简略,但对广义西域海外民族的记述,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将目光从黄河流域放眼到中亚乃至更加遥远的地区,从而使《史记·大宛列传》具有了世界史和世界民族史的性质。(39)王文光,曾亮:《中国正史中的古代海外民族史志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从此以后,在中国的正史中就有了海外民族的记载。一般情况下记载顺序为:“其国来历、族类、地理位置、物产、语言、风俗、宗教、政权更迭、与中原或中国交往等。所叙史实时间愈近愈详。”(40)赵俊:《〈梁书〉、〈陈书〉的编纂得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3期。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汉朝还没有在西域设置都护,公元前60年汉朝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其重大意义在于狭义西域成为了汉朝一个行政区,是大一统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班固把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改为《汉书·西域传》。《汉书·西域传》中记载的海外民族,与汉朝仅仅是保持着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交流关系,所以班固说:“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其来贡献则相与报,不督录总领也。”(41)《汉书·西域传下》,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第3928页。说明了这些海外民族与汉朝的关系是一种经济交往和文化联系,(42)王文光:《二十五史中的海外民族史志与中国的文化边疆、政治边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4期。双方没有紧密的政治关系,特别是没有什么领属关系。
到了东汉时期,东汉与中亚乃至欧洲的海外民族的交往有所扩大。范晔的《后汉书·西域传》中有关于条支国人、安息国人、大秦国人、大月氏国人、高附国人、天竺国人、东离国人、栗弋国人、奄蔡国人等海外民族的记述,都比《史记》《汉书》的记载更加具体。(43)王文光,曾亮:《中国正史中的古代海外民族史志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后汉书·光武帝本纪》还首次记载了东北亚地区三韩、倭人等海外民族与东汉的交往。
《三国志》(44)前四史中《三国志》的成书时间比《后汉书》早,《三国志》的成书时间大约在280—290年间,《后汉书》的成书时间大约在432—445年间。的作者受司马迁民族历史书写正统观念的影响,把曹魏政权作为正统,因此在《蜀书》《吴书》中就没有给蜀国和吴国辖境内的民族立传,(45)王文光,江也川:《二十四史的边疆民族记述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研究论纲》,《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仅仅在《魏书》中写了《乌丸鲜卑东夷传》。《乌丸鲜卑东夷传》中记述的海外民族有韩人与倭人,这是因为曹魏政权的辖境与东北亚地区的海外民族比较接近。
由于北魏的辖境主要在黄河流域,西接西域,东临渤海,所以《魏书》记载的海外民族主要分布在广义西域、北方和东北亚地区,具体有东北亚的百济国人,中亚、南亚、欧洲的安息国人、罽宾国人、吐呼罗国人、南天竺国人、大秦国人等。当然与《后汉书》《三国志》相比较,《魏书》中关于海外民族的记述是比较简单的。(46)《魏书》卷100、卷102、卷103都有关于海外民族的记载,参见《魏书》,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2213—2224页、第2259—2314页。但是,《魏书》的民族列传没有具体的名称。
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宋书》《南齐书》中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东南方的海外民族,中国的历史学家对海外民族的认识和记述,开始从中亚、欧洲、东北亚地区,扩展到了南亚、东南亚地区。
《宋书》记载了东南亚的林邑国人和扶南国人、南亚的狮子国人、天竺迦毗黎国人,还记载了东北亚的百济国人、倭国人等。其中凡是涉及南亚次大陆的狮子国人、天竺迦毗黎国人等的记述都与佛教的传播有关,说明当时刘宋与这些海外民族的交往大多与佛教有关,如果从佛教传播的历史来看,其文献价值是十分重要的。(47)王文光,王玖莉:《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中的民族传记及其特点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书》中第一次出现了狮子国的海洋民族,使中国人对海外民族的认识第一次到达了印度洋,对南亚地区的民族认识也比此前更加深入。(48)王文光:《二十五史中的海外民族史志与中国的文化边疆、政治边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4期。
《南齐书》中记载的海外民族有东北亚地区的加罗(三韩之种族)、倭人,以及东南亚的林邑国人、扶南国人。
(二)唐朝编撰正史中的海外民族记述
唐朝在唐太宗时期编撰的正史有房玄龄的《晋书》、李百药的《北齐书》、令狐德棻的《周书》、姚思廉的《梁书》和《陈书》、魏徵的《隋书》、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等八部正史。
《晋书·四夷传》中记载的海外民族有东北亚的马韩国人、辰韩国人、倭国人、裨离国人等,其中的裨离国人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正史中,“去肃慎西北,马行可二百日”。(49)《晋书·四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2536页。如果记载不错的话,应该是分布于东北亚北部地区的民族;有中亚和欧洲的大宛国人、康居国人、大秦国人等;有东南亚的林邑国人和扶南国人。(50)王文光:《二十五史中的海外民族史志与中国的文化边疆、政治边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4期。
由于北齐政权建立的时间很短,仅有28年(550—577年),此外,北齐的辖境也比较小,为今天黄河下游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以及苏北、皖北地区,这就决定了北齐与海外民族的交往少,而且也决定了北齐民族交往的方向主要是在北方和东北方,因此在《北齐书》中没有民族列传也就可以理解了。但是,在《北齐书》的本纪中仍然有对海外民族的记述,具体有来自朝鲜半岛的新罗国人、百济国人。
陈朝(557—589年)仅存在了32年。此外,陈朝是南朝几个政权中疆域比较小的,能够控制的辖境只是长江以南至交广地区,所以《陈书》是文字最少的一部正史。值得注意的是,陈朝的地理环境特点就是靠近大海,陈朝辖境的东部濒临东海和南海,(51)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4册《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44—45页。因此与陈朝发生交往、交流的海外民族多为能够利用航海技术到达的民族,具体有来自朝鲜半岛的百济人国、新罗国人,来自东南亚的林邑国人、扶南国人、盘盘国人,来自东南亚海岛的海外民族有干陀利国人、狼牙修国人、丹丹国人,来自南亚的天竺国人。
北周共计五帝,享国二十四年。辖境为今天的河南、山东、山西南部、河北中南部、陕西中部、甘肃东部、湖北北部以及长江以北的江苏、安徽地区。上述两个原因就决定了《周书》记载的海外民族不多,具体有东北亚地区的百济人和中亚的粟特人、安息人、波斯人。
《梁书·海南诸国传》是本时期记载海外民族历史与文化最丰富的正史,在东南亚、南亚有林邑国人、扶南国人、婆利国人、盘盘国人、丹丹国人、狼牙修人、中天竺国人、狮子国人;在东北亚有高句丽国人、百济国人、新罗国人、倭国人、文身国人、大汉国人、扶桑国人等;在西亚和欧洲有波斯国人和末国人。
《南史·夷貊传》中记载的海外民族有东南亚的林邑国人、扶南国人,有东北亚地区的倭国人、大汉国人、文身国人、扶桑国人等民族。
《北史》记载的海外民族有东北亚地区的百济国人、新罗国人、倭国人,有东南亚地区的林邑国人、赤土国人、真腊国人、婆利国人,有南亚的吐呼罗国人、南天竺国人,有西亚的粟特国人、波斯国人等等,有欧洲的大秦国人。(52)《北史》卷94、卷95、卷97都有关于海外民族的记载,参见《北史》,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3109—3165页、第3205—3240页。按,《北史》的民族列传没有具体的名称。
隋朝虽然历史短暂,但是《隋书》还是记载了东北亚地区的百济国人、新罗国人、倭国人和东南亚、南亚的林邑国人、赤土国人、真腊国人、婆利国人等海外民族。
(三)五代到清朝编撰正史中的海外民族记述
从五代到清代编撰的正史有后晋刘昫的《旧唐书》、宋朝欧阳修的《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宋朝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元朝脱脱的《宋史》《辽史》《金史》、明朝宋濂的《元史》、清朝张廷玉的《明史》等九部正史。其中的《辽史》《金史》《元史》既是断代史也是契丹民族史、女真民族史和蒙古民族史。
唐代,唐朝的经济实力、文化成就,使众多海外民族纷纷与唐朝交往,唐朝与海外的交往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中华民族与海外民族交往的数量、质量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所有这些都被中国的历史学家写入相关的民族传记之中。(53)王文光:《二十五史中的海外民族史志与中国的文化边疆、政治边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4期。因此在《旧唐书·南蛮西南夷传》中有对东南亚地区林邑国人、婆利国人、盤盤国人、真腊国人、陀洹国人、诃陵国人、堕和罗国人、堕婆登国人等海外民族的记述,《旧唐书·西戎传》中有对南亚、中亚和乃欧亚结合部的泥婆罗国人、天竺国人、罽宾国人、康国人、波斯国人、拂菻国(54)拂菻国是中国中古史籍中对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的称谓。首都君士坦丁堡,亦称大秦或海西国。人、大食国人等海外民族的记述,《旧唐书·东夷列传》中有对东北亚地区百济国人、新罗国人、倭国人、日本国人海外民族的记述。(55)《新唐书》中只记述了日本,而《旧唐书》却有日本和倭国,这样的差别说明,在今天的日本群岛已经开始出现大的政治集团,产生更有政治权威的政治领袖,所以才分别有倭人和日本的记载。
《新唐书·西域传》中有对南亚、中亚和欧亚结合部的泥婆罗国人、天竺国人、摩揭陀国人、吐火罗国人、师子国人、波斯国人、拂菻国人、大食国人海外民族的记述,《新唐书·南蛮传》中有对东南亚环王国人、盘盘国人、扶南国人、真腊国人、骠国人等海外民族的记述,《新唐书·东夷传》中有对东北亚地区百济、新罗、日本、(56)《新唐书》认为日本就是“倭奴”,所以未像《旧唐书》分别叙述倭和日本。新旧唐书对此记录的分歧,反映了海外民族分化融合的复杂过程,导致史料记载的多样性。流鬼等海外民族的研究。(57)《新唐书》卷219《北狄传》、卷220《东夷传》、卷221上《西域传上》、卷221下《西域传下》、卷222下《南蛮传下》,参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6167—6265页、第6297—6308页。
《旧五代史》记载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个王朝五十四年的历史,《旧五代史》与其他正史相比较在记载民族历史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即把海内外的民族历史都写入《外国传》中,(58)《旧五代史》中的《外国传》实际上是“华夷”民族观念的变化,这样的记述方式还影响了元朝和清朝,在元朝编撰的《宋史》《金史》和清朝编撰的《明史》中都有《外国传》。由于五代的五个王朝仅仅经历了五十四年的时间,所以具体涉及的海外民族不多,东北亚地区仅有新罗国人,东南亚地区仅有占城人。(59)占城即历史上的林邑,从8世纪下半叶至唐末,改称环王国。五代又称占城。据当地发现的国碑铭,始终自号占婆。
《新五代史》在编修的体例上打破了朝代的界限,把五朝的本纪、列传综合在一起,依时间先后进行编排。海内外民族历史写在《四夷附录》中,《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虽然有三卷,但《四夷附录一》《四夷附录二》以记载契丹历史为主,《四夷附录三》记载的海外民族也仅仅有东北亚地区的高丽国人、新罗国人和东南亚地区的占城国人。
宋代,在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出现了广州、泉州等港口城市,宋朝还在这些地方专门设置了负责管理与海外民族贸易交换事宜的市舶司,故《宋史·外国传五》中有对东南亚占城国人、真腊国人、蒲甘国人、邈黎国人、三佛齐国人、阇婆国人、南毗国人、渤泥国人、注辇国人、丹眉流国人等海外民族的记述,《宋史·外国传六》中有对南亚、中亚乃至欧洲的天竺国人、大食国人、拂菻国人等海外民族的记述,《宋史·外国传七》中有对东北亚地区日本国人的记述。
《辽史》既是一部断代史,也是一部契丹民族史,所以对海外民族的记载很少,海外民族仅仅在《二国外记》之中记载了辽国东南部朝鲜半岛上的高丽国人。
《金史》的情况与《辽史》大致相同,海外民族也仅仅记载了金朝东南部朝鲜半岛上的高丽国人。
元朝虽然是蒙古人建立的,但是元朝与海外民族的交往不少。在《元史·外夷传》中记载的海外民族有东北亚地区的高丽国人、日本国人等海外民族,东南亚有占城国人、暹国人、爪哇国人、瑠求国人、三屿国人、马八儿国人等海外民族。
明朝与元朝相比较,最大的变化就是明朝有了较为发达的航海业,因此在《明史·外国传》中海外民族就多一些,东北亚地区的海外民族为日本国人,东南亚地区的海外民族有占城国人、真腊国人、暹罗国人、苏门答剌国人、阿鲁国人、和兰国人等,南亚、欧洲的海外民族有古里国人、柯枝国人、阿丹国人、拂菻国人等。
总的来看,从明代开始,中国人大规模与来自欧洲的佛郎机国人与和兰国人交往。佛郎机人在东南亚海岛地区的殖民地拓展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为了取得与明朝的贸易交换权进入中国,他们有着丰富的贸易交换经验,同时还拥有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因此明朝与佛郎机人的交往是不占优势的,当然由于明朝对于佛郎机人的警惕,暂时出现了海禁,使佛郎机人在中国没有获取更大的利益,但是他们的势力已经进入了广东沿海,不断骚扰当地百姓的经济生活。当然,如果从积极的角度看,随着中国人航海技术的发达,有了庞大的船队往来于海上丝绸之路,于是对更多的中亚、南亚海外民族有了认识,特别是郑和出使西洋使中国人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开始与更多的海外民族交往。在《明史·外国传七》中就记载了南亚、中亚的古里、柯枝、小葛兰、锡兰山、榜葛剌、沼纳朴儿、祖法儿、阿丹、剌撒、忽鲁谟斯、溜山、南巫里、加异勒、甘巴里、急兰丹、沙里湾泥、底里、千里达、失剌比、古里班卒、剌泥、白葛达等国及其民族与明朝的交往,同时还记载了这些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虽然比较简略,但是对于今天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相关问题的讨论
中国正史关于海外民族的记述,既是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同时也是世界民族史的研究,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下,是应该作为一个深入研究的领域,具体而言有以下问题值得讨论。
第一,中国正史形成的时间与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历史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史记》形成于多民族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汉朝,虽然在先秦时期有《左传》《国语》《战国策》等著名历史文献,但都不是严格意义的大一统中国历史文本,司马迁完成的《史记》开创了多民族中国正史的编撰体例和书写范式,其他的正史在编撰体例、书写范式都受到了《史记》的影响,对海外民族的记述亦然。从大一统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绝大部分正史都是在大一统时期编撰的,例如《史记》《汉书》是在汉朝编撰的,《晋书》《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隋书》《南史》《北史》全都是在唐朝太宗时期编撰的,《宋史》《辽史》《金史》是在元朝编撰的。西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是中国人系统认识海外民族的开始,一般而言,对海外民族认识比较深入的时代都是在历史上的大一统时期,在多民族中国几个政权同时存在的时期与海外民族的交往、交流,都是在大一统时期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对海外民族的认识与建设大一统国家有关。例如,对中亚海外民族的最初认识,就与汉朝要抗击匈奴、斩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有关。此外,对欧洲海外民族的认识主要是在强盛的汉唐时代。例如,对大秦国人的认识主要集中在汉代,唐代则记载了拂菻国(即东罗马帝国)。
第二,从对海外民族长时段研究来看,中国正史中对海外民族的记述在时间上具有阶段性特征。《史记·大宛列传》记述的中亚海外民族不多,而到了《后汉书》记载的中亚海外民族就比《史记》《汉书》多了许多,因此显示出这样一个趋势,即中国正史关于海外民族的记述是越到后来越详细,记述的内容就越来越丰富翔实。此外,中国正史对海外民族的记述在空间上还具有方向性特征。《史记》《汉书》中基本没有涉及与海洋有关的海外民族,但是从《后汉书》《三国志》开始就出现了对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等海外民族的记述。南北朝时期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的动荡时代,但是因为航海业的发展,中华民族与海外民族的交往却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重要表现就是随着中国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华民族对海外民族的认识从陆地进入到了海洋,所以在《晋书》《宋书》中出现了对东南亚、南亚海外民族的记述,《梁书》甚至还有专门的《海南诸国传》。到了明代,中国人的航海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明史》中就大量出现对海洋民族的记述,说明明朝时期中华民族与海外民族的交往,已经从以前比较单纯的陆地交往,大规模地向海洋发展。(60)王文光:《二十五史中的海外民族史志与中国的文化边疆、政治边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4期。这些都显示了中国正史关于海外民族记述的方向性特征。
第三,中国正史的作者虽然有部分少数民族,但是绝大部分正史的作者是汉人,他们都是以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时间和空间为基点来记述海外民族的,其中不乏自大的文化认知。例如《后汉书·西域传·赞》对大秦、安息就存在着文化偏见,说:“逷矣西胡,天之外区。土物琛丽,人性淫虚。不率华礼,莫有典书。”(61)《后汉书·西域传·赞》,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第2934页。文中说大秦等“不率华礼,莫有典书”,但这样的认识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不能够简单地认为大秦、安息“人性淫虚”,这样的认识是一种农业文明的文化心态,是用唯我独尊的民族思想来认识海外民族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正史的海外民族记述中,一般情况下都是海外民族到中国“朝贡”或者“贡献”,但实际上所谓的“朝贡”或者“贡献”是一种物质交换、文化交流,因为多民族中国丰富的物质财富、发达的文化的确对海外民族有吸引力,所以才会有众多的海外民族不断来到中国。而古代中华民族到海外与海外民族交往交流就比较少,其思想根源是认为中国是“天朝上国”,是中国文化中的“夷夏差序”观念和古代中国以自我为大的世界秩序观念的表现,是中国古代世界秩序观念的反映。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海外民族只不过是“四夷”在空间上的延伸,这样的“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一直到了近代才被打破,使中华民族重新认识世界和世界民族,这从《清史稿》的《邦交志》(62)在《清史稿》中出现了《邦交志》,《邦交志》中记载了俄罗斯、英吉利、法兰西、美利坚、德意志、日本、瑞典、那威、丹墨、和兰、日斯巴尼亚、义大里、奥斯马加、秘鲁、巴西、葡萄牙、比利时、墨西哥、刚果等国家,是以国家关系来记载这些国家及其民族。中可以得到了充分证明。
四、结 语
中国正史记载的海外民族情况,体现出历代对域外民族的认识。这一认识,既有中国民族思想演变的特点,也有自身历史的特定情形。自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以来,对海外民族的认识从陆地向海洋延伸,反映在对外交流交往中就是在陆上丝绸之路基础上生发出海上丝绸之路,认知空间从陆地空间扩展到海洋,体现了中国对海外民族认识的不断扩展和不断丰富。
与此同时,中国民族思想也在不断变化,从华夷之辨的以华夏为基点的世界民族观,逐渐向华夷一体民族融合观转变。从历史上中国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情况看,“一带一路”倡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有深刻的历史脉络可查,有浓厚的历史根源可依。人类命运共同体观点的提出,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点从历代海外民族的认识中可得到清晰的结论。考察历代对海外民族的认识,正具有这样的现实意义,这也是今天重新认识这一史实的价值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