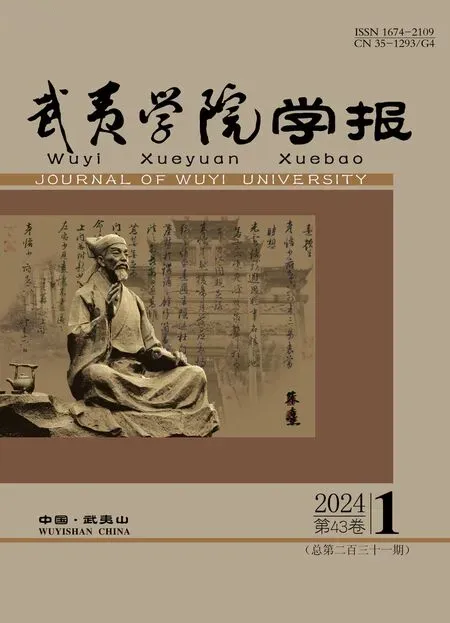福建大圣信俗文化研究回顾与展望
2024-04-15宋宇洁
宋宇洁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在福建的民间信仰体系中,大圣信仰十分特殊。它源自福建先民原始的猴神崇拜,在中外文化互动融合与流行文艺作品的影响下,涵化为极具特色的大圣信俗文化。21 世纪以前福建大圣信俗文化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聚焦在神祇溯源、《西游记》成书与福建联系的探讨上。随着21 世纪初闽北顺昌县“齐天大圣”“通天大圣”相关文化遗存被发现,该领域的研究较以往明显深入,但仍多着力于“孙悟空”艺术形象来源等问题上。2010 年以后,国内外学者们将视角扩大,更多关注到当代的大圣信俗文化,在文艺作品、海外传播和文旅发展等方面研究上出现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成果。总体而言,近年来关于福建大圣信俗文化的研究呈现出逐步上升的态势,但从整体看来,该领域在文献收集考述、区域研究、现代价值等方面还有着耕耘的空间。
一、信俗源流与仪式活动研究
探讨民间信俗的源流,学者们多关注与之相关的地理环境因素与外来宗教文化因素。林蔚文应是国内首位研究福建猴神崇拜的学者,他主要分析了寺院俗讲《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猴行者”形象,以及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神猴“哈奴曼”的形象对福建猴神崇拜的影响。[1]林蔚文认为民间原始崇拜与佛教、印度教的猴神崇拜文化内涵应是福建崇猴民俗的三个主要源流,唐宋时期这三种不同的崇猴文化内涵大致是独立生存发展的,明清以降逐渐合流为大圣信仰。[1]自林蔚文的研究之后,福建学者民间信仰著作中也有猴神崇拜的论述,如林国平、彭文宇《福建民间信仰》爬梳了地方志与文人笔记相关内容,认为福建的猴神崇拜最早可追溯至唐代,至迟则是五代时期。[2]徐晓望《福建民间信仰源流》中关于猴神崇拜的部分在史料的收集上则更为丰富详尽,较为系统地展现了隋唐至明清时期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崇祀事略。[3]陈利华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论述,他认为福建猴神崇拜的产生是出于对猴的畏惧心理,以及人们驱疫避害的需要,而建于五代时期的泉州开元寺猴行者浮雕,又可证明福建猴神崇拜掺杂了佛教成分,并非单纯的动物崇拜。[4]
民间信俗所隐含的文化特征,借助仪式活动这一载体展现。黄活虎的研究视角由小见大,以仪式活动作为侧面揭示了类型信仰现象的文化特征,并收集了大量齐天大圣信仰仪式活动一手材料。他重点调查了齐天大圣信仰的仪式活动,通过分析生日仪式、符篆神咒、游神仪式、大圣对联等六种仪式活动所具有的文化特质,认为福建民间存在的大圣信仰不是对文本齐天大圣的简单翻刻,而是多种文化融合的结果。大圣信仰吸取了福建地域的文化特征,既有《西游记》艺术塑造的影响,也有百姓自身的审美价值取向。[5]陈超、林哲则聚焦了福州地区,福州地区存在着塑像、诞辰日祭拜、春节游神仪式、迎神活动几种仪式活动,它们体现了福州大圣信俗文化的多种文化特征,包括分布广泛、形象多元、故事口耳相传等。[6]
二、区域信俗田野调查研究
(一)闽北地区
林蔚文最早对流行于闽北南平樟湖坂镇的崇猴民俗进行了田野考察。他通过调研发现樟湖坂镇崇猴民俗来源于闽东地区,在当地呈现出拟人化、散祀、善神属性等特征。樟湖坂镇所供奉猴神的神职功能并不复杂,民众所祈求也多与民生相关。林蔚文研究的亮点在于同时考察一地的两种动物神灵信俗,他记叙了樟湖坂镇的蛇神与猴神在祭祀活动中互动的情景,并比较了民众对二者祈求目的的异同。虽然蛇、猴二神都有祈福消灾的神职功能,但蛇神是为闽江水上保护神,猴神无此功能,因而两者神性有所区别。[7]
21 世纪初,福建顺昌县宝山发现了供奉“齐天大圣”“通天大圣”牌位的双圣庙与相关碑刻、石雕,大量宋元时期大圣信仰的实物资料引起关注,学界对于大圣信俗文化的研究开始聚焦于顺昌县。王益民最先研究顺昌县大圣信俗文化,他从宝山南天门、双圣墓、“聖見”石刻等考古发现,以及闽北浓厚的书院文化氛围、发达的刻印业等人文因素中推断顺昌宝山具备“孙悟空”形象产生的条件。[8]杨国学则解读了顺昌南天门、双圣庙建筑中阴刻纪年铭文,从中发现顺昌大圣崇拜大约形成于元末至明中叶时期,且顺昌宝山的“大圣家族”与元末明初《西游记》杂剧中的“大圣家族”基本相同。[9]萧仕平立足于文化地理视角,探讨了顺昌从猴神崇拜、通天大圣崇拜到齐天大圣崇拜的变化经历,重点探析了陈靖姑“通天圣母”称号与闽北刻印业传播对这一过程的影响。[10]
顺昌通天大圣信俗极具特色,王益民首先对顺昌县域内“通天大圣”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遗存进行了详尽调查,认为顺昌大圣信仰与国内最早的“猴行者”文献《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记载同步,因此至迟在宋代顺昌就已存在通天大圣信仰。[11]叶明生从民间信仰角度对顺昌大圣信仰的本质进行了探讨,在对比历史文献中猴妖五通的有关记载和顺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认为顺昌大圣信仰的本质是为五通信仰。[12]黎晓铃亦从五通信仰的密教源头出发,认为顺昌通天大圣信仰与五通信仰有密切关联,且顺昌的通天大圣家族是五通信仰与瑜伽密教结合衍化而来。[13]
(二)闽南地区
尤丽雪调查了漳州市南靖县三卞村的6 座大圣宫庙,分析了齐天大圣信仰在宗族蕃衍发展中的历史传承等问题。她认为随着宗族的发展,齐天大圣信仰逐渐在地化,其职能逐渐契合宗族需求,信仰也融入宗族发展过程,且随着宗族的发展而嬗变。[14]池莉莉则关注泉州沿海地区,对南安石井大圣信仰进行了调查与研究。她详细描述了石井大圣信仰的宫庙建筑、仪式活动与信众生活,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当地大圣信仰与沿海社会文化的融合。大圣信仰最初作为山林的猴神崇拜产生,又以“瘟疫神”的神格传入沿海的石井镇,经过在地化发展,“医神”“平安神”“求子神”等神格逐渐出现,适应了石井沿海社会文化的信仰需求。大圣信仰从内陆向沿海的转移体现了闽南沿海民间信仰格局的多样性。[15]
(三)中国台湾地区
自古闽台同俗,中国台湾地区信仰的大部分神明多是从福建等沿海地区分香割火传入台湾地区的,其中也包括大圣信仰。中国台湾学者郑志明的论著中提及“孙悟空”是由幻想人物转变为民间神明,其主祀庙宇不多见,但是作为陪祀神的地位却颇为重要。[16]吴思慧跨出了台湾大圣信仰在地化研究的第一步,她调研了中国台湾地区北部、中部、东部和南部共计27 座主祀齐天大圣的庙宇,在大量历史文献与田野资料的基础上,勾勒出明清以降齐天大圣信仰渡海来台的概貌。她又透过神祇称呼、塑像、匾联、宝诰与崇祀活动等庙宇相关意象,剖析了齐天大圣在台湾民间信仰中的神格与神职功能,台湾信众心中大圣的功能十分多样,包含医药神、护法神将、护儿、学业神及偏财神五种。[17]
(四)海外地区
福建大圣信俗跨海传播所至之地还有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泰国学者谢玉冰较早关注到泰国的大圣信仰,其著作中介绍了泰国存在的40余座大圣庙宇及供奉有其神位的其他庙宇的分布情形。另外,他还提到泰国许多大圣庙宇的兴建与起源都与大圣显灵有关,当地信众对大圣的崇拜往往也与巫傩文化相结合。[18]班侬·拉姆盖重点分析了泰国崇拜孙行者的原因,认为华人群体祖籍的神猴文化影响、泰国人之于猴子的态度、印度文化的影响、佛教元素以及孙行者形象对于人们心理诉求的满足是泰国大圣信仰流行的重要因素。[19]李天锡在其著作中提到马来西亚的大圣相关庙宇,如砂南坡南山祠、沙捞越河新渔村显圣宫等都供奉有齐天大圣。[20]
三、文学艺术作品研究
(一)《西游记》及相关文艺作品中的“齐天大圣”“通天大圣”
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对福建大圣信俗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关于《西游记》之中“孙悟空”原型是否与福建有关,也是众多学者探讨的问题。关于孙悟空原型考证,学界已有“本土说”“外来说”“混血说”“佛典说”几种主流观点,日本学者矶部彰在“佛典说”的基础上,认为孙悟空形象还吸收了福建民间的猿猴传说故事。[21]自矶部彰始,学者的目光渐转移到《西游记》成书与福建的关系上来。日本学者中野美代子承接了这一观点的余绪,并正式提出“孙悟空诞生在福建泉州”的论断。[22]徐晓望回应了日本学者们的观点,他认为在南方各区域中以福建的猴神崇拜最盛,而《西游记》中孙悟空偷桃、海龙王的水晶宫等故事都可在福建民间传说中找到来源,福建民间流传的猴精形象与“孙悟空”形象也是最为接近的。[3]后来徐晓望从文本故事传播的角度,以《西游记平话》和山西队戏《唐僧西天取经》在福建的出版与传播为佐据,再次论证了福建的大圣崇拜是孙悟空原始形象来源的观点。[23]
上节所述王益民对顺昌大圣信俗的研究引发了“孙悟空”艺术形象是否与顺昌县有关的讨论,将我们的关注点从福建省域缩小到了顺昌县。蔡铁鹰是国内研究《西游记》的专家,他指出“齐天大圣”并非只在顺昌一地出现过,又以二者出现的年代不同为依据,认为顺昌“齐天大圣”与《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无关。[24]但蔡铁鹰的另一篇文章肯定了顺昌大圣信仰实物资料的研究价值,他认为顺昌发现的“齐天大圣”家族可作为中国本土文化中称为“齐天大圣”的神猴故事独立存在过的佐证。[25]王枝忠从顺昌现存的大量实物遗存和口述资料出发,将顺昌大圣信仰与元末明初时《西游记》的成书联系起来,同时认为世德堂本《西游记》的刊行对顺昌大圣信仰的逆向影响和改造作用,也需要给予重视。[26]齐裕焜的观点则侧重于朱鼎臣本《西游记》与顺昌、福建的联系。在朱本成书时期,闽北刻印业十分发达,加之福建省内大量与《西游记》有关的地名与《西游记》中的海洋情结,因此他认为朱本据以改编的《西游记平话》或其他“前世本”极有可能是在福建编成的。[27]针对以上学者的研究,蔡铁鹰予以回应,他认为《西游记》的成书过程有南北系统的区别,而福建存在的齐天大圣崇拜可以证明孙悟空形象的南方文化系统,但不能直接等同于孙悟空这一艺术形象的来源。[28]后蔡铁鹰通过对顺昌实物资料和泉州开元寺的专项田野考察,认为福建普遍存在的大圣崇拜在宋元时属于民间宗教范畴,应与《西游记》杂剧出现的时期对应。[29]
(二)《闽都别记》中的“丹霞大圣”
福州地区流传的小说《闽都别记》包含着大量陈靖姑传说故事,在故事中有一赤毛猴的形象,即是“丹霞大圣”。丹霞大圣作为陈靖姑的偏将受到人们崇祀,由此在闽东地区形成了丹霞大圣信俗。陈济谋、杨少衡、林蔚文的《福建乡土文学的瑰宝》对丹霞大圣有一定篇幅的论述,其中认为丹霞大圣传说的社会文化背景源于福建地区历史悠久的崇猴民俗,正是因为福建民众有着长期猴神崇拜的基础,才造就了陈靖姑传说中出现丹霞大圣这一形象。[30]赖婷对福州地区丹霞大圣与齐天大圣神际关系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作为民间叙事的《闽都别记》与作为文人叙事的《西游记》在福州大圣信仰建构方面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在当地民俗精英的运作下,丹霞大圣所在的陈靖姑神团与齐天大圣神团互动,使得福州猴神的神际关系发生变化,齐天大圣成为了福州猴神信仰的主流代表,具体表现为神像位置关系的变化和各类带有“降伏收编”“结义成团”情节的传说的生产。[31]
四、现代转型与价值研究
2011 年12 月,顺昌“齐天大圣信俗”列入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让以顺昌大圣信俗为代表的福建大圣信俗文化受到了更多关注。同时,福建大圣信俗文化的现代转型与价值的开发,也成为近十年来大圣信俗文化研究领域颇受关注的议题,主要体现在文旅发展与文化交流价值两个方面。
由于顺昌“祖地”的影响力,顺昌大圣信俗文旅发展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黄远水认为顺昌宝山旅游形象可定位为“道教名山与道佛合一”,以增加大圣文化神话色彩与信服度,需着力于大圣文化旅游资源的地位与功能,充分认识其文化旅游产品的生命周期,从而保持大圣文化旅游的持久吸引力。[32]谢辉从文化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入手,指出大圣文化是推动顺昌县域经济发展的生产力,因此建设大圣信俗文化品牌、遵循原则发展旅游经济、调整明确总体思路是更好发挥大圣文化竞争优势的主要对策。[33]彭莎则采用旅游人类学理论和昂普分析理论,从资源、市场、产品三个角度探讨了顺昌县齐天大圣民间信仰的旅游开发,她认为顺昌县大圣信俗文化资源作为民间信仰类非遗,需要依托一定的物质载体(如建筑、艺术品等),将信仰旅游转换为观光旅游产品,并依附于其他资源进行整体开发。[34]
顺昌宝山、福州屏山与南安石井三地都有着大圣信仰“祖源地”的认可,并与中国台湾地区、东南亚的谒祖信众有着不同程度的往来,大圣信俗文化俨然已在海内外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交流价值。王益民研究了顺昌大圣信仰与台湾的神缘地缘关系,他提到台湾信众曾数次组团到顺昌谒祖朝圣并接采香火的事迹。从台中市合安堂的谒祖之旅开始,台湾马祖北竿尚书公府、玄天宫、台北市南港区护国九天宫忠孝堂等进香团也曾前来顺昌寻根,在此背景下,闽台大圣信俗文化的互动与交流持续升温。[35]赖婷通过访谈了解到福州屏山齐天府祖殿与马来西亚交流的情况,据称马来西亚彭亨州云顶塞帕玉封孙灵宫曾于2019年齐天大圣诞辰期间,带领20 多位信众赶到福州,并举行了隆重的谒祖请香分炉仪式,以此扩大马来西亚华人群体和民间信仰圈的影响力。[36]池莉莉对石井大圣宫的调查中提到宫庙捐款名榜上的捐资地区,除了福建省内晋江、泉州、石狮等地外,也包含了中国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可见石井大圣宫与中国台湾地区、东南亚信众也有着往来。[14]
五、反思与展望
上述仅对当前学术界对于福建大圣信俗文化各领域的研究作了一个简要的回顾,还有许多优秀的成果因篇幅所限无法囊括,如徐晓望对福建瑜伽教与《西游记》关系的研究、绕伟新对顺昌元坑镇通天大圣信仰的田野考察报告、陈绍明对闽北建瓯市玉山镇大圣信仰的考察、杨式榕对丹霞大圣文学形象的研究等等。总体而言,由于近年来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福建大圣信俗文化的研究不断呈现上升之势,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仍有遗憾和不足之处。
首先,福建大圣信俗文化的区域研究呈现出不均衡的现状。由于顺昌县文化遗迹的发现与当地政府的推动,学者们的研究聚焦于齐天大圣、通天大圣信俗所在的闽北地区,对于如丹霞大圣信俗所在的闽东、闽中地区研究较少,闽南地区的大圣信俗文化虽有学者关注,但比起闽北地区的研究则显得相形见绌。闽西、闽中地区大圣信俗文化的调研几乎没有,遑论海外大圣信俗文化的调查与研究。这都是有待学者们耕耘的领域。同时,关于大圣信俗与其他信俗文化的交叉与交流,也是目前学界甚少系统考察的地方。总体而言,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学者们逐渐将目光投向除闽北地区外的其他区域,也有学者关注到大圣信仰与三济祖师信仰[12]、陈靖姑信仰[31]的互动,这是值得肯定的趋势,然而在现有的成果中,这样的探讨仍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
其次,大圣信俗文化民间文献收集与考述研究工作还需要继续推进。就史料的利用而言,关于福建大圣信俗文化的史料文献是较为匮乏的。目前所存在的许多关于“孙悟空”原型是否在闽、《西游记》是否与顺昌有关等争论,其主要原因是史料记载的模糊,相关文化遗迹、考古发现也较少,上述争论也大多是基于“《西游记》情结”的研究视角,对福建本土的大圣信俗文化挖掘不够。因此,加快对福建大圣信俗文化相关民间文献的挖掘与整理,尤其是福建大圣宫庙基本资料的收集等基础性工作的推进,有助于我们跳出《西游记》研究的框架,更加准确地掌握福建大圣信俗的文化价值,故民间文献收集与考述研究工作或是接下来研究的重点之一。
最后,大圣信俗文化的精神内核和文化交流价值方面有较大的研究空间。福建大圣信俗文化与其他动物神灵如蛇神、蛙神、灵龟、狐仙信俗文化相比,其独特性与蕴含的精神内涵都还有待比较和挖掘。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大圣信俗文化因与《西游记》等作品的相互影响,其所具有的文学特质更浓,这一点应当继续进行探讨。同时,大圣信仰虽是来源于山林,但由于福建地理位置因素的影响,也曾和妈祖信仰、陈靖姑信仰等一样,伴随着许多前往异国他乡的福建移民,跨越山海,传播至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当代发挥着重要的海内外文化交流价值。就目前看来,这仍是该研究领域一个方兴未艾的板块,需要学界进一步调研与挖掘,以加强大圣信俗文化的纽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