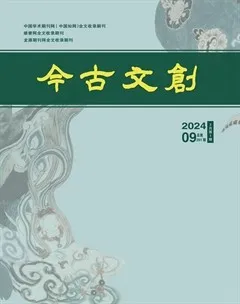论陶渊明诗文对《列子》思想的接受
2024-04-07陈梦梦
【摘要】在晋宋时期的政治环境下,陶渊明仕途受挫,贫寒多病,现实矛盾引发了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和追寻,陶渊明对生命哲学的感悟正与《列子》思想相契合,在诗文中形成了“憔悴由化迁”的自然生死观和“且趣当生,奚遑死后”的贵生思想。陶渊明“回归自然”的生存方式亦与《列子》“从性而游”之旨相合,对《列子》思想的接受与超越使陶渊明从生之困境中解脱出来,回归自然,全性保真,达到了精神与生命的平静和谐。
【关键词】陶渊明;诗文;《列子》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09-0029-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9.009
陶渊明心好异书,擅于融汇各家思想,诗文中对典籍亦多有征引。据朱自清先生所述,陶诗用典取材最多的是《庄子》,其次为《论语》,《列子》居于第三位[1]568,由此可见其对《列子》一书的熟悉。从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所列引书的若干情况看,陶渊明诗文中对《列子》一书的征引化用多达二十几处,集中于五言诗,不只为表情达意,更代表了思想上的认同和接受。对陶诗及其所引《列子》篇目进行解读,可以从更深层感受陶渊明的生命意识和生存状态,探寻陶渊明对生死和人生价值的体悟。
一、“憔悴由化迁”的自然生死观
鲁迅先生言“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2]515陶渊明先后五次出仕,始终面临着生与死、穷与达、衰与荣等生存困境,对人事与生死的沉思贯穿诗文,述及生死时,陶集中常见“化”“大化”“乘化”“化迁”等词:“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连雨独饮》)[3]“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①(《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翳然乘化去,终天不复形。”(《悲从弟仲德》)“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穷通靡忧虑,憔悴由化迁。”(《岁暮和张常侍》)“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窊隆。”(《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己酉岁九月九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还旧居》)“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饮酒二十首其八》)“化”有“改变”之意,陶诗中的“化”“化迁”多指天地万物之变化。《神释》“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还旧居》“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中的“大化”引自《列子·天瑞》:“人自生至终,大化有四:婴孩也,少壮也,老耄也,死亡也。”[4]21言人生自始至终大的变化有四个:婴孩、少壮、老年和死亡,把死亡视为生命变化的一个阶段,看作自然规律。“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二语,据朱自清先生所述,引《列子》《淮南子》解“幻化”“归空无”甚确。[1]569“人生似幻化”出自《列子·周穆王篇》:“有生之气,有形之状,尽幻也。造化之所始,阴阳之所变者,谓之生,谓之死。穷数达变,因形移易者,谓之化,谓之幻……知幻化之不异生死也,始可与学幻矣。”[4]99《列子》中的“幻化”,其意亦近于变化,有生命的气息,有形状的事物,都变幻不定,天地所肇始,阴阳所变化的,谓之生死,生死是造化和阴阳变化的产物。“一者,形变之始也,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为人,故天地含精,万物化生。”[4]8《列子·天瑞》篇以气生万物的观点为基础,言天地蕴含精华,万物和人均由其变化而生,陶渊明亦以此解释人之生死,在诗文中屡次将自身的生命变化与自然化迁相联系。如写于晋安帝义熙五年重阳的《己酉岁九月九日》言秋气摧败零落,诗人由“蔓草”“园木”“哀蝉”“丛雁”等自然景物的衰败和节序的变迁思及自我命运,“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万物生生灭灭,人也如此,有生即有死。《杂诗十二首》之三述人事盛衰如草木荣枯,“三春蕖”对应荣华之时,“秋莲房”暗示生命的成熟,“‘枯悴遽未央句,生命的半死半生之況,尤为惨戚”[5],是对生命衰而未竭的隐喻,充斥了盛时难再的忧伤。“日月还复周,我去不再阳”,日月转还往复,个体生命却不可能重复,由盛而衰变化,一旦逝去不再返阳。《自祭文》作于元嘉四年九月,祭文虚构死后的情景,追述了生之造化、死之归宿,开篇言“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从寥落的自然景物入笔,深秋中天地一片凄凉,大雁集结南飞,草木枯黄凋敝。诗人目睹萧索的季节,意识到人的生命也将遵循自然的节奏凋落,永归其中。
陶渊明把四时更替、景物变迁和人的生死都看作自然规律,否认肉体的长生,并在诗文中屡次论及死亡的必然性。《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云:“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此句化用《列子·天瑞》:“生者,理之必终者也。终者不得不终,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4]19言存在的事物按道理必定终结,这是自然之理。《饮酒》(其十五)中的“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引《列子·杨朱》:“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4]219《神释》“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亦出自《列子·杨朱》:“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4]221世间万物的差异在于生存,相同在于死亡,活着各分贵贱贤愚,死后都同归臭腐消灭。《饮酒》“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咏贫士》“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中的“荣公”“荣叟”,及《饮酒二十首》其二“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句所用典故,均出自《列子·天瑞》中所记“荣启期”。孔子游于泰山,遇荣启期“鹿裘带索,鼓琴而歌”,问其快乐之由,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4]22天地孕育万物,人最为宝贵,安处常情,等待终结,还有什么可忧愁的呢,荣启期以虚静之心应对人生得失和生命的消亡,在无为之中享受生命由生到死的自然之乐。这处于贫,乐于生,安于死的人生态度亦为陶渊明所推崇,其所作《咏贫士》七首叙贫困萧索、抱穷归隐之状和不平怀抱,以诗篇分咏历代贫士品行,正表达了清静守节,贫而乐道的精神追求。
二、“且趣当生,奚遑死后”的贵生思想
对生命有限性的体认引发了陶渊明关于生存状态的思考,个体生命与宇宙自然一体,故不必汲汲于生、戚戚于死,随顺宇宙大化,以适情、适性为主,更加眷恋现实生活、珍视生命,转向对生与死、声与名、穷与达的超越,《饮酒二十首》之三言大道衰微近千载,世人吝惜其情,有酒居然不肯畅饮,只顾世俗浮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生命的价值不系于声名,珍重自身才符合自然之道、人之常性。《杂诗十二首》之四言世人满怀名利之心有如冰炭相加,“百年归丘垄,用此空名道”,身亡后同样归于坟墓,又何必看重空名。《拟古九首》之四亦云:“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後,相与还北邙。松柏为人伐,高坟互低昂。颓基无遗主,游魂在何方!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生前的显耀功名难敌死后的寂寥,百岁之后都一样葬于北邙,坟墓高低相映,何其凄凉!功名外在于个体生命,生前身后之名本不值得追求:“去去百年外,声名翳如同。”(《和刘柴桑》)“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匪贵前誉,孰重后歌。”(《自祭文》)陶诗中这种摒弃声名思想的形成对《列子》多有吸收,《列子·杨朱》篇中也多次否定荣枯毁誉的价值:“矜一时之毁誉,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后数百年中余名,岂足润枯骨?何生之乐哉?”[4]221贤愚好丑之人、成败是非之事无不消灭,顾惜一时的毁誉,使心神和身体焦虑痛苦,死后遗留的名声足以滋润枯骨吗,如此生存还有什么快乐呢。《杨朱篇》亦讲及时行乐,张湛注《杨朱篇》开篇解题即说“达乎生生之趣”[4]216,直指个体现实生存:“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熟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4]221活着无论像尧、舜一样贤明,还是像桀、纣一样残暴,死后都是一堆腐骨。姑且追求今生的快乐,何必管死后的事情呢?《杨朱篇》所“乐”之处在于生时的感官舒适,“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4]222,生之快乐就在于放纵对“厚味、美服、好色、音声”[4]216的现实享受。陶渊明同样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主张在有限的人生中及时行乐。如《岁暮和张常侍》云:“屡阙清酤至,无以乐当年。”此句引自《列子·杨朱》“遑遑尔竞一时之虚誉,规死后之余荣;偊偊尔顺耳目之观听,惜身意之是非;徒失当年之至乐,不能自肆于一时。重囚累梏,何以异哉?”[4]220竟一时之虚名,谋算死后的遗荣,而不能放纵身心,和关进死牢戴着枷锁有什么不同呢。《杂诗》之一云:“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寻得欢乐就尽情享受,有酒就招聚邻人一起喝,生命短暂,盛年逝去不再重来。《酬刘柴桑》一诗由庭院树木的落叶和北墙下新生的冬葵等景物的时序变化思及人生短暂,引发“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的感慨。《游斜川》“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和《咏二疏》“放意乐余年,逞恤身后虑”的感叹中更是浸透了人生悲感,带有明显“且趣当生,奚遑死后”的杨朱色彩。
《杨朱》篇所述公孙朝、公孙穆酗酒好色,沉溺酒色之中,不顾世道安危、存亡哀乐,是常人眼中的狂放之徒,面对子产的劝导,朝、穆二人曰:“以难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礼义以夸人,矫情性以招名,吾以此为弗若死矣。为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忧名声之丑,性命之危也。”[4]226生命难以长久的维系,而死亡却很快到来,活着应享尽欢娱,抛弃虚伪,因荣华利禄改变自我的意志是浅薄又可怜的。陶渊明虽认同其“乐生逸身,任性纵情”的观念,但在接受的基础上又有所超越。陶渊明亦以饮酒为乐,萧统《陶渊明集序》云:“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6]3067于陶渊明而言,饮酒行乐不是声色欲望的满足和放纵,而是去除忧虑之后对生命意趣的享受和“试酌百情远,重斛忽忘天”(《连雨独饮》)的宁静平和。陶诗中常以饮酒为寄托,并深得其趣。如《饮酒二十首》之一“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以杯酒消融对人事衰荣的种种感慨,至于通达之境。《游斜川》“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言酒至半酣,放纵超然物外的情怀。《形影神》三首中对此亦有表现,《形赠影》言“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希望于酒中求得解脱,在乱世中苟存,与《神释》中“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洒脱自由形成对比。《列子》以“纵物”为主,肆情恣意,主张把感官的快乐发挥到极端,而陶渊明则以“纵心”为主,将“适意”作为生命追求的极致,摆脱世俗困境的束缚,平和冲淡,明净淳朴,显示出更高的精神境界。
三、“回归自然”的生存方式
陶渊明由其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引发思考,并在选择中不断靠拢《列子》,对《列子》思想的继承和超越使其从现实矛盾中超脱出来,选择了“回归自然”的生存方式,对外表现为回归自然之田园,对内表现为从心而为,全性保真。
陶渊明《自祭文》言“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并以寥寥几笔述及生之困境:“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陶渊明家贫且多病,其诗文中对此多有记载,《答庞参军并序》云:“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本既不丰,复老病继之。”《与子俨等疏》云:“病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颜延之《陶徵士诔并序》中亦载陶渊明“年在中身,疢维痁疾,视死如歸,临凶若吉”[6]2474,陶渊明幼年丧父,自中年始,家贫多病的状态持续了半生之久。同时东晋作为依靠士族支持建立的偏安政权,末年政治紊乱、民生凋敝,“加以易姓前后几十年中——渊明的大半生中——始而有王恭、孙恩之乱,继而有桓玄、刘裕之哄,终而刘裕推翻晋氏,兵戈扰攘,几无宁日”[7],陶渊明所生活的江州浔阳又是各个阶级激烈斗争的一个地区,残酷的社会现实和“颖脱不羁,任真自得”[8]2460的个性,使陶渊明由积极入仕转向回归自然田园,诗文中常有迟暮之叹,情感上亦不免陷入生死与人事的悲哀之中:“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杂诗》其七)“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饮酒》其十五)“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游斜川并序》)《还旧居》更是言及凄凉衰败的人事变迁,“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诗人回到阔别已久的旧居,却满目萧瑟衰败之景,社会的动荡和生命枯荣的转换带来无限凄凉之感。自身的仕宦经历、对战乱中百姓流离失所的目睹及归隐后所面临的生存困境都迫使陶渊明不断思考生命的终极意义。陶渊明的人生归宿建立在对自然田园的选择之上,解决忧虑的方式也由此生发而来,对生死寿夭的感性叹息与哲理思考相融合,在对《列子》思想的接受中寻求到了“回归自然”的解脱之径。《形影神》三首序言中对此有所阐释:“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营营以惜生”句引自《列子·天瑞》“林类拾遗穗”一段,林类“少不勤行”“长不竞时”“老无妻子”,死期将至却仍“拾遗穗于故畦,并歌并进”,面对子贡的疑问,林类回答出“吾又安知营营而求生非惑乎?”[4]25这一命题,认为生死,往返也,怎知力求生存而忙忙碌碌不是头脑糊涂呢?提出了“贵生乐死”的自然生命观以及“营营以求生”与“乐天安命”两种生存状态。陶渊明化用《列子》之言,论及无论贵贱贤愚,都力求生存而忙忙碌碌,是很令人困惑的,因此充分阐释形和影的劳苦之辞,再用自然之理将它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神释》言“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造化不会偏袒,万物自然而然地生长,繁盛而富于生机。人得以跻身三才之中,无论贵贱贤愚都难逃一死,个体生命与人事变迁都必然走向灭亡,沉醉酒中或赢得声名都不如将个体生命与自然相融合,以“纵浪大化中”作为超脱之径。《列子·杨朱》中对此给出了很好的注解:“太古之人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故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当身之娱非所去也,故不为名所劝;从性而游,不逆万物所好,死后之名非所取也,故不为刑所及。名誉先后,年命多少,非所量也。”[4]220陶渊明超脱生死、摒弃声名的生存态度落实到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审美人生境界,其“质性自然”的独特个性决定了守拙田园的人生归宿,在仕与隐的矛盾中毅然遵从本心,归隐田园,正是《列子》“从性而游”人生观的实践。
陶渊明在诗文中常以“塵网”“樊笼”等为喻,将世俗社会和田园生活相对立,并述及对自然的向往之情。《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作于东晋隆安四年,陶渊明时在荆州刺史桓玄的幕府中任职,因风阻于回家途中,其一言“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计算着日子归家,奔走不停,为能与家人团聚感到无比欢欣,所述行路艰难,亦是言说官场多风险,吉凶难料。其二再次感慨行役之苦,对政途的担忧更加强烈:“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面对行役途中的山川荒野,陶渊明心境孤独而悲凉,以“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言及心声,悔恨不应误入仕途,久久淹留。《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亦迸发出“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的自诘,留恋没有世俗之情的园林,向往像长沮、桀溺那样亲自耦耕的生活。
陶渊明以“回归自然”支撑关于生死问题的哲思,建立了依靠自然准则运行的田园生存方式,追求任情适意的生存状态,由仕而隐,躬耕自资,在个性解放方面做了积极的探寻,这些都能反映出他的“贵己”意识和个体生命意识。陶渊明从自然之中寻求归属,也因此更加亲近自然,“自然景色在他笔下,不再是作为哲理思辨或徒供观赏的对峙物,而成为诗人生活、兴趣的一部分”[9]105,以审美的眼光观照自然,发掘生趣,诗文中处处可见美与和谐之境,在回归自然的基础上获得生之乐趣与慰藉,达到了精神的和谐平静。
注释:
①本文所引陶渊明诗文均出自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
参考文献:
[1]朱自清.陶诗的深度[A]//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3]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8.
[4]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黄文焕.陶诗析义[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三[M].济南:齐鲁书社,1997.
[6](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朱光潜.诗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8]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9]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作者简介:
陈梦梦,女,安徽阜阳人,昆明学院人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