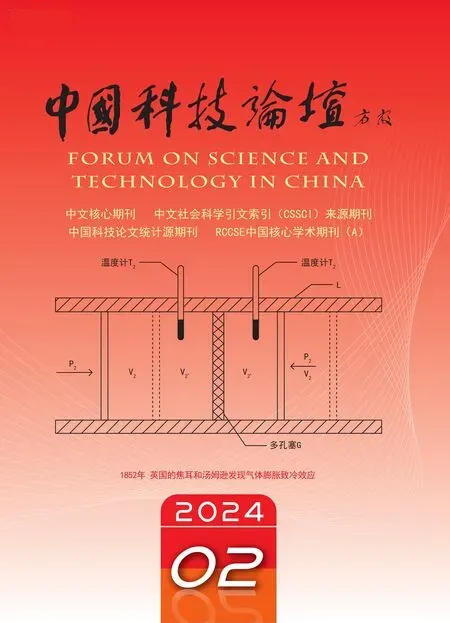专利技术特征溯源及其规范化
2024-04-04饶先成
饶先成
(中国计量大学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0 引言
在我国专利制度产生之前,“技术特征”术语就曾出现在一些介绍国外技术的翻译文献中[1],仅用于表示先进技术的特点,起到了描述技术的作用,但不能构成完整的技术方案,因此也就不能构成专利法的保护客体。在专利制度出现以后,随着权利要求制度的出现,“技术特征”作为权利要求的构成要素,既体现了对技术的认识和描述,同时也在表达和界定专利权的范围。由于权利表达和界定的规范性要求,专利法领域中具有规范意义的术语——“技术特征”得以规范化应用。
“技术特征”作为专利法领域中的重要术语,贯穿于专利权的获取、权利要求解释、无效宣告和侵权判定等诸多专利法相关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当中。在引入专利法之初,我国在颁布第一部《专利法 (1984)》后所制定的《专利法实施细则 (1985年)》中多达8次提及“技术特征”,并在后续的《专利法实施细则 (2010年)》中提及12次之多。而《专利审查指南 (2010)》中提及“技术特征”的表达竟有254处之多,几乎平均每2页就会提到1次“技术特征”。更令人诧异的是,无论专利法还是专利审查指南,均未对如此重要的术语进行定义,以至于只能从“技术特征”与其他术语的关系中获得其大概含义。技术特征虽被作为具有一定规范功能的工具,但“技术特征”这一工具自身概念并不清晰,人们对“技术特征”的认识也不充分。
本文拟从技术特征如何进入专利法领域入手,通过比较分析进行概念溯源,论证从前专利法时代到专利法领域“技术特征”术语的含义变迁。以此为基点,本文拟揭示“技术特征”在专利法领域概念不清的缘由,从而提出规范化的路径建构。
1 专利技术特征的产生
1.1 权利要求书的确立和发展
1793年的《美国专利法》规定了新颖性和实用性的标准,当时主要根据说明书来判断,说明书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与已知技术相区分的功能。专利审查标准有助于确定专利权范围[2],在专利契约理论下,确定专利保护范围时,必须考虑发明人对其发明的披露,专利保护的范围与专利权人披露的内容相当[3]。然而,虽然书面表达完成了对知识产品与有形载体的分离,但将说明书用于界定权利范围显然已无法满足产业发展和技术多样化下侵权判定的需要。法官从说明书中提炼专利权保护范围来确定是否构成侵权,具有较高不确定性,也不利于公众判断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从而增加专利界权的成本。
1811年,Fulton在其汽船发明专利的说明书最后部分记载有“I claim my invention……”,并在其之后记载了3个类似形式的权利要求,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初的权利要求。而这在当时并非强制性要求,只是强调相关专利的重点,虽具有参考意义[4],却没有马上形成需要遵守的先例。可以说,权利要求的出现既有个案和偶然的成分,也是专利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需要。偶然性在于,该案之后的一百多年间,“Claim”并未成为界定专利权的依据,法院仍然基于说明书所记载的内容来确定专利权的范围,“Claim”在专利文献中也仅作动词使用。英国的“发明精髓”原则就是起源于专利法中尚未明确规定专利申请文件中必须包括权利要求书的年代,审理专利侵权纠纷的法院不得不依据说明书记载的内容来辨别发明的实质所在[5]。虽然“发明精髓”原则在权利要求时代仍在发挥影响,但所聚焦的是以权利要求书为中心的点,如权利要求解释中的中心限定主义。而权利要求产生的必然性则在于,法院难以持续承担提炼专利保护范围的繁重任务,导致法律将界定权利范围的责任转移给申请人。
Seed v.Higgins案被认为是权利要求书地位上升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原告Seed因新颖性问题提交了一份放弃声明,从而缩小了权利要求的范围,因而遭受被告Higgins质疑该专利是否有效,该案一直上诉到英国上议院,英国上议院结合其权利要求以及放弃声明判断被控侵权产品是否落入该专利权的范围。可见,权利要求既不能概括过宽的保护范围,以免将现有技术包含进来而面临有效性的质疑,又需要覆盖被控侵权的技术方案,才能构成侵犯专利权。历经判例法实践,英国1883年终于在专利法案第5 (5)条规定:“每个说明书都需要包括权利要求的特别说明,否则任何被官方登记的专利将被视为无效。”[6]往后的司法实践逐渐确立了权利要求的重要地位。此后,如果专利权人无法证明被告的侵权行为直接或间接地落入说明书后面的权利要求书中,就不应当被认定为侵权[7]。
与英国将权利要求书纳入法律要求的时间相仿,1870年的《美国专利法》也开始要求发明人提供权利要求书,并在此后经过判例法的实践。以McClain v.Ortmayer案为例,总结该案得出:如果专利权人只描述并要求其发明的一部分,那么他被认为已经将剩余部分放弃给了公众,如果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的语言清楚表明他希望获得的垄断范围,那么任何不属于专利权人自行选择表达其发明保护范围的行为都不能被视为侵权。
综上,权利要求成为专利权界权的工具有其历史必然性,随着技术的复杂化,法院难以承担从说明书中抽象化地提炼发明创造核心内容的繁重任务,最终导致将这一成本向专利权人转移。对于专利权人来说,撰写权利要求以获得自己起草的保护范围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法院的成本转嫁与专利权人的内在驱动,二者耦合促使权利要求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发挥作用,使权利要求书真正成为界定专利权范围的工具。当然,专利权人自己声明和表达的权利要求范围仍受到新颖性、创造性、可实施等专利实质性条件的限制。
1.2 以权利要求为核心的专利权保护范围
权利要求书充当了界定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工具,通过权利要求书向公众公示权利的范围,以避免社会公众侵权,也便于公众确认权利之外可自由实施的范围。最终当侵权发生时,权利人可凭权利要求与被控行为实施的技术方案相比对,从而判断是否落入专利权的范围。可见,权利要求书扮演着界权的重要使命,但权利要求如何承载上述使命的问题也就随之产生。
专利权依赖语言文字表达权利人要求保护、代表公众的授权机关同意保护、社会公众认为可以获得保护的范围,而通过语言文字体现的是主观意志,且确定性难以与客观存在物相提并论[8]。因此,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不确定性通常被归结于语言表达的模糊性所致[9]。一个已通过专利审查程序并按照相关要求作出修改的权利要求仍存在范围不清晰的空间,这就引发了关于权利要求解释的问题。如果被控侵权的产品并非完全参照权利要求制造,二者在结构上存在差异,通过被控侵权的实物与权利要求书的文字相比对,就更难完全对应。在争议的标的或风险足够高的情况下,律师甚至会揪住权利要求书中的每一词汇提出质疑[10]。为了克服这些问题,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界定不得不面临权利要求书的解释。
权利要求书的解释源于各国司法实践的发展,经历了周边限定主义、中心限定主义和折中主义。纵观权利要求解释方式以及等同原则的发展,从历史维度看,都与权利要求的形成与表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与一个国家专利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脉络相关,还与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市场、科技、产业政策有关。周边限定主义和中心限定主义本质上是形式主义的解释规则和整体论的解释规则之分,不同的解释规则将导致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差异,进而影响侵权是否成立[11]。美国和英国的专利制度均经历了书面披露向权利要求制度的转变,由于司法实践长期存在从说明书中抽象出专利权所保护的范围,两国的权利要求解释均经历了中心限定主义。以美国为例,随着1836年专利法案到1870年专利法案中关于权利要求中语言文字的细微变化,可从中看出美国专利制度从中心限定主义向周边限定主义转变[6]。无论是中心限定主义还是周边限定主义,都伴随着等同原则的适用,在中心限定主义较为活跃的等同原则,于周边限定主义期间相对沉寂,并在Warner-Jenkinson Company,Inc.v.Hilton Davis Chemical Co.案中得以发展。
随着权利要求撰写方式和有关理论的完善,申请人已经掌握了在专利审批中通过权利要求书对其要求保护的发明作出较为准确的定义。此时,英国法院对“发明精髓”原则的依赖程度也就逐渐减少[17],开始向周边限定主义转变。1973年10月5日,《欧洲专利条约》在德国慕尼黑签订,并在1977年10月生效。为了适应《欧洲专利条约》的要求,英国于1977年修改了其专利法,即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的语言确定,说明书和附图用于解释权利要求[12]。此后,英国上议院在Catnic案[13]中,第一次提出了目的解释论,以突破权利要求用语的严格限制,于是,发明精髓原则对于等同物的保护便让位于目的解释论[13]。
各国法院在解释权利要求时,最后均开始向中间地带靠拢,即折中主义,根据折中主义解释,保护范围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权利要求文字所记载的范围,另一部分是权利要求内容相等同的内容[14]。我国自一开始就确立了全部技术特征原则,但在侵权判定过程中,由于专利制度实施时间不长,多数申请人和代理人不精通权利要求书的撰写[15],因此曾在较长时间内适用多余指定原则。多余指定原则源于德国中心限定主义为主的“总的发明构思”理论的引进[16],经历了曲折的发展,我国在2001年发布的《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17条规定了等同原则,自此我国确立了折中主义解释。
权利要求解释经历漫长的动态变化,期间伴随着各国专利法的修改,权利要求的形式要求、专利申请人及代理人技术表达能力因素等推动着权利要求解释的变化。最后,权利要求的解释停留在折中主义下的等同原则,在全面覆盖原则的形式确定性下以寻求保护范围实质上的确定性。否则,争议双方更将无休止地聚焦词汇的文义,等同原则的使用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词义的“射程”范围,在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寻求一种动态平衡,且符合专利契约理论的要求。然而,从宏观上探讨权利要求解释规则以及发展脉络,并未完全消除权利要求书的功能弊端,虽然通常认为权利要求是界定专利权的工具,而权利要求的构成要素是技术特征,真正作为权利边界的是技术特征,即技术特征才是专利权真正的“篱笆”。
1.3 构筑专利权边界的元素:技术特征
倘若将权利要求看作一个集合 (Set),技术特征显然就是集合中的构成要素 (Element),决定集合大小和边界的是具体的构成要素 (Element)。正如我国《专利审查指南》所规定的,技术方案是技术手段的集合。权利要求的内容为技术方案,技术手段由技术特征体现。
从1811年出现的第一个权利要求的撰写方式可知,权利要求书的直接功能就是与现有技术进行区分,从而以此主张本专利的权利范围。而与现有技术进行区分则势必涉及技术的比对,即将权利要求所记载的内容与在先技术进行比对。在先技术可能是具体的有体物,也可能以书面技术资料的形式存在。在侵权判定中,权利要求需要与被控侵权行为实施的技术方案进行比对,即书面记载的内容与专利方法或有形物的产品进行比对。与现有技术区分体现的是专利权有效性问题,专利权有效性和侵权判定都面临着具体边界的问题,尤其是以周边限定主义为权利要求解释方式的情况下,更需要通过权利要求书的分解和比对来实现,权利要求分解后得到的技术特征充当了专利权界定的具体边界。
在哲学上,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与对事物的认识被看作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精神活动[17],文本是一种人类创建的符号,而事物是一种客观存在。将人类所使用的语言符号与有形物进行比较,既需要理解权利要求所记载的内容含义,同时还需要认识有体物,将权利要求中的语言转化为或虚拟化解析为有体物与所比较的有体物对象进行比较,或将所比较的有形物对象抽象化为语言符号再与权利要求中的语言进行比较。
认识一个事物需从特征着眼[18],这或许就是权利要求分解为技术特征的直观理由。所谓“特征”意为一事物异于其他事物的特点,某一权利要求作为一个完整的技术方案,被列入权利要求的内容通常均属于技术特征,此处“技术特征”中之“特征”未必是异于其他事物的特点,否则就不存在比对的必要了。因此,与技术特征相比,用“构成要素”来表示所谓的技术特征,在这里相对要准确得多。参考亚里士多德对于事物的认识,一些未经分析的整体事物在人们对整体中的元素和本原认识出来以后才分析出整体事物[19]。权利要求这个名称笼统地指技术方案这个整体,而定义它或许就要将其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只有分析构成权利要求的构成要素,才能分析权利要求所记载的范围。那么,判断两个事物是否相同或差异,则需要将二者转化成同一维度或尺度进行比较,在数学上被称之为归一化。无论是将权利要求与现有技术相比来判断新颖性,还是将权利要求与被控侵权行为实施的技术方案相比以判断是否侵权,都是寻求两个事物的同一性或差异性的过程。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对同一性和差异性作出说明,即将两个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同性质事物进行比较,用以判断是否存在同一性或差异性[20]。如上文所提到的,笔者以集合理论来分析权利要求的构成问题,正是基于上述同一性理论,从而在比较上也可引入集合与集合之间的比较。有信息领域的专家给出集合的比较方式,对两个集合中的元素一一比较,即遍历集合中的每一个元素[21]。以工程图类比,权利要求相当于一张工程图,表示有体物的符号化实施规则,工程图上的线条代表有体物上的实体界线,而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则表示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具体边界。
2 专利“技术特征”术语溯源
2.1 我国前专利法时代的“技术特征”:技术认识的工具
正如上文所梳理的关于技术特征如何产生,专利法中的技术特征并非与专利制度同时产生,而是随着权利要求书制度的发展而产生的。因而,有必要往前追溯“技术特征”术语进入专利法之前的含义和功能,以此为基础,从历史和逻辑上分析“技术特征”如何进入专利法。
首先,在我国前专利法时代,“技术特征”这一术语是一个组合词,即由“技术”和“特征”组合在一起,“技术”作为对“特征”的限定。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技术特征”没有被作为一个词语对待,查询“技术”的含义为:人类在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积累起来并在生产劳动中体现出来的经验和知识,“特征”的含义为:可以作为人或事物特点的征象、标志等。通俗地说,“技术特征”是用于描述技术上与众不同的特点。笔者通过中国知网以“技术特征”为主题关键词进行检索,并按照时间升序进行排列,发现最早使用“技术特征”术语的文献为1973年发表于《山东纺织科技动态》的文章《新型环锭精纺机技术特征》,该文摘译自美国1972年的《纺织通报》。有趣的是,在1973—1984年期间,提及“技术特征”术语的文献均是国外机器或设备的介绍。所以,本文推断,将“技术”和“特征”组合在一起使用是科技领域对国外技术资料的翻译而偶然形成。因此,“技术特征”这一术语并非一开始就用于专利法领域,而是在科技领域首先被使用,用于技术的描述和表达,是描述性而非规范性的,重在传递技术信息,但表达自由受技术本身的限制。即使在我国创建专利制度和制定第一部专利法以后,技术特征术语所表征的技术描述功能仍被各个领域所使用。
我国专利法主要借鉴于德国专利法,德国专利法在德文中使用“Technischen Merkmale”表示技术特征[22],并在德国专利法英文版中被翻译为“Features”,直译过来便是“技术特点”或“技术特征”,而“技术特点”表述更为口语化,并不适宜作为一个规范性术语,由于“技术特征”已在科技领域对国外技术资料的翻译中形成了使用习惯。早期参与我国专利法立法和国际谈判工作的专家大多来自我国科技领域[23],因此选择“技术特征”术语具有较大的偶然性。本文以“技术特征”为关键词通过中国知网检索显示,江镇华[15]于1988年在《中国法学》上所发表的文章《关于专利侵权的判定》为专利法领域最早使用“技术特征”的学术文献。由此可以佐证,在我国,“技术特征”在前专利法时代以及专利法领域外,均充当了技术认识和技术表达的工具。
2.2 域外“技术特征”术语溯源
在英文语境下,通常使用“Element”“Technic-al Feature”或“Feature”表示专利技术特征。例如,美国专利法在第112条f项中提到技术特征:一项组合的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 (Element),可以表述为为实现特定功能的手段 (Means)或步骤 (Step),而不必描述实现该功能的结构、物质或行为。但对于什么是技术特征,美国专利法也没有下定义,司法判例中也没有明确的定义。德国专利法在德文中使用“Merkmale”表示技术特征,并在德国专利法英文版中被翻译为“Features”。《德国专利及商标局专利程序条例》采用“Technischen Merkmale”表示技术特征,并在其对应的英文版中采用“Technical features”。《欧洲专利合作条约》使用“Element”表示技术特征。通过WestLaw进行案例检索,发现最早使用“Feature”的案例为英国1851年的案例——Goodyear v.Central R.Co.of New Jersey,该案还使用“Technical Character”表示技术特征。HOVEY v.HENRY案是检索到最早使用“Element”表示技术特征的案例,该案例形成于1846年的英国,该案例提到,组合专利并不会因为表明每个零件或技术特征 (Element)之前都已知并使用过而失效。
《布莱克词典 (第8版)》第1576页给出“Element”的定义:一项专利权利要求的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对于预期权利要求的现有技术参考,它必须教导每个权利要求中的构成元素 (Element)。为了从专利侵权中获得赔偿,无论是字面侵权还是等同侵权,原告都必须证明被控产品侵犯了至少一项权利要求的每一个构成要素。构成要素也被称为“Limitation”[24]。由于表示权利要求的“Claim”来自于“Claim”的基本含义:“A demand for a remedy or assertion of a right,especially the right to take a particular case to court (right of action)”[25]。同时,“Element”的其中一个含义便是“A constituent part of a claim that must be proved for the claim to succeed”。那么,专利法中的“Element”表述作为构成要件或构成要素是否来自于侵权法中“Claim”的构成要件“Element”呢?不妨先预设一个前提,若索赔“Claim”与构成要件“Element”的关联组合是由侵权法领域被转用于专利法领域,则在案例中组合使用势必首先存在于侵权法的案件中,反之则相反。故笔者以“claim and element”作为关键词,再次通过Westlaw进行案例检索,发现最早在同一个案例中提到“Claim”和“Element”案件为发生于1857年的专利诉讼案件Forbush v.Cook案,但由于West Law每次检索只显示10000条,故笔者与前述Hovey v.Henry案进行对比,Hovey v.Henry案也使用“Claim”,故将1846年的Hovey v.Henry案作为最早使用“Claim”和“Element”相关联的案件。因此,大致可确定较早使用“Claim”和“Element”关联组合的为专利法领域,而非侵权法领域,故可基本排除“Element”来自于侵权法的构成要件。从柯斯林字典上对“Element”的定义,专利法领域的“Element”符合其基本的定义:“The different elements of something are the different parts it contains.”,并将“component,part,feature,unit”等词作为“Element”的同义词。在专利纠纷案例中,经常将“Element”与“Part”“Component”“Unit”相关联或作为选择并列。
由此可见,即便在国外对于“Element”和“Feature”的使用,仍然是基于物体本身的组成部分之基本含义在使用,正如前文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所提到的,需要通过事物的构成要素才能分析整体事物,[19]因此,在专利法领域表征技术特征的“Element”和“Feature”在前专利法时代也是技术认识和表达的工具,并在专利法领域中获得了该领域的规范性。
3 专利技术特征的规范化困境
3.1 立法和司法中的技术特征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在英文中通常用“Element”“Limitation”“Feature”等表示技术特征,同时还有相近的表述“Part”“Component”“Unit”,基于这些术语构建以“Claim”为核心的话语体系。“Element”和“Limitation”经常被混用,用以表示权利要求的组成要素,在Perkin-Elmer Corp.v.Westinghouse Elec.Corp.案中,判决认为“Element”是权利要求的部件或者实施例中的部件,可以表示单个限定“Limitation”,但更多时候为相当于一系列的“Limitation”的组合,而“Limitation”相当于一个特征“Feature”或限定。在全部要素规则 (All element rule)中,“Element”和“Limitation”均可被视为权利要求的要素,若被控侵权物缺少某一限定“Limitation”或缺少相应的等同特征,则视为不构成侵权。也就是说,在被指控的装置中,必须为权利要求的每一个限定“Limitation”找到等同的特征,而构成等同的特征通常与权利要求的相关限定“Limitation”在相应的组件“Component”中,但未必一定要在相应的组件“Component”中。例如,如果专利权人愿意,他可以将几个限定“Limitation”组合起来用于等同的比对,这样相应的限定“Limitation”则可能就在不同的组件“Component”中。“Part”和“Unit”与“Component”同义,均表示权利要求中的组件。例如,等同原则中的等同物是指与发明中的一个要素 (Element)或部分 (Part)具有可替换被控侵权产品中的相应部分。在诸多案例中,这些术语被混合使用,造成术语不同层次或维度上的紊乱。在Cornell University v.Hewlett-Packard Co.案中,就有这样的表述:“个别侵权部件和非侵权部件 (Component)必须一起出售,以构成一个功能单元 (Unit),或者是整机的部件 (Part)或者单个部件 (Part)总成。”以上从实证角度的案例中分析用于表征技术特征及与之相关的术语,可以看出术语之间的混用以及不同维度和层次的紊乱现象,对于挖掘技术特征的内涵与外延产生了一定的干扰,因此,有必要厘清上述术语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认识技术特征。
相应地,对我国技术特征相关术语的梳理,以统观中英文语境下的技术特征相关术语。在我国以权利要求为核心建立起由技术方案、技术手段、技术特征、组成要素和技术单元构成的话语体系。技术方案是指对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所采取的利用了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的集合;技术手段通常是由技术特征来体现的[26]。“权利要求书应当记载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特征,技术特征可以是构成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组成要素,也可以是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26]技术特征又与技术单元产生关联,即技术特征是指在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技术方案中,能够相对独立地执行一定的功能,并能产生相对独立的技术效果的最小技术单元。在我国专利法领域,同样可能存在同一个技术特征的多个技术单元位于几个组件当中,在云计算领域尤为明显,一部分技术单元可能在云端,另一部分技术单元在本地[27],二者可能作为一个技术特征共同执行某一个特定功能。由于概念的定义是由种差和邻近的属共同组成,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技术单元是比技术特征更上位的术语,一些非技术特征的技术表达也可能被视为技术单元。技术方案与自然规律的关系决定了技术特征也需利用自然规律,但从整体上理解技术方案,并不要求每一个技术特征需要利用自然规律,技术特征或技术手段的集合应在整体上利用了自然规律并解决了相应的技术问题,而不必对单个技术特征施加利用自然规律的限定。
将中英文语境、术语进行对比,很明显,英文表述中并不存在与“技术方案”和“技术手段”对应的术语,直接建立“Claim”与“Element”的联系,将“Element”作为“Claim”的组成部分。《布莱克法律词典》直接从“Element”与“Claim”的关系给“Element”下定义,作为“Claim”的组成部分“Component”,而并非从“Element”自身的属性出发来进行定义。
综上所述,中英文语境虽然都将技术特征作为重要的术语,但两种语言的不同表述存在差异,且都存在不同层次术语混用的情况,下文将对上述情况进一步分析,并试图对比两种语境下的对应关系,以期寻求技术特征术语的确定性。
3.2 技术特征之定义的不确定性
术语或概念的定义是厘清术语或概念作用机理的前提。虽然法律未对技术特征进行定义,但根据技术特征术语的表述和演进,中英文语境下以字典方式或司法实务中都给出了相应的定义。笔者拟检视技术特征的定义,并对其予以修正和完善,以期避免术语使用上的紊乱,建立在准确定义的基础上,尝试为在专利法中规范化使用技术特征奠定基础。
属加种差定义法包括被定义概念的邻近属概念和被定义概念和它同层次的其他种概念相比较的差别,从而能从正面揭示概念的内涵[28],故本文采用属加种差的定义法来检视技术特征现有定义。英文语境下,只揭示技术特征 (Element)与权利要求 (Claim)的关系,没有体现种差和邻近属概念,也就无法揭示技术特征概念的内涵。那么,再来考察技术特征的邻近属概念,实际上即技术特征的上位概念,从几个同义词“Component”“Unit”“Part”的共性上归纳为“单元”“部件”,而技术特征并不仅指的是硬件,还有方法 (Means)、步骤 (Steps),从硬件上归纳无法涵盖方法 (Means)和步骤 (Steps)的特征,因此从技术“单元”概括更能体现其概括性。种差体现于其原有定义中所体现的独立性 (Discretely),这里的意思蕴含着某种可分离的含义,对于技术特征来说,体现其独立性的则是功能、手段和效果等几个维度。与等同判断不同的是,等同技术特征需在满足功能、手段和效果3个要素的基本相同,而限定技术特征是寻求差异的过程,能够体现与其他技术单元的差异即可,只有Function (功能)具有承载差异又能聚合技术单元以进行区分的功能。再结合司法判例对于“Limitation”与“Element”的区分,因此,给出英文语境下的技术特征 (Element)的含义是作为权利要求组成部分的且能相对独立实现特定功能的技术单元,此时,结合表达习惯,“Limitation”也可作为技术特征的邻近属概念,“Element”的含义则可变换为,作为权利要求组成部分的且能相对独立实现特定功能的一个或多个限定 (Limitation)。
在我国专利法领域的语境下,有学者已经从功用的角度对技术特征作出说明,认为所谓技术特征完全是为了对比需要对各种技术内容所作的规范,使之形成特征化。同时,该学者也给出了与最高人民法院相近的定义:“具有独立功能且能对整体技术方案产生独立技术影响的技术单元或技术单元的集合。”[29]在司法判断中,法院又对最小技术单元进行了限定,认为最小技术单元是指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技术方案中,能够相对独立地执行一定的技术功能并能产生相对独立的技术效果的技术内容。与英文语境下不同的是,我国对于技术特征的定义依然借助于“技术方案”这个术语,并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技术单元以多维度信息,即功能和技术效果,因此技术单元实际上被作为技术手段来对待,这也与我国专利法审查指南的描述相一致。“最小技术单元”限定了技术特征划分的量级,“最小”又受到了“独立地执行一定的技术功能”的限制。因此,中英文语境下都采用了技术功能分解法来划分技术特征,而技术功能存在上位功能和下位功能[30],对技术功能的抽象化程度就决定了技术特征划分的量级,即最小技术单元。然而,实现某一技术功能的抽象化本身独立于整体方案,技术特征的划分取决于技术功能的抽象化程度,是否增加“最小”的限定并未影响技术特征划分的量级,而且使用“最小”会让人们对一些从整体上考虑的技术特征划分产生质疑。
有必要说明的是,对于我国专利法中引入“技术方案”这个术语,在英文语境下更多地采用“Claimed invention”(本发明),将技术方案引入的目的更像是对保护客体的限定——利用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而在美国专利法中,奉行的理念是“阳光之下的一切人造物皆可专利”,因此,无引入“技术方案”之必要。
综上,本文对技术特征术语和定义的追溯意在消除各种术语间的混乱,技术特征的定义虽然为技术特征的划分提供了一定的形式规范,但该定义实际上将技术特征划分转化为不同抽象化程度之技术功能的取舍问题。在具有相同技术事实的情况下,不同抽象化程度之技术功能的选择将决定技术特征划分的量级,使技术特征的确定陷入规范化困境,可见完全依赖于技术特征的定义来寻求技术特征划分的确定性是不现实的。而对于如何确定技术功能的抽象化程度,裁判者常常以追求技术事实为目标来探求技术特征划分的理由,这无疑是落入了用事实问题来求解价值判断的“窠臼”,难以成为解释其观点正确的依据。
4 事实与价值二分下确定技术特征的规范化机制
4.1 技术特征确定中的事实因素和价值因素
基于前文所提及的技术特征的定义,其本质上是如何将一个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分解出来,即确定一个技术特征或划分技术特征。对照到实际技术特征的定义和确定上,存在一些事实层面的因素,权利要求所包含的技术特征是客观存在的,技术特征所比对之对象也是客观确定的。但技术特征的确定有赖于前文对技术特征溯源所提出的技术功能抽象化程度的判断,不同技术功能的抽象化程度将造成技术特征划分的差异。上位化的技术功能对应更大的技术特征,下位的技术功能则对应更小的技术特征,如何决定上位与下位之分取决于背后支持其行为选择的价值因素。那么,可以说,技术特征确定中包括事实因素和价值因素,但事实因素和价值因素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鸿沟”。
1737年,英国哲学家休谟在《人性论》中从伦理学角度对事实与价值问题进行阐述,提出了事实与价值二分的“休谟问题”[31],即单纯的事实判断无法推导出价值判断。基于事实与价值二分的原理,可将其用于阐释技术特征确定中事实与价值混淆的问题,并尝试从理论层面予以解决。
区分技术特征划分中的事实与价值部分不仅是为了阐述这种现象,同时也要防止混淆和误判,从而尝试寻求技术特征的规范化机制。沟通技术特征划分中的事实部分与价值部分固然重要,但分别从事实相关的规则下寻求客观事实或接近客观事实和从价值推理规则下寻求价值部分的理性化,也是事实与价值二分所给出的重要启示。若用事实相关规则来寻求价值部分的理性化,无异于缘木求鱼,会造成大量的资源投入而获得一种并不正确的确定性,从而导致资本投入大的主体更易胜出,而价值部分缺乏理性化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纷争。同样地,价值推理并不能代替事实部分的判断,否则将失去事实的客观性而架空案件内容,而且脱离了事实的价值推理显然也无法支撑理性的要求。
4.2 技术特征确定的规范化
在事实与价值二分下确定技术特征需要从中区分事实因素和价值因素,分别采用事实查明规则和相应的价值推理以实现技术特征确定的规范化。理性的裁判建立在对事实的理性主义认定的基础上,在理性主义下世界是可知的,从而有别于人类裁判史上曾经存在的决斗、宣誓或者神明裁判等非理性模式[32],事实查明的理性化有赖于证据以及相应的证据规则。在专利申请的审查中,审查员所检索到的现有技术被称为对比文件,在专利无效请求程序和专利确权诉讼中,无效请求人所检索和提供的现有技术则被称为证据,无论称为对比文件还是证据,实际上均是用以判断发明创造是否为“新”的证据。基于业已确定的权利要求与被用作比对的证据,由于被用作比对的证据往往是已公开的专利文本和出版物等,故这里的证据在真实性问题上一般并不存在异议。专利权利要求以及作为证据的对比文件是一种技术的客观存在形式,在剥离其中的信息内容后这种存在以及所记载的符号是一种客观事实。而作为对比的现有技术只是从茫茫文献中被搜寻到的一小部分,虽与发明创造相近,但却未必是最接近的,在创造性判断中的最接近现有技术自然也未必是客观上最接近的,因此,现有技术所反映的技术只是一种相对事实。虽然需要给出确定性的判断,但人类认识工具和能力的限制导致客观上最接近的现有技术难以被找到,即便被找到似乎也无从确认,从而需要推定其为客观事实,这也成为专利权推定效力的来源。总之,对于事实的判断需要借助于证据,证据的使用和证明效力则依赖证据规则。不同证据间客观存在的各种关系及其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需要借助相关证据规则才能保障裁判事实认定的公正性[33]。202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规定遵循民事诉讼证据一般规则,立足知识产权诉讼特点和实际,对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问题较为突出的证据提交、证据保全、司法鉴定以及诉讼中的商业秘密保护等作出规定。2019年12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办案指南》,详细规定了行政裁决中的相关证据规则。证据规则虽然存在一定的价值因素,但目的仍在于事实查明以及分配当事人之间的举证责任。目前,我国的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以及技术调查官制度均用于技术事实的查明,但将技术特征划分的规范涵摄于具体的技术单元时,可能得到多个相互冲突的规范事实,此时冲突的关键在于规范适用的冲突而非技术事实之间的冲突,所以不宜继续采用证据规则来无限制地寻求技术特征划分的准确性。
在确定或划分技术特征时,在“相对独立地执行一定技术功能的较小技术单元”之形式规范下,选择不同抽象化程度的技术功能便可能得到不同的技术特征。对于一个主体而言,面对多个相互冲突的规范事实就必须进行行为选择,这正是留待价值推理要解决的问题。将价值推理分为评价推理和规范推理,在技术特征确定的场景下,其大前提给出了技术特征划分的依据——将具有相对独立技术功能的技术单元作为一个技术特征,是一种评价性的价值判断,技术特征划分的争议在于不同主体会提出不同的小前提,即上述可能被不同主体主张的规范事实。这些技术特征确定的不同规范事实虽然均符合大前提的规范要求,但却相互冲突,其背后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判断,从而需要利用价值推理来解决。在异质利益的衡量中,价值冲突存在于两个不同的事物之间,可以在实践过程中加以衡量,运用人类的实践理性对冲突的利益通过比较而加以取舍和选择[34]。对于不同价值判断的行为选择则应结合所处的具体情境,基于实践理由支撑下进行价值衡量,从而实现价值推理的理性化。通过实践理由将事实因素与背后的道德考量连接起来,从而将价值冲突予以显性化,进而在实践理由的冲突中求解行为选择的正当性。在实践理由支持下的制度利益衡量能够从正向兼顾后果,而且关于技术特征确定在利益衡量下也兼顾了规范化与灵活性。因此,当支持某一技术特征确定的价值在衡量中胜出时,则以该技术特征的划分作为确定的技术特征。以实践理由赋予某一技术特征划分方式的行为选择以正当性和规范性,从而实现技术特征划分的理性化和规范化。
5 结语
本文在中英文语境下对技术特征术语溯源,旨在澄清现有理论和实务界对技术特征的认知混淆,并获得技术特征的定义及其所呈现出的不确定性。正是由于溯源部分的知识挖掘和理论分析,本文才可深入导向对技术特征的不确定性和规范化困境的研究,从而剖析技术特征划分和确定中的“失范”问题。本文将事实与价值二分的“休谟问题”引入对技术特征确定的观察,从而识别出造成上述技术特征规范化困境的原因——未能有效地从理论层面分解技术特征确定中的事实因素和价值因素。基于事实与价值二分的哲学原理,以证据规则寻求事实因素的查明,适用价值推理机制下的价值衡量以获得支持技术特征确定的实践理由,从而实现技术特征确定的规范化。在此基础上,技术特征的规范化将减少实务中裁判的不确定性,专利法领域中的“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视角也不再以法官的后果考量为准或是空洞的话术。建立在该领域相关人员所构建之共同体上的社会共识基础上,并在具体情境下完成价值衡量,从而在司法裁判中抑制裁判者的不当后果主义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