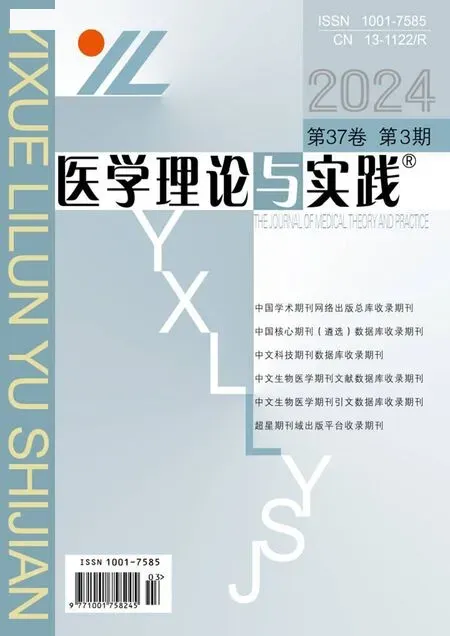医学影像学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中的应用和临床辅助价值*
2024-03-15孙硕辉
孙硕辉 侯 杰 王 娴 阳 韬 张 艳
1 江苏大学,江苏省镇江市 212000; 2 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的诊断是通过RT-PCR进行的,但RT-PCR目前存在三个问题:(1)RT-PCR试剂包的供应跟不上需求;(2)城市以外的社区医院缺乏RT-PCR基础设施以适应高样本通量;(3)RT-PCR依赖于收集的样本中是否存在可检测到的SARS-CoV-2。如果无症状感染者感染了新冠病毒,但后来康复了,则RT-PCR无法识别先前的感染,控制措施也无法实施。而医学影像学对新冠感染具有从诊断、治疗到预后的评估判断,也可识别先前的感染,实施控制措施。COVID-19 疫情发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1],第一次提出将疑似病例中具有胸部影像学特征纳入临床诊断标准,其所推荐的首选影像学诊断检查是胸部高分辨率计算机断层扫描(HRCT,层厚≤1mm)。
CT作为确诊新冠感染重要手段之一已被多个国家认可,但CT与其他医学影像学手段价值比较并未见相关文献报道,系统性综述概括医学影像学对新冠感染的临床指导价值也未见相关文献报道,故而做此综述,旨在阐述医学影像学在新冠感染中的检查手段及其价值,辅助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临床诊疗。
因X 线胸片对检出早期COVID-19肺部病变的敏感度、特异度较低,容易造成漏诊,不推荐使用[2],故本文重点介绍CT对于新冠感染的诊断和外科指导价值,MRI对于新冠并发症心肌损伤的诊断价值[3],US床旁实时评估重症新冠感染患者肺部病变性质、范围的诊断和重症监护的价值[4]以及全身PET-CT成像评估COVID-19肺外表现及全身炎症反应的作用[5]。
1 计算机断层检查
传统X线方式无法提供大量细节,相反胸部CT成像能够提供更详细的肺、软组织和血管的影像信息[6]。Shao等人[7]研究了胸部CT成像诊断COVID-19的灵敏度,该研究表明,有症状的COVID-19患者的胸部CT灵敏度可达57%~100%,无症状者为46%~100%,而RT-PCR仅为39%~89%,因此CT可适用于RT-PCR结果阴性,但临床对患者感染COVID-19的怀疑程度较高的情况。其图像特征可以分为以下四期[2]:(1)早期:包括双肺单发或多发病灶,多位于肺外周或胸膜下,以中下肺的背段或外侧段多见。双肺单发或多发病灶部分呈小叶性或者尖端指向肺门的楔形、扇形,部分呈斑片状或类圆形,多见磨玻璃样密度影或网格状影。(2)进展期:磨玻璃样密度逐渐增高,范围逐渐增大,最终广泛融合成小叶状、带状、大片状密度增高影,其内支气管管壁增厚,支气管血管束增粗,可见树芽征或网格状影,以肺底、非对称性背侧胸膜下楔形、扇形分布多见,少数沿支气管血管束分布。一般无基础疾病的患者多无胸水及纵隔、肺门淋巴结肿大。(3)重症期:双肺弥漫性病变,少数呈“白肺”,以实变为主,常常合并磨玻璃样密度影、空气支气管征、条索影。病灶范围在48h内可增加 50%。双侧胸腔可出现少量胸腔积液。(4)转归期:病变范围较前缩小,密度较前减低,渗出物被部分吸收,肺实变被逐渐吸收消散,可完全消失或残存肺纤维条索影[8]。
目前,已有学者使用深度学习来更为准确便捷地诊断COVID-19。Yousefzadeh等[9]引入了一种基于CT图像的深度学习框架AI-corona,该系统由DenseNet、ResNet、Xception和EfficientNetB0几个CNN变体组成,对COVID-19病例的诊断准确率、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96.4%、92.4%、98.3%,F1-score、AUC分别为95.3%、98.9%。
胸部CT成像还可用于预测COVID-19患者的预后。一项多变量的研究分析表明:铺路石征、支气管扩张、弥漫性肺泡损伤可能提示纤维增生,而胸腔CT影像上特异性节段性血管改变,如血管扩张、变薄或增大,血管管壁呈不规则改变,血管成角,血管环收缩,以上均是COVID-19患者疾病严重程度的预测指标[10]。CT成像在指导COVID-19患者外科手术上也具有重要临床价值,其可为外科医生、内窥镜医生、麻醉师和雾化操作人员提供有效信息。胸部CT成像可以帮助临床医生了解患者感染过程的进展,可以为需要急诊手术的患者提供一个时间框架,使他们能够安全地进行手术和选择最佳治疗措施。因此,建议任何有COVID-19临床症状的患者在某些手术(癌症、紧急腹部手术、内窥镜检查等)之前,除RT-PCR和典型的腹部/骨盆CT外,还应进行胸部CT检查。
总之,CT不仅有助于COVID-19的临床诊断、病情评估和预后进行判断,同时还可以评估感染时间点、感染阶段和持续时间,为临床医生提供重要信息。
2 核磁共振成像
2019全球冠状病毒病大流行(COVID-19)至今仍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引起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多数以急性呼吸道合并症为主,尤以重症病人为主。多个病例报告和研究报告显示[11],COVID-19显著影响心血管系统的患者,通过加重已有心脏疾病患者的心力衰竭程度或使危重患者的肌钙蛋白升高,包括炎性斑块破裂、支架血栓形成、心排血量过高等引起心脏损害的病理生理机制。早期诊断能帮助确定有心脏损伤的患者群体,并有助于预测COVID-19发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或多脏器功能衰竭导致死亡的情况。密切监视COVID-19患者的心脏功能,并利用各种可以预防或限制心血管疾病患者心肌损伤的治疗来干预,可以显著降低死亡率。
评价心肌结构和功能的参考标准是心脏核磁共振成像技术(CMR)。美国心脏病学会、欧洲心脏病学会和心血管磁共振学会一致认为,CMR是一种潜在的有价值的诊断工具,用于COVID-19患者出现心肌损伤和心功能不全的证据:首先,CMR的可重性很高,能起到心室量表的作用; 其次,CMR血液心肌间的差异使之成为“金标准”,对心室功能进行评估;再次,对于超声心动图上显示不太好的结构,CMR允许截面成像;最后,CMR是没有电辐射产生的,其通过多序列成像技术“一站式”评估心脏形态、功能及组织特征,为COVID-19心脏受累早发现、早诊断、疗效及预后评价提供影像学标志物。
CMR表现为左心室和(或)右心室射血分数降低,左心室容积和质量增加,心肌炎症、水肿和(或)弥漫性心肌纤维化。COVID-19心脏病变的CMR分为缺血性和非缺血性损害,缺血性包括心肌梗死和心肌缺血,非缺血性损害包括心肌炎样钆对比剂延迟增强(Late gadolinium enhancement, LGE)[12]和心包炎症。
(1)心肌炎和心肌心包炎:心肌炎是COVID-19心脏疾病最常见的类型。心肌炎的病理特点主要包括心肌组织的水肿、充血、坏死以及纤维化。CMR典型表现为:T1值升高、T2值升高、T2STIR序列高信号。对比剂在心肌血管内和心肌细胞间隙过度聚集导致对比剂的早期增强,随着炎症消退,信号减少,心肌在早期即出现炎症、充血。T2mapping异常与高敏肌钙蛋白呈正相关,可反映COVID-19患者急性心肌水肿状况。COVID-19心肌炎LGE常累及左心室下壁、侧壁及下外壁,而非COVID-19心肌炎患者病灶面积较COVID-19心肌炎患者局限,但心肌水肿及LGE较COVID-19心肌炎患者多。Inciardi等[13]通过CMR对COVID-19患者的心脏病灶进行评估,结果显示COVID-19患者可发生心肌间质水肿、弥漫性LGE、心室功能不全、心包积液、心肌心包炎等病变。(2)心肌缺血及心肌梗死:研究显示,SARS-COV-2可因血管内皮细胞表达ACE-2而感染内皮细胞,造成斑块不稳定或破裂。同时,还可能因斑块不稳定而破裂,导致1型心肌梗死,出现血液高凝状态和全身炎症反应。ARDS、呼吸衰竭引起的低氧血症、发热、心跳过速及败血症导致的心肌缺血加重,诱发2型心肌梗死。(3)心脏扩大及心功能障碍:COVID-19心脏病变严重的患者可发生右心功能紊乱和右心室扩大[14],可能与肺动脉高压和急性肺栓塞密切相关。Puntmann等[15]研究也表明, COVID-19治愈后存在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下降和左心室扩张。由此表明,COVID-19患者心脏受累程度与其预后密切相关,CMR使心肌损害可视化,并将其量化到不同的序列中,可作为敏感无创的影像学检查手段,应用于COVID-19康复者心脏的长期跟踪检查。
3 超声检查
COVID-19重症患者的特点是肺部损害不断加重,引起呼吸衰竭,继发临床循环改变和多脏器功能损伤,因此,控制病死率的关键是重症治疗。疫情一线临床医师因穿防护服无法使用听诊器,COVID-19重症患者因转运风险高而限制CT检查,床旁胸片敏感性不高,故US成为唯一方便且无辐射的影像学检查,具有动态、实时、无创、可重复的特点,肺部超声(LUS)不仅可用于COVID-19重症患者病情评估,还可开展多目标整合动态评估[4]。
COVID-19肺炎患者的组织病理学起始于肺远段,表现为肺泡的损伤与水肿,间质增厚,肺实变。因此,COVID-19肺炎的病理进展非常适用于表面成像技术-LUS,其可以使临床医生确定COVID-19患者相关肺损伤的位置。
LUS主要表现为融合大量B线,部分呈胸膜改变(不光滑、增厚、不连贯)和胸膜下碎片征,伴有支气管充气征,大面积肺实变,少部分伴有胸腔积液,融合大量B线提示肺部大量渗出性病变导致肺充气严重减少,患者可出现严重低氧血症。LUS半定量评分同时结合其他临床指标,可为重症COVID-19的病情评估提供重要参考依据,及时指导临床治疗。当重型COVID-19进一步发展为危重型时,患者可出现严重的低氧血症、细胞因子风暴,继而继发严重感染,发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和多器官功能障碍与衰竭(MODS),进而导致患者死亡[16]。通过对肺部十二分区病灶区域的分析发现,危重型COVID-19患者正常区域面积下降,实变区域面积增加达到90.5%,明显高于重症病人;肺前区、侧区、后区病灶面积逐渐增大,符合ARDS患者肺病理生理特征,重力依赖区肺通气明显减少,可用于评估重症患者肺复张潜力及肺复张效果,有助于指导和保障患者肺保护通气的实施[4]。
因此,LUS可以帮助临床医生判断COVID-19患者肺部病变的严重程度,辅助COVID-19患者氧疗的制定,实现病情演变和治疗效果的持续监测和评估。
4 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成像
炎性细胞中的糖酵解活性增加,使用β-2- [F]氟-2-脱氧-D-葡萄糖 -PET(FDG PET)对于具有全身炎症反应的疾病十分适用,而COVID-19患者常出现全身炎症因子风暴,造成多器官功能障碍与衰竭,常伴有肺外表现和肺外并发症,同时自身免疫缺陷患者(免疫功能低下或高危患者感染COVID-19的患者)的临床症状和影像学特征的不典型也是困扰临床医生的重要问题。
PET/CT在COVID-19诊断患者中最常见的肺部表现为双侧高代谢(75%),实变(34.6%),小叶间增厚(7.6%)。此外,常发现纵隔(27%)和肺门淋巴结累及(19.2%),代谢活动增加[5]。在有免疫缺陷的患者中,也可以通过PET成像绘制COVID-19的急性感染过程[17]。
COVID-19可导致脑、胃肠道、心脏和肾脏等肺外并发症。全身PET/CT可以在一次采集中发现身体其他部位存在的额外代谢活性病变的潜能,这是其独特的优势。Karimi等[18]研究表明,在与COVID-19相关的嗅觉丧失中,眼窝额叶皮层活动减少,这表明神经功能受损是嗅觉丧失的潜在病理,其原因可能为SARS-COV-2的神经趋向性。zou等[19]报告了COVID-19的骨髓吸收,类似于此前关于非人类模型中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报告。这表明,FDG -PET可以对COVID-19的终末器官损伤进行评估。
由此表明,FDG PET/CT在监测COVID-19疾病活动度、肺炎的病理反应评估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PET分子显像可以在治疗肺部炎性疾病时将肺部炎症量化,也可以为免疫缺陷患者提供诊断依据。更重要的是,全身PET/CT成像为评估COVID-19的肺外表现提供了独有的价值和临床指导。
5 结论
本文从CT、MRI、US、PET/CT四种成像技术的角度,系统性综述概括当前主要的几种医学影像学手段对新冠感染的临床指导价值,有利于提高临床医生对新冠感染及其并发症心肌损伤的诊断,并实时评估重症新冠感染患者肺部病变性质及范围,指导临床医生面对不同病情患者合理进行治疗方式的选择,辅助COVID-19的临床诊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