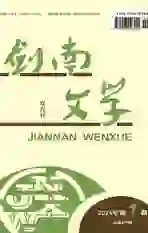斑驳的影子
2024-03-12杨道
一
我并不熟知一个人命运的确切构成,但我相信战争肯定是最黑暗的一种塔罗牌,它代表着毁灭与罪恶。那些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的人是塔罗牌里计算好的,死神挥着镰刀,开疆辟土,海平面像一扇缓缓阖上的天窗,把幸存者埋进沙地里,装扮成无骨的幽灵,在白天里重复着黑暗的勾当。
几十年来,这些场景在我的梦里反复出现,显然是用来适应我九十岁高龄的记忆。
在马来西亚生活了二十多年,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岛上。到岛上的第一天,日本兵把抓来的人都推到海滩上,我看到的眼睛鼻子都熟悉,都是在马来西亚生活的华人。日本兵端着刺刀,用他们绑着腿的右靴子狠狠地踢我们的膝盖,把我们踢跪在地,亮晃晃的刺刀从我们胸前划过,嘴里在吆喝着什么。
一九四三年的夏天,阳光很毒辣,我的腿被日本兵的靴子踢瘸了。我不想跪着,尝试站起来,但没有可以支撑的东西,我一动就摔了下去。一把锃亮的刺刀横在我脸上,从额头往下比划着,我闭上眼睛,等着死亡来临。想起小的时候打架,有一次被别人往鼻子上狠狠地揍了一拳,血流过我的嘴巴,滴到村里的土路上,我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揍我的人吓坏了,落荒而逃。
刺刀没有往我胸口扎下来。我睁开眼,旁边一个羸弱的男人晕倒了,日本兵把他拖出队伍,往海里一扔,刺刀挑着这个男人的衣服。我远远地听到布帛裂開的声音。两个日本兵接着把海里的男人拖上岸,一人架着男人的一条腿,古人凌迟的形状。惊醒的男人挣脱了,没命地往海里跑。两个日本兵也没追,只是闪到一边,兴奋得嗷嗷大叫。这时一直站在我们面前看热闹的日本军官从腰里掏出手枪,把胳膊端平,闭上一只眼睛向奔跑的男人瞄准。枪声响了,没打中,打在华人身旁的沙砾上。飞起的沙砬像夜里的礼花,晶亮亮的。日本军官狠狠地骂了一声,往前走几步,端起胳膊,又开了一枪。“砰”,这一次,男人应声倒地,他在倒下的瞬间回头看了一眼,像只夜里的麻雀。
我的腿在打哆嗦,我没见过枪,不知道从背后把人打死之后,死人的眼睛还能从前面鼓出来。
夜里,日本兵在他们临时搭建起来的木屋里喝酒,被抓到岛上的几个年轻女人被他们推了进去。木屋里有火光明明灭灭。我们被隔离在木屋的篱墙之外,一整夜都听见日本兵杀猪一样的嚎叫和女人凄厉的哭声。有几个青壮男子朝木屋冲过去,愤怒地喊着:“天杀的,我要杀了你们这帮鬼子!”把守在篱门前的日本兵端起胳膊,枪响了,“呯呯呯……”这几个刚才还充满愤怒的年轻人手高高举着,往前一扑,就一动不动了。
到了后半夜,女人的哭声渐渐小了下去。我想她们都哭累了吧。木屋外的华人就在沙滩上坐着,看着那几个死在木屋前的年轻人。有细细的哭声在人群里呜呜地响,声音低沉,像是从沙滩里发出来的,悄悄地在我脸上飞来飞去。我听得心酸,眼泪都流了出来。周围没有一点响动,海潮也静静的,只有这一个声音,长久地在人堆里转来转去。月光惨白,照得人一心的寒。
天亮时,哭声停了。日本兵从木屋里扔出几具尸体,我们探头一看,昨晚被推进木屋里的几个女人全死了,被日本兵扔出来后,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旁边是昨晚被日本兵打死的那几个青壮男子,头朝下卧着,身上盖了一层薄薄的沙土。我们都远远地看,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敢去给他们收尸。
我们的肚子是空的,心也是空的,没有希望,只有无穷无尽的死亡。华人的命在日本兵的眼里,甚至不如一只蚂蚁。日本兵随意在马来西亚的街头抓走当时下班回家或者在做生意的华人,妇孺和老翁也不放过。他们把抓到的人双手反绑,扔上各色各样的罗厘车,然后集中一起送到了这座荒岛上。
日本兵毫无人性,杀人花样百出,并且以杀人为乐。他们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在岛上,他们每天只需要少许的食物就能过活,他们的腰间挂有藏着白米的铁盒,再配些大豆和咸鱼,也就足够了。在岛上,日本兵无事可做,每天醒来,他们就在空地上进行劈刺操练,岛上的华人成了他们操练的靶子。每刺一次,他们都会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呐喊声。刺中要害的人死了,直挺挺地躺在沙滩上。有不听命令的,日本兵就把他反绑起来,逼着他向海边走,在他行走过程中,日本兵用机关枪对着他扫射。被射中倒下了,日本兵要上前确认,用脚把死去的人踢来踢去,然后刺刀戳下去,直到看见血汩汩地喷出来。
日本兵不打算埋葬他们杀死的那些华人的尸体,任由海水把海滩上的尸体冲上冲下。有一些尸体开始腐烂了,发出酸臭的霉味。海面上浮着一层白白的泡沫。我们说是那些亡魂显灵了,再从海里汲水时便战战兢兢的。
岛上的尸体越来越多,活着的华人越来越少。到这时候没有人会认为自己能活下来,随时做着被刺穿肚膛、抛尸荒滩的准备。
事实上,是之前那个被杀男人鼓出来的眼睛救了我。经历了那么多恐惧和绝望,我达到了一个可以鸟瞰这个荒诞世界的高度。
战争的进程如何,没有人知道,我们在岛上,天天面对的是日本兵的机关枪和亮晃晃的刺刀。还有一批又一批的华人被反绑着送到岛上来。
一天夜里,我在一批新抓上岛的人群中看到了移居马来西亚十多年的舅公。
后半夜,日本兵睡着了,舅公悄悄地挪到我身边。舅公被砍过的膝盖流血不止,后来就生了奇臭的蚀烂症。他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亦喜亦悲,眼睛也忽睁忽闭。他使劲地攥着我的手,嘴大张着,仿佛痒丝丝地要抓捞什么。
被抓之前,舅公正在自己临街的米铺里卖米。日本军队占领马来西亚以后,粮食越来越缺乏,一些走投无路的人为了活命开始抢劫。那天舅公的米铺里也来了三个抢米的人,这乱世里活命是唯一的主旨。舅公没敢阻止,只是静静地看着。后来日本军队过来了,一阵胡乱扫射,把那三个抢劫者都杀死了,把他们的头砍下来,并排悬挂在舅公米铺门楣上。
日本兵以搜查为名,进入舅公铺子内,把所有的白米都搬走了,舅公身上的钢笔和手表也被日本兵生生夺走。舅公本能地大喊“救命”,日本兵拔出刺刀就砍了过来。舅公闪了一下,刺刀砍到膝盖上。这一次,这个日本兵没有再砍第二刀,舅公活了下来,被五花大绑着送到了这个岛上。
舅公带来的消息让我绝望,被看成救星的盟国军队并没有显出多大的威力,当时日本军队在海上节节胜利,不久之后,日军在陆上的胜利超越了海上,马来半岛与英国在新加坡的庞大海军基地被轻而易举地征服。
舅公看着日本军队的木屋,叹了口气:“英国人应该感到悲哀,这是他们在军事史上蒙受的奇耻大辱。那些英国军队士气低落,一被日军围困就弃甲而逃,想要战胜是难了,等死吧。”
二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三日,炮声响了,是从海上传来的。一炮一炮之间,我们看到了远远驶来的船只。早晨的阳光渐渐散开,岛上活着的华人都向海上看去,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桅杆上挂着的骷髅旗。舅公兴奋地喊了一声,说“开仗了,开仗了”。谁都不能够相信,我们会遇上海盗,然而毕竟是要开始另一场战争了。我们也许能在日本兵和海盗开仗的间隙逃离这个死亡岛。
岛上的日本兵迅速地列好了队,步枪上的刺刀在阳光下亮晃晃地,刺得人眼睛生疼。但岛上的日本兵只有步枪,没有炮的日本兵在海盗面前显得无力了。日本兵的枪声“突突”“砰砰”地响,海滩上扬起一地的沙粒。有几颗子弹落到海面上,卷起一柱柱的水花。海盗的船只还在往岛的方向靠近,船头架着高射炮,流弹不停地飞过来,尖锐地转换着几声长叫,“吱呦呃呃呃……”,在我们头顶上绕了一圈,然后“砰”的一声落到岛上。那一声声尖锐的长叫撕裂了空气,撕碎了沙砬,撕毁了神经。阳光被斯扯成一条一条的,在岛上轻飘飘地挂着。日本兵搭建的木屋被炸裂了,木头碎屑落了一地,在风中卷成浓烟混淆视线。风里同时飘着无数剪断了的神经末梢。
岛上的华人都没命地往海盗船的方向奔跑。一具具横着的尸体腐烂后,岛上的空气里弥漫着酸臭的霉味。即使去了海盗船上也是死,但总归是死在海里的,干干净净。
身后的枪声越来越紧。中了弹的人嗷嗷乱叫,和受伤的野狼没什么两样。嗷嗷乱叫的声音越来越密,我往后一看,突然扑倒在地的华人起先是一个一个的,没多久就连成了一片,像北方女人纳的鞋底一样,一层叠着一层。那些凄厉的叫喊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心里一阵一阵地冒寒气。
迎面的炮火逐渐猛烈。好在岛上的木屋才是高射炮注意的焦点。我拉着舅公在浓烟里奔跑,海盗高射炮的炮弹与日本兵步枪里射出的子弹似乎在我的头顶上短兵相接了,“轰”,我眼前是炸弹爆炸后猝然闪烁的火光和弥漫整个世界的黑烟。
我只道自己没命了,谁知还活着。一睁眼,只见满地焦黑的沙砾,满地横着的尸体,满地的太阳影子。舅公死了,死了还紧紧地抓着我的手。舅公睁圆了眼睛,脊背上有一滩血,那地方又湿又烫,我用手一摸,血还在流,从我指缝流出去,渗到了沙土里。我豁出去了,挣扎着爬起来,再跑。
又听到“轰”的一声,我感觉自己像一座被台风肆虐过的废墟一样倒下了。留在我记忆中最清晰的印象仍旧是那一团火光和黑烟。
醒来时,我躺在海盗的船上。我面前是一张西方人雕塑般年轻英俊的脸,这和我想象中胡子拉碴的海盗形象是完全两样的。看到我醒过来,这张英俊的脸转过头去,用英语对着他的同伴兴奋地报告我活着的消息。自从买了船来做生意后,我就学会了很多种语言。年轻人看我听得懂他说的话,有些激动,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端来一个大盘子,是一大块烤焦的鸡腿和一大块面包。
我开始狼吞虎咽。这是我被日本兵抓到岛上后近一个月来吃到的唯一有质感的食物。我吃着吃着就哭了。半个多月喝海水,吃生的东西,我的脸都吃肿了。到这时候死活已经不重要,能在死之前吃上鸡腿和面包也就够满足了。
因为我会说好几国的语言,海盗们決定留我在船上当翻译。我活了下来。
我开始做噩梦。梦里都是那耀眼的火光和浓浓的黑烟,还有岛上横七竖八的尸体,它们仿佛我身体的某个部分一样伴随着我。每一次醒来,我都泪流满面。有时我强烈地渴望把它们遗忘,但它们一到夜里就像扭曲的蛇,把我整个人都箍起来,几乎要把我整个吞噬。第二天早晨起来,我的眼睛也总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挣扎适应。当初爆炸后的黑烟和舅公睁圆的眼睛在我眼前久久散不去,它们驻扎在我的瞳孔中,就像黑夜里的噩梦,对我永无止境地进行纠缠。
后来我还常常梦见我的老母亲。她还是当年在渡口时给我送行的样子,慌里慌张的,没了力量支撑的身体像筛子掉到了地上。关于母亲的梦总是固定的场景,除此以外,我什么也看不见。醒来时,我感到寒冷和恐惧。我的眼睛大睁着,但什么也看不见,世界呈现的是一片黑暗。我担心母亲是遇到劫难了,我感觉自己身上的某种东西在破碎,锥得生疼。我想我可能也要死了,昏昏沉沉的,生命从那个破碎的缺口悄悄地流出去。
我还想到了村庄里那个娇小可爱的女孩,不知道她嫁人了没有,是不是过得很幸福。可是我想起这些时便觉渺茫,原本就隔了千山万水,现更如同隔世。从荒岛上日本兵的刺刀下逃生,累累荒尸切断了我所有温暖的记忆。现在的这一段,看海盗们有时对一些“猎物”残忍的屠杀,我便觉得自己不在原来那个世界上,更与过去的村庄毫不相干。
三
和海盗在同一艘船上相处了五天,没有人问我的过去,我就像他们抢来的一个物件被抛掷在一个固定角落。海盗们天天喝很多的酒,放声狂笑。船上没有女人,喝了酒的海盗们,常常把衣服脱光,赤身裸体地在船舱里走来走去。吃饭的时候,那个有着雕塑般脸庞的英俊年轻人会在盘子里装满各种食物给我送过来。
在远古的传说中,海盗们往往被描述成英雄般伟大,生活也充满刺激和浪漫,但我看到的海盗并非如此,冒险几乎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他们的生命大都短暂,一只脚踏进棺材里,一只脚撑在船头桅杆上。
那个英俊的年轻人会在半夜里找我聊天。他告诉我他叫杰斯,在还没开始学会记忆的时候,就被一群海盗抱走了。后来,有一些海盗说,他是他们在一次洗劫英国商船时的战利品。
杰斯在海盗船上长大,船上的海盗换了很多茬,杰斯把每一个人都叫父亲,每一个人听到小杰斯的叫唤时都特别兴奋,掏出他们最贴身的礼物,挂到小杰斯身上,大声嚷嚷着抱起小杰斯狠命地亲。船上的海盗们没有机会娶妻生子,但人类最朴素的情感仍然深植于他们的生命当中,和常人并无不同。
小杰斯最初叫的第一个父亲是海盗们的首领,是那艘船上的船长福森。福森船长年纪有些大了,原来也是一个普通的英国商船上的船员,几个人合伙做生意,在海上航行了几个月,福森得到的分成最丰厚,有很多的钱和珠宝。然而,回到家时妻子已经成了邻居那个杂货店老板的妻子。这个可怜的人失魂落魄回到船上,两个生意上的伙伴陪着喝酒,喝着喝着,这两个伙伴的脸变绿了,眼露凶光,接着福森感到自己的后脑勺被一个坚硬的东西重重击了一下,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过来后,当时还是年轻船员的福森发现自己被丢在一艘海盗船上,他们自己的船被海盗洗劫一空,那两个同伴被海盗打死了,扔了海里。被同伴们抢去的珠宝和钱海盗们没有拿走,还装在那个简陋的小木盒子里。海盗们把它随意地丢在福森的脚跟前,像是扔去一袋毫无用处的废铜烂铁。
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个年轻的英国商人成了海盗。因为知书达礼,福森很快得到了船上海盗们的尊敬,他们甚至推选他出任船长,给了他这艘船上至高无上的权力。
我从杰斯嘴里听来的关于福森的故事像一部彩色电影,和当年的海南毫无瓜葛,一点点可以联想的空间都没有。当福森们在海上掠劫的时候,我也许刚刚学会骑着家里的那头黑猪去上学,或者站在父亲面前背《三字经》,中国的历史就这么在我乏力的背书声中沉沉老去。
福森当了船长以后,这艘海盗船去过很多地方,美洲的加勒比海、西太平洋、印度洋都去了,但当年的这些路线已经不似十八、十九世纪一般属于海盗的黄金地盘,福森和他的海盗们也少有能劫到那些丰厚的“宝船”。后来海上的商船拉的金银珠宝也少了,烟草、丝绸、咖啡等都成了当时商人最为喜欢的物品。那个时候的欧洲男人,对于烟草和咖啡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喜爱,而女人则是对中国的丝绸情有独钟。
福森和他的同伴们后来都成了生意场中的绅士。他们从商船上掠劫来大量的货物和钱财,钱财大家就地分了,长年在海上漂,海盗们的生命都只争朝夕,对于钱财,大家都没有过分的欲望,不会因此对同伴产生杀机。掠劫的财物达到了一定数量,海盗们就把船驶回自己的据点,然后打扮成商人的模样,通过另一途径把货物转手卖出去。这些货物都珍稀,动物的皮毛、烟草、棉花、胡椒、糖酒、咖啡等,海盗们总是能狠狠地赚上一笔。
福森后来老了,能自然老去的海盗极少,福森就几乎成了海盗们眼里的上帝。海盗们常年在外航海,除了掠劫,一生就只有一件事情可做:生存在天空与浩瀚大洋之间,与狂风,与敌船,与命运独立作战。无论你愿不愿意,来到海盗的船上,就意味着要征战四方,大洋上硝烟弥漫。对于喜欢冒险的人来说,海盗的生活也许是极富诱惑力的,世界版图好像会被自己重新描绘。在海盗的历史上,海盗船队有着许多传奇,是除了古代国与国的战争之外最激荡人心的历史记忆。
但老去的海盗福森对于从英国商船劫来的小杰斯没有说这些。他用掠劫来的财物换来许多书,在没有敌情的时候,老福森就教小杰斯认认真真地读书、认字。老福森的床头一直放着一本《圣经》,每天海上出现第一缕阳光时,老福森就把小杰斯叫起来,教他诵读《圣经》中的某个章节。到了夜里,临睡前,老福森会要求杰斯和他一起,把手放在胸口,背诵一遍早晨读过的那些段落。杰斯说,老福森在诵读《圣经》的时候,脸上安宁祥和,似乎沉浸在某种美好的回忆当中。
老福森说,他希望杰斯记得自己并非出身海盗,而是英国绅士的后代。老福森也许读过很多很多的书,学识渊博,到了后来,他会给杰斯讲述关于海盗船队的传奇、冒险和征服的历史,但更多的时候,老福森讲述的是英国绅士的故事。老福森擅长演绎,表情丰富,杰斯說他倾听的过程就像在翻阅书本,一页一页古老的历史开始被唤醒,他在不由自主中就踏上了海盗们经历过的那些传奇之旅。而对于老福森说的关于英国绅士的部分,他的记忆一直模糊,没有具体的印象。因为从小生活在海盗船上,天天面对着死亡,对于守时、谦逊、悲悯、谨慎、保守秘密、谈吐优雅等诸如此类关乎英国绅士的品质,杰斯觉得过于飘忽疏离了,想起来时都茫然,没有踏实的安置。
在杰斯长到十五岁那一年,老福森死了。老福森是投海自杀,在发现自己患了疟疾之后,老福森也许就策划了这次死亡。那天夜里,他和往常一样,临睡前给杰斯诵读了《圣经》中的一些章节,然后微笑地看着杰斯入睡。杰斯做了个梦,醒来时却到处找不着老福森。船上的海盗们都知道,老福森已经死了,大部分海盗最终的结局都是如此,来时不问出处,走时了无痕迹。
四
杰斯的讲述让我回到了无数巨舰在世界大洋上熙熙攘攘的时代。那样的历史我并不熟悉,我小时候熟读的《三字经》里没有切近的记载。这些关于人类探索求知的历史,承载着生于大海死于大海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往而不返,无论商人、海盗或水手。海盗天天都要遭遇死亡威胁,最可怕的不是剿灭海盗的军舰,而是飓风和疾病。飓风呼嚎,再结实的船只最终也不过是几块木板,风过木板就沉了海底,直至朽烂也不一定被人发现。而疾病更甚,与船上的人如影随形,长年在海上漂流,淡水极度缺乏,蔬菜和水果几乎吃不着,每天都要和发霉的面粉、吃腻了的咸肉打交道。杰斯说,他有时看到那些咸肉就想吐,但不吃活不下去。更恐怖的是,坏血病流行,而船上没有任何医疗条件,生活状况极其恶劣。杰斯说,老福森的死让他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它并不像岸上的人想象出来的那么浪漫,而是沾满了死亡的腥味。
老福森死后,杰斯学会了喝酒。船上的酒只有一种,是长年依附于冒险家身上的朗姆酒。杰斯说在海上学会喝酒不是什么坏事,海盗们都喜欢,天天当饮料喝。
在很多文学作品里,朗姆酒充满了野性和浪漫,它充当过德国哲学大师叔本华宣扬唯意志论的道具,美国文豪海明威当年在哈瓦那出海时还以此来换取船票。它甚至在100年前就已成为古巴革命军对抗西班牙殖民者自由呼喊的代表。
我并不是个好酒的人,但对于朗姆酒我充满兴趣。在和杰斯一起喝酒的时候,我能暂时地忘却自己的将来和生死。而且朗姆酒能消毒伤口,能驱寒,还能壮胆。朗姆酒喝到兴浓的瞬间,整个人也会变得野性,充满了活力。这是一种具有冒险精神的人都喜欢的酒,有着明显粗犷的男人的气息。
五
我最后一次和杰斯喝酒时,我们遇上了日本军队的船。那时候天已黑了,三艘日军的船把我们围在中间,而曾经和我们并肩前行的另一艘海盗船却不知去向。
这是一场异常惨烈的战斗,海盗们都悍不畏死,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狂野,只有我和杰斯抖抖瑟瑟地躲在船舱里。日军的武器过于先进,枪炮声密集。海盗们不能再遵守古老的传统,在船头搭上跳板,然后依次上场单挑,但他们依旧像以往的每一次交火一样,把衣服脱了往海里一丢,赤裸着上身,发着粗野的狮吼,迅速地投入了战斗。
枪炮声持续地与海风纠缠,海和天空似乎都要被撕裂了。我蜷缩在船舱里,用被子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了起来。杰斯什么时候跑出去的,我一点也不知道。他必须这么做,在海盗的传统中,放弃战斗资格的人与死者无异,从此连家人都会忽视他的存在。他们只能忘情地享受战斗的酣畅,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脚下的跳板浸透着他们祖辈的鲜血,自己的后代也会落脚在同一个地方。
这艘船上的海盗最终都死了。我被日本士兵从船舱里揪出来的时候,看到甲板上到处都是尸体,血流了一地,潮乎乎地发出燥热的恶心气息。
我的脸和额头被日本兵用刀划了几下,血一滴一滴地落到甲板上。我咬着牙忍着疼痛,不出声就有可能存活。我一定要活下来,一定要寻找机会把这些毫无人性的日本兵都消灭掉,哪怕只能杀死一个,也是值得的。
四五个日本兵因为我没有嚎叫最终放弃了他们的这场死亡游戏。后来怎么到了底层的船舱里,我已经不记得了。从额头滴下来的血模糊了我的视线,我的手被扎扎实实地反绑着,像个球一样被日本兵踢来踢去地取乐。
在底层的船舱里,人很多,都是被日本兵随处抓来的华人和马来西亚人。我听到了久违的汉语,甚至还有人在说海南话。那一瞬间,死亡似乎离得有些远了。我兴奋地用海南话大声呼喊。有人捂住了我的嘴巴,船舱里变得死一般地寂静。我知道我闯祸了,因为过度兴奋,我的叫喊声惹来了日本兵,他们持着枪,对着我们作扫射的姿态。在这艘船上,我们就是日本兵脚底下的蚂蚁,随时兴起,就可以一脚踩死,尸骨无存。
死亡的气息越来越重,日本兵却突然收起枪,离开了。
六
这天晚上,我胸口很闷。从额头滴下的血迹干了,我看得见船舱里的人脸上的伤痕和愁苦,一个个在浓重的咸腥味里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我算计着自己活不了几天,也许明天就轮到我去死了。几年来在枪炮和尸体堆里混,我倒不怎么怕死,只是觉得自己死得不明不白实在冤,我可怜的母亲和刚刚过门的妻子都不知道我死在何处。
在我旁边把头压在我腿上的志方,也是从海南过来的。他在马来西亚没待到一年,日本兵就来了。他的小货铺被冼劫一空,他自己也被日本兵用刺刀抵着背赶到了集中营里。后来集中营里的华人都被日本兵用机枪扫射死了,不知道为什么他却活了下来。被丢到这艘船上以后,他一直觉得饿。船上的日本兵有时候会丢一些生米进来,我们就用生米沾着海水吃。吃了几天的生米,我们的脸都肿了,腿脚发虚,志方伸出舌头舔舔嘴唇,对我说:“我想吃家乡的米粉了。”
志方在这船舱里已经被囚禁了近一个月,这一个月里没有接触过一丝阳光。我心里有模糊的哀戚,一丝不挂的黑夜令人惊慌,陆地上的空间都被隐藏了起来。我不是个喜欢冒险的人,在经历了这么多恐惧和绝望之后,我达到了可以鸟瞰一切苦难的高度,我的太阳穴附近感觉到了命运的呼吸。
第二天中午,我们被集合到船头甲板上,整整齐齐地坐着。原来船已经靠岸了,我们活着回到了马来西亚。我们自动排出了五个队形,一个挨一个地上岸。没来得及看一眼岸边有没有吃的,就又被日本兵塞进了一个黑屋子里。
有一些新抓来的华人也被抓到黑屋子里,他们带来了一些令人振奋的消息:战争的局势已经开始改变,日本开始节节败退。但也因为如此,强弩之末的日本兵更加疯狂地肆虐控制在他们手里的华人。
黑屋子里一百多个被日本兵“验证”出来的华人被这群野兽用钉子钉在了黑屋子的墙壁上。那两天,黑屋子里哀嚎声此起彼伏,钉在墙上死去的华人面部表情都是扭曲的,眼睛都大睁着。整个黑屋子泛着阴森森的冷气,活着的人像是来到了阴曹地府。这种惨状在我后来的生活中成为永远的恶梦,周期性的,隔几天就要爆发一次。
志方也被钉死了。我因为会说马来西亚的语言,逃过了这一劫。
1945年8月15日,我们从黑屋子里被放了出来,据说受降仪式也是在那天举行的。
我直奔马来西亚的家里。院门敞开,几个木椅子横倒在地板上,卧室的木门被劈成了两半。我的妻子不见了,屋里空空荡荡的。我喊着妻子的小名,跌跌撞撞闯进妻子的父母家里。
老人的家也被洗劫一空。看到我,两位老人就呆住了,岳母颤颤巍巍地走到我面前,两条腿僵住似地站在那里,随后身体往下一倾晕倒了。我知道妻子一定出了事,就拼命地喊着:“妈妈,你快醒来。”
喊了几声,岳母的眼睛睁开了,岳父却吓得瘫在了我身上。
我被抓走后的第三天,妻子就知道凶多吉少,日本兵持着刺刀四处晃悠,烧杀淫掠,没有什么是能够幸免的。因为担心被强奸,在我被抓走后的第五天,妻子给岳父岳母送来一笔钱,高高兴兴地和老人一起吃了饭,当天晚上回家后就上吊自杀了。
那年秋天,我成为马共组织的一名地下交通员。为了方便与组织联络,也为了供养岳父岳母,我开了一家小餐馆。有一天,我接待了一位特殊的顾客,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脸色苍白,手在发抖,两只脚看起来有些局促,以致站立的姿势像失去支撑的枯木,而他的神情,仿佛永远处于一种极度焦虑的状态中。
他說他叫陈卫,是我的同胞,很早就离开了家乡,在新加坡一家罐头厂里打工,直到日本兵进驻,新加坡沦陷。幸亏他命大,后来从日本兵的枪子眼里逃了出来。他的一口闽南音和类似的经历让我相信了他的陈述。
我把他安顿在店里当个帮手,这样他至少不用颠沛流离。
1948年,战争结束后,马共开始转入反殖民运动,发动了罢工和骚乱,与英国当局矛盾激化。这一年,英国殖民政府推行的马来西亚联邦宪法对非马来族群很不利,因此遭到以华人为主的马共的强烈反对。这一年的6月16日,马共在霹雳和丰的一次行动中杀死三个欧洲种植园经理。这个事件成了英国殖民政府与马共之间斗争的导火索。英国殖民政府由此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
我的身份一直对外保密。组织有秘密会议要在店里召开时,我就提前一天把陈卫支开。陈卫有时候会显得有些迷惑,但他从不探问。这一点让我很是欣赏,同时也放心许多。
时光流逝,陈卫在店里一住就是一年,这其间我们相处和谐,我把他当成了来自家乡的亲人。我陷在对家人愈来愈强烈的思念当中,因为我知道了很多冒险的行动,我了解自己一直处于危险之中。但我无法预知敌人要采取的行动将如何发生,我能清晰地想象出随时可能到来的打斗、抓捕——有人如飓风一般抓住我,而我则像木偶一样,在那些强硬的手里被扭来扭去,衣服撕得咔嚓作响,眼睛被硕大的拳头直击,肿得什么都看不见,头晕目眩,最后,被狱卒的铁腕紧扣,投入大牢,严刑拷打,甚至被送上断头台……我不希望牵连我的同胞们,我算不上是为人民而死的国家英雄,我只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如果不幸死了,那也只是为了我自己而死,为了我自己心中的信仰——那个善与真与美的世界。
这一年的冬天,我生了一场大病。在卧床疗养的这个万物萧瑟的季节,我心情有些灰暗,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撑得过去。早年经历的那些逃亡生活,严重影响了我的身体健康,陈卫让我不用太操心,自己就想好好放松一下,跟人玩玩纸牌,店里的活,都交给他,他能经营得很好。
这一年来,我发现陈卫做生意的能力要远超于我,把店交给他管理,我也乐得讨个清闲。
1949年1月20日这一天,是我们中国人节气里的大寒。早晨起来,我就觉得心里闷着,胸口鼓起,仿佛鼓起了那些痛苦的过去。一种不祥的预感拽着我。我决定去店里看看。
天色尚早,店里还没开始营业。我自己开了门进去,坐在黑暗中,我一边喝着苏打水,一边揪心而忧伤地回忆过去。我痛惜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瞬间。
天色渐渐亮了起来。阳光从窗叶的裂口透进店里,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影子。这其实是一个明媚的清晨,路边高耸的树上有鸟儿啁啾。店里进来三个人,是英国殖民政府的人——我的马共地下交通员的身份暴露了。
直到我被带走,日夜值守店里的陈卫都没有出现。我隐隐地明白了什么,我心里的愤怒和悲哀,比当年被日本兵折磨时更甚,因为他是我的同胞,我倾注了我所有的悲悯和亲情。
我又被关进一处密闭的空间里。在我进来之前,这里已经关了五个人。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话的欲望,这些年因为见过太多的死亡,我对于人性之恶,不再像从前那样,随随便便从哪个人身上都能获取到一种高度浓缩、未经稀释、满满地装在一个大瓶子里的密封起来的恶。
当我重获自由时,时光已经过去了十年。陈卫把我的小餐馆变成了一个享誉当地的星级大酒店,法人是陈卫的名字,他也自然成了当地新闻里举足轻重的著名商人和企业家。他有时候会参加当地一些电视访谈节目,西装革履,正襟危坐,从一些迂腐的诡辩者那里学一些冒牌格言,转手塞给电视机前的观众。他试图表达出让人类幸福是他至高无上的理想,但他最终塞给人们的,是没有真实内容的空壳。然而,他凭着这些虚假的智慧,仍然赢得了一众的追随者,或者,更确切地说,他自己就是大众。
我决定离开这片土地。因为每一次从报纸或者电视里看到他,我的心里就充满仇恨,生活几乎被仇恨淹沒了,连起码的快乐也没有。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头脑清醒,手脚自由——如果这片土地需要的是和我不一样的人,我就该甘心承认自己对这片土地毫无意义,离开也算是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常常想到普罗米修斯,他盗了天火,却被发怒的诸神弄瞎了眼睛。这个事件背后的真相很可怕,没人敢去寻找真正的答案。世间万物,总是各有其妙,天空再辽阔,每个个体也都是孤星一颗。我们站在地平线上,铆足劲仰望,终究只能窥得一些模糊的星辰,一些无从知晓的脚注。所以,我要踮着脚尖离开,向曾经的梦想告别,梦想一个秩序被重建的世界,同时,也是梦想按自己心意来重建一个世界。
我无法抑制回溯过去,那是一部关于苦难的编年史,而非一首集合浪漫情怀的交响乐。
杨道,中国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天涯》《北京文学》《青年作家》《四川文学》《诗刊》《扬子江诗刊》等,出版散文集《终古凝眉》、史地集《珠崖碎影》。获南海文艺奖文学奖、晓剑青年文学创作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