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爱欲:《理想国》与《会饮》中的两种灵魂图景
2024-03-02田书峰
田书峰
中山大学 哲学系,广州 510275
一、引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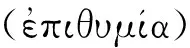

柏拉图在《会饮》和《理想国》中给我们提供了两种关于人的灵魂结构的图景或解读方式,前者给我们塑造的是一个向着美本身或美的理念不断攀升的爱若斯的形象,因为爱若斯对美的欲求只有在对永恒不变的美的理念那里才能得到满足,后者为我们所描绘的是一幅关于灵魂的不同部分或力量之间的冲突画面,理性有被激情和欲望奴役的可能性。我们的问题是,这是否为两种互相矛盾的灵魂图景?我认为,这看似彼此不相容的两种灵魂图景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将柏拉图的道德心理学呈现出来,《理想国》关注的是城邦与个体的正义如何得到实现,自然地会更加突出灵魂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而《会饮》所要揭示的核心问题则是爱欲的本质和爱欲的真正对象,呈现出来的是爱若斯向着美的理念的攀升图景。攀升图景和冲突模式并不能被视为柏拉图的两种实践哲学,而是对同一种实践主题的两种不同描述或展示方式:即欲求的秩序。无论在《理想国》还是在《会饮》中,柏拉图都强调只有理性的统治才符合正义的要求,因为只有理性才能把握到那真正意义上的善,而对美的理念的沉思和静观也是理性欲求的实现。对此,首先,我们需要理解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之所以要对灵魂进行三分的目的和意义,因为学者们对灵魂的三分并没有什么异议,但对柏拉图是否认为存在着一种非理性的、与善完全分开的或独立于善之概念的欲望有着极大分歧;其次,我会对柏拉图在《会饮》中借狄奥提玛女祭司所说的爱欲向着美本身的攀升进行分析,例如爱欲攀升的动力是什么,为什么爱欲的终极目的必然是超验的美的理念自身而非尘世间的可见的美之事物;最后,借助于对柏拉图所说的心灵结构和爱欲的本性的理解,我希望能够揭示出人的欲求的逻辑和爱的秩序。
二、理性与欲望的角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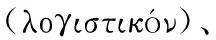
柏拉图在《理想国》435a-439e中使用了不同的论证来证明人的灵魂内存在着不同的部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相反者原则”(the principle of opposites)。苏格拉底在《理想国》436b中这样说:
很明显的是,同一事物不会在自身的同一部分中,且就同样的事物来说,并在同一个时间内进行或承受彼此相反的东西,因此,如果我们发现这种事发生在灵魂中,那么我们就会说,我们不是在与一个事物而是与多个事物打交道。

因此,我们宣称这是两个彼此不同的部分不无道理,我们将会把灵魂借以进行推算的部分称为理性部分,而把那个用以进行爱欲、感觉饥饿和干渴并通过别的欲望而变得兴奋起来的部分称为无理性的欲望部分,而且常常伴以一定的放纵和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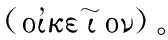
三、理性的奴役
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四卷中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充满冲突和斗争的心灵图景,既然理性、激情和欲望构成三个彼此独立的灵魂部分或动力来源,那么,这三个部分都可以根据自身就能引起行动,所以这种灵魂三分的直接后果就是,理性可能会被其他非理性的部分所奴役(enslaved)。当然,按照柏拉图的理解,因为人借助于理性部分能够认识事物的真相,理性根据自身而不需要借助任何其他来源就能够欲求真理和智慧,理性所欲求的善总是关乎人的整全的善——整个灵魂和身体的善,就像好的统治者寻求的是整个城邦的善,所以,理性应当居于统治地位,而其他两个部分要像理性的帮手那样服膺理性的统治。如此,这三个部分才能按照自然的秩序各尽其职、各安其位,这就是柏拉图所说的个体灵魂所处的正义状态。他在《蒂迈欧》中指出,只有理性部分才是真正不朽的有神性的部分,所以,死后的灵魂就会将与身体掺和在一起的激情与欲望部分剥离出来,但是,只要我们还活在尘世,而激情和欲望部分就会暂时地伴随着具身化的(embodied)灵魂。同样地,理性部分的统治地位在柏拉图的《斐德洛》的灵魂马车的比喻中更是活灵活现地被表达出来,因为只有理性部分是御马者,整辆马车才能顺利地前行,两匹骏马才能并驾齐驱。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五卷中所构建的善的理念的图景根本上就是灵魂的理性部分的专利,能够从充斥着影子的洞穴世界中走出来,在太阳下看到真实的事物,或者能够挣脱感性的意见世界,而进入理性的理念世界,最后这都是理性部分才能胜任的事情。面对纯粹的理念世界,我们所具有的仅仅剩下属于理性自身的欲求和属于理性自身的快乐,纯粹的激情和肉体的欲望会就此止步。
但是,事实上,理性的统治地位并非自然天成,具身性的灵魂在尘世生活中始终要面对其中的不同部分或动力来源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理性部分并不能高枕无忧地端坐庙堂之上发号施令,相反,柏拉图通过灵魂的三分给我们证明了这种理性部分被非理性的激情与欲望部分所控制或奴役的可能性。因为既然每个部分都具有动机性的作用,都可以独立地引起我们的行动,那么激情与欲望当然也可以进行统治。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八-九卷谈论了理性的被奴役问题。他认为,正确的德性只有一种形式,而错误的或不好的恶则有多个甚至数不清的形式,这些恶的形式可以表现在城邦和个体灵魂中,城邦与个体灵魂是相呼应的,其中,四种形式的恶值得我们关注:荣誉制(timocratic)、寡头制(oligarchic)、民主制(democratic)和僭主制(tyrannical)。这四种形式在柏拉图看来之所以是恶的,是因为它们都表达了理性被奴役的某种形式,他在《理想国》553d1-7中这样来描述在寡头制中理性被奴役的状态:
他使理性部分和激情部分置于欲望之下的境地,被迫折节为奴,侍立两边。他不允许理性去思虑别的事情,除了只被允许计算和研究如何更多地赚钱。他也不允许激情部分去赞赏任何其他的事情,除了对财富和富人加以崇尚之外,并且只对财富的获得或有助于获得财富的事情有野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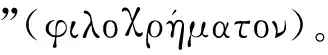

四、爱若斯的攀升
与此相反,柏拉图在《会饮》中通过爱欲向着美本身或美的理念攀升的图景给我们展示了另外一种心灵模式:灵魂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消退不见,留下的只是一位爱者通过爱欲的力量开始攀登美的阶梯,逐渐从对形体的爱上升到对灵魂的、对美丽的言辞和城邦的、对各种知识的爱,最后直达对美本身或美的理念本身的爱。我们的问题是,一个人如何能够不费气力地就能从形体开始逐渐拾级而上,终止于对普遍的或完全不再是具身性的或形体性的美的理念的静观和沉思呢?为什么爱若斯的终极目的是对美的理念的静观和沉思,而非可感世界的美?爱若斯逐渐拾级而上的力量又是从哪里来的?
当然,我们可以说,柏拉图写作《会饮》的年代要早于《理想国》,至少早于《理想国》的后九卷,他在《会饮》中更为强调的是美的理念以及爱欲在城邦教育中的重要性,所以带有更强的理想性色彩,而在《理想国》中更加强调城邦与个体的正义,所以要直面现实。我认为,这种解释仍然只是基于一种柏拉图对话的发展论的视角,而没有对为何两篇对话展示给我们不同的心灵结构的原因或内在意涵进行分析。虽然《会饮》与《理想国》所展示的心灵结构不同,但这两篇对话的目的是同一个,那就是只有理性进行统治的心灵结构才是正义的,才能使人幸福。如果说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认为,人的心灵结构的真正稳固性是建基于理性部分对善的理念的攀升和静观之上的,那么他在《会饮》中同样强调人的爱欲只有在静观美本身或美的理念中才能得到安顿和实现。接下来,我想着重分析柏拉图是如何赋予爱若斯一种新的意涵的,以及如何将人的爱欲天性与爱智慧的哲学天性联系起来的。我想从以下几点来论述:(1)爱若斯的本质是欲求智慧;(2)欲求的秩序与美的阶梯;(3)对美的理念的静观使得我们的生活在最大程度上值得过。
(一)爱若斯的本质是欲求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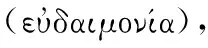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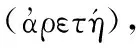
(二)欲求的秩序与美的阶梯
柏拉图赋予了爱若斯一个更为高远、更为超绝的哲学意涵,那就是爱若斯的真正所归就是理性对美的理念的沉思和静观,以及由此静观而生产出真正的智慧和德性。柏拉图打破了当时流行的对爱若斯的狭窄看法,这无疑是一种革命性的观点。但是,我们并非生来或一蹴而就地就能达到这如此超绝高明的目的,我们需要经历不同的阶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是柏拉图在《会饮》211c中所说的美的阶梯:
所以说,人们凭着那种纯真的对少年人的爱,一步一步向上攀登,能够看到那个美时,他就几乎说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就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或者也可以由别人领着而进入到爱欲的奥秘之中:我们总是从这些美的事物开始,为了美的目的而逐渐拾级而上,它们就像阶梯那样,从一个美的形体到两个美的形体,再从两个美的形体到一切美的形体,然后从美的形体上升到美的操持或习俗,从美的行动再上升到美的种种知识,最后,从各种知识终于达到那种无非是关于美本身的知识,如此,他最终认识到美之所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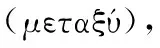
(三)对美的理念的静观使得我们的生活在最大程度上值得过
柏拉图在《会饮》212d中说:
亲爱的苏格拉底啊,如果有什么生活值得人去过,那就是对美的静观。如果你一旦看见它,你就会觉得那些金器和丽裳、俊男和美少都不值得一顾了。
柏拉图为什么会认为只有对美的理念的静观才使我们的生活最大化地值得过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美的理念是最可靠或最牢固的一条路,因为美本身或美的理念是始终如一,永不变化的。柏拉图在《会饮》211a-b中这样来形容它:
首先,它恒常永在,不生不灭,不盈不亏或不增不减;其次,它既非在这点上美,在那点上丑,亦非此时美,彼时丑;亦非与一物相比美,与另一物相比丑;亦不是在此处美,在彼处丑,就像对某些人来说美,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又是丑的。这美者并不表现于一张面孔或一双手,或身体的某一其他部分,也不呈现为某种言辞和知识;并不呈现为在某个处所的东西,不在动物身上,不在天上,不在地上,或在其他什么东西上,毋宁说,美本身自根自存自在,永远与自身同一;所有的其他美的事物都以某种方式分有其美,那些其他的美的东西生生灭灭,而它自身却始终如一,不会承受任何损益或变化。
通过柏拉图在这里所说的美的理念的特性我们得知,这是一条甚为稳妥的道路,因为美的理念摈弃了所有的相对性和他异性(heterogeneity);美的理念永远与自身同一,也摈弃了载体与特性或对象与属性之间的二元区分,它并不存在于某个地方或某个载体的身上;美的理念也不会被美的东西所作用或受影响,它在自身并为了自身而存在。
对美的理念的静观可以使我们生产出真正的德性和智慧,如果说,对美的形体、美的城邦律法和美的诗歌的欲求者都属于较低一级的欲求主体,那么,对美的理念或知识的欲求者可以被视为更高一级的欲求主体。这种欲求的价值序列的基础在柏拉图看来就在于,较低一级的欲求主体所欲求的美的对象的价值在本质上来说都可以归结为荣誉,他们所获得的善也大都是完成了的外在产品(finalized products),所以,这些事物的价值取决于外在的善,柏拉图喜欢将其称为智慧和德性的影像(images),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和德性。与此相反,如果一个欲求主体拥有对美的理念的知识,那么,他就能生产出真正的智慧和德性,而非德性和智慧的虚假影像。所以,可以说,对美的理念的沉思就是产生真实的智慧和德性,这不是两种行动而是一种行动的两个方面。与美的理念的照面就是我们对自身的理性能力的意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欲求主体与美的理念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对称的关系(asymmetry),因为二者的关系并不具有一种完全对称的互反性(reciprocity),美的理念永远与自身同一,没有匮乏,自根自存,永不变化,但欲求主体则会意识到自己对所欲求对象身上的品质或其他的善的匮乏,并且通过生产出不同的善来弥补这种缺乏。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对称性或非互反性,哲学才注定了它永远在路上的命运。
